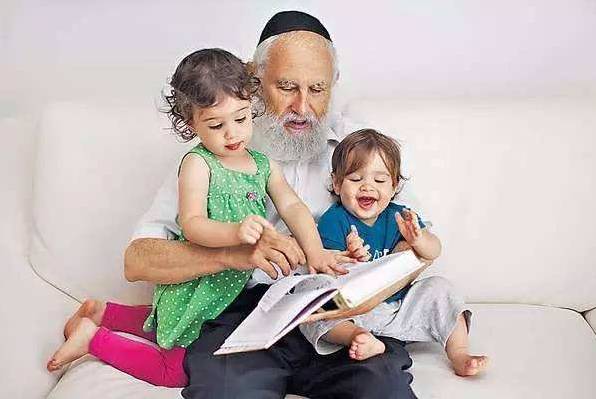文 |平原公子
一直以來,大家對“讀書人”是有濾鏡的,總以為他們有“操守”、“風骨”,實際上,那只是他們的人設,是他們確認身份、謀求利益的“封建紋章”。
有些人,你明知他們學歷水、水平差、道德低,但他們依然可以在他們的世界裡如魚得水、名利雙收,因為他們是教育界的前輩、高校的“領導”、“圈子”的老師,他們不是一個人,他們是一股力量,朋黨糾結、門生故吏遍天下,他們還代表著一股強大的“舊勢力”和“舊利益”,他們必然是要抱團取暖,結夥捍衛自己的特權和利益的。
就算他們的某些醜行曝光了,但你依然會看到,未來有很多人給他們洗地、翻案,甚至替他們站臺。甚至你熟悉的那些領導、前輩、老師,忽然暴露出來,他們也是這個體系的支持者。
自古以來,教育系統,最容易近親繁殖、盤根錯節、滋生腐敗和利益交換。因為教育和學術,屬於真正的“獨立王國”,有著所謂“士大夫讀書人”群體的共同堡壘,針插不進,水潑不進,鐵板一塊……在古代封建社會,讀書人和士大夫往往罔顧國家利益、無視朝廷法度,結黨營私,把持科舉考試,壟斷晉升通道,把國家的用人牢牢掌握在少數的門閥、世家手中。看起來公正的考試,也變成了他們投機取巧、勾兌利益、打造朋黨圈子的工具。為什麼古代某些名臣“門生故吏遍天下”?因為一次科舉取士,就可以讓他網羅世家新貴,讓下一代各部門的接班人成為他的“學生”,將來,這就是個同榮辱、共進退的利益共同體,哪怕是國家,也休想撬動他們這鐵板一塊的“同盟”!為什麼歷史上會有那麼多“科場舞弊案”?為什麼殺的人頭亂滾他們依然要鋌而走險?因為他們不會輕易放棄他們的特權。比如明朝的“南北榜”案,為什麼最後會鬧成血流成河的結果?因為南方士大夫同盟的這塊鐵板太硬了,朱元璋都踢不動,他們設計的考試製度、他們定的考題、他們選的考生……完全就不給北方考生任何機會,再考一次,選上來的還是他們的人!他們還義正辭嚴說這就是“公平”!他們完全不考慮南北經濟差距、戰亂對北方的破壞、不考慮南方士族在朝中早已盤根錯節、不考慮國家安定人心重振北方的大局!他們就是要和國家大政對著幹!

他們信奉的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搞科研,兒子自然也可以從小搞科研,這是得天獨厚的優勢,時間長了,這就叫“科研世家”,出身高貴,根肥苗壯。
兒子從小熱愛科學,對真理奧秘的探索精神,是刻在骨子裡的,基因出色,血統高貴,雖然他只是一個小學生,雖然他曾經學藝術、學商科,但他“理想遠大”啊,但他比你們那些為了五斗米搞科研的窮人出身博士生純粹多了。師門“過度參與”一下,怎麼啦?
那個古人幾歲的時候就是“神童”,出口成章,下筆千言,能掐會算,不就是那麼回事嘛!就算當代,那些搞文學創作的,多少“作家世家”啊,多少父子文豪、母女才女啊,搞理科的也“世家”一下,不行嗎?財閥有什麼了不起?銅臭味太重,學閥名利雙收,才叫一個“風雅”。
拼爹太難看,讀書人喜歡拼老師拼師門了,你若是名師門下,自然所到之處如魚得水,步步高昇;你若是老師無名,你自己水平再高,也只能一輩子當打下手的科研民工。科研首先要問師承,問血統,只有祖傳科研,才是真科研。為什麼進學都要問家長啊?這就是看你屬於哪個“世家”,什麼官員,什麼富豪,都不如“學閥世家”管用。官員的權力有期限,財富的力量有界限,唯有讀書人的勢力,才是真“無冕之王”,這個“科研世家”出身,才是真名門貴族。
什麼叫“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啊?就算你拼勁全力,考進985,讀研讀博,但你依舊是個“庶人”,你沒有後臺,沒有背景,沒有可以輕鬆調動的學術科研資源,掙扎個幾年,也只能去企業打工,借貸買房結婚生子,過完平庸的一生。
但你的“同學”們不一樣,國家級的實驗室,他們可以隨便進,價值幾百萬的實驗裝置,他們隨便用,師兄師姐們日日夜夜加班爆肝的實驗資料、論文成果,他們隨便用。他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他們不怕公眾對他們的批評,他們掌握筆桿子和喇叭,他們擅長轉移矛盾、渾水摸魚、抓小放大……然後就是反攻倒算,把帽子扣到人民大眾頭上去,罵泥腿子沒文化,罵泥腿子不懂“科學”和“審美”,罵暴民迫害“知識分子”,這一套話術屢試不爽,,一時的勝負得失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只需要活得長,只需要時間夠久,最終他們總是能贏。
千萬不要小看“讀書人”、“士大夫”、“學術圈子”。改天換地能怎樣?革故鼎新又如何?只要“考評”掌握在他們手上,“用人”也就掌握在他們手上。從貴族世襲、到舉孝廉、到九品中正、到科舉……他們總能鑽到空子,最終竊取一切。哪怕有人想奮發、想革新、也動不了這個利益共同體,因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古代王安石變法為什麼失敗?重要原因是——裝模作樣執行他新政的人,還是那些“舊勢力”!舊勢力混進了“新政”中,宣傳、執行、組織都是他們的人,新政還新得起來嗎?他們就是來摻沙子、搞破壞、然後把黑鍋扣到王安石頭上。近代辛亥革命為什麼失敗?重要原因是——那些號稱革命、鹹與維新的人,還是舊時代的鄉紳、地主、地方實力派,用竹竿把衙門前的瓦片挑落幾塊,就算是革命了!滿清王朝的巡撫、提督們,衣服一脫,帽子一換,立馬就是“革命政府”的元帥、議員。常言道——“百年的王朝,千年的世家”,你看世界風雲變幻,革命轟轟烈烈,其實那都是人類歷史上的意外……除了那幾個千年一遇的“異數”之外,其他時候,歷史似乎就掌握在那幾個熟悉的姓氏手中,無論怎麼改,怎麼變,怎麼發展,他們似乎永遠都是勝利者。

商朝的時候,他們是溝通天神的“大巫”,周朝的時候,他們是“諸侯”,春秋戰國的時候,他們是“貴族”,漢朝的時候,他們是“豪強”,隋唐的時候,他們是“門閥世家”,宋朝的時候,他們是“士大夫”,明清的時候,他們自稱“讀書人”……他們和他們的世家門閥子弟,可以世世代代鑽空子、享紅利、不交稅、不服役、無視法度、橫行鄉里、欺下瞞上、以權謀私、尸位素餐,他們可以公然反對改革,陽奉陰違,在執行政策的時候摻沙子、拖後腿、帶節奏、吹陰風、燒陰火、煽動“民憤”、故意把政策執行歪,讓好的設計偏離軌道……最終他們還掌握話語權和解釋權,他們可以把天下衰敗的根源都甩給改革者和革命者,因為“書”是由他們來寫。
這群人平日裡滿嘴的反封建、反獨裁、反特權,實際上他們在自己的領域裡,乾的就是封建、獨裁的事情,享受的就是無與倫比的特權。他們的飯碗是鐵打的,父子師生能夠把持學科建設幾十年,門生故吏能夠掌控學術體系幾十年,他們的論文直接一路綠燈,因為整個行業都是他們的“後輩”、“學生”。他們這個圈子,針扎不進,水潑不進,不接受任何監督,不接受任何批評,簡直就是一言堂唯我獨尊,這些先生們向來只會接受同行、晚輩、學生們的溜鬚拍馬、互相吹捧,你誇我仲尼不死,我捧你顏回復生——全世界沒有比他們更封建、更保守、更倒退的圈子了。
這些人平日裡滿嘴民主、自由、進步,總想著“啟蒙大眾”,實際上他們和這些詞一點關係都沒有,如果他們真心相信自由、民主,為什麼一點批評的聲音都聽不得?一點人民的聲音都聽不得?他們口口聲聲說“是制度限制了他們的學術工作”,是“國內大環境限制了他們的自由發揮”,實際上,他們吃著制度的紅利,躺在“知識的特權”上掙得盤滿缽滿,卻還滿腹牢騷,這個社會確實有問題,有問題的正是他們這些文藝界的“閻王”。
他們擅長搞“同學會”、“同鄉會”、“師生情”,互相扶持,投桃報李,結成利益共同體,謀劃各自的“生意”。人性有很多的弱點,強者總是想要讓自己的基因遺傳下去,這就導致很多強大、聰明、能力超群的“一代”,不願意看著自己的後代庸碌無能、衰敗下去……所以他們就會被這個“體系”所以引誘、腐蝕、利用。宰相會栽培名將的兒子,名將也會投桃報李,給宰相家的公子鍍金,教授會收“大師”的廢物兒子讀博士,大師也會給教授的廢物後代站臺“開光”……其他體系運作有困難,但“教育”、“學術”體系運作起來就太容易了,因為這是“獨立王國”。

這個群體自古以來就有著宗教般的“價值觀”,善於對抗世俗政權,不給國家行政機構、監察機構進入的機會,他們甚至認為,這是“讀書人的堅持”、“士大夫的操守”、“學術自由”。實際上,他們只是用這些作為幌子……來捍衛他們的共同利益。
這套邏輯,甚至反客為主,綁架了教育本身,以至於哪怕發現了問題,第一反應也是壓下去,頭可斷、血可流、信仰可以拋棄、家國可無視、祖宗可以賣,利益鏈不能斷。
他們天然站在老百姓的對立面,他們可以公然喊出“君王與士大夫共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他們一貫站在世俗政權的對立面,因為我們的世俗政權自古以來就過於先進——大一統、廢分封、立郡縣、削諸侯、抑豪強、設定流官、創科舉、國家統一財政教育軍事……這從根子上在抑制“世家門閥”千秋萬載的機會,所以,他們不甘心,明著對抗不了,他們就會千方百計混進來,利用人性的弱點、利用規則的漏洞、最終鳩佔鵲巢、蛀空整個體系。

他們對特權和利益絲毫不放手,賺得盤滿缽滿,吃得滿嘴流油,卻罵秦始皇,罵商鞅,罵漢武帝,罵王安石,罵所有觸及他們特權和利益的人……他們發明歷史,批判無中生有的“秦制”,批判“公權力”,只要國家開始對腐肉和腫瘤動刀子,開始關注大多數,開始重視公平,他們就嘰嘰歪歪什麼“與民爭利”,實際上,他們從來就不是“民”。他們喜歡給自己的行為“神聖化”,特別擅長拉大旗做虎皮,在古代,他們滿嘴“聖人之言”、“三王之治”、“天命所歸”;在現代,他們會一口一個“歐美慣例”、“西方先進經驗”、“和國際接軌”、“向文明世界看齊”。這一切,我們都讀過、學過、聽過、見過、經歷過,而且是無數次。你要真懂歷史,就會發現,秦始皇太溫柔、商鞅太天真、漢武帝太慈祥、王安石太善良……甚至連黃巢、李自成、張獻忠都太“軟弱”。歷史還故意保留了一點“味道”,或許是想讓我們這些“傻孩子”知道,當年為什麼會發生那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