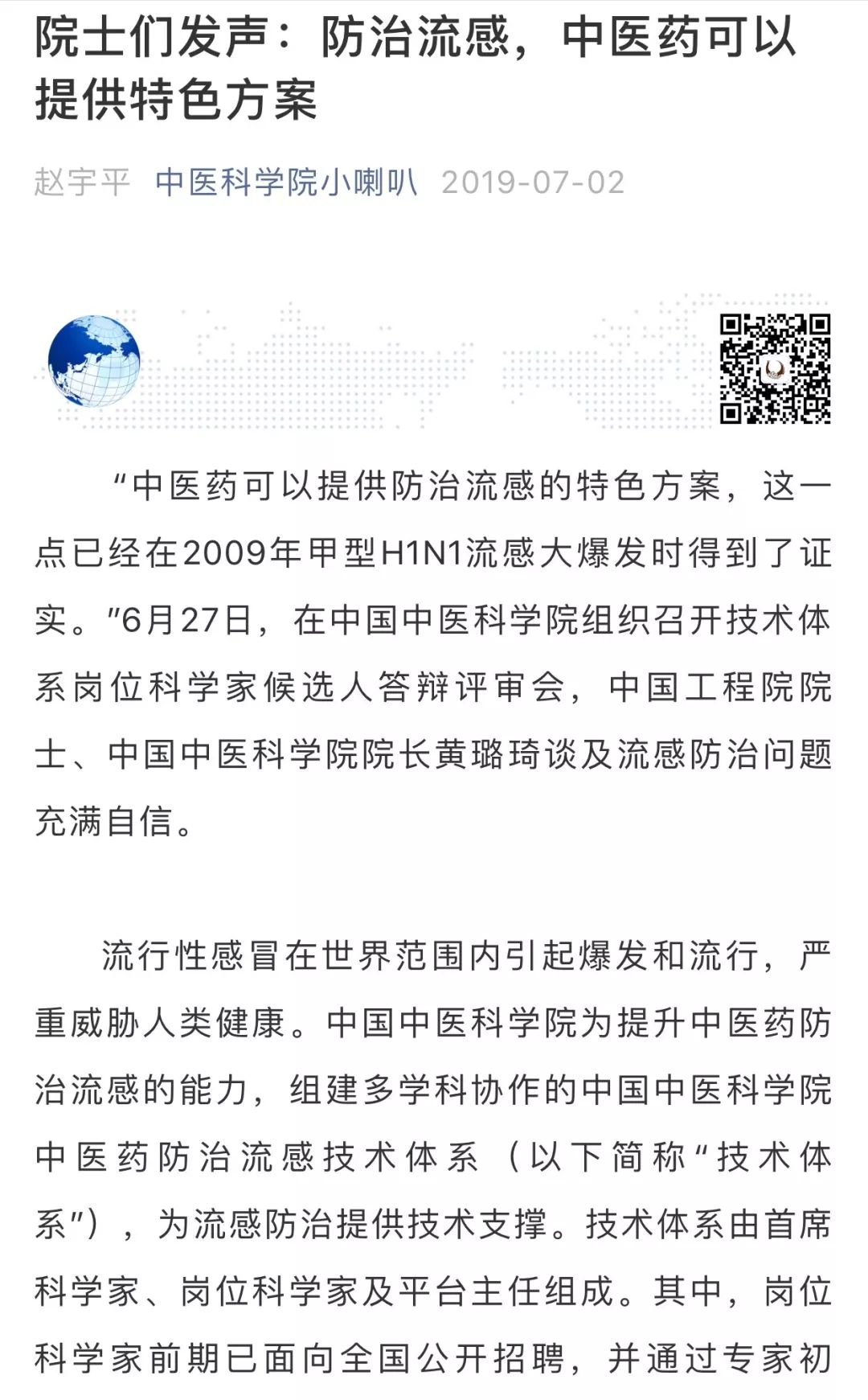藥櫃是亮紅色的,裡面相當一部分是常備藥。乾眼症患者的玻璃酸鈉滴眼液,緩解拉肚子的整腸生膠囊,腰突常用的消痛膏,失眠會吃的安神藥。
一款燻蒸面膜,只有拿到醫院才能做,要把摻了中草藥的濃稠液體塗在臉上,再用醫用儀器照射,主治“改善膚色”。六盒治療性功能的顆粒,塞在櫃子的一角。匆匆路過的人看到留下一句,“媽耶,這不會是作者大學四年吃的藥吧?”
藥物的所有者叫王博,30歲。這個夏天,剛從中央美術學院實驗藝術與科技藝術學院畢業,亮紅色藥櫃,是他畢業創作《毛病》的一部分——王博用一個多月,跑了四十幾趟醫院,除兒科、婦科、神經外科、感染科,把能看的門診都看了一遍,做了211項檢測,查出190個診斷異常,以一種近乎偏執的方式,試圖重新認識自己的身體。
作品展出後,引發了不少關於健康問題的反思——飲食是否在看不見的地方危害著我們的身體,工作壓力、精神隱疾、快節奏的生活方式又是怎樣影響著我們的健康?有觀眾看完感到,就醫也變成了一件荒誕的事,“人到底要做多少檢查,才能確定自己是不是真有病?把病治好,又要花多久?”
文丨解亦鴻
編輯丨陶若谷
紅色藥櫃正對的檔案櫃裡,存放著一個30歲男人的就診報告。依照門診科室分為43層,男科和焦慮障礙,這兩層抽屜常常開著,被翻得最頻繁。看的人多了,會把病歷翻亂,肛腸科錯放到了腎內科。
就診資訊彙總在3.5米的表格裡,表格從地板延伸至天花板,幾乎不可能看清最上方的資訊,也很少有人俯下身,仔細閱讀底部的內容。這是王博刻意製造的閱讀障礙。他想透過這種“上下不及”的體驗,傳達一種感受,“只要願意,針對身體的檢查可以無窮無盡。”
他這次極端“看病”的經歷,從今年4月15號開始,最先看的是眼科,最後一個看的是藥學重整科。
每去一個科室前,王博會提前問人工智慧,這科常見疾病有哪些,症狀是什麼,在已有的病裡,找跟自己可能相關的部分,再一一排除,對號入座。
比如“乾燥綜合症”,人工智慧告訴他,症狀有“眼乾、口乾、皮膚幹、尿黃口苦”,王博覺得,自己好像都有點兒。寫論文有一回眼睛腫,他以為是用眼疲勞,沒去醫院,買了點眼藥水和紅黴素,但從那之後,看螢幕久了眼睛還是不舒服。
就診時,他提前備好了話術,裝作不知道這個病,跟大夫說,“我最近眼乾口乾,滴眼藥水也沒用,後來查了下,有可能叫乾燥綜合症?”大夫讓他抽了三管血,測了15種抗體,最後排除了“乾燥綜合症”,確診了“寒溼阻絡症”和“膝關節痛”。
能在風溼病科查出“膝關節痛”,他覺得有點歪打正著。幾天前看骨科,他就提到膝蓋不舒服,“總覺得涼颼颼的”。醫生告訴他,這不屬於骨科,讓去掛關節科。關節科說“這個不在我們的範圍”,王博又去掛了骨傷綜合門診,仍無法確診膝關節問題。醫生開了一些輔助治療,要4900塊,治療半年,他放棄了。
在風溼病科,他又提到這個毛病,確診了膝關節痛,“總算給我的不舒服,找到了一個對應的科室,至少是寫到病歷裡面了。”
遇到耐心的醫生,王博有時也直接坦白,“我在做畢業創作,想知道身上所有的毛病,所以來掛這科,能不能直接幫我看看?”其中有三個大夫,聽後不僅不反對,還提出要來看他的畢業展。

看完軀體疾病,王博去掛了精神科。在走廊裡等結果時,旁邊坐著一位女士,大約五六十歲,拿到檢測報告當場大哭。她怕自己患上阿爾茲海默症,來做認知檢測,看到結果,發現記憶力真的大幅下降。
最忙的時候,王博一天看3個科室。在不同科室上廁所,也觀察裡面貼的小廣告。“代開病假條”“試管嬰兒諮詢”“互助獻血”“規培保過”,什麼都有。王博把廣告卡片取下來,消毒後封存在塑膠袋裡,算是畢業創作的一條分支。
他的創作靈感源於四年前一次“瀕死體驗”。
王博講述,八月的那天,從傍晚開始胸口發悶,九十點鐘開始心慌,心臟像被什麼東西壓住,越來越壓得慌,到晚上十一點左右,心跳得越來越快,爸爸立即開車帶他去縣城醫院。三十多公里路,大概開了三分之一,他就“感覺前所未有的痛苦”,當晚送入急診搶救。脫離生命危險後,王博感到後怕,想好好查一查發病原因。
王博在安徽亳州的王金寨村出生,初一開始在學校待不住,休過學,16歲到城市闖蕩,幾番周折,2021年考上央美。發病的時候,他正在老家等待入學。那次之前,他除了感冒,幾乎沒正經吃過藥,為數不多幾次去醫院,是外婆腳燙傷了,爺爺退休後的體檢,他陪著老人去,自己沒在醫院看過病。
之後一個月,王博總覺得心臟不舒服,乏力,急症發作的瀕死感,經常在腦子裡重演。那家搶救的縣城醫院條件有限,除了血液裡鉀含量略低於正常,也找不到其他問題。他就以準備上學為由,提前離家,到北京看病。
北京的一位醫生告訴他,症狀有點像“驚恐障礙”,屬於心理疾病的一種,建議去精神專科醫院掛號。在此之前,王博一直以為,如果查不出心臟上的問題,就是神經方面有問題,“從沒想過,自己可能是心理上有疾病。”
到了心理門診,他直接問醫生,“我有沒有可能是驚恐障礙?”最後確診。王博回憶起來,覺得能找對病因,或許也有運氣的成分。
王博介紹,就診的這家醫院,2021年,“驚恐障礙”仍分類在焦慮症下面,2022年,有位教授在帶團隊做課題研究,提出應該重新分類,把焦慮和驚恐分開,將“驚恐障礙”獨立成一個病症。招志願者進行對照試驗,一組吃精神類藥物,另一組不吃,用其他方法治療。王博主動報名了後者——他之前吃藥的體驗不好。
醫學試驗結束,驚恐障礙的情況基本沒有了。但王博對自己的身體仍然感到陌生,“以前自己和身體是一個整體,生病後想法變了,身體好像變成我的朋友,而我並不瞭解他。”
診療經歷也讓他意識到,一個病的病理、診斷、治療方法,甚至醫學對病的命名,“它不是一個固定的東西,甚至會包含錯誤被修正的過程。”
單純買一個體檢套餐,已經解決不了他對於身體的疑問。所以在這個畢業創作季,他選擇主動掛號,跑43科門診,檢查總計211項,以一種近乎偏執的方式,渴望重新認識自己的身體。
王博最早給這個作品起名叫《有毛病》。因為看病過程中,他向一些大夫坦白在做創作,大夫跟他說得最多的兩句話,一是“你這不是沒病找病麼”,另一個就是,“你是不是有毛病”。
他想玩個諧音梗,“我們口語裡總說‘你有毛病啊’,帶著點調侃甚至指責。”答辯老師卻覺得不夠簡潔,要求改為《毛病》。王博不甘心,在展覽現場額外貼了一張自己手寫的作品名片,又改回《有毛病》。

32歲的袁媛也覺得,“有毛病”讀起來更有意思。6月22號,她被央美畢業展廳裡的紅色藥櫃吸引過來。
這天是她一週當中難得的休息日,上午來央美看畢業展,下午準備去看一場話劇。“有毛病”讓她聯想到一些有疑病傾向的人,還有生活中人們關於就醫的常見說法,“你去看了就會有病,不去看可能就沒病。”
近三年,袁媛去過十次醫院,其中呼吸科三次,骨科兩次。自從她開始從事攝影助理的工作,身上多了許多小毛病。胸悶氣短,後背發麻。但每次去醫院,都查不出問題。頸椎和脊椎拍了兩張片子,都沒有問題,骨科大夫判斷,背部疼痛可能是肌肉勞損導致。而呼吸科的醫生乾脆告訴她,“你沒問題,下回別來了。”
實在查不出病症,她只好把毛病歸結為工作。這一行鄙視鏈嚴重,袁媛經常搬重物,電箱、閃光燈、各種架子,從貨拉拉搬到片場,結束再搬回車上。工作時間短則10小時,長則12小時,凌晨才到家,第二天又要早起,但藝人對攝影助理普遍缺乏尊重。
查不出病,她認為問題都在工作,“只要換一份工作,身體就能好起來了。”這樣跟朋友抱怨了三年,袁媛還在拖延。疼起來就去醫院,不疼了又覺得還可以繼續忍受,工作也不是說換就換的。沒有治療方法,她全靠自己調節,後背疼就捶一捶,或者多躺躺,這個姿勢能讓後背放鬆,好受一些。
一個來旅遊的遼寧女孩來看展,是前一天恰巧刷到短影片,被一句話擊中:“《毛病》將赫胥黎的名言演繹得淋漓盡致——現代醫學已經進步到不再有人健康了。”
她今年27歲,跟袁媛一樣,苦惱於工作帶來的毛病。她在瀋陽一家央行做管培生,辦公室人情複雜,精神壓力加重了她多囊卵巢的症狀。去看婦科、心理科、內分泌科,醫生說得最多的是,“多運動,減減肥。”但她覺得,“如果我真的每天能8點起來下樓跑一圈,還來看病幹嘛?”
作品引發人們關於現代醫療的討論,在王博看來屬於觀眾解讀,“至少我做研究的時候,是不知道(赫胥黎)這句話的,也沒考慮過以此為方向去做。”他更關注的是身體本身——以前不把身體當回事,做藝術覺得意識更重要,注重的是自己的“腦袋”,現在更多開始思考和身體之間的關係。

小時候,身體記住的都是自然中的活動。光著腳在麥地裡跑,餓了就在誰家地裡順手摘點瓜,和小夥伴追野雞,能一口氣跑兩個小時,還喜歡爬樹,從樹上下來,胳膊劃出紅印和口子。破了不要緊,抹點土,慢慢地就會好。
他在亳州林場鎮北邊的王金寨村長大,父母常年在浙江打工,王博跟爺爺、外婆生活,兩家村子挨著。他見過許多老人把小病拖成大病。縣城醫院在三十五公里外,村裡沒車,看病要走著去,年紀大的更嫌麻煩,不愛去看醫生,會說“小病不著急,大病趕緊死”。
高一那年,同村學長在北京學設計,讓王博發現“藝術原來不只有畫畫”,他想去外面看看。感官上最大的變化是,城裡的晚上是明晃晃的,不存在真正的黑。身體會記得,躺在老家的床上,真正伸手不見五指,一點輪廓都看不到的那種感覺。
用現代醫學極其精密的檢查手段,試圖去捕捉身體裡那些潛在的、尚未被確診的、或者僅僅處於亞健康狀態的“病”——在王博看來,這種行為既有“沒病找病”的荒誕感,也隱喻了他想透過最細微的檢查去重新認知自己身體的出發點。
看完這一圈病,王博在創作筆記中寫下,“看了那麼多科室,終於得到了緩解,這或許也是治療的一部分吧。”
但他也在過程中感受到,“現代醫學似乎把人當作一把椅子,哪裡壞了修哪裡。”為了檢查這把椅子的每一個零件,他一共抽了20多管血,排查了3次尿蛋白。做完肺部CT,他原本還想做全身的CT,因為有輻射作罷。
醫保報銷了一萬七,自費一萬一。男科大夫一口氣開了兩千塊錢,其中有的症狀,比如睪丸增生和前列腺鈣化灶,王博後來去網上查,“都說是正常現象,可治可不治。”
體檢結束,他最終查出了190種小毛病,除了確診的疾病,還包括9項體檢異常指標。其中也有一些沒出現症狀的“未病”。比如骨密度下降,醫生說在他這個年齡很罕見。還有白內障,因為是早期,眼睛還沒有任何異樣的感覺。
相對嚴重的是肺結節、甲狀腺結節,這些結節都不大,大夫告訴他,“未來如果變得很大的話,大概微創拿出來就行了”。他覺得,醫保應該鼓勵治“未病”,而且,也應該對心理健康和精神健康進行體檢。

查完之後,生活最大的改變是,他開始曬太陽。這是王博小時候最怕的事。那時大人下田做農活,媽媽把他背在背上,或抱在懷裡,戴一頂寬大的帽子遮陽,別的孩子都這樣過來的,只有他不行,媽媽說他一曬太陽就會哭。到了現在,王博在夏天,還是常穿一件黑色風衣。
他適應不了暴曬和悶熱。但醫生說,要想改善骨密度低,需要多曬太陽。王博逼著自己曬。體檢第二個月起,他在附近找到一條河,盤腿坐在河邊的大石頭上曬太陽,或是在學校操場的乒乓球桌上,肚子貼桌面,雙手向後抓著雙腳,擺各種奇怪姿勢,充分用身體感受世界。
在傳統相馬術裡,“毛病”指觀察馬匹毛髮的狀態,來判斷它的健康,是一種古老、甚至有點直覺性的健康評估方式——在儀器檢測不到深層問題時,外在的細微變化可能就是最早的預警訊號。
王博在作品取名字的過程中,接觸到這個概念。“這是藝術創作常見的手法,追溯詞的詞源。”他覺得這個詞源,非常契合創作的出發點。
211項體檢開的藥,他全放進紅色藥櫃,當作展品,一口沒吃。只有犯鼻炎,鼻涕流得實在忍不了了,會往鼻子裡噴兩泵。
作品引發的討論還在繼續。6月22日,在央美展出的最後一天,一個高個子女孩停在紅色藥櫃前,拿出裡面的一味中藥,拍下照片。這味藥是她外公常吃的,外公臨終前三四年,在ICU和養老院之間數次往返,身體機能不斷退化。
最後是一次喝水嗆到,胃部積水,導致便血,救不回來了。她在《毛病》作品展的留言本里寫,“我恨不得醫療技術能再發達一點,讓身邊的人都陪伴得更久。”
而另一位42歲的媽媽,隨意翻了幾本病歷,就離開了。她在一家國企做工程師,生完孩子後,尾椎骨總有隱痛。去醫院看過一回,醫生給開了幾片膏藥,疼了就貼上。
夏天起溼疹,春天鬧鼻炎,這些都時好時壞。有時貼了膏藥,在辦公室坐久了,尾椎還是疼,“那就疼嘛,人都是和毛病共存的。沒人會把病查得這麼細,年紀越大毛病越多,全查出來還活不活。”
(文中人物除王博外,均為化名。)
版權宣告:本文所有內容著作權歸屬極晝工作室,未經書面許可,不得轉載、摘編或以其他形式使用,另有宣告除外。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