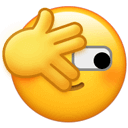索廷,音樂人。
歷史投影在
我悲傷的腦袋裡
2024.11.16 深圳
大家好,我是索廷,一個來自廣東吳川的獨立音樂人。
今年我發行了首張吳川話專輯《俚人往事》。這張專輯我做了八年,很榮幸能來到一席分享我是怎麼用這張專輯去和我的土地做連線的。
我出生於廣東吳川的一個村莊,本姓冼,世代生活在鑑江流域。這個地方離鑑江入海口不遠,在國境南端,是我國颱風較多的地方。

我的祖輩都是農民,當然到我父母這代還是農民。所以我的童年其實是在一場場耕種和收割中度過的。
我記得,颱風過後禾稈子會被一大片一大片地吹倒,搶收不及時的話,稻穀會栽在田地裡爛掉。那種情況是最辛苦的——因為沒有收割機和拖拉機,我們只能用人力把那些農作物拉回房子旁邊晾曬。
我在我的村莊度過了十五個年頭。在我童年時,那裡大概生活著六千人,都是俚人的後代。俚人在歷史上是難以被發現的角落,《隋書》記載:“俚人率直,重賄輕死,巢居崖處,盡力農事。”所謂的“重賄輕死”就是重誠信、輕生死的意思。
今天的俚人已融入了多個民族,冼姓也一樣併入了漢族。但稱謂的消失並不妨礙俚人強大的文化傳承力量,俚語的很多音調就是從先秦時期保留下來的。比如我的村莊叫馬兆村,就是俚語音譯成的漢字——“馬”是存在的意思,“兆”是首領的意思,我們村莊其實就是“首領的存在”。
漢文化傳進吳川之後,和俚人文化發生了許多碰撞,從而衍生出很多比較有趣的民族活動,比如專輯裡面的《搜捕》就是講這些民族活動之一的(注:搜捕,流行在粵西一帶的民間習俗活動,有壓舟趕鬼、納福祈福的意思)。


我剛才演唱的《黎家》是收錄在專輯《俚人往事》裡面的第一首歌。俚人在兩宋後被稱為“黎”,是漢人對蠻夷的又一種蔑稱。有趣的是,現在吳川人把不會說吳川話的人稱為“黎”。
《黎家》之中的“黎婆”,就是在對越自衛反擊戰中從越南邊境逃過來的難民。她就地嫁給了吳川當地一個57歲的中年,並生了一個兒子。

▲ 源自《黎家》VJ
我記得小時候放學經過她的窗邊,經常看到她用越南的文字寫信回家。那些拉丁字母寫得很漂亮,並不像一個老農民寫出來的字。我因此產生了好奇,問了她很多問題。
她說逃難的那段時間,衝過戰區時炸彈總會在身旁不遠的地方爆炸。她來到我們村莊的那天,就是下著濛濛小雨的初春清晨,雨水把腳上結痂的疤痕衝開了,流了一路的血,最後都長蛆了。

▲ 《黎家》繪畫
在2002年,她由於一直沒有收到回信,就產生了回越南尋親的想法。我記得我們一群小孩站在村口,看到她坐上半封閉式拖拉機的畫面。
後來過了好長時間,黎婆回來了,在樹下跟我們一群小孩聲淚俱下地說,她爸爸已經不認她了。爸說,出走的那一天就已經當她是死掉了,消失的人永遠消失就好了,反正都已經傷心過了。
《黎家》這首歌不單純是一首記錄的歌,更是這張專輯的引子。2015年我抑鬱症好轉後,決定做一張吳川話的專輯,開始苦思冥想專輯的概念、角度和具體事件。
我想什麼樣的歌既能訴說我的身份認同,又有歷史的投影,還能把這個專輯的世界觀一下子撐開?這時我想起了魯迅先生的《狂人日記》,我想站在既是親歷者又是觀察者的角度把自己放進故事裡,而我在其中依然是一個渺小的個體。

這首歌叫《塘上兩兄弟》,是用吳川木偶戲的音調和結構做的。木偶戲是吳川特有的戲種,又叫“鬼仔戲”,曲風哀怨神秘。民間藝人騎著二八大槓改裝的三輪車,上面放著兩個箱子,一個放木偶,一個放搭建戲臺的工具和樂器,穿街過巷,一人一擔一幕戲。

這首歌裡的樂器是透露著荒謬的,比如裡面的琵琶掃弦和電吉他的彎音是反常的。我想表達的不是什麼炫酷爆炸的事,而是一個非常黑色幽默,非常荒誕,非常悲哀的一件事情。
馬兆村裡面有七個小村子,我所在的那個小村子叫塘上村。村上的兩兄弟,一個叫阿瘸,一個叫土弟,都屬於低智人士。弟弟更糟糕,還患有小兒麻痺。他們經常會擔著菜去集市上賣,當時吳川的人文環境惡劣,兩兄弟常被圍觀捉弄。

▲ 《塘上兩兄弟》繪畫
我妹妹以前聽這首歌的時候,不明白我為什麼會這樣反覆地吼叫。你設想一下,當你大老遠挑著一擔子蔬菜、揹著弟弟去集市時,你面對的是一群智商和體態都高你很多的人。他們一會拿走你的蔬菜,一會打你的弟弟,一會對你推搡捉弄的時候,你環顧四周,內心一定是吶喊的。
但是這些吶喊都是無聲的,是永遠不會從嘴巴里發出來的那種吶喊。

兄弟兩個死於2008年的寒冬。在那個冬天,他們因為保暖工作沒做到位而出現了“反常脫衣現象”。家裡面的老人跟我講,說冷過頭會產生一種非常熱的感覺,他們還以為是在夏天,脫光衣服在小河裡面洗澡凍死了。
我記得那兩具屍體都順著河流流下來,就卡在渡口裡面。
其實他們在我小時候已經是五六十歲的人了,大多數事蹟都是村內老人講給我聽的。但就算這樣,在我做小孩的十幾年間,我依然會看到其他頑劣的小孩捉弄他們。比如有一種樹叫苦楝樹,它的果實苦楝子掉落並枯萎後非常像曬乾的紅棗,他們就會拿那些苦楝子去騙兩兄弟吃。

南宮渡是我們村莊旁一個古老的渡口,是商人、商船的休息區。1978年因南宮渡大橋建成,渡口就此作廢。

▲ 《南宮渡美遇》繪畫
這首歌我沒有什麼特別想說的,只是簡單寫了我爺爺的故事是怎麼在渡口上發生的。我想看一看兒時老人說的那個畫面,是如何地漂亮,如何地美,可惜如今只能靠想象了。
不過話又說回來,渡口的繁華更加說明了俚人其實長時間控制了鑑江水網最豐富的地方。《南宮渡美遇》送給大家。

《掙脫》這首歌是用我10歲左右的視角去寫的。在我小時候,我模模糊糊地看到很多鉅變之中的東西,比如穿過我們老家的鐵路、飛過天空的飛機,我以為它們是發出巨大響聲的小鳥。
還有在乾枯的河裡吃著塑膠袋的巴西龜,以及想吃麻雀蛋而撲空的鶴子——它的天性就是是吃麻雀蛋,但那時蛋已經被低壓電線給燒焦了。
這些東西在我幼時的印象裡都是突然出現的,但當我帶著這些問題去問我的長輩,得到的答案卻是含糊其辭。
我後來就在思考,是從什麼時候大家面對這些變化都如此麻木的呢?是從學漢字開始的嗎,還是從宗祠的建成開始的?是從十里八鄉都舞龍舞獅開始的,還是從請修譜匠修改我們的族譜開始的?
在我們那邊,大家都在努力地掙脫俚人這個身份。但讓我很費解的是,既然想擺脫,為什麼還要保留原先的姓氏呢?一系列的疑問讓我寫下了這首歌。
我覺得客觀的變化應該是要客觀去面對的,而不是一代一代地含糊其詞下去,讓很多東西被遺忘掉。


下面這首《魚蝦蟹鬥》是講明朝末期,漢人不斷南下,使得俚人耕種的土地再一次減少。俚人因為是“飯稻羹魚”的種族,失去土地後只能隨鑑江流域不斷南遷而下,至南宮渡上岸建立村莊。
初遷此地時,土地資源還是非常充足的,人口增長也很緩慢,所以大家可以做到“同飲一江水、同趁一條圩、同拜一堂廟”。
但隨著時間推移,人口不斷膨脹。到了清末,土地兼併嚴重,加上地方行政機構癱瘓,治安問題也沒有人管。在這樣的背景下,俚人村莊就發生了內鬥事件。他們都屬於底層,但是他們之間又互相傷害。
小時候我的奶奶經常叮囑我不要去藕塘玩,她說那裡曾經是村莊內鬥的戰場,死過很多人。


2014年,我失業在家,長期處於失眠狀態,總想起小時候停電的日子。因為吳川地區在21世紀初電力系統還非常落後,每次晚上停電,我們全家都會跑到屋頂上睡覺。
那時我就是不肯睡,要看星星、看月亮。我奶奶就總是在我耳邊講故事,給我唱吳川話的童謠。小時候不想睡,當下想睡卻睡不著,我不禁感嘆著寫下了《往》。
這首歌的副歌,就是奶奶給我唱的童謠:
糠牛儂 牛吃禾
牛光惃 打頭鑼
這個童謠講了個什麼故事呢?說從前有頭牛,它趁放牛的孩子睡著,偷偷跑去河邊的稻田偷吃稻禾。河裡的河蟹看到了,就大聲喊“放牛的娃,牛吃稻禾了,快快來抓它回去”。然後牛就說,喂,你不要亂說,再叫我就踩你一腳。
怎知那個河蟹根本沒怕,又叫了一句,然後牛就真的踩了它一腳。所以這個副歌我唱了兩次,因為奶奶在這個童話裡也唱了兩次。奶奶說那些螃蟹背部的殼上會留有一個牛腳印,都是牛踩的。
我非常想念我的奶奶,但是現在她已經不能陪伴我了。

▲ 《往》繪畫

我們再唱一首《森林裡的大傻》。“大傻”是我兒時的綽號,小時候因為我有鼻炎,總是張著嘴巴呼吸,村裡大一點的小孩就會說,不要張著嘴呼吸,蒼蠅會跑到嘴巴里面去。當時我就是那麼一個傻乎乎的樣子。
二三年級的時候吧,我經常因為交不起學費被老師打,拿巴掌扇,拿鞭子抽,臉上和手臂都會留下傷痕。這時我會離開我的學校,但是又不敢回家。我害怕我爸爸打麻將輸錢,他看到我身上的傷疤,會以為我在學校惹事,不分青紅皂白地又打我一頓。
我非常的孤獨,就跑到外婆家吃晚飯,等到傷痕褪去後再回家。去往外婆家的路邊總是佈滿野草,隔開的水溝處是一望無盡的水稻田。

▲ 《森林裡的大傻》繪畫
那時我經常聽到外公對我的埋怨,後面我想明白了,他其實就是藉著我的耳朵埋怨我爸,埋怨我爸爛賭,輸掉了學費錢,而九年義務教育還沒普及到這個偏遠的村莊。
但那時候我不明白,經常生悶氣,就會不吃飯走進樹林裡發呆,偶爾沉沉地睡過去,等我外婆叫醒我,拿飯過來給我吃。
我經常在松樹林裡面想,為什麼風吹過樹梢的聲音,和風吹過野草的聲音、小鳥的聲音、昆蟲的聲音是不一樣的呢?為什麼雲彩和松樹針葉的形狀顏色都是不一樣的呢?是不是大自然本來就有畫面和音樂,只是藝術家們把它梳理成藝術品呈現給大家?
但我當時沒有這麼高的覺悟,只是模模糊糊地想了這些。

下面我們演唱最後一首歌《卬》。我想給大家科普一下“卬”這個字,它念áng,在吳川話中是第一人稱“我”的意思。
但是現在的吳川話已經摒棄了這個字,說“我”的時候大多數用的是“伝(yún)”。我們老家那邊一些早期的語言學者用“伝”這個字編著了一些詞典、百科。但如今經過更多的學者考究,其實是應該用回“卬”的。
在成長過程中,我不斷地想了解自己的村莊,發現其實吳川的文化是很深的,但經過歷史的拳打腳踢,吳川人變得非常零散,且自我認同感很弱。

▲ 《卬》繪畫(在各地做工的吳川人)
我想身為文藝創作者,我應該盡我的努力,去提升一下吳川人的自我認同。同時我也想呼籲那些早期撰寫詞典的學者,去考慮一下自己的研究方向是否是偏離和錯誤的。

謝謝大家,我的演講就快結束了。

▲ “這裡不能安可”
這張專輯其實是寫了一個村莊的輓歌,總共12首歌,裡面還有更多可說不可說的故事,等著大家去發現。
很開心來一席,我從沒做過這樣的演講,因為我是今年才出來的新人。一席邀請我的時候,我非常緊張,因為這是我過去在影片網站上面很熟悉的節目。大概2019年的時候,我還在一席的官網上買過一個帆布包,那個包現在在我吳川老家,哈哈哈。
謝謝大家,再見!

文章綜合現場演講和試講整理而成。
策劃丨陽子
剪輯丨chaos
一本好書👇👇👇

▼ 永珍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