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在我年幼的歲月,沒有谷歌,沒有 OpenAI,舅舅就是我的超級人工智慧。

每個人的人生都會被周遭的人和事推動。在某個地方、某個時間和某某人因緣際會,往往會決定一個人的人生抉擇。在軌跡的初期稍有偏離,二十年後這個人就可能會出現在一個截然不同的地方,過著天差地別的生活。
比如,我今天是一個老程式設計師,住在離開家鄉幾萬公里的美國大西北,寫了三十多年軟體,每天跟程式碼庫中的各種臭蟲奮戰,業餘寫點公眾號。這樣的人生,自然是在小學三年級放學路上躑躅在國營食品店裡裝滿橘餅和天冬蜜餞的玻璃罐前的我無法想象的。
去年底,意外地在公司拿了個 craftsmanship 獎。查了字典,原來這詞就是大家常說的“工匠精神”,歷史上得過這個獎項的還有賣油的老翁和解牛的庖丁。公司是誇我牛馬當得好啊,不用揚鞭自奮蹄的意思。
在太平洋的另一端拿到這個小獎,我要歸因於我的舅舅。從小到大,我的理想就是長成舅舅那樣的人。他是我的初代偶像,除父母外對我影響我最大的人。他在我聽說“炫酷”這個詞之前就向我生動展示了它的真實含義。
用今天的話說,我舅舅是個六邊形達人,特立獨行的搖滾青年。
你可能會覺得我是在吹牛逼—-誰不願意給自己家門楣上貼金呢?沒關係,我會用事實證明我所言非虛。
~~~~
舅舅準確地說是我的七舅。我外公在成都育有七子七女。雖然有的子女夭折了,還有的像我母親一樣在成年後把家安在了外地,但我們大家庭的根基還在成都。每次家族聚會,出行都浩浩蕩蕩如旅遊團,合影必須站三排,攝影師後退二十米才可能拍下所有人。
外公的子女們相處融洽,所有的舅舅和姨媽都對我關愛有加,但只有七舅跟我母親才是一母所生,尤其親近。於是"七舅"就簡略成了"舅舅"。
舅舅讀完中專後分配到簡陽縣四川拖拉機廠工作。簡陽離成都只有幾十公里,中間隔一座龍泉山,山上的水蜜桃遠近聞名。他在廠裡結識了舅媽。舅媽是內江人,而我母親在內江工作,我們兩家都在小東門附近,步行五分鐘就可以串門。每年春節舅舅都會從兩百公里外的簡陽來到內江,一來回舅媽的孃家,二來跟我母親姐弟團聚。所以,相比於其他舅舅姨媽,我跟舅舅見面次數多了許多。
舅媽家也是一大幫兄弟姊妹。她排行老四,我便叫她四孃。她家的“劉抄手”是內江名小吃,鄧小平經過內江時曾專門品嚐(見拙文《四孃家的抄手》)。我小時候沒少吃過小平同款的紅油抄手跟清湯抄手。劉抄手現在店名叫“老劉抄手面”,除了抄手,他家的牛肉麵跟熗鍋面也是有口皆碑,常出現在我夢裡。
舅舅和舅媽是在拖拉機廠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認識的。舅媽歌唱得好,模樣更是標緻,《紅燈記》裡的李鐵梅非她莫屬。舅舅不唱歌,但是會拉手風琴。那個年代幾乎見不到吉他鋼琴小提琴這些現在的主流樂器,手風琴既可獨奏,又可伴奏,表現力豐富,是當仁不讓的樂器之王。舅舅因為要給舅媽伴奏革命歌曲,一來二去兩人便好上了。兩人都是知識青年,舅媽長得百裡挑一,舅舅也是濃眉大眼,走到哪裡都是拉風的一對。
外公外婆解放後生活拮据,吃飽飯都是大問題,不可能花錢讓舅舅去學樂器,所以手風琴是他自學的。我舅做事的套路就是無師自通,這一點在很多毫不相關的領域被一再驗證。
舅舅的音樂天賦跟我外公家的音樂傳承有一定關係。我很小的時候便知道我家有好幾個舅舅和姨媽都在解放前參加了海星合唱團,經常表演抗日救國歌曲。後來三孃成了音樂老師,四舅會拉小提琴。我母親出生晚,沒趕上參加合唱團,但也一直喜歡唱歌。
我喜歡翻看母親的手抄歌本。母親的字寫得很好看,歌本抄了二百多頁,上面有當時流行的革命歌曲,有民間小調和蘇聯歌,還有母親精心手繪的插圖。童年時,我家雖然沒有樂器或音響裝置,但音樂沒有斷過,我在母親的歌聲中周遊世界:“冰雪覆蓋著伏爾加河,冰河上跑著三套車(俄國)。”“把我引到了井底下,割斷了繩索就走開了,你呀,你呀,你呀(敘利亞)。”“人們說你就要離開故鄉,要離開熱愛你的姑娘(加拿大)。”“亞克西亞克西,我們的生活亞克西(新疆)。”“小乖乖來小乖乖,我們說給你們猜。什麼長,長上天?哪樣長,海中間(雲南)?”“一送哩個紅軍,蓋子個下了山(四川)。”這最後一首歌被熊孩子改成“掰掰(四川話‘瘸子’)去找紅軍,紅軍不要他。說他是個掰掰,走起來一拐一拐。”紅歌歪唱,是那時小孩子們不多的娛樂活動之一。
八十年代中期,流行音樂開始進入大家的生活,我也有了一個自己的手抄歌本。但我蚯蚓爬的字完全不能和母親娟秀的筆跡相比擬,實在是羞於見人。
舅舅舅媽作為老一輩文藝青年,在變革之際緊隨潮流,與時俱進。我上大學時,他倆聽的是童安格和王傑,跟我完全可以聊到一塊兒。當然,他們是有自己的標準的。舅媽問起我在學校聽哪些歌星,我齊秦羅大佑崔健張洪量說了一圈後,意猶未盡,畫蛇添足說偶爾還聽聽小虎隊。舅媽一聽就笑了:這跟音樂也扯不上關係啊。
我聽過舅舅在電子琴上彈奏《紅河谷》,結尾是 6 ♭6 5,7 1 2 2 3 2 1。我印象裡那個 ♭6 應該是 6。到底哪個是對的?舅舅說他一直彈的都是♭6。那時候沒有谷歌,紅河谷的歌就成了懸案。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查了一下:舅舅是對的。

除了音樂,舅舅還玩攝影。我小時候沒有數碼相機,拍照要用膠捲,拍完了還要衝洗。真正的攝影愛好者都不把膠捲送到照相館去,而是用自己的暗房和藥水 DIY。舅舅就是這樣的。那個年代照相機也極其罕見。所幸我有個玩攝影的舅舅,童年才留下了為數不多的幾張珍貴照片。
~~~~
我上初中後,以學英語為名求爸媽買一臺錄音機。爸媽猶豫再三,還是覺得以家裡的經濟條件有點負擔不起。舅舅那時靠手藝掙了些外快,按今天的標準算不上多驚人,但在那個大家都在國家單位領死工資的時代絕對是一馬當先。是不是簡陽縣首富我不知道,但肯定屬於小平允許先富起來的那一批。因他手頭更寬裕,便資助了我這外甥一臺單聲道收錄機和幾盤空白錄音帶,讓我喜不自勝。
這臺錄音機對我學英語的幫助程度值得懷疑—-反正我上大學英語課還是開不了口。但是,它極大地豐富了我的文娛生活。有了它,我做作業的時候要聽歌,睡覺的時候要聽歌,早上起不了床也要聽歌—-音量開到頭就是我的起床鈴。多少個夜晚,我都把它放在床頭,聽著成方圓、張行入睡。但是有一回失策了:那天我選的睡前音樂是《新長征路上的搖滾》,聽得我渾身燥熱,越聽越睡不著。我算是知道崔大爺的厲害了。想到第二天還要上課,只好換成齊秦,才慢慢把自己哄睡。
初中時,有部風行全國的香港電影《霹靂情》導致了無數青少年沉迷霹靂舞。這部片子的情節很商業,但是音樂製作卻非常精良,作曲人都是大師(黃霑、顧嘉輝、譚健常),歌手則是梅豔芳和香港小虎隊(跟後來的臺灣小虎隊是兩回事)。我一刷之後就迷上了裡面的插曲,果斷二刷。二刷時我長了個心眼兒,穿了一件大衣,把錄音機藏在大衣裡面夾帶進了內江人民電影院,非法盜錄了全部歌曲。出院後,這盤磁帶被我聽得快卷邊了。
那幾年我也在學吉他,跟同班其他三位男生經常在週末一起合奏,其樂融融。這部錄音機也留下了我們稚嫩的演奏。可惜的是,當年的錄音帶已經消失無蹤了。

和初中好友攜錄音機出遊內江西林寺。
倒立者為老萬。
因為這部錄音機是單聲道的,我對傳說中的的立體聲心馳神往。有一天,我在《電子報》上讀到一篇把錄音機從單聲道改裝成立體聲的攻略,大喜,便按文章所說買來了立體聲磁頭。但我很快發現換磁頭只是一百八十步的第一步,整個工程太過複雜,遠超我的能力,最終只能作罷。
不過,立體聲磁頭花了我好幾塊錢,不能浪費。我退而求其次,給錄音機換了新磁頭,又加了一組開關:開關撥到左邊可以單聽左聲道,撥到右邊聽右聲道,撥到中間就是聽兩個聲道的混合。
這聽起來相當無聊:一首曲子只聽一半聲道有啥意思呢?其實這跟太陽能手電筒還是不一樣的。關鍵是這個開關在錄音時也可以用來選擇聲道。於是,我在錄製長篇節目時可以先用左聲道錄一遍,再用右聲道錄一遍,實現了磁帶長度翻倍。雖然不是立體聲,但結果相當令我滿足。
我用這個方法錄了 86 年全本央視春晚(內含陳佩斯《羊肉串》),並攜機在中學課堂上播放,收到大家點贊。不過,有人向我借這磁帶回家聽時,我只能說抱歉:這種特殊磁帶天下只有我這部錄音機才能放,換一部放出來就會聽見侯耀文跟蘇小明打擂臺,成方圓跟唐傑忠幹嘴仗,都串臺啦!
快進到大學二年級,我放寒假回家,又被舅舅的新玩具震撼到了:他居然買了一臺頂配日本原裝愛華隨身聽:杜比降噪、鉻帶支援、數字調諧、自動翻面,而且,整個機身幾乎只有一盤磁帶大小,電池就像一條口香糖。日本人真是把電器捲到了極致—-後來我才聽說這叫“工匠精神”。
~~~~
要是你以為我舅舅就是個一抓一大把的文藝青年而已,那就錯了。我說舅舅搖滾,不是指他會上舞臺飆高音,而是說他不甘平庸,做事的風格很搖滾。
除了音樂,舅舅還精通無線電技術,這也是他無師自通學會的。在那個年代,那可是一件了不得的本事。那時候大部分家庭每天還在為吃飽飯發愁,有錢人家裡能買得起一臺收音機,沒錢的人唯一的電器就是電燈和手電筒。在六十年代的中國玩無線電,相當於今天玩超跑。
舅舅不但學會了組裝收音機,還給自己造出了一臺磁帶錄音機。這會儲存聲音的機器太過神奇,超出了普通人的想象力。我上幼兒園的時候,有一年冬天,舅舅和四孃帶著他的錄音機來到我在朝陽巷大院的家裡,開起了家庭演唱會。我家沒有不透風的牆,訊息傳開後,鄰居們接踵而至紛至沓來來了就不想走,不大的房間裡很快擠滿了好奇的觀眾。那天晚上,大家聽得如痴如醉欲罷不能,算得上我院歷史上的一件文化盛事。
再後來舅舅折騰出了裝電視機的本事,在家裡攢出了一臺九寸的黑白電視。不知道別的地方有沒有這種神器,反正據我所知是沒有的。我還記得去舅舅家眼巴巴地等著電視臺開播的情景。那天放的是電影《我們村裡的年輕人》,巴掌大的螢幕上,幾個大人晃來晃去說著我聽不懂的話,從頭至尾沒有我愛看的打仗場面,但我還是堅持坐到“劇終”兩個字亮起。
後來舅舅做出了更多的電視機,便送了一臺給舅媽的孃家。我終於不用去簡陽就能看電視了。那幾年,我放了學不回家,先跑到舅媽家去看電視,週末有好節目也賴在電視機前不走。在舅舅的電視機上,我看了《加里森敢死隊》、《敵營十八年》、《鐵臂阿童木》還有春晚。先做功課?不存在的。
因為稀罕,電視機成了公器。整個院子的鄰居都上門來看,好客的四孃家人也是來者不拒,所以他們家二樓放電視的小屋總是擠滿了人,讓我一度擔心會不會壓塌。
再後來,大家兜裡有了幾個錢,可以自己買這些家電了。舅舅抓住這個機會,業餘搞起了家電維修。那時候國內沒幾個人有這種技術儲備,他的服務供不應求,家裡堆滿了等著他修理的電器。機會只偏愛有準備的頭腦,舅舅就是有準備的頭腦。這就是舅舅先富起來的途徑。
八十年代,海外傳來了錄影機,價格高昂。舅舅又自己琢磨,在沒有資料的情況下搞清楚了錄影機的工作原理,在把自己的技能從電子管升級到電晶體之後,再次升級到積體電路,成功把業務拓展到了錄影機維修。
舅舅甚至自己做出了一臺電子琴,有各種音色和自動伴奏功能。不過,舅舅還是偏好手風琴。他說:原聲樂器才能表現感情。
該怎樣描述舅舅這種不斷開拓新領域的精神呢?我覺得可以叫做 DeepSeek(深究)。
~~~~
因有了這樣一個牛人舅舅做榜樣,我對無線電技術也躍躍欲試。小學五年級,我讓爸爸買了一套《少年科技》雜誌組織的電晶體收音機套件。這個套件很有意思,它從一個二極體和高阻耳機並聯的最原始的收音機開始,逐步加上調諧器、放大功能等,從單個電晶體擴充成七個電晶體,做大做強。一切順利的話,照著做下來可以打下一個堅實的無線電技術基礎。
然而我的鑽研精神和動手能力都略顯不足。跟除錯電路相比,我更喜歡的是把零件焊在電路板上的快感。所以學了幾年無線電,除了歐姆定律只學會了烙鐵的使用。要是零件拼裝在一起不工作了,我完全不知道怎樣去排查問題,用今天的話說就是不會 debug。所以我裝的收音機不會響,最後還是得靠舅舅春節回來幫我完成。
~~~~
我上中學的時候,舅舅彰顯了他勞動致富的實力,玩上了摩托車。這又是一個超前於時代的愛好。本田摩托不是在市面上想買就能買的。舅舅到廣州提貨,把摩托運到簡陽。
有了摩托,舅舅回內江更方便了。有天下午,我還在學校上自習。舅舅把我叫出去,帶著我騎摩托在內江的街頭兜了一大圈。我坐在後面,兩手緊摟著舅舅的腰,相當拉風。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在交通路口掉頭的時候我摔了下來,雖然人沒事,但影響了我拉風。
舅舅騎摩托自然也是自己學會的,所以他一度對我學不會騎腳踏車難以理解。內江地勢起伏,而且市區狹小,基本上沒有人騎腳踏車,所以我考上大學後才開始學車。有一次,有女同學要搭我的車從科大西區到東區。我從沒帶過人,女同學一坐到我的車後座上,腳踏車就開始瘋狂蛇形走位。可憐的女同學嚇得馬上跳車。試了兩三次,沒有任何進展,最後放棄了。總之舅舅小腦很發達,我小腦很不發達。
退休後,舅舅又玩出了新花樣。他和四孃組織了一個四川拖拉機廠腳踏車隊,和朋友們去全國各地騎行。他們以“住遍天下雞毛店,吃遍天下蒼蠅館”為口號,足跡遠至西藏、海南島。每次活動之後,舅舅還會在電腦上把出行的照片和錄影整理成影片節目和大家分享。而抖音的出現則是多年以後了。
~~~~
小學畢業時,我突發奇想要去簡陽找舅舅過暑假。我媽也是心大,給舅舅寫了封信說我某月某日到簡陽,買了張火車票送我上車就不管了。綠皮車晃到簡陽車站,我下車之後卻沒見到舅舅和舅媽。
還好我媽是親媽,給我做了第二手準備:她憑記憶畫了從簡陽火車站到川拖的簡易地圖。我按圖索驥,邊走邊問,還真讓我找到了。進了廠就好辦了,舅舅舅媽是名人,我三兩下就打聽到了他家的住處。
敲開門,比我小五歲的表弟強強比我還懵逼。原來舅舅和舅媽兩個人瀟灑地外出旅遊去了,讓兒子一個人在家每天吃食堂。我們倆每天吃完了飯沒事就去公園磨皮擦癢。過了幾天,他們老兩口旅遊回來了,才發現我已經不請自來自助消費好長時間了。原來,我媽發信的時候他們已經出門了,根本沒得到訊息。
雖然開局出了點狀況,餘下的那部分暑假我過得很愉快。舅舅有高倍軍用望遠鏡,可以讓我看對門鄰居家。舅舅還帶我去廠裡的計算機房,那裡有 IBM 計算機,可以打電子遊戲,還可以用中文寫信。能在電腦上寫出一段中文,讓我頗感幸福。1983 年的夏天,是我中文碼字生涯的開始。
到了初中三年級,我的課外興趣從無線電轉向了微型計算機。我請教舅舅:我該學硬體還是軟體?舅舅說:“當然是硬體。軟體這東西太簡單了,隨便一個人一兩年就能操會。不像硬體,需要實打實的多年經驗。”
這話在我耳裡起了反作用。我還沒有從裝收音機不響的陰影裡走出來,自認不是啃硬骨頭的料,於是默默選擇了軟體。至少,軟體出了問題,我還知道從哪裡入手除錯。
後來,我發現軟體雖然入門更容易,但是學到後面難度也是蹭蹭蹭地漲。世上無捷徑。捷徑走的人多了,也就捲起來了。
~~~~
我們那時候,小孩子十有八九都盼著家裡來客人,有好吃好喝不說,更重要的是自己的表演終於有了觀眾。我說的可不是啥正兒八經的才藝表演,純粹就是平時在家裡無人關注的小孩故意搞些小動作吸引客人注意,今天的說法是尋找存在感,四川人有個形象的說法叫“人來瘋”。
我小時候也鬧過人來瘋,在客人面前把自己的發條玩具弄得畢畢剝剝不停歇地響,遭人厭煩。大一點後,發覺大人們在一起總是自顧自講他們那些婆婆媽媽的事,無聊之至,我也就沒了摻合的慾望。
但是舅舅舅媽不一樣,他們的話題更有趣,更離經叛道特立獨行,也不把我當小孩,我很樂意跟他們聊天(舅舅話不多,主要是和舅媽聊)。我喜歡動手做各種模型,但平時難得見到同好。等舅舅舅媽上門,我才找到了有共同語言的交流物件,喜不自勝。所以,每年寒暑假我最盼望的事就是他們帶著表弟一起來訪。
我盼星星月亮一樣盼舅舅來我家,重要原因還包括他每次都帶來我在其它地方接觸不到的好玩的物件,讓我大開眼界。有一年,這個物件是他自己做的十通道遙控汽車(所謂十通道就是有十個引數可以獨立控制,除了前進後退轉彎這些常規操作,還可以鳴喇叭,打大燈和轉向燈等等)。我迫不及待地在樓下壩子玩開了,周圍很快就圍滿了鄰居,大家哪見過這種洋盤啊!美中不足是續航時間不夠理想,才玩了二十分鐘就不得已收工了,意猶未盡,百爪撓心。
還有一年,他帶來的是一臺中華學習機,也就是蘋果2電腦的仿製藥版本,做工自然要糙一些,但是軟體都相容。那年夏天我過足了程式設計遊戲癮,警察抓小偷、吃豆人、小蜜蜂、武士、交叉火力,玩得我不亦樂乎。我每天早上起床就開始鏖戰,直到月上三竿才跟電腦依依惜別,把學習的事完全忘到了九霄雲外。
不過,我學到了最最重要的知識點:只要我也像舅舅一樣學好技術,有獨門絕技徬身,啥別人沒見過的好玩意兒都是我的。
因為這樣的驚喜每年固定來兩次,我們可以推匯出一個公式:
我舅舅 ≈ 2*聖誕老人
科學地說,舅舅比聖誕老人還要高出兩篾片兒,因為:第一,聖誕老人只會給你你想像得出的禮物,而舅舅帶來的好玩意兒經常是我想不出來在這個世界上可以存在的。因為這一點,我對我的強強表弟各種羨慕嫉妒。第二,聖誕老人放下禮物就不見了,舅舅還會經常參與玩耍的過程,讓樂趣加倍。
現舉一例說明:在全國禁放煙花爆竹(四川叫火炮兒)之前,我們這些兒童每年春節的娛樂重頭戲就是把壓歲錢換成一支一支菸花和一餅一餅火炮兒,再一個一個點燃化成灰,也就是燒錢。過年那幾天出門有特別的風險,因為隨時會有熊孩子從樓上點燃了火炮兒扔下來。這些炸彈投放時並無一定目標,爆炸時機也缺乏精確控制,炸到哪個行人的哪個器官完全看緣分,據說市醫院每年這時候都是急診的高峰。
作為小孩兒的一員,我對放炮一事非常上心,畢竟可以正大光明使用攻擊型武器的機會難得。不過我曉得哈數,不扔殺傷力強的電光炮兒,只(捨得)把一毛錢一餅的小火炮兒拆散了一個一個扔。只有一回大手大腳了:我覺得老是單發不過癮,便把兩枚甚至多達三枚火炮兒的引線強扭在一起,做成集束炸彈,達到一次點火多次聽響的至高享受。但我很快發現這樣粗鄙的工藝良品率是個問題,集束炸彈經常空中解體,三枚火炮兒只有一枚能響,其它兩枚在被引燃之前就脫離了母彈,落到地面時還是完好如初,白白便宜了候蹲在樓下撿耙貨的唐二娃。
舅舅會帶著我們小孩兒們一起放火炮兒。他一手拿炮,一手拿煙,先吸一口煙,待菸頭紅亮之時將引線點燃,再隨手丟擲,動作優雅,姿態瀟灑。又或將火炮預先埋設在目標(比如花盆裡用做養料的蛋殼)下方再行點燃,是為定向爆破。舅舅還敢放一種特大號的電光炮兒,叫“雷鳴”。雷鳴炮名符其實,威力相當於毛時代的石油工人,平地一聲吼,地球抖三抖。我從來不敢親自放雷鳴炮,只會支使舅舅去,我則遠遠地捂著耳朵等著看熱鬧。
炮放多了,啞火的情況總是少不了的。通常這是因為引線質量不過硬,還沒燃到火炮兒內部就熄了。這時我們便會廢物利用,把火炮兒的外殼拆開,露出火藥,再直接點燃火藥。這種玩法叫做“噓”。因為不在一個密閉的環境裡,這時火藥的燃燒不會引起空氣劇烈振動,只有噗的一聲。
有次我們遇到了雷鳴炮啞火。舅舅拆開外殼,問:哪個來噓?
我跟強強面面相覷,都不敢上前。舅舅對我們這種懦夫行為大搖其頭:這有啥子好怕的,出息點!然後,他左手持雷鳴,右手菸頭直接就杵了上去。
聲震寰宇!
它它它,咋不講武德?開了包的火炮兒咋也會響?
舅舅一邊吹著手指,一邊自言自語:它咋個炸了喃?
我又學到了兩個知識點:
-
舅舅也有知識盲區。
-
雷鳴炮裡面填充的是炸藥,不是火藥。
~~~~
出於對舅舅的無比信賴,我在參加《我們愛科學》雜誌知識競賽時,拿出自己的答卷去和舅舅對答案。其中有一道題問“輪船浮在水面上是因為浮力等於還是大於輪船的重量”。我記得在以前在書上看過是“等於”,雖然我也不太明白原理。但是舅舅說是“大於”,我將信將疑,還是改成了舅舅說的“大於”,後來發現這是錯的。
經過這一件事,我意識到舅舅也不是完人,任何專家都可能犯錯誤,尤其是出了自己的領域。於是,每次見到有人牛皮哄哄地擺資格,我就會提醒自己:我舅舅都會犯錯,你以為你是老幾?
舅舅才藝出眾,但並非完美到不真實的地步。他也有缺點。在我看來,他的主要缺點是一心撲在愛好上,把家務事都推給舅媽了。這麼多年來,舅媽把他的生活照顧得妥妥帖帖,也是辛苦極了。
~~~~
母親小時候的照片中,有一張跟舅舅的合影。那時候舅舅大約五歲,跟強強小時候長得一模一樣,臉圓乎乎的,拿著一塊餅乾,眼睛裡滿是好奇。我特別喜歡這張照片。

母親曾指著這張照片說舅舅小時候胖乎乎的,所以小名叫皮球。相對於外型,我倒是覺得這名字更契合舅舅的精神氣質:四川人把個性張揚不曉得天高地厚叫“跳站”,皮球在地上反彈起來也叫“跳站”。這個詞在傳統觀念裡略帶貶義,言下之意你這麼牛你咋不上天呢。但我願意把它當成一個褒義詞。舅舅不按別人劃的規矩來,把自己的愛好做到極致,活得瀟瀟灑灑,這種精神確實很“跳站”。
舅舅這個星期去世了。曾經我心中的蓋世英雄,終究化成了一抔黃土。我很懷念跟他一起的時光,希望他在天堂繼續跳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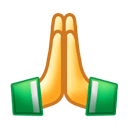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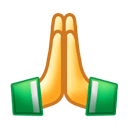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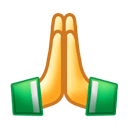
~~~~~~~~~~
猜你會喜歡:
-
二〇八四 – 原創科幻小說
-
鋼鐵理呆是怎樣練成小說闖作者的 – 我編小說的法子
-
陽光燦爛的日子 – 我的美國兄弟大強
-
小說:美樂火鍋店 – 西雅圖不眠夜
-
從莫斯科郊外開始的回憶 – 紀念我的同學 L
-
睡在我上鋪的郭教授 – 我是如何同室操戈的
-
睡在我對角的老廖 – 大學生活,無非就是睡來睡去
-
白水繞東城 – 關於老內江的回憶
~~~~~~~~~~
關注老萬故事會公眾號:
碼字不易,嘔心瀝血只是希望更多人看到。如果喜歡這篇文章,請不吝訂閱、轉發、評論。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