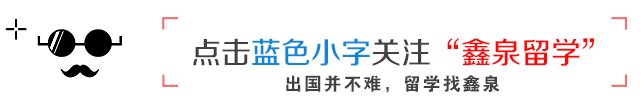文章來源:麥哥自留地
好友留言,提出了一個很有價值的問題:以格隆維為發端和代表的北歐教化(Nordic bildung)與中國傳統教育理念有何異同?
自2022年開始深入接觸以丹麥為代表的北歐教育理念、實踐和演變歷史以來,這個問題曾多次浮起在心頭,但至今也深感自己的學識積累不太足以回答這麼“大”的問題。與好友的這次討論,讓我感到有必要先把目前的體會總結出來。未盡部分,偏差部分,不妨留作以後補充、修訂。
值得說明的是,本文所指的“中國傳統”,是秦漢以來長期實際執行的觀念、習慣。很多學者認為,這些“傳統”與先秦(及更遠)時代的儒、法、道等原初概念和理念已經大不相同。但,竊以為,“傳”下來了且成為“統”合性的思想和行為規範、習慣的,才是真實的“傳統”。
在我看來,中國傳統教育理念的核心是以“至善君子”為目標的“修己”(不斷自我完善)和以“修齊治平”、“三不朽”(立功立德立言)、橫渠四句(為百姓立身,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天下開太平)為目標的“達人”——其中最重要的目標就是“做官”,幫助皇帝治理天下。
而北歐教化理念的核心是教化(可參見《教化(Bildung)的詞源、譯名及其核心理念》)——幫助學生找到自主成長的動力、信心和方法,使其“身心靈”全面成長。目標層面,北歐教化力圖培養“完整的人”,培養有自主思辨能力的“自我創作者”(可參見《北歐的發展秘訣對中國有什麼借鑑意義》),使其既珍賞個體的自由,也具備對集體、民族國家及更大“社群”的歸屬感和責任感。
如果說共同點,兩者都認同學習是一個不斷提升的修習、進化過程,也都強調責任感,除此之外,還有待進一步挖掘。差異點則明顯得多。
1. 君子與常人
好友與我一致認為,中國傳統教育的第一特徵是,要培養“君子”。何謂君子?在《詩經》、《論語》、《大學》等典籍中有不同角度的描述(“君子不器”、“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等)。好友把“君子”比作馬斯洛模型的“自我實現”,我覺得後者只是定義了最高階的個人需求及追求,而前者要比後者標準高很多,簡單理解就是“明德”、“親民”、“至善”的完人。
以君子為培養目標,當然志存相當高遠,可是“步子邁得太大,容易扯著蛋”。與社會構建領域的各種烏托邦夢想類似,著力培養“君子”的結果,反而是產生了一代又一代的“偽君子”。大家都知道自己不是君子,但都是要臉的人物,不能自貼標籤為“不合格產品”啊,於是必須把各種“口號”、“標語”、“禮儀”講究到極致。臺前必須演好“正人君子”,哪怕做的是枉法苟且之事。
好友說得好,“我們在倡導君子人格時,是將君子作為我們的方向而不是要做到的標準。不可以用君子的標準衡量自己,使自己沮喪而放棄。更不能用君子的標準衡量別人,做道德綁架。” 我倒覺得,就連“把君子作為教育的方向或目標”本身都是弊大於利的。雖然幾千年歷史中不乏意志堅定、始終如一、堅持追求完美的光輝個例,但不可否認的是多數學子逐漸習慣了背誦不可行之文字,生活中說冠冕堂皇但並不信之話,踐著“不合知”之行。
北歐教化的思想基礎之一,是基督教之承認人性中的複雜,特別是,存在極難革除的“惡”的誘因和所謂“撒旦”的強大。它要培養的是“幸福的普通人”,是自我心智不斷發展(從自我發現、自我鞏固、自我管理,到自我創作和自我轉化,從認同個人、同伴、家庭這樣的小歸屬圈到社群、民族、國家、人類、地球這樣的大歸屬圈,可參見《北歐的發展秘訣對中國有什麼借鑑意義》)的常人。正因為坦然承認大家起點都不高(但誰也不比誰低),所以大家平等、寬容以待,一起互相鼓勵,為彼此的每一點點“進步”加油喝彩。
2. 精英與民眾
在中國傳統裡,“做官”是受教育的壓倒性目標(“學而優則仕”),而與民相比,官總是少數人。何況,開民之智對專制統治者從來沒有好處。中國傳統教育的主體始終是精英貴族教育。“芸芸眾生不足掛齒,不在視野之內。”(好友語)“民貴君輕”也就是孟子時代的驚鴻一瞥,沒有機制配合,就是一個說法而已。
而北歐教化最突出、最獨特的地方,就是它旗幟鮮明地以最底層的民眾教育為主體。除了基督教思想的影響,彼時(1850年前後)丹麥社會正在徹底擺脫封建制度,較低階層會渴望且必然獲得政治權力;如果他們沒有能力把握他們所追求的權力,那將是一場災難。以格隆維為代表的北歐教化開拓者們堅信,以農民為主體的底層民眾必須得到精神和認知上的全面提升,才能適應工業化和民族國家時代的需要。他寫道:
“光明照耀學者,是否只是為了拼寫正確?
不,天空希望更多的人擁有美好的事物,光明是天賜的禮物,
太陽昇起與農民同在,而不僅僅是學者……”
北歐教化的以民眾為主體的理念,還深刻影響了其同時代的合作社等民間社會的發展。創辦丹麥第一家農民合作社的牧師漢斯·克里斯蒂安·索恩說,合作社的目標是:
“……提升在社會中處於較低境地、備受壓力、習慣於依賴的人群,使他們達到更高的道德、智力和社會化層次,從而在社會中獲得更體面的地位。”
3. 自由與責任
北歐教化之父格隆維把自由和責任作為培養目標的兩個關鍵詞,前者又是重中之重。他的自由理念,是德國的內在自由(源自歌德、費希特、席勒等的德國唯心主義和浪漫主義,可參見《丹麥的秘訣——是什麼塑造了北歐國家》)和英國的政治自由(包括宗教自由、新聞自由、貿易和商業自由,以及教師與學生之間的平等合作關係、以平等討論為主的教學方式等)的結合。摘錄《北歐秘訣》中對格隆維的自由觀的描述:
“這是作為個人追求進步的自由,也是作為公民參與社會的自由。它是有根基並生長的自由,也是四處傳播和改變一個人心智的自由;是學習的自由,也是教導的自由;是與他人在一起同時又保持自我身份的自由。這是透過“教化”實現的自由;個體的教化以及民族的教化,即民眾教化。”
中國傳統教育缺乏“個體自由”概念,反而強調集體、服從和犧牲。其“責任”,雖然在理念上沒有拋開“百姓”、“生民”,但首先是“忠君”,是在服從君主的絕對權威這一前提下,造福百姓蒼生。而北歐教化的“責任”,是基於自由平等理念和內心對集體(社群、歸屬圈)的認同,對彼此、對集體的責任。
4. 規訓與思辨
中國傳統強調“禮”,也就是秩序、規範,因此教育要培養“克己復禮”的人,也就是遵從規範、規則、“上意”、習俗者。這樣的“產品”可以很好地成為社會等級秩序和運轉機制的一個部件和工具,滿足維持現有統治的需要。在自我發展理論裡,這就是自我層次的第3層、即自我管理者(可參見《北歐的發展秘訣對中國有什麼借鑑意義》)。
格隆維啟動的北歐教化1.0的主要目標,也是促進年輕人向自我管理者轉變。但與中國傳統教育不同的是,它培養的是活力、熱情、有目的 / 意義感的的自我管理者,前者的產出則是被教育過程及其社會環境強迫進入的、消極被動、無意義感的自我管理(服從規範)者。
北歐教化1.0並沒有明確培養學生的自主思辨意識,但其平等討論、鼓勵不同觀點的教學方式,實際上有助於學生們自然形成一些自己的判斷力和自主性。十九世紀末期和二十世紀早期,隨著現代經濟和文明的發展,過去強調的服從性和追求一致性已經不再適應現代化社會的新要求—民眾都應該“自我創作”(基於自主思辨的自主性)。以易卜生的《玩偶之家》為代表的北歐“文化激進運動”,則及時促進了北歐教化2.0的形成,自我創作者明確成為北歐教化的培養目標。
在中國,除了約100年前和約40年前的兩個特殊歷史階段,教育的規訓傳統以頑強的生命力一直延續下來。
5. 知識與生命
中國傳統教育,以灌輸知識和技能為主。有用的知識的範圍是具體、清晰、狹小的——以“四書五經”為代表的“聖賢書”(典籍)。有用的技能,主要是寫評價標準明確的應試文。雖然也出現過“學、習並重”、“有教無類”等具有“現代”色彩的教育理念,但或淡出或原本就不是主流。
格隆維則認為,首先必須激發學生的生命活力和熱情,知識和技能的學習才會真實有效。這一理念在第一批民眾學院尚未貫徹成功,但很快被北歐教化的另一關鍵人物科爾德發揚光大,他創辦的雷斯林格(Ryslinge)民眾學院的巨大成功,很快被複制到如雨後春筍般湧現的100多所民眾學院,並深刻影響了大量的職業學校和常規學校。
科爾德明確提出“先啟用,後啟蒙”的口號,甚至自評“啟用比啟蒙做得好”。他的“啟用”方法,是從學生們熟悉的生活場景和材料入手。例如,他帶第一批學生學習世界史,不是從講歷史課本,而是從一起讀學生們熟悉的流行作家英格曼的流行小說開始。小說、故事、詩、歌,都成為科爾德學校的學習材料。科爾德民眾學院的師生“同吃、同住、同玩、同勞動、同討論”,共同創造“家”一樣自由、舒適、讓人放鬆的環境,也是科爾德啟用學生生命的重要方法。
科爾德還把格隆維的“在實踐中學習”的理念落了地。他很可能借鑑了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齊的做法,在學校開辦了農場,並經常帶學生們去裝置和技術更先進的大型專業農場學習、實踐農業技術。
格隆維和科爾德把彼時丹麥的傳統學校稱為“死的學校”,以民眾學院為代表的新學校則稱為“為了生命的學校”——這真是對北歐教化理念的最凝練的總結!
回顧傳統,目的當然是以古觀今。對照他人,目的還是回看自己。他鄉之石,未必可以攻吾鄉之玉(形成中國的良好教育),但,至少可以有助於我們把手裡的刀、斧、鑿子弄得更鋒利些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