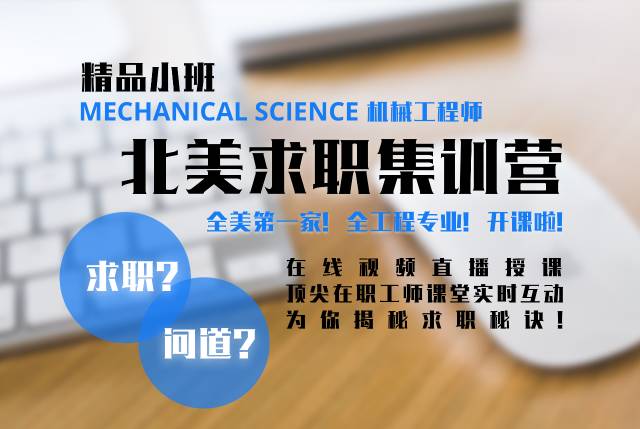文 |蔡家欣
編輯 |王珊瑚

一個老師的“罪與罰”
直到接到停課通知,28歲的孫依才知道自己被舉報了。
這是發生在2022年年末的事。某個週三的傍晚,黨委書記、副校長,再到教導主任,幾個校級領導坐在會議室裡,逐字念著那封針對孫依的匿名舉報信。
“罪名”被一項一項羅列出來。首先是在網路上發表不當言論,證據是孫依的一個微博小號,就像是私人日記,她在上面記錄生活,也吐槽工作。相應的“罪名”還有“看不起同事,不團結同事”、“辱罵學生”……沒拿獎的運動會,也被扣上了“組織能力差”的帽子。
每一項“罪名”底下都會附上她的微博截圖,“這就是人家的證據。”她無法認可,“我只是有這麼一個臭毛病,愛在網上記錄東西,但我私下的情緒從來不會帶在辦公的場合。”
學校直接給了孫依一個處分:停課,且沒有說明期限。孫依試圖辯解,但校方沒有給她機會。那份人事決定已經被蓋上紅戳,“這是來通知我的,不是讓我解釋的。”
孫依是江蘇某中學的語文老師兼班主任,入職不到三個月。就在被處分的半個小時前,她還主持著一堂校級戲劇選修課,給學生示範表演方法。被舉報之前,她從來沒有收到過任何不滿的訊號,不管發任何通知,班級群裡家長都是一連串的大拇指和玫瑰花,“都很有禮貌,沒有任何一個人表面上對你提出不滿。”
在那間被審判的會議室裡,孫依感受到了屈辱和難堪,“你就是透明人,所有的隱私都沒了。”就連非工作時間抽菸也被稱為“生活方面有問題”。
在教師的圈子裡,遭遇類似不實或者不合理的舉報,並非孫依獨有。舉報通常來得很突然,還帶有隨意性。在蘇州的一所鄉鎮小學,多名老師被同時舉報,理由是“學校伙食不好”,事後的調查中,學生坦承,自己的班主任之所以“逃過一劫”,只是因為班主任名字中帶有生僻字,打不出來。
有些時候,舉報的理由聽起來荒誕、無厘頭。一位學生報警,稱個人財物被老師拿走了——事情的起因是,他在課上玩手機而被沒收。還有一位男生向學校舉報,自己被女老師“摸了”,監控呈現的事實是,他在課上睡覺,老師把他拍醒了。
2010年以來,教師的思想政治和師德師風建設被提到了一個重要位置,多個會議精神強調,要加強師德師風建設,培養高素質教師隊伍。2014年教育部出臺《關於建立健全高校師德建設長效機制的意見》,劃出針對高校教師的“紅七條”,2018年,相關的紅線被擴充到“紅十條”,包括不得損害國家、學校和學生的利益,不得違背黨的政策方針路線、不得徇私舞弊、收受財物等。
相應的體系建構也在並行。比如,形成以“師德為先”為核心的教師考評制度,同時還有社會監督體系,不僅有多種形式的投訴和舉報平臺,還鼓勵學校、教師、家長、學生參與。
作為一種監督手段,投訴和舉報進入公眾視野。班級層面,有家委會、校委會的渠道;學校有專門的舉報電話、郵箱,以及處理舉報的辦公室,往上還有教育局、教育廳。此外,市長熱線、以及12345投訴電話也能受理。舉報者的身份從學生,到家長,有時甚至是一個鄰居,“你有一個教師的身份 ,如果哪裡做得不好,道德都會把你綁得高一點。”一位被舉報的老師說。
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這張監督的網正在收緊,甚至出現了擴大化的趨勢——具體表現為針對教師群體的不實或者不合理的舉報正在增多。一位教齡20多年的老師回憶,從2017年開始,針對教師的舉報,特別是不實的、不合理的舉報開始增多,以她所在學校30個班級為例,每兩天大概就能收到一個舉報。
根據公開報道,學生丟了橡皮,教師開車上班,甚至是吃一份外賣,都有可能成為舉報的由頭。2024年10月,《半月談》雜誌發表文章顯示,2024年1月至8月,西南某教育局共收到128條舉報教師的信件,其中僅有7起屬實。


系統“風暴”
在現如今的教育系統裡,舉報就像是那顆丟進湖面的石頭,會引發一系列的震盪和漣漪。
27歲的曉糖是河北一所職業學校的班主任。2023年,這位從業不到三年的年輕教師,收到了人生的第一個舉報。“怎麼辦?都捅到教育局了。”曉糖還記得當時的慌張和恐懼。這通舉報電話從市長熱線層層往下,先到教育局、再到學校領導,最後來到曉糖的手上,舉報理由是“侮辱學生”。
舉報者曾是她班上的一名女學生,多次霸凌另一位失去母親的同學。一個晚自習,曉糖把那個女學生喊到走廊談話。曉糖描述,對方罵她,甚至還衝上來要打人。考慮到霸凌者以往的行為,以及借讀、留級等因素,學校開除了這位女生。
即便如此,從流程上來說,曉糖還是必須接受調查。這也是處理舉報的流程之一。目前,各個地區的教育部門不僅要求完善舉報制度,而且都會要求“有訴必查”,“有查必果”,“有果必復”。
關於答覆的材料,不同地區有不同的規定,有些只需老師說明原委即可,有些地方甚至要求學校出具老師的“現實表現材料”。
曉糖需要準備三份材料。首先是紙質說明材料,寫明事件原委,雙方言行,以及時間,具體到幾點幾分。其次,還要有七八個目擊證人,有老師,也要有學生,每個人寫一份證明材料,再簽字摁手印。最後附上現場的監控材料,曉糖甚至有點感激學校那幾乎沒有死角的監控。
但舉報並沒有結束。“侮辱學生”的調查流程結束後,那位霸凌者又以勒索、非法拘禁等理由繼續舉報曉糖。每一次舉報來臨,曉糖都要配合調查,準備材料。久而久之,曉糖的生活陷入了自證的迴圈裡。每一次澄清之後,事情不了了之,沒有人跟她說一聲道歉。沒完沒了的舉報,學校也苦惱,領導埋怨曉糖,“當時為什麼沒有注意處理好分寸?”
後來,這位舉報者衝進學校毆打其他同學,被送往派出所後,要求當面質問曉糖為什麼開除她。半夜12點,學校領導讓曉糖去派出所,“讓我去解釋,哄哄她,讓她不要再舉報了”。曉糖拒絕了,“我沒辦法服這個軟!”
“投訴全憑一張嘴,然後我們就要去調查事實,有一些屬實,有些純屬沒有發生過,有些是誇大事實。”在東部沿海某省份學校做副校長的陳震說。
兩年的任職經歷裡,每隔幾天,陳震都會收到一份舉報,不合理或者不符合事實的能佔到一半。有老師因為作業被反覆舉報——先是作業過多,減少後又被舉報太少,老師最後設定了“作業超市”,由學生和家長自行選擇,還是被舉報了,理由是“不負責任”,“區別對待”。
按照規定,陳震要對舉報作出解釋,同時提供解決方案。從學校的層面來說,最理想的方案是舉報者撤回舉報,“撤銷等於沒有記錄嘛”。為了解決舉報,學校通常要使出“十八般武藝”,比如反覆家訪,甚至求助派出所和社群協調、溝通。
有些時候,終結的開關,握在舉報者的手上。以陳震的學校為例,形成調查報告以後,還要聯絡舉報者,告知處理結果,只有當舉報者選擇“滿意”或者“理解”,舉報才能算解決,如果“不滿意”了,學校就要重新調查,再次撰寫報告。
如果舉報者提出特殊的要求,比如公開通報批評老師,讓老師寫保證書,為了息事寧人,學校甚至會各打一大板。一名舉報者因為給班上女同學造黃謠,被班主任批評後,轉頭舉報了老師。學校因為“造黃謠”給舉報者以處分,另一頭也希望這位女老師道歉,不再提及此事。
陳震坦言,這些情況都會讓老師失去信心,甚至與學校產生隔閡,“答覆(舉報)理由對於學校來說是應當的,但答覆要求一定要解決投訴,而無視投訴背後的原因就不對了。”


“捷徑”
面對不實舉報,大多數老師選擇忍氣吞聲,一旦系統被啟動,他們只能跟著鏈條轉動。舉報之所以給學校和老師帶來壓力,是因為它與教師的成長、學校的考核緊密掛鉤。嚴重的,學校負責人連帶會被約談、寫書面檢討,甚至是免去職務。陳震坦言,即便最後調查出舉報不實,一旦舉報次數增多,一所學校、一個老師的考核依然會受到影響。
績效捆綁之下,一旦舉報降臨,系統的神經就會緊繃,而老師通常會成為“犧牲者”。
一位老師在班上批評了作業不合格的學生,被家長舉報到教育局,學生也不去上課了。那段時間,學校領導帶著一堆人上門道歉,這位老師的教學比賽、公開課都被停掉了,她要每天晚上給在家的學生髮簡訊、發作業關心,幾乎所有的精力都用來應付家校矛盾。一個學期後,這起舉報終於解決——老師被調走了。
跟大多數老師不一樣,因為私人微博言論被舉報的孫依,選擇對抗。很長一段時間,那封舉報信就像一根刺,紮在她的心裡。
被停課期間,她一個人在出租屋裡,整夜睡不著覺,“到底是誰(舉報)?”為了弄清楚舉報者,孫依開通可以看到訪客記錄的會員,建立了一個文件,裡面記錄著有“嫌疑”的訪客資訊,“有蛛絲馬跡的我都會截圖下來。”她還跑到教育局的官網反映自己的遭遇,在網路上直播曝光。
一位年長的老師勸她忍下來,什麼都不要說,然後道歉,等風頭過去。孫依拒絕了。“我為什麼要認下來?如果我容忍,那他們會以為自己做對了,只會更猖狂。”
遺憾的是,像有一道銅牆鐵壁,不管她朝哪裡撞,都被彈了回來。她被那所民辦學校以違反規章制度為由,解除了人事關係。“他們本來可能想把這個事壓一壓,結果發現我這個刺頭壓不了。”孫依報警自己被惡意舉報,學校給民警的回覆是,這屬於內部人事決定。
就連父母也不理解她,“如果你沒做錯什麼,別人為什麼要舉報你?”
從效果上看,舉報作為一種教育監督手段,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學生的權益。自2019年以來,教育部至少通報了93起違反教師職業行為十項準則典型案例,包括學術不端、體罰學生、性騷擾學生,補課收費、收受禮金等行為。2022年遼寧大學一輔導員被實名舉報騷擾女學生,查實後被免職、撤銷教師資格。去年1月,華中農大一名教授被11名學生聯名舉報學術造假,調查核實後也被停止了職務和工作。
與此同時,硬幣的另一面也在顯現。舉報出現了擴大化的趨勢,許多教師公開表示,已經影響到日常教學,令他們深陷自證的泥潭中。
被不實舉報以後,一位老師記得自己在教育局第一反應是“委屈到哭”。想到平日裡的付出,為了鼓勵學生,甚至會自掏腰包買禮品,“這種子虛烏有的髒水潑到我身上,我很委屈。”她搜尋過維權路徑,但沒有,“我只能自證清白,然後調節自己,沒有任何渠道去維權,為自己做什麼,這是我最傷心的事情。”
網際網路上,很多人提到,不實舉報氾濫的根源在於舉報匿名以及沒有規定舉報者舉證的義務。僅有少數高校提出“若存在捏造事實、誣告陷害”,“應當承擔責任”。但更多學校,特別是義務教育階段,對舉報者幾乎未有明確的約束。
沒有義務的束縛,舉報一旦進入私人領域,很容易會變成報復或者是謀利的工具。作為副校長,陳震曾在校門口聽到家長的對話:“你投訴呀,打電話,我們上次投訴以後當天下午就弄好了。”輕飄飄的語氣,令陳震不是滋味。舉報脫離了監督的範疇,變成“家長達成目的的黃金手段”,或者說,“人民滿意的教育被解讀為一個人的滿意吧。”
在陳震的學校,一位老師曾被舉報“師風師德有問題”。監控畫面顯示,課堂上這位老師批評學生字寫得不好,作業本恰好放在桌角,老師轉身時碰到地上,舉報者將此描述為“甩作業本”。
在所有的舉報當中,對“師風師德”的指控最為嚴重。師風師德貫穿教師管理的全過程,包括資格認定、招聘、職稱評審、年度考核、推優評先等,一旦被認定為師德失範,在評優評先中都會被“一票否決”。關於其內涵,教育部曾印發相關通知,比如中小學教師要遵守的十項準則,包括堅定政治方向、愛國守法、傳播優秀文化,堅持言行雅正等。
但在實際操作中,相關界定帶有一定的主觀性。邊界的模糊,通常會使調查變得被動。在陳震看來,“甩作業本”就屬於“不合理”的舉報,但舉報者不依不饒——必須更換老師,否則孩子會有心理問題,對語文會有厭學情緒。“當一個人對學校或者老師有意見時,任何一件事都可以被放大”。


一個舉報者的素描
舉報擴大化的背後,那些隱藏的面孔究竟如何?他們是否知道,隨手發起的一個舉報,有可能改變他人的人生軌跡?
網際網路上盡是教師的怨聲,20歲的小悅是第一個願意向我們講述的匿名舉報者。
她是湖南一所大專學校空乘專業的學生,2023年,在陽光教育平臺上舉報了自己的任課老師,理由是“侮辱學生”。
衝突起源於一次“加課”。在小悅的描述中,為了能選上課拿學分,自己曾在課堂上多次舉手示意,“老師,我要加課。”但都沒有得到回應。直到她在講臺下大喊,“我說要加課,你沒聽到嗎?”
任課老師把小悅叫上講臺,看到簽到記錄後,拒絕了小悅的加課,“上次沒來上課的同學就不要加了。”爭執由此產生。當著全班同學的面,那位老師批評了她,“不想上課你就出去,你來學校幹嘛?想掛就掛了吧。”
小悅回憶當時的場景,“聲音非常大”,她只想逃離現場,“沒有考慮一個學生的自尊,那麼多人在上課,就批評你一個人”,“我人都要死掉了”。
離開教室後,小悅決定舉報,“恨不得她馬上從學校消失”,“(她要是)丟了工作我會很開心”。在那通舉報電話裡,小悅隱藏了自己的名字,“之後不給我補考怎麼辦?”
來到這所學校這個專業,小悅說是為了完成家裡給她的任務——拿到大專文憑,“我就是混日子,不是真心實意想讀書的。”其他同學也經常性逃課,“為什麼只針對我一個?”
委屈感或者覺得被針對,是舉報者普遍存在的情緒。一個學生因為期中作業有問題被掛科,計劃舉報老師。在他看來,任課老師在群裡催促別人交作業,也反饋過別人的作業問題,卻直接將他掛科,這屬於老師的教學責任。一個正在尋找舉報途徑的學生,成績被打不及格,老師拒絕加微信,不溝通,他認定這是“惡意”和“區別對待”。
在一位班主任的觀察中,很多時候,學生舉報或者報警,都只是為了發洩當下的情緒。曾有一舉報者在課上與人打架,被英語老師拉開後,這位學生直接報警,稱老師打人罵人。英語老師還在為報警的事而奔走、說明情況時,舉報者照樣上課、打鬧,“可能覺得跟在家裡一樣,耍一頓脾氣,爸媽還會跟沒事人一樣。”
舉報老師以後,小悅直接放棄了那門課。她形容自己“被打倒了”,“那個陰影一直在我的腦海裡”。父母指責她,要求她去上課時,她只有委屈和憤怒,“每次都把老師的話當聖旨,我在他們眼中什麼都不好,從來不問原因。”好朋友勸她,在學校老師就是權威,給老師帶一杯奶茶。
小悅反思,自己是不是錯了?但又放不下面子,“我覺得自己像在討好她一樣。”
那個學期末,這起舉報風波有了尾聲。被舉報的老師找到小悅“攤牌”,“尊重是互相的”,提到小悅平時遲到、提前溜走的表現。小悅不知道匿名舉報後為何會被發現身份,而在她看來,老師的解釋,是指責和教訓,為自己開脫。而她需要的是一個真誠的道歉。
她並不滿意這個結果,在學年的評價裡,她給這位老師打了0分。
如今,距離舉報過去一年,小悅已經在一家企業裡實習了。回過頭看,她覺得當時不上課的決定“太幼稚了”,她也不再希望這個老師被開除,“沒有必要”,“我也不想她沒了工作”。但被當眾批評的陰影還沒有褪去,痛苦依然真切,“她畢竟傷害了一個女孩的自尊,這種東西說廉價也廉價,說貴也貴。”

●一所學校公開的舉報電話。視覺中國

邊界
被霸凌者反覆舉報後,職校老師曉糖選擇離開這個行業。
離職前的三個月,每天早上醒來,曉糖都能感受到心臟“突突”地跳。舉報的事情在學校鬧得沸沸揚揚,課堂上,曉糖糾正紀律或者學生的行為,底下的學生就會起鬨,“你等著,我把你舉報到教育局去。”
她也陷入自我懷疑的漩渦中。當時,邯鄲一位小孩被霸凌至死的新聞備受關注。曉糖認為,霸凌需要被正視。“如果我打罵學生,你可以說是我的工作失誤。但她霸凌別人,我批評她,最後我被舉報,這個工作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做了。”
她多次向學校領導求助,對方的回覆是,能做就做,不能做就別做。她決定離職。“我寧願不幹,也不想再這麼尷尬下去。”
更多的教師則對職業的邊界感到困惑。一位年輕的教師因為學生打盹,讓全班站著晨讀而被舉報體罰學生。她說,再也不敢管了,“怕又被舉報”。
一些老師互相調侃,放下助人情結。一位曾被舉報過的老師表示,在工作中會時刻提醒自己,“太有責任心的老師沒有好下場。”對於違紀的學生,她如今只是告知,不再試圖去糾正。擔心被“誣告”,她甚至不敢跟學生髮生任何肢體碰觸。
作為一名校園管理者,陳震認為,不應該否定舉報這種監督手段,問題在於要“有餘地”,也就是具體問題要具體分析,“不能一投訴,就一定要投訴者滿意”。更應當重視的是“集體性投訴”,因為“一定有它的問題所在”。
在制度上,許多人認為應該考慮舉報者的責任,主張教師的權益。在2023年香港教育局更新的《學校投訴處理指引》中,校方被賦予了退出權利。比如,投訴者需要提供姓名、地址、電郵或者電話,以提供充分的(證明)資料,如若拒絕,校方均可不受理投訴。如果學校遇到不合理的持續投訴,也有權利限制或停止與投訴者的接觸,也可以發出《重複投訴覆函》,重申校方將不再回復或聯絡。
2023年11月,關於惡意舉報的問題,教育部也曾公開表示,對惡意歪曲事實,誹謗詆譭教師的蹭流量行為堅決回擊,維護教師的合法權益。
行業性的探討之外,一些影響更為幽微而個體。
很長一段時間,因為微博言論而被舉報的孫依,似乎停在了原地。“對我打擊確實很大,沒把這個事情弄清楚,我都不想往前走。”無處維權,孫依選擇直播,在網上曝光自己的經歷。那段時間,她讀得最多的就是魯迅的《故事新編》和《朝花夕拾》。“有些人會因此不說,但是我不,我就要戰鬥,不會因為他們而退卻。”
2023年底,孫依考上一所985高校的文學博士。儘管已經開始新生活,但她還在尋找那個舉報者。她說,“情緒上已經走出來了,但理性上還是想知道是誰,這成了我的人生問題。”
在QQ 空間訪客裡,她發現了一位男性頻繁訪問的記錄。那是原來學校的物理老師,四十多歲,多年前也曾經被舉報過,在圖書館工作一年之後才返回教職,“他可能想看看,這個跟他有同樣經歷的小女孩咋樣了。”
(文中講述者為化名)
版權宣告:本文所有內容著作權歸屬極晝工作室,未經書面許可,不得轉載、摘編或以其他形式使用,另有宣告除外。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