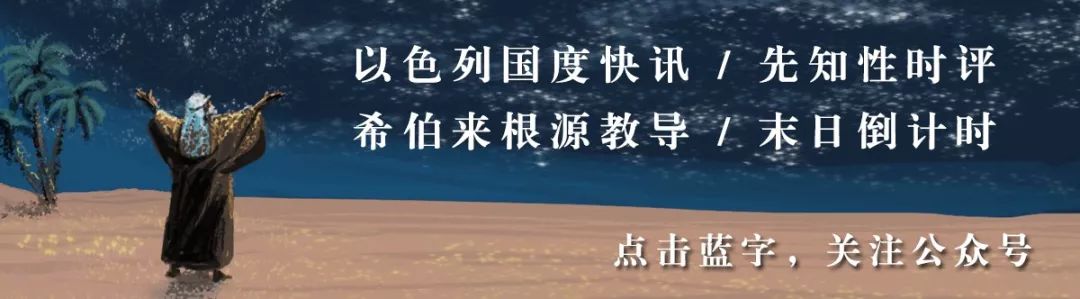文丨古原
1979年1月16日,德黑蘭的梅赫拉巴德機場寒風凜冽。
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這位自稱“王中之王”、“雅利安人之光”的伊朗沙阿,正準備踏上他永不復返的流亡之路。
他的臉龐,曾經在無數官方肖像中顯得威嚴而自信,此刻卻寫滿了疲憊、困惑與難以置信的傷感。
他親吻著一小袋伊朗的泥土,淚水悄然滑落。
這位統治伊朗長達37年的君主,一手將國家從一個半封建社會推向現代化門檻的建築師,始終無法理解,為何他傾盡心血澆灌的子民,會如此決絕地將他驅逐。

他的皇后法拉赫·迪巴站在一旁,優雅中透著哀傷。
停機坪上,少數忠誠的軍官和政府高官強忍著淚水,進行著最後的告別。
而在機場之外,德黑蘭的街頭是另一番景象:汽車鳴笛,人群歡呼,慶祝著“暴君”的離去。
收音機裡播放著革命歌曲,人們高喊著一個名字——魯霍拉·霍梅尼。
巴列維登上了那架名為“沙欣”的波音707專機。
當飛機引擎轟鳴,緩緩升空,他最後一次俯瞰這座他親手塑造又最終失去的城市。
那些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樓、寬闊的公路、現代化的大學和工廠,在他眼中,既是榮耀的豐碑,也彷彿是此刻無情的嘲諷。
他堅信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伊朗的偉大復興,為了讓波斯文明重現榮光。
他給了人民土地、教育、健康和前所未有的富裕,為何換來的卻是背叛與仇恨?
這個問題的答案,並非一個簡單的“獨裁者被推翻”的故事。
它是一部交織著雄心、善意、致命錯誤、民眾誤解與政治野心的複雜悲劇。
一)白色革命
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的統治,始於一個屈辱的時刻。
1941年,他的父親,一手建立巴列維王朝的禮薩·汗,因其親德立場被英蘇聯軍逼迫退位,年輕的巴列維在一片混亂中繼承了王位。
這段經歷在他心中種下了兩顆種子:
一是對於國家主權和強大的極度渴望,二是對外部勢力干涉的深刻警惕。
早年的統治充滿了動盪。
其實伊朗一直是中東國家最民主的國家。
巴列維剛上臺時,伊朗本質上是君主立憲制,是有選舉的,民選首相負責國家主要事務。
但民主,不代表正確。
1953年,民選首相摩薩臺推動石油國有化,與西方國家發生了摩擦,最終,民選首相在美國中情局和英國軍情六處的策劃下被推翻。
這時,巴列維的王權才真正成為了實權。
這次事件,後世稱之為“1953年政變”,成為了國王統治合法性的一個永久汙點,也為他後來的悲劇埋下了伏筆。
但在巴列維自己看來,這並非是充當“西方傀儡”的開始,而是撥亂反正的必要之舉。
他認為摩薩臺的激進民族主義正在將伊朗引向孤立和混亂,甚至可能落入蘇聯的懷抱。
他相信,只有他,一個擁有絕對權威的君主,才能在複雜的國際格局中,帶領伊朗穩步走向強大。
他需要西方的技術和資本,但他內心深處的目標,是利用這些來建立一個不受任何人擺佈的、現代化的波斯帝國。
這種信念在1963年達到了頂峰,巴列維發起了雄心勃勃的“白色革命”。
這並非一場流血的暴力革命,而是一系列自上而下的社會經濟改革方案,旨在將伊朗從一個由地主和部落首領控制的傳統農業國,轉變為一個工業化的現代國家。
其核心內容包括:
土地改革,這是白色革命的基石。
巴列維強制性地從大地主手中收購土地,再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出售給農民。
從國王的角度看,他認為,這是一石三鳥的妙計。
它摧毀了傳統封建貴族的經濟基礎,這些人是王權潛在的挑戰者。
透過賦予數百萬農民土地所有權,他試圖創造一個感恩戴德、忠於王室的龐大社會階層。
他相信,一個由自耕農組成的農業體系會比傳統的租佃制更有效率,能為國家的工業化提供穩定的糧食保障。
一位名叫哈桑的農民,生活在伊斯法罕附近的村莊。
他的祖祖輩輩都在為當地的大地主勞作,所得僅夠餬口。
突然有一天,政府官員來到村裡,宣佈他可以擁有自己的土地了。
這對於哈桑而言,是天翻地覆的變化,是國王賜予的、想都不敢想的恩典。
在最初的幾年裡,像哈桑這樣的農民,無疑是巴列維最堅定的支持者。
可是,國王並沒有想到,這其實是整個王朝崩潰的起點。
白色革命還有世俗化改革。
白色革命授予了伊朗婦女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並廢除了一些歧視性法律。
國王的妻子法拉赫皇后,本身就是一位受過西方教育的現代女性,她成為了這項政策的優雅象徵。
巴列維認為,一個國家若想實現現代化,占人口一半的女性就不能被束縛在家庭的角落裡。
他看到的是解放生產力,是提升國家形象,是向西方文明世界看齊的必要步驟。
他或許無法理解,這一舉動在傳統社會,尤其是宗教階層眼中,是多麼驚世駭俗的“西化”和對伊斯蘭教法的公然挑戰。
巴列維前所未有地推動教育事業,他建立識字軍團、衛生軍團和發展軍團。
成千上萬受過教育的年輕男女,代替了傳統的兵役,被派往偏遠的鄉村,教孩子們讀書寫字,普及衛生知識,幫助修建基礎設施。
這無疑是白色革命中最具理想主義色彩的一筆。
國王的設想是,透過知識的普及,打破愚昧和迷信的枷鎖,培養出一代忠於國家、而非忠於毛拉(教士)的新公民。
從宏觀資料上看,白色革命的成就斐然。
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初,伊朗的GDP年均增長率接近10%,文盲率大幅下降,人均壽命顯著提高,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開始形成。
德黑蘭的街頭,女性可以不戴頭巾,穿著時髦的西式服裝;大學裡充滿了渴望知識的年輕人;國家的財富,似乎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積累。


對於巴列維而言,這一切都證明了他的道路是正確的。
他以一種“大家長”式的心態統治著國家,認為民眾就像是需要引導的孩子,而他,作為父親,知道什麼對他們最好。
他將反對的聲音,無論是來自左翼知識分子還是保守的宗教人士,都視為阻礙進步的噪音。
他建立了令人生畏的情報機構“薩瓦克”,殘酷鎮壓異見者。
在他看來,為了實現國家現代化的宏偉目標,犧牲一些個人的政治自由是必要的代價。
他堅信,當伊朗人民享受到富裕和尊嚴時,他們終將理解並感謝他的“開明專制”。
他沒有想到,今天伊朗的女人是這副裝扮了。

然而,在這片繁榮的圖景之下,裂痕早已悄然出現。
土地改革雖然讓許多農民獲得了土地,但分配的土地面積往往過小,難以維持生計。
土地規模化,才能集約化生產,小農經濟的結果是農民更窮。
許多農民因缺乏農業技術、信貸支援和灌溉設施,最終不得不放棄土地,湧入城市成為打工仔。
他們脫離了熟悉的鄉村社會網路,卻又無法融入光鮮亮麗的城市生活,在德黑蘭等大城市的邊緣地帶,形成了巨大的貧民窟。
雖然他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遠高於他們務農,但在情緒上,他們成了現代化程序中的“失落者”,心中充滿了對未來的迷茫和對現實的怨恨。
更重要的是,白色革命嚴重觸動了宗教階層的根基。
土地改革沒收了大量的宗教“瓦剋夫”地產,這是清真寺和神學院重要的收入來源。
賦予婦女權利,在他們看來是對伊斯蘭家庭價值觀的顛覆。
識字軍團的世俗教育,則直接挑戰了毛拉們在鄉村地區作為知識和道德權威的傳統地位。
在這些反對者中,一個來自庫姆市的教士,魯霍拉·霍梅尼,發出了最尖銳的聲音。
1963年,他公開發表演講,將國王的改革斥為“美國和以色列的陰謀”,旨在腐化伊朗的伊斯蘭靈魂。

他將國王比作伊斯蘭曆史上的暴君,並直接質問:“國王先生,我勸你善良一點……難道你想讓人民在你被迫離開這個國家的那一天,彈冠相慶嗎?”
這句充滿預言性的警告,讓巴列維勃然大怒。
霍梅尼被逮捕,隨後被流放海外。
國王以為,拔掉了這根最硬的釘子,反對的聲音就會平息。
他低估了霍梅尼在信徒心中的地位,更低估了宗教作為一個組織和動員網路的巨大能量。
流亡在外的霍梅尼,反而成為了一個更純粹、更具感召力的象徵,一個反抗世俗化和西方影響的殉道者。
他的錄音帶,透過複雜的地下網路,源源不斷地從伊拉克和法國傳入伊朗的千家萬戶,在清真寺裡被反覆播放。
他的聲音,在國王的現代化高歌猛進中,如同一支低沉而固執的潛流,等待著合適的時機,匯成滔天巨浪。
二)石油的詛咒
1973年10月,第四次中東戰爭爆發,阿拉伯產油國對支援以色列的西方國家實施石油禁運。
油價在一夜之間飆升了四倍。
對於擁有豐富石油資源的伊朗而言,這彷彿是天降橫財。
在短短一年內,伊朗的石油年收入從約50億美元暴增至200億美元以上。
這筆鉅款,讓巴列維的雄心壯志徹底掙脫了束縛。
他宣佈,伊朗不僅要成為一個發達的工業國,更要建設成世界“第五強國”,一個“偉大的文明”。
他用近乎癲狂的熱情,將雪片般的石油美元投入到最大、最快、最先進的專案中:最尖端的武器裝備(伊朗一度成為美國武器的最大買家),核電站計劃,龐大的高速公路網路,以及在德黑蘭北部興建的奢華住宅區。
其中核電站設施,一買就是三十套。
1971年,為紀念波斯帝國建立2500週年,他在古都波斯波利斯的廢墟上舉辦了一場極盡奢華的慶典,邀請世界各國的王室和政要,宴會上供應的是巴黎馬克西姆餐廳空運來的美食。
在巴列維看來,這場慶典是在向世界宣告:古老的波斯已經甦醒,伊朗不再是任人擺佈的棋子,而是一個值得尊敬的、擁有輝煌歷史和光明未來的強國。
這是他民族主義情感的極致體現。
然而,對於大多數伊朗人來說,這場盛宴與他們無關。
不管如何,君主制的剝奪性顯而易見,國王和權貴們在沙漠的帳篷裡享用香檳和魚子醬時,那些得到土地分配的人,被鎖在農村的最低階層的農民,還在為清潔的飲用水而掙扎。
這場盛宴,在民眾眼中,不是民族榮耀的象徵,而是王室脫離人民、揮霍無度的證據。
真正致命的問題,始於這場石油財富的盛宴之後。
突然湧入的巨量資金,引發了災難性的通貨膨脹。
一個德黑蘭巴扎(傳統市場)的布料商人阿里先生是這麼看這個時代的。
在1970年代初,他的生意穩定,生活殷實,是一個典型的中產階級。
他或許對國王的某些西化政策不滿,但總體上享受著經濟發展帶來的好處。
然而,1974年之後,一切都變了。
他進貨的成本每個月都在上漲,他不得不提高售價,但顧客的抱怨聲也越來越多。
更讓他難以忍受的是,德黑蘭的房租在短短兩三年內翻了幾番,他幾乎要付不起店鋪和住所的租金了。
與此同時,阿里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
那些與王室和政府有關係的“新貴”,憑藉著政府的大型合同和進口許可證,一夜暴富。
他們在德黑蘭北部修建起一棟棟別墅,開著進口的賓士轎車,他們的妻子穿著巴黎的時裝,在高階俱樂部里社交。
這種貧富差距,不是抽象的數字,而是阿里每天都能看到的、刺眼的現實。
問題的關鍵在於,阿里的生活水平實際上可能並沒有下降,甚至還在緩慢提高。
但與那些暴富階層的差距,卻在以驚人的速度拉大。
這是一種相對剝奪感,比絕對貧困更具心理上的破壞力。
阿里和千千萬萬像他一樣的普通伊朗人,無法理解複雜的宏觀經濟學原理,他們不會將自己的困境歸咎於“貨幣供應量過大”或“經濟結構性失衡”。
他們的解讀方式是直觀的、道德化的:物價飛漲,是因為有人在囤積居奇,是政府無能;有人暴富,是因為他們腐敗、不道德,是“賣國賊”。
國王對這場經濟危機也感到焦慮和憤怒。
但他採取的手段,卻進一步加劇了矛盾。
他將通貨膨脹歸咎於商人的“貪婪”,發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牟取暴利”運動。
成千上萬的商人,其中許多是巴扎裡虔誠的信徒,被當作“經濟破壞者”遭到逮捕、罰款甚至監禁。
這對於視商業信譽為生命、在傳統社會中備受尊重的巴扎商人階級而言,是奇恥大辱。
國王非但沒有解決問題,反而將他們變成了替罪羊。
阿里先生和他的同行們,感到自己被那個他們曾經或多或少支援過的政權背叛了。
他們憤怒、屈辱,開始尋找新的同盟和庇護。
而他們天然的盟友,就在清真寺裡。
幾個世紀以來,巴扎與清真寺在伊朗社會中形成了一種牢不可破的共生關係。
巴扎商人是虔誠的信徒,他們為清真寺和宗教學校提供資金(奉獻“胡姆斯”和“天課”);而毛拉們則為巴扎的商業活動提供道德和法律上的背書,調解糾紛,維繫著社群的秩序與信仰。
當國王的現代化鐵拳砸向巴扎時,商人們很自然地倒向了他們的宗教領袖。
他們將資金、資訊網路和對社會基層的強大影響力,毫無保留地交給了反對國王的教士集團。
他們將霍梅尼的錄音帶藏在布匹裡,分發給顧客;他們在自己的店鋪裡,低聲傳播著對王室腐敗和“不虔誠”的批評。
伊朗的還有一群年輕人開始在行動。
這裡的學生,是白色革命的受益者。
他們中的許多人來自小城鎮甚至農村,正是憑藉國王大量的投資教育所提供的教育機會,才得以進入伊朗的最高學府。
然而,他們非但沒有成為王權堅定的擁護者,反而成為了最激進的反對派。
對於一位名叫萊拉的文學系女學生來說,她所看到的世界是分裂的。
她可以在校園裡和男同學自由辯論,穿著牛仔褲,閱讀薩特和馬爾庫塞。
但她也知道,在薩瓦克的陰影下,國王不能被批評。
她渴望的不僅僅是經濟上的富足,更是西方式的政治自由和真正的民主。
她看不起國王的專制,認為他不過是美國扶植的獨裁者,他的現代化只是為了更好地服務於西方主子的利益。
她和她的同學們,沉浸在左翼革命理論的激情中,將國王視為人民的壓迫者。
於是,一個奇異的聯盟在伊朗的地下悄然形成了。
德黑蘭北城追求西式自由的左翼知識分子,與南城巴扎裡渴望維護伊斯蘭傳統的保守商人,以及散佈在全國各地的宗教網路,他們唯一的共同點,就是對國王的仇恨。
國王對此並非一無所知,但他完全無法理解這個聯盟的邏輯。
在他看來,這些人是忘恩負義的。
他給了農民土地,他們卻聽信毛拉的煽動;他給了女性權利,她們中的一些人卻重新戴上了頭巾以示抗議;他給了年輕人教育,他們卻用學到的知識來反對他。
他覺得自己的善意被嚴重誤解了。
他看不到,他的改革雖然帶來了物質生活的飛躍,但如何解讀經濟發展,卻是由不同的觀念主導的。
伊朗民眾強烈的不滿,與伊朗高速發展的經濟完全不匹配。
是的,從1963年到1977年,伊朗的人均收入增長了近十倍,擁有汽車、冰箱、電視的家庭數量呈爆炸式增長。
一個在1960年還食不果腹的農民,到了1975年可能已經擁有了自己的拖拉機。
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也是國王自認為統治合法性的最大來源。
但普通人不是經濟學家,他們的觀念由知識分子塑造。
真正引發伊朗民眾革命的導火索,在於通貨膨脹。是國王錯誤的經濟發展觀念,導致了凱恩斯主義的後果爆發。
當他們看到德黑蘭的交通堵塞日益嚴重,港口因無力處理雪崩般湧入的進口貨物而癱瘓,當他們辛苦工作一個月掙的錢,還不夠在飛漲的房價面前支付一個月的房租時,他們不會認為這是“經濟過熱”的副作用。
他們會認為,是這個國家出了問題,是頂層的人腐敗透頂,將財富竊為己有。
霍梅尼的宣傳,精準地利用了這種普遍的道德焦慮。
他從不談論複雜的經濟理論,他只談論“正義”與“非正義”,“伊斯蘭”與“腐敗的西方”。
他將所有的“社會弊病”,無論是通貨膨脹還是“貧富分化”,都歸結為一個簡單的原因:國王背離了伊斯蘭,成為了“大撒旦”美國和“小撒旦”以色列的走狗。
這個解釋簡單、直接、動人,為所有感到迷茫、憤怒和被剝奪的伊朗人提供了一個清晰的敵人和一個神聖的鬥爭目標。
實際上,巴列維王朝治下的民眾生活水平,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提高。
但這種提高,伴隨著劇烈的社會變遷和價值觀的衝突。
人們得到的越多,期望也越高,對不平等的容忍度也越低。
國王以為他用麵包和黃油就能收買人心,但他錯了。對自身生活狀況的認知,是由每一個具體人的觀念決定的。
經濟的波折,如同催化劑,將這些潛在的不滿,徹底點燃了。
三)革命的烈焰
1977年,一股意想不到的微風從大洋彼岸吹來。
美國新任總統吉米·卡特,將“人權”作為其外交政策的核心。
作為美國在海灣地區最重要的盟友,巴列維感受到了巨大的壓力。
為了維持與美國的關係,也或許是為了向世界證明他的“開明”,國王決定略微放鬆高壓統治,開啟一絲“自由化”的縫隙。
他允許國際紅十字會探訪監獄,釋放了一些政治犯,並對媒體進行了一定程度的鬆綁。
這是一個致命的誤判。
對於一個長期處於高壓狀態的社會而言,突然的鬆動並非壓力的釋放,而是積蓄已久的洪水衝破堤壩的開始。
各種被壓抑多年的聲音,立刻從這道縫隙中噴湧而出。
律師、作家和學者們開始發表公開信,要求政府保障基本人權。
在大學校園裡,詩歌朗誦會變成了激烈的政治辯論會。
國王以為這只是可控範圍內的“噪音”,是他向西方展示姿態的道具。
他沒有意識到,他親手開啟了潘多拉的魔盒。
真正的導火索,在1978年1月7日被點燃。
德黑蘭的官方報紙《世界報》刊登了一篇匿名文章,題為《伊朗與紅黑殖民主義》。
文章用極其粗俗和侮辱性的語言,攻擊流亡在外的霍梅尼,稱他是英國的間諜,生活放蕩,甚至質疑他的伊朗人血統。
這篇文章的意圖,顯然是想透過抹黑霍梅尼的個人形象,來削弱他的宗教權威。
這步棋走得愚蠢至極,其效果適得其反。
對於無數將霍梅尼視為聖徒的信徒而言,這是對他們信仰的直接褻瀆。
第二天,在宗教聖城庫姆,大批神學院學生和市民走上街頭抗議。
當局出動警察鎮壓,槍聲響起,數名示威者倒在血泊中。
革命的引擎,就此以一種古老而神聖的方式被啟動了。
根據什葉派伊斯蘭的傳統,人們會在死者去世後的第四十天舉行隆重的悼念儀式。
2月18日,也就是庫姆慘案四十天後,伊朗第二大城市大不里士爆發了更大規模的悼念遊行,以紀念庫姆的“烈士”。
遊行再次演變為警民衝突,軍隊開火,造成了更多的死傷。
於是,一個無法停止的死亡迴圈開始了。
四十天後,為了悼念大不里士的死者,伊斯法罕、設拉子、亞茲德等多個城市同時爆發了示威。
每一次鎮壓,都製造出新的“烈士”;每一批新的“烈士”,都為四十天後的下一輪更大規模的抗議活動,提供了燃料。
霍梅尼的追隨者們,將這個什葉派的宗教傳統,變成了一個完美動員和組織全國性抗議的政治工具。
革命的火焰,就這樣以四十天為週期,在伊朗的版圖上,從一個城市蔓延到另一個城市。
面對這愈演愈烈的局勢,國王的反應顯得猶豫、矛盾且無力。
他一會兒更換首相,試圖以溫和姿態與反對派對話;一會兒又授權軍隊,進行更嚴厲的鎮壓。
這種搖擺不定的政策,在反對派看來是軟弱的表現,只會讓他們更加大膽。
此時的巴列維,正承受著常人難以想象的身心煎熬。
他已身患淋巴癌多年,病情正在惡化,化療的副作用讓他身心俱疲。
這個秘密,他向全世界,甚至向他最親近的臣民隱瞞了。
他越來越孤立,困在尼亞薩蘭宮的深處,只能透過一小撮親信的彙報來了解外界的局勢。
這些彙報,往往經過了粉飾和過濾。
他無法相信,那個他認為已經馴服的、保守的宗教勢力,竟然能爆發出如此巨大的能量。
他更無法理解,那些享受著現代化成果的中產階級,為何會與他眼中的“中世紀黑暗勢力”站在一起。
1978年8月19日,一個事件徹底改變了民意的天平。
在伊朗西南部的石油重鎮阿巴丹,雷克斯電影院在放映電影時突然起火,大門被從外面鎖上,消防隊也姍姍來遲。
超過400名觀眾,包括許多婦女和兒童,被活活燒死。
這是一場慘絕人寰的悲劇。
幾乎在火焰被撲滅的同時,一個謠言如野火般傳遍全國:這是薩瓦克的特工乾的,目的是為了嫁禍給宗教反對派!
儘管沒有任何證據,儘管後來的調查表明這極有可能是伊斯蘭極端分子所為(他們視電影院為西方腐朽文化的象徵),但在那個群情激憤的時刻,真相已經不再重要。
人們願意相信他們想要相信的。
雷克斯電影院大火,成為了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在公眾的想象中,國王的政權已經變成了一個不惜屠殺平民來維持統治的、毫無人性的惡魔。
憤怒的洪水,終於在9月8日沖垮了最後一道堤壩。
當天,德黑蘭宣佈戒嚴。
但成千上萬的民眾無視禁令,湧向市中心的賈勒廣場。
這一次,國王決心不再退讓。
軍隊得到了開槍的命令。
在密集的槍聲和坦克的履帶下,廣場變成了屠場。
這一天,後來被稱為“黑色星期五”。
“黑色星期五”的槍聲,徹底擊碎了任何對話與和解的可能。
它讓成千上萬原本只是同情抗議的普通市民,變成了不共戴天的革命者。
國王與人民之間,從此只剩下血海深仇。
一位當時在場的年輕士兵後來回憶,當他奉命向人群開槍時,他看到對面的人群裡有他的鄰居,有他妹妹的同學。
那一刻,他感到的不是忠誠,而是撕心裂肺的迷茫和罪惡感。
軍隊計程車氣,從那一刻起,開始瓦解。
四)王座崩塌、教士登頂
“黑色星期五”之後,伊朗社會陷入了全面的癱瘓。
大規模的罷工席捲全國,從石油工人到銀行職員,從教師到公務員,整個國家機器都停止了運轉。
石油出口中斷,切斷了王室政權的經濟命脈。
城市的夜晚,常常被“真主至大!”的呼喊聲劃破,這聲音從千家萬戶的屋頂上傳出,匯成一股令當權者不寒而慄的聲浪。
而在法國巴黎郊外的諾夫勒洛沙託小鎮,霍梅尼的住所成了全世界媒體的焦點,也成了伊朗革命事實上的指揮中心。
這位蓄著白色長髯、目光銳利的老人,透過電話和源源不斷送來的錄音帶,遙控著整個國家的命運。
此時的霍梅尼,展現出了他作為一位頂尖政客的全部才能。
他冷靜、堅定、不妥協。
他拒絕了國王提出的一切妥協方案,包括組建聯合政府。
他的目標只有一個,也從未改變:徹底推翻君主制,建立一個伊斯蘭共和國。
他的口號極具煽動性,卻又在具體細節上刻意保持模糊。
他向農民許諾土地,向工人許諾更好的福利,向知識分子許諾自由,向所有人許諾一個獨立、公正、不受外國干涉的“真正的伊朗”。
他巧妙地將所有反國王的力量團結在自己的旗幟下。
那些曾經領導反抗的左翼學生、自由派知識分子,天真地以為霍梅尼只是一位精神領袖,革命成功後,權力會回到人民手中,建立一個他們所期望的民主共和國。
他們成了霍梅尼最有力的宣傳者和組織者,他們沒有意識到,自己只是這位老教士用來奪取政權的“有用的傻瓜”。
一位叫萊拉的文學系女學生和她的同學們,日以繼夜地印發傳單,組織罷工,甚至學習使用武器。
她相信,她是在為自由和民主而戰。
當她高喊霍梅尼的名字時,她喊出的其實是自己對一個新世界的渴望。
她無法想象,在不久的將來,她所珍視的自由——不戴頭巾的自由,自由辯論的自由,閱讀禁書的自由——將會被這個她幫助推上權力寶座的政權,無情地剝奪。
民眾的選擇,是複雜的。
這不僅僅是對經濟困難的反應,更深層次的,是對一種文化和身份失落感的反抗。
巴列維的世俗化改革,是強加的、自上而下的,它粗暴地衝擊了伊朗社會根深蒂固的宗教傳統和生活方式。
對於許多普通人來說,德黑蘭街頭那些穿著迷你裙的女性、播放著靡靡之音的酒吧,不僅是生活方式的選擇,更是對他們信仰和尊嚴的冒犯。
這種被稱作“西方中毒”的現象,讓他們感到自己的國家正在失去靈魂。
霍梅尼提供的,正是一劑解藥。
他承諾的“伊斯蘭共和國”,是一個迴歸“本真”的承諾。
在這個理想國裡,伊朗將不再模仿西方,而是找回自己獨特的、以伊斯蘭為核心的身份認同。
經濟上的不滿,為這股強大的文化保守主義浪潮提供了現實的動力。
極端宗教思想與對經濟的錯誤不滿觀念,在此時完美地結合在一起,形成了一股摧枯拉朽的力量。
1978年底,國王做出了最後的、絕望的嘗試。
他罷免了軍政府,任命了長期以來的溫和反對派領袖沙普爾·巴赫蒂亞爾為新首相。
巴赫蒂亞爾是一位值得尊敬的民族主義者,他接受任命的條件是國王必須離開伊朗。
然而,對於已經徹底倒向霍梅尼的革命浪潮而言,巴赫蒂亞爾的政府既沒有合法性,也缺乏權力。
他被革命者斥為“叛徒”和國王的“看門人”。
1979年1月16日,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這位孔雀王朝的末代君主,永遠地離開了伊朗。
他的離去,引發了全國性的狂歡。
半個月後的2月1日,霍梅尼乘坐法國航空的包機,在萬眾矚目下降落在德黑蘭梅赫拉巴德機場。
數百萬人湧上街頭,迎接這位他們心目中的救世主。
那一刻,德黑蘭沉浸在一種近乎宗教狂熱的喜悅之中。
霍梅尼回國後,巴赫蒂亞爾的政府瞬間瓦解。
最後的抵抗來自國王最精銳的“不朽衛隊”,但當國家廣播電視大樓被佔領,當總參謀部宣佈軍隊在“革命”中保持中立時,一切都結束了。
1979年2月11日,巴列維王朝,這個統治了伊朗半個多世紀的王朝,正式覆滅。
五)苦澀的果實
革命的狂歡是短暫的。
隨之而來的,是血腥的清算和權力的無情鞏固。
革命法庭在霍梅尼的授意下迅速成立,對前朝的將軍、部長、薩瓦克官員乃至任何被視為“效忠國王”的人,進行草率的審判和處決。
曾經與教士們並肩作戰的左翼和自由派盟友,很快發現自己成了新的鎮壓物件。
他們被清洗、逮捕、流放,他們的報紙被查封,他們的組織被取締。
霍梅尼向人民承諾的“伊斯蘭共和國”,最終以“法基赫的監護”——即最高宗教領袖擁有絕對權力的神權政體——的形式得以確立。
婦女被強制要求佩戴頭巾,大學被關閉進行“伊斯蘭化”改造,音樂和舞蹈被禁止,社會的每一個角落都被嚴格的宗教教條所籠罩。
伊朗社會,從一個開放但專制的社會,倒退回一個封閉而保守的社會。
經濟上,革命並未帶來承諾中的繁榮。
相反,長達八年的兩伊戰爭耗盡了國力,西方的嚴厲制裁使得經濟發展舉步維艱,人才和資本大量外流。
國家經濟被掌握在各種不透明的宗教基金會手中,腐敗問題比巴列維時代有過之而無不及。
那個曾經被許諾給大眾的“經濟正義”,成了一個遙不可及的幻影。
伊朗,這個曾經有望成為中東最發達的現代化國家,陷入了長期的經濟衰退和國際孤立。
回望那段風雲激盪的歷史,我們不禁扼腕嘆息。
巴列維國王,雖然犯了很多經濟學的錯誤,比如分土地、控制價格等,但他還算是是一位有遠見、有抱負的現代化推動者。
他真心希望自己的國家富強,人民幸福。他的治下,伊朗民眾的實際生活水平其實是突飛猛進的,當時的伊朗是中東最為繁榮、現代的國家。
然而,他在經濟高速發展期犯下的錯誤,尤其是應對通貨膨脹的拙劣手段,親手將社會中堅力量推向了自己的對立面。
而伊朗民眾,在享受著生活水平飛速提高的客觀事實的同時,卻被相對剝奪感和對社會劇變的不安所困擾。
他們無法正確理解經濟波動背後的複雜原因,輕易地將所有問題都歸咎於統治者的腐敗和道德淪喪。
這種錯誤的認知,讓他們極易被極端主義的宣傳所俘獲。
最終,霍梅尼和他的教士集團,作為精明的政治反對派,敏銳地抓住了這個歷史的視窗。
他們利用國王的失誤,煽動民眾的不滿,將一場本可能導向政治改良的社會運動,引向了一場顛覆性的原教旨主義革命。
他們成功了,但他們帶給伊朗的,卻是一個更加保守的社會和數十年的經濟停滯。
巴列維王朝的覆滅,不是一個簡單的“暴君被推翻”的童話。
而是他們以為推翻了一個"暴君“,卻沒有想過,這個”暴君“居然是這幾百年歷史上,伊朗發展最快、最繁榮、大多數方面最開明的時代的創造者。
更沒有想到,他們迎來了一位更為”殘暴“的霍梅尼。
親手毀掉了伊朗這四十年民眾的生活。
經濟的暫時波折,與民眾對現代化的誤解、對世俗化的恐懼以及政治野心家的煽動相結合時,足以將一個充滿希望的國家,引向一條截然不同的、充滿荊棘的錯誤道路。
尼亞薩蘭宮早已人去樓空,孔雀王座上落滿了塵埃。
但它留下的悲劇故事,仍在歷史的長風中迴響,提醒著後人,通往繁榮的道路上,不僅有光榮的夢想,更有致命的陷阱。

今天鄭重推薦張老師的新品“張是之經濟圈”,簡單來說,這個下單是“買一得三”:
一個是我的經濟學的教學影片;
二是圈子裡其他內容資源和社群討論;
三是我們智谷趨勢的趨勢研判。
定價499,現在上新優惠只需要365。
下單後停留三秒鐘,會彈出一個微信二維碼,加上我們客服微信,拉你進群。
張老師本人微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