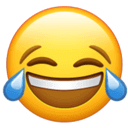第一批迴家過年的人已經“瘋了”。
當代年輕人與情緒的糾葛,在春節的時刻再次達到頂峰。
曾經用一句 “我素質不詳,遇強則強” ,懟得親戚啞口無言;到如今他們“心平氣和,保持呼吸”,情緒穩定成了新的座右銘。
這個春節,不只是團圓,更是年輕人重新審視情緒與自我的時刻。

當代年輕人與情緒的鬥爭從未停歇。
最開始是 “發瘋文學”,用看似荒誕的言語宣洩內心積壓的煩悶,尤其是在職場當中。
早起坐到工位,精神開始渙散:

人生目標是成為峨眉山猴子,天天搶人吃的然後蹲在山頭傻樂;

當然,網上發瘋的年輕人,現實中卻常常自稱任人拿捏的軟柿子:“惹到我,你算是惹到棉花啦。”
每天“好的”“收到”是他們真正的日常。

也因此,發瘋文學的情緒席捲而過之後,“淡人”漸漸成為更“高階”的應對方式。
“算了”,“就這樣吧”,“都可以”——主打一個情緒穩定,直接入土,淡然處世演到極致。
無法退化成猴的他們,甚至決定扮演“人機”。
低能量,低功耗,無意義,無波動,如同“半死不活”的NPC,自願成為別人故事的背景板。

而這種人機般的“淡淡的”,也真正對映到了人們在現實世界中的心態之中。
情緒穩定,開始成為人們信奉的四字箴言。
不爭辯,不解釋,不發瘋;不悲傷,不生氣,也不開心。
把情緒全部縮到名為“人機”的軀殼當中獨自消化。
春節回家,親戚問東問西,微笑回覆說“好的謝謝關心”;父母猛灌雞湯,頻頻點頭說“收到您說得真對”。

“如果我放棄自我,如果我沒有自我,那是否我也就沒有那些傷痛和掙扎。”
在情緒和自我的漩渦中掙扎的年輕人,偶爾這樣想著。
可隨之而來的壓抑、爆發,卻讓他們意識到,追求情緒穩定,只是面對傷痛時的“緩兵之計”。
情緒穩定,並非靈丹妙藥。它很難和炙熱的自我、濃烈的熱愛共存,甚至還會讓人更加情緒內耗。
讓人感覺自己彷彿一直沒什麼長進,始終會大笑、會落淚,有自己的追求、性格和苦惱,內心從不平靜。
也讓人進而生出更濃郁的挫敗感:“怎麼我就是做不到情緒穩定?”
但當下,越來越多年輕人開始自覺:“做不到情緒穩定,好像也沒什麼大不了。”
他們不想再遮掩情緒,也不想再裝成別的東西。
這一次,他們更想做自己——“什麼情緒穩定,我要情緒自由!”

某種程度上,很多人追求情緒穩定,只是面對自我和情緒迸發、又不知如何處理時的慣性動作。
從小到大,“穩定”都像我們懸在頭上的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
你要做一個“好學生”,滿足他人期待為先,滿足自我在後,要穩定地考公考研,穩定地開始工作,被告知忍耐是美德,在春節面對“你要清醒理智”的冷水。
就連情緒穩定也一樣。
一切的不穩定因素都被視作風險,偏離軌道的因素需要被絕對消除,帶著“好學生心態”,很多人成為了過度反思自己的自我PUA大師。

當我們產生悲傷,感到憤怒,甚至過於興高采烈時,總是充滿了“壞孩子”的恥感。
面對挫折如果哭泣,會反思自己是不是思想不夠堅強;
面對工作如果焦慮,會反思自己是不是心態不夠樂觀;
面對世界心懷熱望,也要反思自己是不是精神太過幼稚;
世界總想把我們雕刻成一種忍耐、穩定、體面、光滑的模樣。過於激烈的情緒應當被剔除,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人生態度被追捧。“如何保持情緒穩定”應該被放上神壇。

它被用來批判我們自己,甚至也被很多人用來審視他人。

但《普通生物學》教材上曾寫到:“人類的心臟於第21天即出現,到第30天左右心搏開始出現,從此再不停止,直至死亡。”
我們一味追逐著人生的穩定和情緒的冷靜,卻忘記了起與落的時刻,都是心跳加速的瞬間。
掙脫束縛之後不穩定的情緒,意味著我們在面對令人流淚也令人喜悅的生活時,更加坦然。
它意味著我們是鮮活的個體,在探索自我和世界的路途上,跌落又爬起,直面快樂,也直面悲傷。

每一次開懷大笑和痛哭流涕,都在與心臟一起跳動不息起起伏伏。
真正健康的情緒管理,或許並不是情緒穩定,而是情緒自由。
它意味著我們敢於真誠地直面自我,敢於勇敢地表達自我。
當我們憤怒,是因為我們有自己看待世界的角度,有自己所期待的人生,有屬於自己的話要表達;
當我們悲傷落淚,其實是讓自己慢下來,開始瞭解、積聚更多的自己,從而繼續前行。
每一次表達,每一道傷痕,每一種收穫,都對我們非常重要。
那些愉悅和傷痕,共同組成了我們,是我們自己的歷史,是我們自己的未來,是我們生命的閱歷。

“我們終其一生,就是要擺脫他人的期待,找到真正的自己。”
我們總會去追尋熱愛,奔赴自由,在激情中迸發旺盛生命力,感受生生不息的濃烈情感。
我們總會是我們自己。
成長的過程中傷痕不可避免,但它也同樣見證了我們在不同的情緒起伏中遇見自我的每一面。
或是探索未知的勇氣,或是永不磨滅的激情,或是歲月不敗的本真,或是無拘無束的自由。
熱愛仍在,何懼傷痕。
有所愛,無所畏——
在這個春節,Jeep也將與無數車主一起,攜手去往下一個新年,共同奔赴瀟灑、坦蕩而熱烈的自我。
所謂傷痕,只是他們驗證自我的戰損;而他們的內心,永遠指向自由與熱愛的方向。

阿威的角鬥士上一道道的傷痕,是他探索自我無限可能的證據。
從創立汽車改裝品牌到勇闖大洋彼岸,一路上的跌跌撞撞,都化作了車身上獨特的印記。
年輕的他,不相信穩定,只熱愛折騰。
在阿威看來,自己這一路,正因為歷經風雨而無比珍貴,也正因為那些傷痕而值得銘記。
朝著更遠的地方,他將繼續勇往直前,去折騰,去熱愛,去成為自己。
探索的路上總有傷痕, 但所有的痛與淚,都在滋養著成長與盛放。
DD的牧馬人,承載著她在攝影之路上的點點滴滴。
駕駛牧馬人,她在城市與山野間穿梭,也在車內工作室揮灑熱情。車身上的磕碰與掉漆,正是她在尋找獨一無二自己的征程中留下的勳章。
不相信千篇一律,無限的Passion,鼓動在DD的眼前與心中。
於是,她出發遠方,追逐未知。在與世界磕磕碰碰地交手時,用鏡頭定格一個又一個全新的自我和未來。
所謂傷痕,在她眼中不過是追夢路上的美好回味。
無論何時,踏上新的拍攝之旅時,她總是充滿激情,毫無畏懼。
黑松是一名越野拉力賽車手,他的大切諾基渾身是傷。
從美國的橄欖球賽場,到建立越野俱樂部,再到成為越野拉力賽車手——自由,是他的人生宣言。
越野路上的任何路段,他總是第一個開著大切諾基嘗試。縱使傷痕累累,但那正象徵著黑松對自由的執著追求。
“過自己喜歡的人生,不需要在意別人的看法。”
如今,黑松依舊在駕駛著大切諾基,奔赴心中的詩和遠方。
世界在變,而他始終如一,看著那些傷痕,他彷彿看到自由自在的自己——我還是我,我就是我。
秒哥和他的牧馬人,都像一部傳奇。
人到花甲之年,難道就該暮氣消沉、心無波瀾嗎?車開了12年,難道就會失去闖勁、沒有動力嗎?
他們說不。
60歲的秒哥,依舊在駕駛著牧馬人去野;而那輛12年、70 萬公里行程的“老馬”也還是活力滿滿。
他們攜手走過祖國的大江南北,也召集眾多車主,舉辦一場又一場活動。用熱愛,詮釋著一切都無法成為阻礙。
“老馬”身上當然有傷痕,而那傷痕,是秒哥心中歲月的詩篇。車會變舊,人會變老,但只要心中有夢,熱愛永遠年輕。
“歸來時的傷痕,是出發時的初心”——心無所畏的人生,總能奔騰不息。
每一道傷痕,都代表著一次追逐、激情與喜悅。
是勇往直前折騰自己的熱愛,是用Passion面對自己無限的可能,是永不停止追逐自由的腳步,是60歲、70萬公里,“我們依舊年輕”。
一路上刻下的磨難痕跡,是自我與熱愛交織的篇章。如同一團永不熄滅的火焰,讓人無畏前行路上的風風雨雨。
我們哭過笑過,有時站起,有時失敗,但從不缺乏向前的勇氣。
有所愛,無所畏——縱有滿身傷痕,下一次出發,我們仍然意氣風發。
追逐熱愛與自我的路上,總有Jeep相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