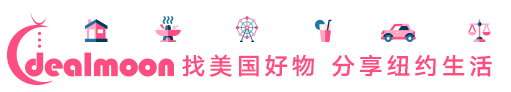物價持續偏弱已經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制約。物價低位執行的背後有哪些原因?
文|沈建光 姜傳鉞
從月度資料看,6月,CPI同比增長0.1%,結束了連續4個月的負增長,但連續28個月低於1%,逼近1998-2000年(35個月);PPI同比下降3.6%,是2023年8月以來最大降幅,也是連續第33個月負增長,2012-2016年PPI曾連續54個月負增長。
在此背景下,7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六次會議,明確要求“依法依規治理企業低價無序競爭”。上述經濟資料以及政策表態均指向,物價走勢偏弱已經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制約。那麼,這一現象的背後有哪些原因?如何擺脫物價持續低位執行局面?

對策一:大力提振居民消費
物價水平根本上由供求關係決定。近年來,中國的產出缺口(實際產出與潛在產出的差額佔潛在產出的比例)持續為負,表明實際產出長期低於潛在產出(即總需求小於總供給),物價面臨下行壓力。
根據IMF中國2024年第四條磋商報告(2024年8月釋出)測算,2020-2023年,中國的產出缺口分別為-4.0%、-1.1%、-2.8%、-2.0%;2024-2025年,產出缺口預計為-1.2%、-0.5%,似乎呈現出收斂態勢。然而,考慮到近兩年國內物價走勢明顯不及預期(IMF預計2024年中國GDP平減指數為0.1%,實際只有-0.7%),2024-2025年實際的產出缺口可能顯著高於上述IMF的預測。
內需不足是產出缺口為負的主要原因,消費不振又是內需不足的突出癥結。2020-2024年,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五年複合增速為5.5%,2025年上半年為5.2%,均大幅低於2019年的8.6%;2020-2024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五年複合增速為3.7%,2025年上半年升至5.0%,但仍顯著低於2019年的8.0%。消費需求疲軟的背後是就業收入承壓、居民財富縮水、高水平供給不足、社會保障不完善等一系列制約因素。
因此,提振居民消費,是緩解供需失衡、推動物價企穩的關鍵。在筆者看來,以下兩方面政策措施尤為重要:
一方面,更大力度支援服務消費。據估算,2023年中美商品消費佔GDP的比重差別不大,但服務消費佔比相差巨大,中國服務消費佔比僅為17.9%,遠低於美國的45.8%。相比商品消費,服務消費透支效應更小,且能夠吸納更多就業。可以透過特別國債籌集資金,在全國層面發行服務消費券或消費補貼(涵蓋餐飲、文旅、體育、健康、家政等領域),釋放服務消費潛力。
另一方面,改善農村居民社保水平。中國在社會保障領域的投入相對不足。2021年,我國社會性支出佔GDP比重約為11%,比OECD國家低約10個百分點,也比OECD國家人均GDP相近時期低約4個百分點。同時,我國城鄉居民在養老、醫療、住房等方面的內部差距較大。建議推進社保體系改革,提高國有資本劃撥社保基金比例,藉此改善農村居民社會保障水平,緩解消費的後顧之憂。

對策二:促進工資合理增長
工資走勢也是觀察物價的重要視角。理論上,工資上漲會推高生產成本,進而導致產品價格上漲,形成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反之亦然。
當前結構性失業矛盾依然突出。6月,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為5.0%,但不包含在校生的16-24歲、25-29歲勞動力失業率仍達到14.5%、6.7%。迫於監管要求或經營壓力,金融、地產、汽車等行業裁員和降薪現象也屢見不鮮。5月消費者信心指數為88.0,連續26個月低於90。其中,就業分項指數只有71.4,逼近歷史最低水平。智聯招聘大資料也顯示,一季度中國就業市場景氣(CIER)指數同比環比均下降,預計二季度將進一步走低。
在此背景下,工資增速明顯放緩。2021年,城鎮非私營和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增速還達到9.7%和8.9%,但此後三年快速走低。最新資料顯示,2024年,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同比降至2.8%,創1982年以來新低;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名義同比也跌至1.7%,是2009年有統計以來的新低。
農民工收入呈現相同特徵。2024年,農民工月平均收入為4961元,同比增速為3.8%,處於歷史較低水平。其中,佔比約60%的外出農民工月均收入同比僅為3.5%,是2015年以來的第二低水平。
面對上述趨勢,筆者建議,一方面,加大穩就業政策力度。在近期公佈的強化專項貸款、失業保險穩崗返還、社保補貼、擴崗補助等政策基礎上,透過稅收減免、補貼獎勵等正向激勵措施,鼓勵頭部企業、平臺企業等吸納擴大就業。同時,透過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深化集體協商制度等方式,完善勞動者工資決定、合理增長、支付保障機制。
另一方面,加快清理拖欠企業賬款。除了積極擴內需、促消費外,也要充分利用財政空間,加快推進清欠工作。比如,將更大比例新增地方專項債額度用於償還拖欠企業賬款,或者將符合要求的欠款納入隱性債務置換範圍,有效緩解企業經營壓力,暢通企業和居民之間的“資金迴圈”。

對策三:儘快穩定房地產市場
2021年下半年開始,中國房地產市場持續深度調整,對經濟發展造成了巨大沖擊。截至2024年,新房銷售面積、房企到位資金、新開工面積、房地產投資分別較歷史高點下滑45.7%、46.5%、67.5%、32.1%。
在經歷了兩個季度左右的修復之後,今年二季度開始,房地產銷售再度走弱。高頻資料顯示,截至7月22日,30大中城市新房成交面積同比下降21.4%。房地產下行從多個渠道拖累物價走勢:
首先,房價持續下跌透過房租直接影響CPI增長。截至2025年6月,全國70個大中城市新建和二手住宅價格指數同比連續39和41個月下降。伴隨房價下跌,2022年二季度開始,絕大多數月份房租CPI同比均為零增長或負增長。
其次,地產投資萎縮引發建築原材料價格下跌,制約PPI增長。6月,與建築行業密切相關的黑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業(鋼鐵)、非金屬礦物製品業(水泥、玻璃等)PPI同比為-11.3%、-4.3%,分別是連續38、34個月負增長。
再次,地產銷售下滑拖累地產後週期消費,相關消費品價格承壓。2021年下半年一直到去年四季度以舊換新政策顯效前,家電、傢俱、建材零售表現乏力。受此影響,家用器具CPI同比經歷了連續28個月的負增長,直到6月才轉正。
從更宏觀的維度看,房地產對中國經濟具有系統性影響,其大幅調整對就業市場、居民收入、存量財富、消費信心等均帶來負面衝擊,這也對物價水平產生了普遍的下行壓力。
6月13日國常會提出“更大力度推動房地產市場止跌回穩”,傳遞穩樓市積極訊號。筆者建議,首先,全面取消一線城市限購措施,進一步降低購房成本、下調存量房貸利率,釋放潛在購房需求;其次,由中央而非地方主導商品房收儲(針對一二線城市為主的人口淨流入城市),儘快推動一二線城市房價企穩,提振市場預期;再次,加快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縮小未落戶常住人口與城鎮居民在教育、醫療、養老、住房等公共服務的差距,釋放相關群體購房需求。

對策四:“反內卷”推動深層次改革
“內卷式”競爭是指經濟主體為了維持市場地位或爭奪有限市場,投入大量精力和資源,卻沒有帶來整體收益增長的惡性競爭現象。其典型特徵便是無序價格戰,結果往往導致行業盈利水平下滑、產業鏈上下游受損、產品質量下降、創新投入不足等一系列問題,嚴重危害行業發展。
“內卷式”競爭及其引發的無序價格戰已經從傳統行業蔓延至部分新興產業。以汽車(新能源車)行業為例,截至6月,交通工具CPI同比連續36個月負增長,汽車製造業PPI同比連續34個月負增長;1-5月,汽車製造業利潤同比降幅擴大至11.9%,是2023年4月以來新低。同時,產品和服務質量下降、企業研發投入不足等問題也逐漸暴露。
政策層對於“內卷式”競爭高度關注。202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便提出,綜合整治“內卷式”競爭。今年初,《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指引(試行)》正式釋出;4月,《公平競爭審查條例實施辦法》正式實施;6月,《保障中小企業款項支付條例》正式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完成修訂。
7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六次會議上提出“依法依規治理企業低價無序競爭”,釋放強烈訊號。7月18日,工信部宣佈將實施新一輪十大重點行業穩增長工作方案,涵蓋鋼鐵、有色金屬、石化、建材、機械、汽車、電力裝備等行業。
不同於2015-2018年主要針對上游行業、以行政性去產能為主的供給側改革,本輪“反內卷”面向更多下游新興行業(比如光伏、新能源汽車等),政策重心也將從行政性去產能轉向規範地方政府和企業行為。
筆者以為,清理過剩產能固然重要,但引發企業低價無序競爭的根本原因在於財稅體制和地方考核體系。如果本輪“反內卷”能夠“健全有利於市場統一的財稅體制、統計核算制度和信用體系”、“完善高質量發展考核體系和幹部政績考核評價體系”,推動政策層逐步轉變對供給側的路徑依賴,將有助於從根本上治理企業低價無序競爭,當然也會對中國擺脫物價持續低位執行大有裨益。

責編 | 張生婷
題圖 | 視覺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