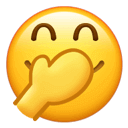《哭泣的草原》
很多年輕人會如此自嘲:我們是吃盡時代黑利的一代。
必須承認,這不是一個付出和結果成正比的時代。精神和經濟上的緊縮帶來全方位的內卷,越來越多人被迫擠進自己不喜歡的賽道,成為麻木不仁的一員,只是因為不做就會被甩下。
無論好與不好,這就是我們生活的時代,放在歷史的長河裡,或許只是一瞬間。這不是最好的年代,同樣不是最壞的年代。
不同年代有不同的危機和苦難,上一代人,如何面對自己的時代命運?或許有些閱歷和態度,具有穿透時間的力量,能給予不同代際的人安定感。今天的文章與大家分享歷史學家許倬雲先生的故事。為什麼他會說“往裡走,安頓自己”?如何面對人生的苦難?

講述 | 唐小兵
來源 | 看理想節目《回憶錄裡的20世紀中國》
01.
往裡走,安頓自己
2023年,在鳳凰衛視的一個頒獎典禮上,許倬雲先生錄了一個影片講話。其中有一段話談到,在所謂“下沉”時代裡,我們如何安身立命。
許倬雲先生講,我們要往裡走,安頓自己的人生。這讓我想起之前余英時先生的話,他說很多人讀書,讀的書跟自己內心沒有任何關聯,於是書讀再多也沒有辦法安頓自己,沒有意義。
無論是當讀書人還是知識分子,如果書和知識不能轉化成智慧,那麼你只是個兩腳書蟲,因為書本身並不能解決生命意義來源的問題,也不能推己及人。所以許倬雲先生所說的“往裡走,安頓自己”,十分有深意。
他在談話錄裡還有一段特別有意思的話。他在臺大從事行政工作的時候:“從三十歲到四十歲之間,是完全建立自主性的一個人生階段。”而他之前在美國留學就認為,自己和許多留學生的“立”不一樣,也就是立己、立人、立德、立功、立誓、立言不一樣。
“他們是在學問裡立,我在做人裡立。我讀書以外,做人,處事,關心社會,關心世界,找自己的路。”
“而我的目標是希望重建新的價值是以人為本,因為人是真實的。你可以否認別的,不能否認自己。你尊重你自己,你尊重別人投射給你的他,你也尊重別人投射給你看見的自己,一層層投射,可投射到無窮。”

《永恆和一日》
研究晚清史的學者楊國強,是一位傑出的歷史學家。他曾說,人是尊重出來的,不是批評出來的。如果以這樣一個標準,作為一個善良、政治上公平的社會的定義的話,誰也不希望不公平出現在自己的身上,於是推己及人,由此我們可以重建價值觀念。
許倬雲先生是一位非常儒家化的自由主義者。他認同自由主義的理念,當年在臺大讀書,到美國芝加哥大學留學,後來又回到臺灣,接著又在美國匹茲堡大學任教,王小波等人都是他早年的弟子。
《許倬雲八十回顧:家事、國事、天下事》是幾位臺灣知名學者訪問許倬雲而形成的書,2011年在香港出版。另一本書,《許倬雲訪談錄》,則是記者李懷宇做的採訪。
很多朋友可能知道,許倬雲先生是江蘇無錫人。無錫最重要的一個書院就是東林書院。
東林書院是明末顧憲成、高攀龍等人議論朝政的一個地方。明代書院制度繁盛,書院成為中國古代士人比較集中的地方,而東林書院代表的,就是中國讀書人那種“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蒼生意識和天下意識。
所以用“家事、國事、天下事”作為口述的標題,十分契合許倬雲先生一生的準則。
02.
苦難對人生的意義
許倬雲出生於1930年。他的母親當時是高齡產婦,生下一對雙胞胎,許先生還有一個弟弟,叫做許翼雲。他在採訪時提到:
“我因為肌肉無法生長,骨頭彎了下來。所以並不是骨頭壞,而是肌肉壞,肌肉沒有彈性,人也矮了,整個縮小,出現殘疾。”
“我出生時頭蓋骨還沒合縫,不但凹陷下去,還可以看到它一蹦一蹦地跳,體重只有三磅,約1362克,只有手掌心大。大人可以直接把我抓在手裡洗澡。本來我應該活不了,但最後還是活下來,算是不幸中的幸事。”
“我一直到6歲都不能動,7歲才能坐在椅子上面,8歲時我發明了一個辦法,手拖著圓凳子,一步一步往前移動,後來才慢慢能站起來,一步步撲移動。在廈門的時候,無所謂上不上學,反正一直有人抱著我,抱到哪兒擺到哪兒,有空才把我抱到另外一個地方。所以我從小就必須學會忍耐,在哪個角落都能夠隨遇而安,有時在椅子裡面坐上一個小時,也得乖乖忍受,直到有人把我抱到別的地方。”
生命有偶然也有萬幸,許倬雲先生活了下來,而且這一輩子還有如此大的學術成就,放在今天都難以想象。
一個人如何接受生命中的缺憾,如何突破身體對行動的限制,並且開拓出一個思想自由和學術自由的世界?許倬雲的一生創立了某種典範。

《無問西東》
許倬雲先生有太多理由可以怨天尤人,但他沒有。他在訪談裡感謝他的弟弟,認為弟弟就是他的手和腳。
許倬雲先生的一生充滿苦難,無論是早期逃難,後來到臺灣,還有到芝加哥大學讀博士時做矯正手術。關於苦難對人生的意義,他說:
“我自己經歷了考驗,幾個月躺在病床上,不能動,兩隻腳輪流,左腳開刀掛左腳,右腳開刀掛右腳,掛著一隻腳睡覺,動不了,就是想自殺都不能。
我是很痛苦,但是看見別人經歷許多比我更痛苦的事情:看見十二三歲的孩子患血癌,進來活活潑潑的,兩個星期就死掉了;看見一輩子長不大的孩子,十七八歲只有小女孩子還那麼大,看他們感情的激越和無奈;看見黑人孩子得了一種特殊的血液病,進來時瘦弱枯乾,卻不捨棄他們求生的希望,我看見種種神態,看見生死病痛,這對我幫助很大。”
人生當然不是要比誰更苦,但是當你看到有人承受著更多痛苦,卻仍然活著,你就會產生一種安頓感,對自己的生命會有負責任的態度。
許倬雲先生在香港出版的口述裡講了很多做手術的細節,兩年半里耗費十幾個月出入手術室、病房,一共動了五次手術。
“第一次動刀的時候蠻傷心的,我弟弟也來了,但同意書是我自己籤的,連死活都不知道就進手術室去了,等到我醒過來,弟弟已經在旁邊。那五年之中我沒有參加過什麼節日,都在醫院裡的,護士都變成我的好朋友。
我們住在病房靠內都有玻璃窗,護士臺在中央,每個房間都看得見,沒有隱私權,老護士長對我很好,我一搬回宿舍,要是有什麼傷風、咳嗽,她就說:‘你回來!’安排病房給我睡。我跟她說我腳趾甲長了,她也要我回去,幫我剪指甲。醫院可以說是我在外面的另一個家,home away from home,對我實在不錯。”
我們今天看到的許倬雲先生好像很通透豁達、很有生命智慧,學術成就斐然,是“中研院”院士、終身教授,但他經受過人間煉獄。
“結果總算是熬過去了,很大原因是讀書讀得很快樂。我的讀法不同於一般人,我認真地重新思考許多的問題,在課堂上也罷,課堂外也罷,老師就在病床旁邊教,不止顧立雅,威爾遜、Nef有時也會來教我,這些樂趣,讓我平衡了不幸的感覺。”
有書讀就很快樂,和朋友交流也很快樂,這些事讓許倬雲先生平衡掉身體上的殘疾,以及反覆手術帶來的巨大痛苦感。
許倬雲先生非常特殊的地方在於,他一生所經歷的病痛,是常人難以想象的痛苦,但是他不僅活了下來,還活得很豐富。

《十三邀》第八季
我們常常說“人是會思想的蘆葦”,這是帕斯卡爾的一句話。蘆葦雖然脆弱渺小,非常卑微,但是因為你有思考的閱歷,有思考的激情,你仍然可以按照內心的意願往前走,活出生命內在的價值和尊嚴。
許倬雲先生推己及人,立人立己,他先把自己立起來,然後向外普照,成為一個有“瀰漫性”的君子人格、學院人格。他透過《十三邀》,透過寫作,以及面向公眾的演講,緩慢但持續地影響著世人。
03.
悲天憫人的情懷與“四不”人生觀
正因如此,我們可以看到,許倬雲先生悲天憫人的情懷是怎樣形成的。
他講自己在湖北沙市的時候真正有了記憶,某一天突然從小娃娃變成有悲苦思想的人,一夜成人。人的成長有時不是一個緩慢的過程,而是瞬間的事情。
我想起1992年我的祖母去世,因為從小祖母照顧我比較多,回去我看到祖母彌留之際的樣子,也覺得自己一夜之間變成大人,童年一下就終結了,突然對生死、對人的理解就變了。我覺得許倬雲先生同樣如此。
每個人都有身體或者心理上的某種缺憾或不完美,而許倬雲先生的生命狀態和人生態度,可以總結為“四不”——不怨天、不尤人、不自責、不訴苦。
這當然很難做到,但因為許先生經歷過非常漫長、痛苦、堅韌的歷程,整個生命所展現出的氣象和格局,讓人感慨。許倬雲先生有菩薩心,他生命深處的悲憫情懷是一種對人的命運往何處去的關切。

《尤里西斯的凝視》
他在口述中談到少年時代逃難過程的所見所聞,比如有一次在四川坐滑桿:
“有一次很驚險,走完棧道下坡時,天快黑了,有個滑桿夫忽然出了問題,我坐的是最後一個滑桿,我一開始就覺得越走越慢,不久聽到‘碰’的一聲,前頭滑桿夫倒地不起,我的滑竿跟著滑倒在地。後頭的滑竿夫立刻去追前面的人找救兵,因為他們已經走很遠了。
這次的經驗至今仍然讓我感到恐懼,那個時候我一個人坐在路中間,荒山野地,天又黑,旁邊死了個滑竿夫,和一個翻倒的滑竿,另外一個滑竿夫去追人,我也不知道他回不回來。過了很久很久之後,才看到遠處出現火光,有人打了火把過來,原來是滑竿夫帶了人回來,把我的滑竿抬回去。這種經歷我一輩子也忘不掉,所以我常說我能體會中國內地窮人過的日子,就是因為有這種經歷。”
這些經歷讓許倬雲先生有一種非常強烈的悲天憫人的情懷。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生命經驗,對他人的苦難感同身受的能力,不是在書齋裡就輕易能獲得的。
04.
共情與同情
作為歷史學家,許倬雲先生在訪談裡講:
“我覺得不能盲目地愛國,我發願關懷全世界的人類跟個別人的尊嚴。”
一方面要有人類大同的思想,另一方面要關心個別人的尊嚴,對具體個人處境的同情、理解、實踐是非常重要的。極端、狹隘的民族主義,最後往往是用一種狂妄的自大來掩蓋內在的自卑。

《十三邀》第八季
我在文章《阿倫特論同情與憐憫》裡寫,20世紀的世界好像對普通人有一種無邊無際的、悲憫的情感,但是對於具體的個人缺乏同情、理解和共情。我們往往是抽象地憐憫,具體地冷漠。
話劇《大先生》的第一幕,魯迅的原配妻子朱安質問他:“大先生,你不是說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跟你相關嗎?我在你家幾十年了,你從來沒對我有一個笑臉。”當時演魯迅的演員,穿著牛仔褲、白襯衫,就苦笑了一下。
朱學勤關於法國大革命的著作《道德理想國的覆滅》也談到,雅各賓黨人一方面對湧上巴黎街頭的底層的苦難充滿巨大的同情。另外一方面,他們對人頭落地又持完全不同的態度。那種最悲憫的情懷跟最具體的冷漠,很奇特地聚集在一起。
整個20世紀的世界有那麼多政治的、人類的、社會的苦難,就是因為盲目極端的民族主義。直到今天,俄烏戰爭、巴以衝突等,都是以國家和自由的名義對個別人的傷害。

《狐步舞》
不是說民族主義完全沒有存在的必要,近代中國的歷史就是民族主義展開的歷史,但是你不能把它推到極端,不能把它當作追求私利、宣洩的東西,當作冠冕堂皇的話。
許倬雲先生既是歷史的當事人,也有一種旁觀者的心態。他對歷史、政治、人性、生活、家庭、單位有一種隔離的智慧,超越了那種自輕、自賤、自憐、自傷的心態。如果把許倬雲先生作為一個案例,可以看到同情與共情的區別。
共情有時候會導致個體沒有真正解決要解決的問題,同時陷入無邊無際的情緒對自我的包裹、傷害和壓抑。情緒往往來無蹤去無影,只有當情感成為真切、踏實、穩固的生命體驗,才能夠成為持久的內在動力。
而同情,更多強調的是一種感同身受的理解。你願意在一個細小的方面,採取具體的行動去改變你所同情物件的處境,這是我的感受。

*本文整理自看理想節目《回憶錄裡的20世紀中國》第4期,有編輯刪減,完整內容請至“看理想”收聽。


音訊編輯:小馬
策劃:看理想新媒體部
封面圖:《哭泣的草原》
商業合作:[email protected]
投稿或其他事宜:[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