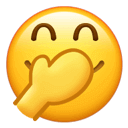自稱「心裡住著一個直男」的女編劇會如何講述一個傳奇女人的成長?
這是編劇李瀟兩年前接手《玫瑰的故事》改編時要想的問題。
《玫瑰的故事》是作家亦舒長篇小說序列中的代表作,它講述的是生長於優渥家庭中的傳奇女人黃玫瑰一生飄蕩的故事。接到這個專案後,李瀟花幾個月時間讀完了亦舒大部分小說作品,對亦舒女郎有了最直接的印象,「獨立如風,嚮往自由」。
也正因為如此,黃亦玫的出現顯得更新鮮、更現代、更具有千禧年代的審美,觀眾們會覺得「誰能不喜歡張揚而又實在美麗的玫瑰」。李瀟不避諱地稱黃亦玫是一個充滿了理想主義色彩的女主角。在集美貌、才華於一身的同時,黃亦玫還有完滿的家庭和充盈溫暖的女性友情,她不再像黃玫瑰那樣是被不同男性講述的美麗符號,而是有自我的個體。
很久沒有一部都市劇像《玫瑰的故事》吸引眾多觀眾的注意,它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爽劇,卻每天都掛在熱搜上,豆瓣開分7.1,有近十萬人給出了自己的評價。
在《玫瑰的故事》熱播之後的幾天,我們在北京國貿附近見到了這部劇的編劇李瀟。見面那天,李瀟穿一身寬鬆的白色T恤和短褲。對談開始前,她隨性地把長髮紮起一個丸子,盤在頭頂。那時,豆瓣還沒有出分,每天還是會有很多觀眾跑到她的微博底下評論,熱度不減。
對談的時候,李瀟告訴我們,自己在寫作的時候有一個小小的「怪癖」,必須要坐在自己最鍾愛的一張宜家椅子上,椅子已經坐了很多年,但她覺得安定、平和。
入行二十年,李瀟曾經創作了《大丈夫》《好先生》《戀愛先生》等多部熱播都市劇,這些劇目塑造了豐富的精英男性、市井男性,她也毫不遮掩地將男性的「小油膩」拋給觀眾。
她成長於山東濟南一個普通家庭。小時候,她一直被爸爸當作男孩養育,爸爸鮮少誇獎她又對她有著高要求,會反覆告訴她,要「自尊、自愛、自強」。李瀟覺得,正因如此,她在創作中鮮少帶著性別的眼光出發,表達反而是更中立的。她從沒覺得,自己是女性,就應該只寫女人。
40歲之後,李瀟看到了玫瑰的瀟灑、成長,也由此看到了自己的變化。到了生命程序的某一個階段,女性要面對的坎兒自然就來了。她開始關注女性的生存困境,開始思考女性與社會的關聯。
李瀟開始珍視女性的這種本能。
以下是李瀟的講述——
文|令頤
編輯|楚明
圖|(除特殊標註外)《玫瑰的故事》
我在改編《玫瑰的故事》之前,沒有讀過亦舒的任何一本小說。準確地說,沒有完整讀下來過。兩年前,剛拿到這個專案的任務時,我就覺得「頭皮發麻,覺得發怵」。
接了之後,我基本上把她所有的長篇,還有大量的中篇都讀完了。
我的另外一位搭檔叫王思,她的父親是北大教授。她從小見過非常多天之驕子和天之驕女,都是那種很美貌、很帥氣,家庭出身也很優越,同時自己很聰明,卻還都特努力的人。這些人會讓她一直仰望。
所以,我想把這些特質都放在黃亦玫身上。這是我們作為內地人,尤其在千禧年前後理解的一個女孩最完美的出身。其實這個設定的形象,是有點理想主義的,也是非常非常罕見的。
但亦舒寫的黃玫瑰就是一個傳奇女人,她是一個你在生活中基本上見不到,要仰望天空,在星河之中才能看到的一個女子。改編亦舒的小說嘛,最重要的還是領會精神。
亦舒原著的故事是發生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香港,劇裡的故事卻是發生在千禧年後的北京。改編的過程比較困難的地方就是如何讓這樣的設定落地。我們能做到的就是大量做調研,看那個時代的圖片,首先道具是一方面,他們用的手機型號,中間換了幾次手機,他們用什麼東西發影片,怎麼在國外插IC卡聯網,這些東西都是非常非常細節的。

劇裡使用的諾基亞手機
除了這些,在精神層面也要有所契合。那個年代看上去比現在思想更開放。你可以想象一下,2007年播出的《奮鬥》,女孩們穿露肩的吊帶,露著漂亮的鎖骨,穿短短的小熱褲。在感情選擇上,她們可以不顧一切地追求男性。沒關係,我愛就愛了,會愛得非常熱烈。
我跟王思是同齡人,那個時候我們也20多歲,可以說是黃亦玫的同齡人。正好就是我們大張旗鼓談戀愛,奔向新生活的時候。所以我們去還原那個時代的情感和狀態,其實並不是很難的事情。
把故事落地北京,是因為我自己對北京有非常深的感情。我是千禧年到北京來讀書的,是00屆的學生。
我當時藝考的時候考了很多個院校,有上海的,也有浙江,也有北京的其他院校,但我最心儀的就是中央戲劇學院。理由特簡單,我去中戲藝考的時候,看到一對陌生的師哥師姐一邊聊著天,一邊穿著拖鞋去開啟水,我覺得這種鬆弛的感覺,哎呦,太好了,太嚮往了。我就希望成為他們的一員。
我是從小地方來的,一路考出來我其實是很緊繃的,那是一種從來沒有見過的狀態。中戲當年在衚衕裡,那幾年感受最多的就是衚衕文化,還有鬆弛感。而他們身上散發出來的氣質,是我對北京最初的理解,北京恰好就有一種包容感,它很寬厚。
而且,那個時候人們的精神面貌是很向上的,我們談論理想、夢想,你的理想是可以實現的,是有那種往前走、往上走的感覺,我們想展現這樣的時代氛圍。
前幾天,我看到一些觀眾看到黃亦玫上班之後,覺得她沒有班味兒,她對自己的工作應對自如,第一個交到她手裡的展覽,她就能做得出色,得到了領導的讚許,和領導之間更像朋友。觀眾會評論說這個編劇肯定沒上過班,我確實是沒有上過班。但我的搭檔王思40歲才轉的行,之前她一直在上班、工作,而且跳過好幾次槽,先是在兩家小公司工作,最後也是在千禧年後跳到了一個外企。
這種情況也是王思自己的經驗寫照。那些小企業人數很少,所以企業文化是隨著老闆自己的喜好和風格、性格而定的。王思跟她的第一個老闆是不打不相識,因為她有一次頂撞了老闆,反而得到了老闆的賞識。
而且王思每一次跳槽都是裸辭。這可能是當下的年輕人不太能理解的,你怎麼會有這種底氣就敢裸辭。但更深層次的原因是,那時機會比較多,人們往往可以找到一份餬口甚至是很好的工作,不管你是什麼樣的人,什麼地方來的,你懷揣著什麼樣的想法和慾望,北京都能容得下你,人的可能性是無限的。

黃亦玫和蘇更生在辦公室
2
黃玫瑰不光是美,美的人多了,但不是說每個美人都可以成為傳奇,都值得被書寫。
觀眾都說劉亦菲是天選黃亦玫。我第一次見劉亦菲的時候,能感受到她美得很正面,她沒有那些特別複雜的誘惑力,沒有邪魅的東西。亦舒在原小說裡特意提到玫瑰的美是那種不光可以吸引男性,對女性也沒有攻擊力,女人看見她,也會突然軟下來,這個與女孩內在的氣質有關。
其次是,劉亦菲的工作態度很好,她自己的觀點是,要慢慢來,用自己的節奏選劇,但是每拍一部戲就要成一部戲,要對得起所有工作人員,也對得起自己,對得起這個角色。
劉亦菲是有一點慢熱的女孩,是一個很持重的人,和黃亦玫的性格區別很大。
剛一出場的黃亦玫是嬌憨天真的。劉亦菲拍的第一場戲就是她入職成功,在家裡接到了電話,她馬上跑到父母面前張牙舞爪跳著說:我被錄取了!那種帶著瘋瘋癲癲的感覺,也讓網友給她起了一個綽號叫「玫超瘋」。這種張揚的狀態,從來沒有在劉亦菲身上見過,那是她表演出來的。
看完了第一集之後,我給製片人鄭中莉發了一條微信,說這個角色必須得劉亦菲來,她跟這個角色水乳交融的好,你會覺得她生活裡就是這樣的。
我們每個人所幻想的黃玫瑰的風采、風韻都不一樣。作為編劇,我不想只呈現黃玫瑰的美,還希望能多一點內在。她敢愛敢恨,自由灑脫,同時,她有自己的表達和成長。
我覺得亦舒寫的核心並不是黃玫瑰這個人,她寫的是她旁邊那些男人。她是透過黃玫瑰這個人物去反襯她周圍所有男人那些不堪的一面,還有那些小陰暗、小心思。但她可能更多是隨波逐流,像是一個美麗的符號。
而黃亦玫和黃玫瑰最大的不同是,她要把自己作為主體,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考慮問題,她絕對不會忽略自己的真實感受。她可能會受一時的委屈,但她不會永遠沉浸下去,她一定會掙脫囚籠。
黃亦玫的成長當然不只是侷限在情感上。一開始她對自己就有很清晰的認知,她會想,我擅長讀書,所以考研對我來說不是大挑戰,但工作可能是大挑戰,因為我接觸的人不多。大學畢業之後她去就業,在就業的過程中,她也在運用自己的主觀能動性,比如說她拿到自閉症兒童的畫展,儘管是給同事打下手失去了主控權,但她還是調動了非常多思考,包括節省成本、考慮未來的可持續性,去把畫展做得有聲有色。在這個畫展期間,她對心理學研究產生了很濃厚的興趣,轉而去學習。我覺得這幾步就是她的成長,她享受工作、事業帶給她的成就感和滿足感,也始終都認識自己。
乃至於後來她去上海讀書之後,其實說過一句話:「以前我老覺得莊國棟自私,老覺得他把事業放在第一位,不把我放在第一位。但是其實當時的我是把愛情放在第一位,我也要求他為了我把愛情放在第一位,那麼我也是自私的。」她學會反思,學會去總結愛情、總結人生,也是成長的一個標誌。
我們做改編不能說只改編亦舒這一本小說,我就只讀她這一本小說。當我把亦舒的大部分作品都讀完後,我最大的感受是,我很喜歡「亦舒女郎」的這個稱號,這些女郎們都獨立如風,嚮往自由,愛男人,也懂得怎麼愛男人,但又不依賴男人。
這些都是很有魅力的特性,我想把這些都淋漓盡致地體現出來。
這就需要好幾個女性作為載體,所以有了我們虛構出來的Tina、白曉荷等等。很多網友會調侃說,黃亦玫、蘇更生、Tina你們仨把日子過好了就行(笑)。
首先這種關係是因為玫瑰所處的行業使然。她們本身在藝術行業,本就很鬆弛,大家可以直呼其名、有話直說。另外我也是希望把女性對於女性發自內心的欣賞、幫助、提攜寫出來,女性之間的相處可以是溫和、美好的。
一開始Tina跟蘇更生交代說讓你找的這個人其實是很為難你的,你要找一個優秀的,讓我能看得上的,但是她又不能優秀到足以威脅你的。有很多觀眾會擔心是不是會有女生之間互相撕扯、構陷的情節。
我不是單打獨鬥的編劇,我和很多搭檔一起寫過不同的專案,女孩佔大多數。與她們合作更多的感受是,有人在跟我並肩作戰,我不孤單。從情感上來說,會有一種不管你什麼時候回到這個房間,燈都是為你開著的感覺。
我們兩個人有商有量,我想出來的主意、情節,可以在搭檔那論證一下,如果它不夠完美、不夠嚴謹,我們一起來補足它。比如這次劇本里,王思有過工作的經驗,她就會把工作經驗告訴我,我再去豐富我們的創作。大家互相照顧,互相幫襯。
女生之間沒有敵對,沒有互相傾軋的關係,而是大家互相尊重、互相欣賞,是一種很愉快的氛圍。而且這種關係也是亦舒女郎會有的選擇,她們可以大大方方地競爭,可以毫不遮掩自己的野心,也都有這樣拿得起放得下的勁兒,可以非常灑脫。

黃亦玫和蘇更生
我們還給蘇更生賦予了一段晦暗的被繼父強姦的經歷。
一方面,我們想做一組跟黃亦玫的對照。黃亦玫出身書香門第,家境優越,父母的感情都很健康,是一種光明的寫照。但現實裡,這樣的人是少數,我們想再呈現另一種人生,一位女性出生於極其破碎、不健康的家庭。
這種對照想表達的是,像黃亦玫這麼好的家庭出身的姑娘,她照樣要吃很多愛情的苦,要吃很多生活的苦,要走一些彎路。但是出生於如此不堪環境下的蘇更生,她照樣能靠自己走出來,照樣能遇到良人,遇到朋友,能重建自己的生活。這其實比玫瑰更貼近亦舒女郎的標準——現代、獨立。
另外一方面是,我因為別的專案去北京的檢察院做過一些調研採訪,看過一些卷宗。翻閱的時候,讓我印象最為深刻的是,在中國,尤其是在二三線城市,以及大量農村中,對未成年人的侵犯,很多都是熟人作案。
這類案件通常涉及到家庭內部問題,受害者會因為家庭紐帶的束縛、經濟依賴、情感依賴或社會輿論的壓力難以揭露真相。而且,除非在刑偵劇裡,都市劇中這樣的現狀其實是很難呈現出來的。
所以我有一點點私心,想把這種經歷放在一個角色身上,其實就是放在蘇更生身上最合適。因為她這樣內心裡很柔軟,外表帶刺的女性性格成因一定是有原因的,而它的原因是什麼,我們用這段過去給她做了一些合理化。
同時,我也是想透過這個經歷以及蘇更生向母親喊出來的那一句「你為什麼不保護我,為什麼不報警」,提醒大家,保護好身邊的人,尤其是未成年人,尤其是你的女兒、你的妹妹。

萬茜飾演的蘇更生一角
黃亦玫的媽媽是物理系教授,她父親是歷史系教授,其實這種設定也是反常規的。我們想要打破固有的思維,認定男性有理性思維,才是學理的料,女性不適合。但劇裡,反而黃亦玫的母親是偏理性思維的。在黃亦玫準備去上海讀書的時候,兩個人吃著甜品,她媽媽是用非常理性的表述給她分析人類的情感。
她爸爸就會去畫室給她送紅燒肉,會跟她說你想怎麼樣就怎麼樣,天地很寬,你展翅去飛就行,一直是更加細膩感性一些。她爸爸去上海看她,會仔細地覺察到她的心思,覺得女兒現在不開心了。
這種細膩我沒有體驗過,但是一直期盼體驗的。
我曾經也在一些同學發小身上見到過類似的父親對女兒的牽掛,他們對女兒有很細心的體察,甚至當爹的比當媽的還細心,這是我很羨慕的一種東西。
我是家裡的獨生女,從小就被我爸當男孩養的,他會一直強調六個字,自尊、自愛、自強。我們之間缺少那種很親暱的記憶,幾乎沒有。我看到同學跟父親的關係都是那種很親暱、很自在,會在爸爸身上爬來爬去,會跟爸爸撒嬌,我是特別羨慕的。

編劇李瀟受訪者供圖
一直以來,我爸對我的成績永遠不滿足,他也很少表揚我。他對我的每次表揚我都記得非常清楚,一個手就能數得過來。
我很小的時候,剛搬好家,他的朋友來暖房,他喝了點酒,跟他的朋友說:「我女兒是一個很自律的人,她自己心裡有數,知道什麼時候該幹什麼事,學習也從來不用監督。」我在我的小房間裡偷偷聽到了這一句,當時覺得很難得、很感動,記到了現在。
再後來到學生時代這種誇獎就沒了,直到工作之後,偶爾能聽到他說,這個劇播得還挺不錯的,能看出來你是思想成熟了。
更多的時候還是掃興,不管我寫的電視劇熱度到什麼程度,他都會說,唉,我看到網上有說怎麼不好的。本來我挺開心的,讓他一句話就一盆冷水給我澆下來。哪怕我得了很多獎,哪怕我很努力地以每年一部劇的速度在出作品,他還是會有意無意地說,你看那個誰誰誰那個導演,那個誰誰誰那個編劇,又怎麼怎麼好了。比如說他前兩天跟我媽媽在國外旅遊,他沒有辦法看劇,但是會看網上的評論,他就說,現在的評論還是有一半好,一半不好,還有好多這樣那樣的爭議。把我給氣的,我就想你是我親爹,你能不能盼我點好?(笑)

編劇李瀟受訪者供圖
他是無意識的,他希望我做得更好、對自己更嚴格。所以,我是很想要去取得他的表揚的,越是這樣,我越是想努力做好得到他的表揚,我想證明給他看。這是不是很多東亞人共同的處境?
聽到這些的時候,我也不會反駁他。直到最近幾年我才覺得,我爸的這種掃興變得少了。我過了40歲以後,他可能會更多地說一些,注意身體,差不多得了,也不用那麼拼命了,也可以適當的休息休息。
黃亦玫是在很健康的家庭環境中長大的。
這種愛不一定要有物質的託底。黃亦玫的家庭環境物質條件其實一般,大學教授的工資也不會特別高,就是溫飽線以上,風吹不著雨淋不著,說不上大福大貴。但健康的家庭關係反而是更難得的。她父母之間少有爭執,還經常會開個小玩笑,兩個人都很會溝通,也很會跟孩子們溝通。他們也知道跟孩子之間是有分寸的,兒子這段時間有不順心的事了,其實他們很想去看看的,但又要往後退一步,要把選擇權交給他自己。
所以黃亦玫會愛,也願意接受愛。她敢於付出,也會非常欣然接受別人的付出。
我覺得敢於付出、敢於愛別人,是很難得的。現在年輕人經常說,自己要麼封心鎖愛,要麼面對愛情這種很珍貴的東西時,要把它放在秤上去稱,你要選擇一個性價比合適的物件,要計算你的付出收穫比。
但黃亦玫不是這樣的,她從來不會計算。她跟哥哥說過,你知道的,在我這裡沒有什麼值不值得。
在現實中,這種人也挺珍貴的。我相信黃亦玫這種人在我們生活裡一定是有的,只是她太罕見,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幸運地遇到她。但是她的出現,哪怕她只是作為一個影視劇裡的人物,能喚起我們一點點對於愛情的真摯付出,只要有一點點,我覺得就挺好的。

電視劇裡的黃振華離原著很遠。有觀眾會稱:「現在的窩囊廢賽道又擁擠了一點。」
一方面是考慮他的出身,他父母的教育是很健康的,他身上勢必不會帶有太多大男子主義的東西,會懂得尊重女性,也尊重知識。當時的人物小傳裡,我寫道,他喜歡班長型別的女孩,喜歡很強勢的、高於自己的女性。
現在的女性觀眾之所以會發明一個詞「窩囊廢賽道」,是因為大家對於這種沒有攻擊性的男人和男性角色越來越接納。生活中女性面臨的處境都很複雜,但還是不太經常能遇到特別放鬆、給予我們充分尊重的男性,所以我們很希望在影視作品中看到一些這樣的角色。
其實黃振華這個人身上也有他的小缺點、小問題。前兩天觀眾又有說黃振華竟然人設崩塌,竟然跟白小荷去釣魚,他跟蘇更生接吻的時候竟然還看了一眼魚竿。
我之前在採訪中也提到過自己現在其實不太願意去寫婚外情、第三者出現這樣的劇情。因為我們缺少能夠接受複雜性與真實性的土壤。像早些年《牽手》那部劇就是在探討第三者、婚外情。但現在的確會發現,大家要求純愛,要求人的絕對正確,不可以有瑕疵。
回到《玫瑰的故事》裡,除了黃亦玫這個角色有點偏理想化之外,我們其實想做一個比較現實主義的劇,而不是一種補償性的浪漫愛情故事。
真實的人就是會有缺點,會有瑕疵。我們在生活中誰談戀愛又沒有走過神兒的瞬間?誰又沒有權衡過自己的物件呢?當然我們都不希望自己被這樣對待,但在現實中它確實是不可避免的。
其實黃振華在輕微走神之後,他還是很快地迴歸到了正軌,他非常勇敢地向他的女朋友坦承了自己做錯了,勇於承擔後果,就是如果你要分手也OK,大不了我再重新追你。做錯事敢於承擔後果,這比從來都做不錯,完美無瑕的人更可愛。
現在有時不允許出現複雜的人類情感,不去面對真實的情感。這樣一來,創作的複雜性就少了許多,對人性的一種描摹和揭示會少很多,其實是挺可惜的。
我再舉個例子,之前我在《好先生》裡寫過一個女性角色,是江疏影飾演的。當時這個角色很多人很喜歡她,大家是覺得她敢愛敢恨,能承擔自己的選擇。但是這樣的一個角色,如果我現在把她寫出來,就會被很多人批判為戀愛腦。
現在已經有些人說黃亦玫是個戀愛腦。但是你分析她對莊國棟的感情就知道,她很清醒,包括她後面選擇跟方協文在一起、提出離婚。她跟另外兩位「男嘉賓」之間,也是她佔有主動權。她可以是主動索愛的那一個,也可以是主動放棄的一個。我的一切選擇都遵從於我的內心,我愛你的時候你就是天是地,我不愛你的時候你什麼都不是。
我也聽到有一些爭論是說黃亦玫和莊國棟一見面就接吻。
兩個人熱戀,見面的時候不接吻,做什麼呢?我們允許用身體來談戀愛,我們也允許用精神來談戀愛,我們也允許既有精神又有身體。我覺得黃亦玫和莊國棟是後者。
他們很年輕,黃亦玫又是遇到了初戀,兩個人對彼此的身體有好奇、有探索、有熱烈的慾望,這非常正常。黃亦玫與莊國棟相愛的時候,他們也不僅僅愛對方的身體,也有對方的人格。
我對於普通人的觀察是,在面對感情的時候,80後可能會更容易all in,上天入地、敢愛敢恨,90後可能會更加穩一點,00後可能又穩了一步。他們不會像我們一樣做很多瘋狂的事情,會更考慮現實成本。就是因為現實世界告訴他們,一旦走錯,付出的現實成本會非常高。
每一代都是有區別的,但共性是人都需要情感,需要實現自己的理想。所以我才一直希望大家能寬容一點,能多接納一些跟自己不同的人,多接納一些自己沒見過的人。很多東西不是你沒有見過,它就沒有,它就沒有發生。這個世界太大了。

黃亦玫和莊國棟
面對觀眾的時候,我感覺我內心還是挺強大的。昨天我跟王思說上一次看到30 多條罵我的,我悄悄看了一眼,預期可能會有100多條罵我的,沒想才70 多條(笑)。剛開始罵是覺得吻戲多,後來是說把黃振華寫「精神出軌」了,說「這麼好的人讓你寫成這樣,你真是心理陰暗」。
但你反過頭來想,要不是我把他寫得這麼好,你現在會這麼失望嗎?
現在觀眾的審美喜好差異越來越大,你沒有辦法顧及所有的觀眾,比如說我知道觀眾可能會喜歡看打小三兒的劇情,比如說之前編劇的《驕陽伴我》,一開始其實就是有第三者出現的,但最後我故意弱化掉了那個情節。我知道把這個大張旗鼓寫出來一定會有高收視率,但那是我不能接受的方式。所以,觀眾的喜好和我自己的表達之間,我就不做平衡了。我只遵從自己,遵從自己的心,自己想寫什麼,善於寫什麼就寫什麼。
我在中戲讀大二的時候就開始寫劇本,因為作為一個女生,我們能進組去跟著實習,做副導演的機會不是很多。但是市場上需要大量的像我們這樣的編劇,一開始是沒有名的,但是能賺一些錢。我還做過一個公司的職業編劇,一個月1500塊錢的薪水,我最多的時候能寫四五集,差不多一週一集。
這樣其實也積累了一些人脈和經驗。大學畢業之後沒多久,我接到第一個劇本,就是《搭錯車》,那個時候遇到了李雪健老師,團隊給了我一個很寬鬆的創作環境,大家可以商量著來。倒不是說我拿到了話語權,而是作為新人得到了很充分的尊重,可以很敞開、很包容。
作為年輕編劇,資歷很淺,只有一部代表作,沒有留給你太多選擇,有的作品完全不署名的,投資方說啥就是啥。直到《當婆婆遇上媽》播出之後,很快就感覺不一樣了。這個劇名字現在聽起來很drama,但當時特別火。
之後,我寫了一系列以男性為主角的劇本,《大丈夫》《好先生》之類的,我之所以寫好多男性視角的東西,是因為我壓根就沒有意識認為這個是男性視角,那個是女性視角。我也沒覺得說,因為我是個女的,我就要寫女的。
我以前在採訪的時候說自己內心深處一直住著一個直男(笑)。我的情感表達很直接,平時跟搭檔、伴侶,甚至跟我的老闆,都不太會拐彎。同時我也覺得男性身上有一些特質值得我們學習。比如他們的勇敢、不拘小節。或者說,這些品質我們天生也有,但是在後來的教育中,有人太強化我們是女孩了,所以給弄沒了。
在我的觀察裡,內耗的女孩比男孩要多,我自己就是一個超級內耗王。我之前看心理醫生的時候,很坦誠地說我有一些陰暗的小心理,比如說我會羨慕某某人,甚至有點嫉妒,為什麼他沒有付出多少努力就可以過這樣的人生?但男性經常會覺得世界上的一切都與自己相關,他們會覺得,哇,我好優秀啊。
這方面我們女性應該學習一下男性,減少內耗。

對女性的關注其實是隨著我自己年齡的增加是有所變化的,這是自然而然的轉變。
我今年43歲,但我沒有生育。我把好多青春的時光都放在了工作上,年復一年,你跟這個人分了手,跟那個人離了婚,經過很多分分合合之後就是走到這兒了。現在我已經過了最佳生育年齡了,生孩子對我來說是非常困難的。但這個困擾和無奈對男性來說就不會有,只要保持健康就好。
在我身體適合的時候,別人結婚生子的時候,我覺得這就結婚生孩子了,我沒做好準備,我還有更高的目標想要實現,我想寫出什麼樣的作品,我要去奔那個慾望。因為孩子真的會耗費很多時間和心力。但是等做好準備而且我有經濟條件去撫養孩子的時候,我已經40歲了,不那麼適合了。
這是我的切身體會之一,從這一件事上感受到的是,女人和男人完全不一樣。男性幾乎不用擔心時間會帶給他們什麼,包括衰老的體現維度也是不太一樣的,女性怕老、怕皺紋,因為社會就是有可能不接納她們生長的痕跡。女性在更年期或者更年期到來之前都會很敏感,但男性可能就從來不會有。
我接下來正在創作的劇本包括女性相關的社會議題。不再是家庭劇、情感劇,很體面的都市劇,而是想更關注於女性跟社會之間的關係,以及她的存在對於社會的價值。
這些都是我切身經歷後感知到的,所以才有了現在視角的轉變,到了生命程序的某一個階段時,女性的困境,女性的這個坎自然就來了。那這個時候,你要做些什麼嗎?你要如何看待自己呢?這些都會讓我思考很久。
另外一個方面,其實是《玫瑰的故事》播出後更堅定的,我現在看到有些觀眾的評價,他們喜歡說怎麼她老談戀愛,能不能不讓她談戀愛,她怎麼把一手好牌打爛了,她怎麼能這樣上來就能跟人發生關係呢?
說實話,黃亦玫現在還是一個影視劇裡的人,都有那麼多人對她有規訓,對她有規範,認為她應該怎樣,不應該怎樣,那我們現實生活中的女性又面臨多少這種規訓規範?有多少人會跟她說你應該這樣,不應該那樣,而我覺得這個東西不應該我們承受。
年輕的女孩如果不受到這些規範的影響,她們的世界可能會更寬闊。



「是個人物」系列帆布包
點選圖片掃一掃購買↓↓↓

親愛的讀者們,不星標《人物》公眾號,不僅會收不到我們的最新推送,還會看不到我們精心挑選的封面大圖!星標《人物》,不錯過每一個精彩故事。希望我們像以前一樣,日日相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