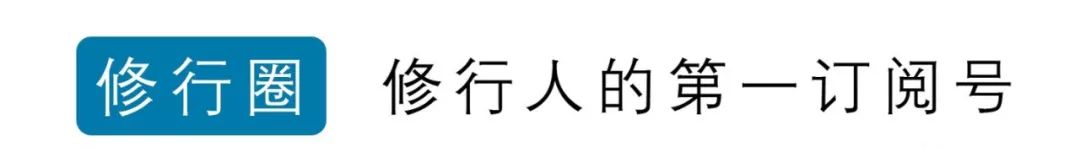文 | 通吃島島主
最近知乎平臺突然給我推送了很多批判、攻擊錢學森的回答,每天總能看到幾個。而且那幾位有名的自由派大V樂此不疲地為這些回答點贊,有的已經衝到大幾千贊。不久後,在國外的網軍殖人聚集地推特,也給我推送了一堆簡中推文,其中夾雜著很多攻擊錢學森的內容,和知乎上的回答出奇的像。
錢老已經仙逝多年,最近沒有和他相關的任何新聞。怎麼突然這麼多人開始黑他,而且言辭極其惡毒?



最近突然冒出的大量問題和高贊團建回答,比如上面這個,都2025年了還擱這敬酒
這咄咄怪事背後明顯有跡可循。之所以突然出現組團的有組織的黑錢學森現象,就是因為中國近幾年在高新科技上迅速突破,許多領域已經領先世界。這引起美國的恐慌,已經把遏制中國高新科技當作其重大國家戰略。也不得不說,美國智庫裡面還是有高人,已經看出了錢學森對於中國高新科技發展的極為重大的意義,儘管他早已不在人世。
錢學森不僅是“中國航天之父”、“火箭之王”、中國近代力學和系統工程理論與應用研究的奠基人,還是最重要的戰略科學家和整個中國科研系統的奠基人之一。更重要的是,他是堅持維護科技主權、發展自主技術路線(堅決反對一味追隨模仿西方技術路線,乃至造不如買買不如租)的最核心的代表人物。
錢老的學術貢獻和制度設計至今惠澤著中國的科研工作,而其晚年那些尚未得到應有重視的思想遺產,在未來的中國科技突破中必將發揮重要作用。
所以我說美國智庫裡面有明白人,知道要想遏制中國高新科技全面突破、最終領先全球的勢頭,在輿論場打倒錢學森是很高明的一步棋。
我這篇文章就來正面回擊,正本清源。
攻擊錢學森的那些回答大都是不斷復讀兩大黑點。第一,他大躍進時期論證“畝產萬斤”合理。第二,他80年代以黨性保證特異功能是真的。然後網軍們以此證明他是靠“逢君之惡”搞政治投機的人,進而全盤否定其人。
一些支援錢學森人予以反駁,也大都是從兩個角度。一個是批評黑子們抓住一兩個黑點無限上綱上線,無視他總體上的重大貢獻。這個角度類似“三七開”吧。另一個角度是把錢學森的這些行為動機解讀為類似“明哲保身”,而非政治投機,在動亂年代保有用之身以圖繼續做出貢獻。
這些反駁和辯解也都是錯的,因為他們是按照對一般科學家的認識來推測錢學森的動機的,而錢老不是一般科學家。我會首先梳理這兩大所謂“黑點”的真相,解讀錢學森獨特的科研哲學,最後說明他的重大貢獻。
錢學森是浮誇風元兇?——搞新聞學的乾的
要理解錢學森在“畝產萬斤”問題上的真實立場,我們必須首先釐清一個核心事實:他探討的是一個科學理論上的極限問題,而非一個農業實踐中的現實問題。將兩者混為一談,正是所有誤解的根源。而故意把二者混為一談的人,是當時《中國青年報》的編輯。
那些攻擊錢學森的人拿出的所謂“罪證”,就是1958年6月16日《中國青年報》的署名錢學森的文章《糧食畝產量會有多少?》。實際上,這個文章的發表是極其缺乏職業道德的行為。
它不是錢學森的投稿,或者對他的約稿。而是編輯從錢學森另一篇文章裡面擷取一段,再加上各種加工後的內容。關於此,葉永烈有過詳細考證,我就直接引用了:
在“大躍進”年代,作為“海歸”的代表人物、作為科學界的頭面人物錢學森應約就《1956-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發表談話、發表文章,原本不過是表態談話、應景文章而已。《中國青年報》編輯擷取他的文章的一小段,經過改頭換面式的編輯加工,演變成為1958年農業“高產衛星”提供科學依據,在廣大讀者中產生極大的負面影響,責任在《中國青年報》。
經過《中國青年報》編輯的“戴帽穿靴”,加上了井岡山民歌,加上來自河南“高產衛星”的“動人的訊息”,把錢學森原本應《1956-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之“景”所寫的文章,變成了應農業“高產衛星”之“景”而寫的文章,使讀者誤以為錢學森在為農業“高產衛星”充當吹鼓手,因而使錢學森蒙受不白之冤。應當說,由那篇“戴帽穿靴”的短文引出的種種嚴重後果,其實與錢學森無關。
錢學森在1958年6月《科學大眾》上發表文章《展望十年———農業發展綱要實現以後》。文章很長,對農業發展綱要各個方面都從科學角度加以評價、分析。當然,洋溢著當時普遍的樂觀情緒。其中論述糧產量的其實就一小段,根本不是文章的重點。而且當時浮誇風還沒那麼誇張,只是有試驗田說達到畝產2000多斤。錢學森就提到了這個例子,並且說,“只要我們有必需的水利、肥料動力和勞動力條件,產量是可以不斷提高的”。然後就被無良媒體擷取改編,去給他們後來的畝產萬斤浮誇風站臺。
錢學森的論證,本質上是一個基於光合作用能量轉換效率的理論推算。他計算了每年投射到一畝地上的太陽光能,再根據植物對太陽能的最高理論轉化效率,推匯出農作物產量的理論上限。經過嚴謹計算,他得出結論:太陽能轉化為有機物的效率如果能達到極高的水平,糧食產量確實可以達到非常驚人的數值。當時他在幾篇文章中的推測大概都是畝產4萬斤左右。
這絕非他一時的心血來潮,更不是故意在大躍進時期迎合。作為一個嚴謹的科學家,他一生都對這種理論上的可能性抱有信念。1993年,在給友人通訊中他對糧食最高畝產的估算達到了幾十噸,遠超畝產萬斤:
“據氣象記錄,在中國大地上每年每平方釐米上接受的日光能量為120-200大卡,即每年每畝地接受日光能量為8-13。3×108大卡。如百分之百地用空氣中的CO2和從根吸取的水合成碳水化合物,則每畝地每年有190-320噸。光合作用的能量效率可達50%,而糧粒只佔全部產物的1/3,故理想最高年畝產是32-53噸。說畝產萬斤,才5噸,遠遠小於理想數。所以充分發揮科學技術的作用是可以實現的。”
簡單提一下錢學森的科研哲學——理論上能實現的,現實中就一定能想辦法實現。如果長時間都不行,那應該是技術路線錯了。他和導師馮卡門,以及其他同事們在加州理工學院研究導彈的時候就是這麼做的。
當時,火箭技術在主流學界眼中幾乎等同於科幻,甚至被嘲笑為違揹物理常識。然而,他和導師馮·卡門以及那群被稱為“自砂小隊”的同事們,堅信基礎理論的正確性。他們所做的,就是將一個理論上成立、但工程上被認為不可能的設想,透過開創全新的推進劑、發動機設計等技術路線,硬生生變為了現實。
這種科研哲學是錢學森能取得重大科研創新的原因,根本不是迎合誰或者政治投機。只是被當時的某些媒體和官員利用為自己站臺。
可笑的是,2009年,新聞系畢業的財經作家吳曉波又在媒體《新週刊》發文《錢學森的偉大隻欠一個道歉》:“行將百歲的錢學森,度過了一個壯麗而偉大的人生,他所欠的,或許只剩下這一個道歉。”

到底誰TM該道歉?
“特異功能”和人體科學
說完了“畝產萬斤”,我們再來看第二個被反覆攻擊的“黑點”:錢學森支援特異功能。
在網軍殖人們的敘事裡,這被描繪成錢學森晚年糊塗、陷入封建迷信的鐵證,或者是他為了迎合某位領導人的喜好而再次“逢君之惡”。他們拿出錢學森“以黨性保證特異功能是真的”這句話,如獲至寶,試圖將其釘在“偽科學”和“政治投機”的恥辱柱上。
然而,這種非黑即白的拙劣抹黑,再次暴露了他們要麼是無知,要麼是刻意無視一個最基本的歷史事實:在那個年代,對“特異功能”的研究,根本不是中國的獨有現象,而是一場發生在全球兩大超級大國之間的、高度機密的“心靈軍備競賽”。
就在錢學森倡導人體科學研究的同時,美國和蘇聯正投入鉅額國家資金,動用頂級情報機構,進行著持續數十年的特異功能研究。
先看美國。 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出於對蘇聯可能掌握“心靈武器”的恐懼,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和國防情報局(DIA)啟動了一系列高度機密的特異功能研究專案,最終被統一命名為“星門計劃”(Project Stargate)。這個計劃從啟動到1995年被解密,持續了二十多年。
其核心研究內容,就是利用“遙視”(Remote Viewing)能力來獲取情報——即讓特異功能者在不離開房間的情況下,描述千里之外的蘇聯核潛艇基地、秘密武器設施,甚至是被劫持人質的位置。這絕非地攤文學,而是由斯坦福研究院等頂級科研機構承接、耗費超過2000萬美元的國家級嚴肅專案。美國情報界非常擔心在“心靈能力”上落後於蘇聯。
再看蘇聯。蘇聯的研究起步更早,規模也相當可觀,他們將這類研究統稱為心理電子學。從60年代起,在克格勃和軍方的支援下,蘇聯投入了大量資源,希望將遙視、心靈感應等能力武器化,用於情報竊取、遠端影響敵方人員身心狀態,甚至干擾電子裝置。正是來自蘇聯的威脅情報,直接催生了美國的星門計劃。
所以,當錢學森倡導對特異功能進行研究時,他看到的是世界科技強國正在秘密佈局一個全新的、充滿不確定性但可能具有顛覆性潛力的戰略領域。他所做的,是站在一個戰略科學家的角度,呼籲中國絕不能在這一未來的可能性上缺席或落後。
那麼,他為什麼會“以黨性保證”特異功能是真的?這就要回到他獨特的科學哲學——複雜性科學與人體科學。
就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西方科學界開始反思還原論思考“複雜性科學”,並建立了像聖塔菲研究所這樣的重鎮。錢學森幾乎在同一時間,甚至更早,就已經獨立地構建起了一套更為宏大和系統的理論框架。這正是中國複雜性科學研究至今仍在世界範圍內保持比較先進水平的根本原因之一。
錢學森將他領導“兩彈一星”等超級工程時運用的系統工程思想,昇華到了哲學高度。他認為,宇宙間的大量事物,從航天工程到社會組織,再到我們人體本身,都不能用研究鐘錶零件那樣的簡單思維去理解。它們都是“開放的複雜巨系統”。
巨系統:指系統由海量的、成千上萬億的子系統構成。比如人體,就是由億萬個細胞、組織、器官構成的巨系統。
複雜:子系統之間不是簡單的線性關係,而是存在著強烈的、非線性的相互作用。這使得系統的整體行為,會湧現出無法透過簡單分析區域性而預測的全新屬性。
開放:系統不是孤立的,它無時無刻不在與外部環境進行著物質、能量和資訊的交換。

詳細內容可參見本書
這恰恰是錢學森的超前之處。他認為,過去幾百年的現代科學,非常擅長研究“簡單系統”(比如一個槓桿、一個行星的運動),但一旦面對“開放的複雜巨系統”,傳統的還原論方法(即將系統拆解成部分來研究)就會失靈。
在這個宏大的理論框架下,錢學森將複雜性科學劃分為不同的領域進行研究,而“人體科學”正是其中之一(等會兒還會講到另一部分“思維科學”)。在他看來,人,就是宇宙間已知的最複雜、最高階的“開放的複雜巨系統”。所以他才會把“人體科學”和量子力學、相對論的重要性作對比。
現在,我們再回頭看所謂的“特異功能”和氣功,錢學森的邏輯就非常清晰了:
他認為,這些看似神奇的現象,很可能就是人體這個最複雜的巨系統,在與內外環境進行資訊和能量交換時,在某種特殊的“功能態”下,所“湧現”出的特殊表現。它們不是迷信,而是等待被納入新的科學體系進行研究的“前科學”現象。一旦能夠掌握其規律加以一定控制,對個體和國家都是大有裨益的。
他“以黨性保證”特異功能是真的,這句話出自1982年他給中宣部副部長的信。當時,特異功能引發了巨大爭議,主流媒體發文批判。這直接影響到中國科協,發文說不再研究特異功能。本來要在上海《自然科學》雜誌上面發表的幾篇研究特異功能可能性的科研論文,也因為行政壓力被撤稿。
錢學森在信中,明確提到“您是知道的,一到下面去執行,就會一棍子打死。”並舉出了歷史上對摩爾根遺傳學、控制論、人工智慧等科學的批判的例子。隨後說“我建議您通知上海市宣傳部門的同志,正確處理《自然雜誌》的問題,不要禁止它刊登科學論文。我也向您表白我的判斷,我並以黨性保證人體特異功能是真的,不是假的,有作假的、有騙人的,但那不是人體特異功能。”
他是擔心,對“人體科學”這個極具潛力的新生科學領域的探索,也會重蹈覆轍,被扼殺在搖籃裡。
因此,用“黨性”這種在當時語境下最鄭重、分量最重的詞彙作擔保,其真實目的,根本不是為什麼神功大師站臺。而是作為戰略科學家的他,為了排除行政干預,為一門他認為可能引發“新科學革命”的、充滿爭議的新生領域,爭取一個最起碼的、能夠自由探索的寬鬆空間。
之後高層的處理其實是不錯的。允許少數科學家繼續研究,但大眾媒體不能再報道未經證實的東西,因為中國大多數人受教育程度還很低,難以分辨真假,容易被騙子利用。
後來,隨著冷戰的結束,特異功能的研究在全球都停止了。中國更是如此,在錢學森的晚年,中國科研體制很大地鼓勵了有短期可預測性成果的專案。作為戰略科學家的他,很多構想都無法得到資金落實了。
但我們現在已經能夠看到,錢學森的很多戰略構想已經被證明是非常正確的。下面試舉幾例。
戰略科學家錢學森
錢學森不僅是科學家,更是中國最重要的戰略科學家。他思考的,從來不只是某個具體的科學問題,而是中國科技發展的整體佈局、根本路線和未來方向。
當他那些看似不切實際的探索因時代所限而被放棄時,他在同一時期提出的其他一系列重大戰略建議,卻在幾十年後的今天,以無可辯駁的事實,印證了他那超越時代的驚人遠見。這些建議,無一不是基於他的複雜性科學理論,以及“自主創新”、“非對稱競爭”和“換道超車”的核心思想。

1. 優先發展導彈
上世紀50年代,新中國百廢待興,國力孱弱。在國防建設上,是優先發展更容易在區域性衝突中見效的飛機,還是直接挑戰技術門檻極高的“兩彈一星”?這是一個重大的戰略抉擇。錢學森以其在美國的親身經歷和對世界軍事技術格局的深刻洞察,力排眾議,向中央明確建議:必須以有限的國力,優先發展導彈核武器。
他的邏輯,是典型的“非對稱”戰略思維:在飛機技術上,我們與美蘇差距巨大,全面追趕耗資巨大且短期難以奏效。而導彈核彈,是能從根本上改變國家安全格局的武器。擁有它,就擁有了最有效、最經濟的戰略威懾力,能為國家的和平發展爭取到最寶貴的戰略機遇期。這一決策奠定了中國的大國地位。
2. 倡導沙產業,變劣勢為優勢
對於中國廣袤的沙漠和戈壁,當時的主流思路是“防堵”和“治理”。而錢學森在1984年提出的“沙產業”理論,則完全是另一種思維。他運用系統工程的觀點,認為沙漠不應被視為負擔,而是一種獨特的資源。那裡雖然缺水,卻擁有取之不盡的太陽能和廣闊的土地。他主張建立“多采光、少用水、新技術、高效益”的知識密集型農業,利用太陽能和現代生物技術,在沙漠中創造出新的經濟價值。如今,從內蒙古庫布其到甘肅河西走廊的光伏農業和沙生經濟,完美印證了這一將生態劣勢轉變為經濟優勢的構想。
3. 建議新能源汽車,實現“換道超車”
上世紀90年代,中國汽車工業的主流是“市場換技術”,幻想透過合資來追趕西方在燃油車領域的百年積累。錢學森反對,認為應當走自己的技術路線,不能亦步亦趨。1992年,他在給國務院領導的信中明確建議,中國應該跳過汽油、柴油階段,直接發展新能源汽車。

他準確預判到:在傳統燃油車的賽道上,我們已遠遠落後,追趕無望;而新能源汽車是一個全新的賽道,大家起跑線相近。中國如果能集中力量攻關電池、電機、電控,就有可能擺脫技術依賴,實現“換道超車”,同時還能解決國家能源安全問題。三十年後的今天,中國已成為全球新能源汽車的領導者,這一逆襲證明了錢學森當年驚人的戰略遠見。
4. 思維科學與人工智慧的未來
在錢學森所有的戰略構想中,極具前瞻性的、也與他的人體科學思想聯絡最緊密的,是他對“思維科學”和人工智慧的深刻洞察。“思維科學”也是錢學森對複雜性科學下的一個分類。
在80年代,當世界主流AI研究還聚焦於在基於邏輯規則的“符號主義”中,試圖讓機器像數學家一樣思考時,錢學森已經看到了這條路線的根本侷限。根據他的“思維科學”框架,人類思維劃分為三個層次:
抽象(邏輯)思維:即當時AI研究的主流,嚴謹但脆弱。
形象(直感)思維:處理影像、模式、直覺的非線性思維,這正是人類智慧的強大之處,卻被當時的AI所忽視。
靈感(頓悟)思維:創造力的源泉,是思維的最高層次。
這預言了未來AI發展史。

錢學森實際上預言了,只靠邏輯的“符號主義AI”必將失敗(後來果然迎來了AI的第二次寒冬)。他極力倡導的“形象思維”,其本質正是模式識別。這與21世紀初,由大資料和算力突破推動的深度學習革命,在思想核心上完全一致。今天的人工智慧,無論是識別圖片、理解語言,還是自動駕駛,其核心正是透過神經網路對海量資料進行“形象思維”式的模式學習,而非生硬的邏輯推理。
而他提出的最高層次——“靈感思維”,則直指今天通用人工智慧面臨的最大挑戰:如何讓機器擁有真正的、從0到1的原創能力?
錢學森倡導思維科學,不僅是技術上的遠見,更是戰略上的佈局。他認為,真正強大的人工智慧,必須與對人腦和思維本質的研究緊密結合。所以,研究人體科學和思維科學的重要性就在於此。他相信,一旦揭示了思維的奧秘,就能從根本上激發整個民族的創新能力,引發一場比量子力學和相對論更偉大的新科學革命。
走出“錢學森之問”
行文至此,我們再回頭看網軍有組織攻擊錢學森的事件。這絕非偶然,因為他一生的思想和實踐,恰恰是對那些鼓吹“造不如買、買不如租”、“全盤西化”、“放棄自主創新”的思潮,最有力、最徹底的回擊。這恰恰是美國和殖人們最害怕的。在20世紀80年代至21世紀初,為了快速發展經濟,我們確實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選擇了“跟隨”和“引進”的技術路線。這種策略在特定歷史時期有其合理性,但其代價,是創新精神的磨損和核心技術的空心化。這才引出了世紀初的“錢學森之問”。他反覆追問:為什麼我在加州理工時,校園裡充滿了顛覆性的創新?為什麼在建國後最困難的六七十年代,我們能獨立搞出“于敏構型”、“人工合成牛胰島素”、“層子模型”等世界級的原創成果?而到了後來,我們的創新卻乏善可陳了?他的答案是:“我們太迷信洋人了,膽子太小了!”


如今我們更能夠理解錢老。中國在高新科技領域從一個追隨者,不可避免地走向領跑者的位置。要想不被“卡脖子”,要想真正實現科技自立自強,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回到錢學森為我們指引的那條路上來:
建立強大的科技主權,發展自主的技術路線,敢於去想別人沒有想過的東西,敢於去做別人沒有做過的事情。這就是錢學森留給我們的最寶貴的思想遺產。
近期文章導讀:
大爭之世,中國就是和外國不一樣
伊朗被炸,臺灣怎麼成了“最大贏家”?
美國人已經天真到,想用石油卡中國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