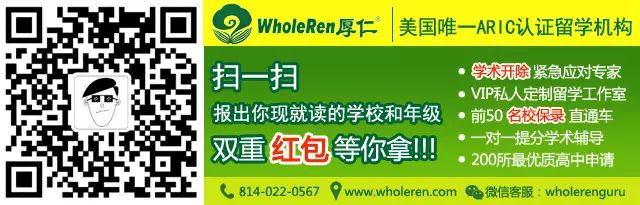《東京家族》
女性作為照護者在今天依然是一種主流的觀念想象,也是一個不可否認的社會現實。然而照護的工作,為什麼常常是由女性承擔?女性是天生的照護者嗎?
今天的文章,學者安孟竹將多角度為我們講解女性作為照護者的困局,以及如何打破它,實現更多人的解放。
讓我們先從“家”這個最為親密的空間裡談起。

講述 | 安孟竹,人類學研究者
來源 | 看理想節目《良善照護如何可能?》
01.
照護工作,為什麼常常由女性承擔?
早在1980年代,社會學家萊斯利·裡默(Lesley Rimmer)就用“照顧迴圈”(caring circle)這個詞來描述女性婚後照顧子女、中年時照顧父母、到了晚年還要持續照顧配偶的生命歷程。承擔家庭照護,幾乎構成了女性生命的一根主軸;而女性在家庭照護中的投入與奉獻,也常常被視為理所當然。
拿育兒這件事來說,一些人認為,女性擁有子宮,就天然地意味著她們有孕育和撫養生命的職責。因此,給嬰兒餵奶、換尿布、哄睡、安撫情緒等,對女性而言如同一種基於生理結構的天然使命。
而這樣的觀點其實是站不住腳的。人類學家發現,並不是在所有文化中,女性都扮演著主要的育兒角色。比如在中非共和國的Aka部落,嬰兒降生後,留在家裡照顧孩子、陪ta們玩耍、給ta們洗澡的通常是以父親為代表的男性親屬,而母親的主要職責是外出打獵。
不過,在人類社會邁向資本主義工業化的幾百年歷史裡,那種將女性與屋簷下的種種照護勞動綁在一起的觀念,的確佔據了上風。當工人階級男性進入工廠,成為“養家餬口的人”,工人階級女性卻被限制在一個“次要的家庭私領域”。
她們餵飽丈夫、養大孩子、維持居所的清潔和家人的健康,整個家庭享受著女性的照顧,就像享受空氣和水一樣自然。然而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正是女性在屋簷下的勞動貢獻,維持了資本主義體系中勞動力的再生產,與其說女性理應照料家庭,不如說是資本主義要透過“女性照料家庭”的意識形態來實現自身的積累。

《坡道上的家》
女性在長大成人的過程中受到性別社會化的影響。歐美20世紀中葉的好萊塢電影裡,那些優雅得體、為丈夫準備好早餐、洗曬完衣物後還能輕鬆享受一杯下午茶的主婦形象,是當時許多中產家庭的女孩想象自己未來身份的模版。直到今天,洗衣粉、油煙機、嬰兒紙尿褲的廣告裡,主角還是女性。
在華人社會,女性不但被潛移默化地賦予了照護的責任,其貢獻也經常被隱藏在崇高的文化理想之下。比如,兒子贍養年邁的父母會被視為“孝順”,但實際承擔日常照護工作的往往是兒媳婦。
儒家的道德教育從來不會告訴你,兒子對父母的孝,很多情況下也是透過兒媳侍奉公婆實現的。兒媳婦對養老的付出,也很少讓她們父權家庭等級秩序裡獲得地位的提升。
女性的照護維繫著家庭日常生活的運轉,但照護的投入卻無法為女性換來經濟與社會地位的回饋。這是因為,無論是在父權家庭還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照護都不被視為一項重要的生產性勞動,其社會價值很少得到認可。
一直到 1960年代的第二波女性主義浪潮中,包括照護在內的家務勞動報酬問題,才開始被廣泛討論。
02.
女性的“第二輪班”
在今天的工業化國家,女性已經衝破了私領域的束縛,普遍走向職場,從事有薪工作。那麼,女性走向職場的情況會改變她們作為家庭照護者的角色嗎?
社會學家霍克希爾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提醒我們,職場女性的“第二輪班”正是從她們下班回到家的那一刻開始的。
霍克希爾德指出,工業社會試圖構造出一個可以周旋於家庭照料與工作負擔之間的超級母親形象,從而逼迫職場女性去接受一張超負荷的時間表,把她們承受的額外負擔隱藏起來。然而身體是最誠實的見證。2022年柳葉刀雜誌的一項統計顯示,職場女性在家庭中肩負的無償照料勞動,正威脅著她們的身心健康。
1950-60年代,從舊禮俗、舊道德中獲得“解放”的中國農村女性,也沒能擺脫這種“生產”與“再生產”領域的雙重負擔。1950-60年代,農村女性雖然被大規模動員起來參與社會主義建設,很多人還因此評上了勞模,但回到家,女勞模們也繼續操持大量家務,侍奉老人和照顧子女。
歷史學家賀蕭(Gail Hershatter)發現,對這一輩農村女性而言,勞動者身份帶來的價值感和榮耀感,常常被私人領域裡照護的艱辛感所稀釋。

《坡道上的家》
雖然女性進入勞動力市場並沒有撼動她們作為家庭主要照護者的身份,但勞動力市場上的性別不平等,卻深刻影響著一個家庭中“誰去照護”的選擇。
一個普遍的情況是,在今天,當一個家庭面臨長期照護的需求,比如有一個身心障礙的孩子需要密集的早期干預、或是父母生病臥床,雙薪夫妻之間,往往是那個在職場上薪酬更低、晉升機會更少的妻子,選擇了放棄事業、成為全職照護者。
也有人會說,女性更耐心細緻、更有共情能力、更善於人際溝通等特質,讓她們比男性更適合承擔照護工作。這些品質對照護實踐而言很重要,但這裡有一個不容忽視的性別氣質養成問題——為什麼大多數男性沒有被教育成更細心、更共情、更適合照護的人呢?
更重要的是,在照護勞動本身的價值依然被貶低的前提下,將照護所需的情感品質歸於女性,並不會提升女性透過照護獲得的回報,反而鞏固了不平等的性別分工,甚至還會讓正在承擔照護的女性面臨更多的要求——彷彿為了成為一個好的照護者,她們不止要付出體力上的勞動,還需要調動性別氣質,變得更細膩、更包容、更懂得溝通。
那麼,這種將照護與女性繫結的觀念定式會帶來怎樣的社會後果?
一個眾所周知的情況是,時至今天,在醫療場所、養老院、幼兒園裡從事有薪專職照護工作的依然主要是女性。這樣的職業身份幾乎成為了女性的家庭角色在職場上的延伸。
相比之下,選擇做護士、幼師、看護的男性則十分罕見。從事“照護”這種傳統意義上的女性工作,會被視為有損陽剛的男性氣質。

《坡道上的家》
此外,“女性作為照護者”的想象也讓“如何平衡家庭與工作”變成了專屬於職場女性的問題,人們更習慣看見一個因為談生意而晚回家的爸爸,卻不一定寬容一個因為加班而沒有給孩子做飯的媽媽。
而當男性需要成為照護者時,這樣的性別想象也給他們帶來了特殊的困境。相比於女性照護者,男性照護者經常會陷入一種無法自我肯定的消極情緒。這是因為,男性的成長環境一直鼓勵他們透過追逐事業上的權力和成就來建立自我認同,透過“賺錢養家”而不是直接照顧家人去獲得價值感。
因此,當他們迫於現實壓力不得不離開職場去照顧家人的時候,如同做出了一項違背社會期待的選擇,是沒面子的事。
03.
將家庭照護交託給“外人”,
意味著什麼?
在今天,緩解都市女性家庭照護負擔的一種主要方式,是將煮飯、接送孩子、看護老人這類任務外包給“家政工”“育兒嫂”“家庭看護”來完成。人們已經越來越習慣一個有償照護服務產業的存在。
構成這個勞動力市場的,通常是來自全球的欠發達地區的女性移工。在香港、新加坡街頭,她們是接送孩子上學放學的菲傭印傭;在北京、上海,她們是操著小地方口音的保姆阿姨。
當這些低階層、少數族裔的女性來到發達地區,維繫著中上層家庭的日常運轉,她們自己的家庭照護,往往會交給留在故鄉的父母、或是僱傭當地更加貧困的女性來完成。
這種“照護”沿著勞動力全球流動的路徑層層轉包的現象,被社會學家稱為“全球照護鏈”(global care chain)。這個概念讓我們看到,一些女性得以從家庭照護中獲得某種解放,往往是以另一些女性離土離鄉為代價的。
為什麼這些女性移工寧願離開自己的家、去服務別人的家?一個重要的背景因素是二戰後全球經濟發展的地域不平等。在今天的菲律賓,一個擁有大學文憑的女性在銀行和當地企業工作賺到的錢,遠遠不及在香港做家庭傭工的收入。對於中國的農村女性來說,在城裡做家政的收入也遠高過在家種地。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進入發達地區的照護產業的女性,就能享受到當地平等的勞動待遇。根據2017年香港中文大學的一項調查,超過七成的外傭每天工作13小時,時薪只有13.7港元,還不及全港法定最低工資的一半。面對嚴苛的移民工作制度,她們即便遭遇了僱主的不公平對待,也往往極力隱忍,因為対她們而言,被解聘不僅意味著失去收入,更意味著失去居所和簽證。
在不平等的勞動條件之外,這些來自偏鄉的女性移工還時常承受著歧視和汙名。一些僱主會把家政工、保姆想象成一群無知、懶惰、貪小便宜的人。在僱主家中,她們的工作經常是在提防與監視的目光下完成的。

《坡道上的家》
如果回到照護勞動外包的初衷,我們還可以去問一個問題:僱傭專職照護者,真的卸下了僱主家庭女性的全部照護責任嗎?
如果我們去看照護的實際運轉,就會發現都市家庭裡往往存在 Archbold 所說的照護管理者(care manager)和照護提供者(care provider)兩種角色:僱主家庭的女性依然承擔著照護的規劃協調和資源連結的工作,比如幫孩子安排好上補習班的時間,規定大掃除的頻率,為患病的家人尋找治療資源、制定康復計劃等,而受僱的育兒嫂、家政工、看護們則身體力行地執行著這些照護的規劃。
然而,在照護的具體實踐中,照護管理與提供的職責邊界並是那麼明晰。
照護從來就無法被簡化為服務的提供與購買,它也容納了人與人之間的相互成就,對彼此脆弱性的回應。
很難總結家庭照護的外包究竟給這些離家的女性移工、給我們自己的家庭生活帶來了什麼影響,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在照護者與被照護者的相遇、相處中,人與人之間彼此的敞開、交付與回應,總是與不平等階級結構的交織在一起,這也讓照護本身變成了一種複雜的人際關係。
04.
家庭之外,照護還能依賴於什麼?
儘管訴諸市場尋求照護服務已經成為一種趨勢,但這樣的選擇本質上依然是對家庭資源能力的考驗。在中國大陸,面對水漲船高的生活成本,個體重新轉向家庭尋求保護和支援已經成為一種普遍趨勢。
有學者稱這種現象為“新家庭主義”,其中一個鮮明的體現是,老年人,或者說家中的祖輩,正在被重新調動起來,成為育兒這件事上不可或缺的力量。
這些作為輔助照護力量被動員起來的老年人,構成了推動中國經濟發展重要的隱形助力。參與和協助子女的生活,給祖輩們帶來了新的價值感,但也常常引發代際之間的摩擦和紛爭。而且,勞動付出並不足以讓ta們享有育兒問題上的話語權和決策權。
我們多數時候仍然在以“家庭”為單位面對照護這件事。尤其當家庭消費不起市場提供的照護服務時,親人往往成為了我們最後的依靠。但僅僅依賴於家庭和家人的照護也會因家庭本身的解體、資源不足、和突發狀況而陷入危機。

《東京家族》
需要追問的是,在家庭之外,照護還能依賴於什麼?
以育兒為例,如果年輕的父母不願把照料孩子的事假手他人,也不願依賴老人的付出,那就必須去問,一對工薪家庭的夫妻究竟有多少育嬰假可以請?我們的職場環境對生育足夠友好嗎?社群裡有沒有負擔得起的 24 小時托育服務?遇到突發情況,他們可以把孩子託付給誰?
在人們訴諸市場或發動親屬力量的照護選擇背後,一個很容易被忽視的現實是,公共托育制度和措施的匱乏。
當然,不是說公共福利的提供可以一勞永逸地解決照護中的所有問題,但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的建設,的確可以有效地緩解家庭照護者的負擔。
目前,中國的家庭照護者們主要是透過找親朋幫忙、或是與特定照護機構建立私人關係,來主動尋求“喘息”的可能。然而如果要讓這項服務變得更加制度化、更加便利可及,依然要依賴於公共財政對專業服務團體的持續補助和服務申請渠道的建設。
公共服務的建成並非一日之功。但我們可以看見,許多非政府組織已經開啟了對“照護者”進行支援的行動探索。比如,一些心智障礙者家庭支援組織會定期為家長們舉辦分享會、親密關係支援營,組織家長們成立興趣小組,一起唱歌、讀書、做手工。
雖然這些活動並不直接提供照護的支援,但卻讓處在相似困境中的父母們彼此結識,為他們提供了釋放壓力和情緒的空間,以及交流照護經驗與困境的契機。更重要的是,透過這些活動建立的關係和情誼會逐漸匯聚成社群的力量,讓照護從一件“私人”的事變成“我們大家共同”的事。
社群是分享資訊、資源和知識的網路,也是跨越家庭邊界的互助力量。它可以減輕家庭獨自面對照護問題時孤立無援的感受,也可能改變照護髮生的時空和方式。在我們生命陷入脆弱的許多時刻,幫我們修復生活的故障、讓日子繼續過下去的,都是朋友、鄰里這些血緣家庭之外的力量。
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把這些基於友誼和鄰里關係的互助行動,稱為“日常生活中的共產主義”。它在個人或社會遭遇危機時促進了人與人之間相互照顧的責任感,也鼓勵我們用一種更加激進的社會想象取代“照護責任歸於家庭”的陳舊觀念。
此外,在全球的自動化研究領域,照護機器人的開發,正在成為一種趨勢。
功能各異的照護機器人被開發出來,其中的許多設計都蘊含幫照護者緩解勞動負擔的願景。比如,日本開發的Robear機器人可以根據不同病人的身形體重,幫照護者解決攙扶、搬動病人上下床的問題。雖然只是一項簡單的工作替代,卻大大地緩解了長照帶來的身體損傷。
照護的安排與交付,往往與一個社會的性別結構、階級秩序、勞動力的流動和公共福利體制息息相關。這些宏觀的結構性力量,也深刻地影響著每個家庭“讓誰成為照護者”的具體選擇。
照護勞動的價值被貶低的情況,在今天依然沒有發生什麼改變,並且持續影響著女性的家庭和社會地位,以及家政、看護等照護從業者的處境。大多數面臨長照需求的家庭依然像孤島一般,隨時可能被耗盡。
我們離那種關懷倫理學者們暢想的以“care”為基本原則的社會理想,還有很大的距離。這樣的距離,召喚著公共政策的介入、社會資源的配套,以及更加富有創意的社會行動。

*本文整理自看理想節目《良善照護如何可能?我有一個問題05》第2期,有編輯刪減,完整內容可點選下方圖片,進入“看理想”小程式收聽。

音訊編輯:LinQ
策劃:看理想新媒體部
封面圖:《坡道上的家》
商業合作:[email protected]
投稿或其他事宜:[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