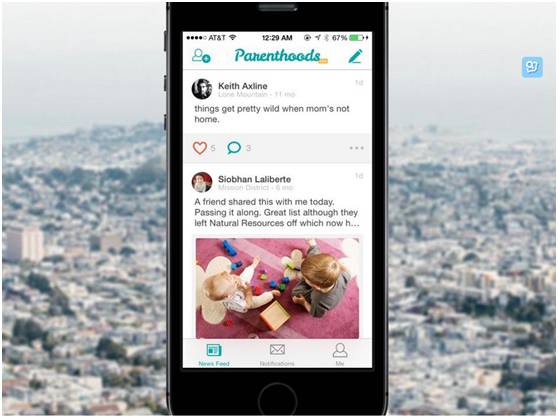在維多利亞的一個週六清晨,天還沒亮,Jeni Gunn的的拉布拉多犬Shelby——就在床邊輕輕搖尾巴。她睜開惺忪的眼,摸黑起身,卻踢到了一張路邊撿來的六邊形木桌。她想,哪天攢點錢,就把它打磨、上漆,再賣個45塊。
這些年,她的家從來沒缺過“免費傢俱”:一張書桌、一個書架、一把椅子,都靠路邊撿。

Jeni租住在一間地下室單元裡,屋主允許她利用那小塊室外空間。她夢想著種些豆子、番茄、草莓,盆器已經到位,唯獨缺土。那些花盆還空著——因為她買不起土。對,現在的生活預算裡,連一袋“土”,都是奢侈品。


今年51歲的Jeni,月入約2800加元,看上去有幾份“體面”的工作:緊急事務協調員、私人偵探、自由撰稿人……聽起來像個自由體面的中產階層,但實際上,她早就陷入了“窮忙族“(working poor)的處境:常年有忙碌工作有收入,但卻始終活在貧困線以下。


她的收入幾乎全都交了房租、保險、汽油、吃飯和還債。
Jeni跳進淋浴間,腦子裡已經飛快運轉。她在社群組織做的“應急管理協調員”合同快到期了,續約計劃還沒敲定;中午要幫私人偵探客戶去監視;有時間的話,還想接個除草修樹的園藝活兒等等。一份她幫地產經濟寫房地產部落格的75刀稿費還沒到賬呢,她得記得去提醒那位房產經紀人。而沒到賬的錢意味著連帶點菜去聚會的預算都沒有。
她用一條“一元店”買來的粗糙毛巾擦了擦頭髮,那材質吸水效能堪比塑膠膜。然後她匆匆登入Facebook,把自己的聚會狀態從“參加”改成“不能參加”,順便留言:“抱歉啦,臨時家裡有急事。”其實所謂“急事”,不過就是她這個月的臨時工收入不夠,沒錢買乳酪拼盤帶去。


她和朋友之間的經濟差距正在越拉越大。朋友們有大理石地磚玄關的房子,帶孩子說走就走去旅遊,超市買牛排不眨眼。有人家請人打理院子、修房子、甚至重新粉刷碼頭。還有人家草坪打造小橋流水,栽上幾千刀一棵的日本楓樹。
Jeni每次去朋友家感受到這些“精緻生活”的時候,都要提前練習自己“震驚但不失禮貌”的表情。
但她很少跟人談論自己的財務。她在外人看來像箇中產階級:開SUV(雖然是一輛2008年的三菱,儀表盤上常年亮燈);穿的是精心挑選的二手衣服;買東西時常常站在貨架邊用手機查品牌和原價,看準了才買。
她不是不努力,恰恰相反,她的每一天都被各種打工填滿——寫部落格、做調查、幫人搬家、剪草坪、教表演、寫賀卡劇本甚至填問卷。但收入仍然不穩定,還常被拖欠。
有一次她幫人做園藝工作,手上磨出了水泡,僱主卻一拖再拖不肯支付那區區250加元的酬勞。
Jeni與很多加拿大人一樣,其實屬於“隱形打工貧民”:天天在工作,可收入還是低於貧困線。
為了省錢,她甚至自己剪頭髮。
如果不只看收入,而是看“能不能過得像樣”來定義貧窮,比如能不能買新鞋、給人送個小禮物、偶爾外出慶祝,那全國大約四分之一的人——差不多1000萬人其實都勉強餬口。
Jeni 不是不拼,只是生活的公式早已變了。她的父母靠一份小學教師工資養家、有房、還能帶孩子們去歐洲度假。而她,即便拼命工作三十年,如今連退休儲蓄都只是一隻陶瓷儲錢罐,銀行戶頭上只剩下$6塊錢。
她曾試圖改變,2022年,她帶著狗和貓從溫哥華島一路搬到新斯科舍省,希望能降低生活成本。她找到了紅十字會的全職工作,生活以為就要步入正軌。但現實是,省稅更高、物價差不多、房租仍貴……她第一次陷入信用卡負債。
Jeni 說:“那是我人生第一次欠債。”也是她第一次感受到,即便再努力,也很可能永遠買不起屬於自己的房子。


雖然生活艱難,但Jeni依然感謝“自由職業”曾帶來的陪伴孩子們的時光。女兒患病時,她可以隨時往返醫院;孩子小時候,她有空陪他們在海灘築堡、燒熱狗。這些記憶,是她人生中最溫柔的部分。
現在,加拿大約有四分之一的成年人都在做做“gig工作”——零工、專案合同、時薪短工……這比2022年增長了85%。Angus Reid研究所聯合Securian Canada做過一個調查,發現大多數人做零工是“為了錢”。四分之三的受訪者在全職或兼職之外,還要額外做零工來維持生計。甚至有三分之一的人表示,零工已經是他們收入結構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其中近一半的人年薪超過10萬。
Jeni只是加拿大數百萬“窮忙族”(Working Poor)中的一個縮影。她拼盡全力維持體面、不掉隊,只為了不被生活開支吞沒,日復一日忙碌只為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