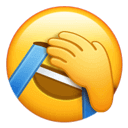作者 – 溪棠
監製 – 她姐
女性做生殖器官改色手術的段子,餅乾2023年就寫了出來,線下對稿時,這個段子被同行評價為“令人感到不適”。
那時的餅乾31歲,講脫口秀不過1年,表演時總下意識低著頭,把手塞進兜裡,常常自我懷疑。同行的差評讓她深受打擊,她將段子擱置,沒再提起,卻也一直沒忘記。
2025年雲南某個小酒館的開放麥上,前排被一群女大學生佔領,不論表演好笑與否,她們都會鼓掌稱讚。她們的尊重給了餅乾勇氣,她又拿出了那個段子,覺得“可以講一講”,沒想到全場沸騰,全場拍手叫好。

尤其是幾個學醫的女大學生,她們說“我很喜歡你的段子”。
餅乾把段子放到網際網路上,又掀起新的討論熱潮,無數深受其害的女孩湧入評論區。
有人受社會風氣影響,以為只有“粉嫩”的顏色才正常,花費上萬元,忍受鑽心的刺痛,做了6次雷射手術去除黑色素;有人被母親羞辱“下體的顏色很奇怪,是不是不檢點”;還有女性說“看到你的段子後,我決定不做那個手術了”。
那是餅乾人生中少有的高光時刻。
採訪中,餅乾形容以前的自己“懦弱”,就連媒人也識破她的本性,給她安排了“同等懦弱”的相親物件。
她把那次相親稱為“loser聯誼會”,寫成段子帶到舞臺上,臺下觀眾的朗朗笑聲,消弭了她對舞臺的恐懼,支援她在舞臺上講述那些“不被看見的女性”。

她們,無法對女性的遭遇視而不見
直到現在,餅乾依然很震撼生殖器官改色的段子,能引發這麼多女性的共鳴。餅乾之前一直以為這是很小眾的話題。
線下讀稿時,還沒等她講完,同行打斷她,一臉無奈:“我覺得我聽不下去,觀眾應該也聽不下去。”
他的語氣很真誠,她沉默了一會,附和道:“那不講這個了,換一個聊吧。”
那是她很信任的朋友,作為行業新人,餅乾信任對方的評價。儘管潛意識中,餅乾不認為段子有問題。
當她站上一個以女性觀眾為主,無論講什麼段子,都有人耐心傾聽的舞臺時,餅乾鼓起勇氣,再次拿出了那個段子。
餅乾做好了“冷場”的心理準備。上場時,她故作輕鬆地問觀眾:“大家都成年了嗎?那我要講一個很嚴肅的生理知識,大家覺得可以嗎?”
臺下的觀眾開始把腰板挺直,氣氛變得有些緊迫,丟擲第一個梗時,觀眾放鬆大笑,餅乾越講越自信。
“我們來說說這個男性的心理,到底是什麼原因,導致他不喜歡黑色,可能醫學、心理學有解釋,但我也不懂,我只能靠我的生活經驗擅自揣摩,我一直想不通,直到我上個月,去了一趟西雙版納的動物園……我就發現啊,大多數動物的生殖器都是黑色的,大象河馬長頸鹿,但只有一個動物是極其豔麗的粉色,那就是猴子,醫學、心理學我也不懂,按我自己的生活經驗,我得出的結論,這個男的是個戀猴癖……”
後來的9場開放麥中,餅乾每場都講這個段子,場場笑聲都響徹雲霄。
餅乾講流產手術、改生殖器官顏色、醉酒後侵犯女性等話題的段子之前,一直擔心這類話題太沉重,無法引起觀眾共鳴。
觀眾們花錢、花時間來看脫口秀,是為了得到快樂,而不是看她大段大段輸出“女性苦難”。
如何把沉重的話題加工好笑,一直是困擾餅乾的難題。
入行前,餅乾並未想過會寫專門寫女性相關的脫口秀,她想寫“觀察式喜劇”,生活中司空見慣的人和事,都能成為素材。
可當她仔細觀察生活,她發現,作為女性,她所觀察到的社會現象繞不開女性視角,也永遠無法繞開生活中觀察到種種跡象:高鐵上沒有衛生巾售賣、公廁裡藍色印章的賣卵代孕廣告、沒有休息室蹲在廁所吃飯的保潔阿姨、叫“招娣”的女孩們……
餅乾見過許多像她一樣的脫口秀女演員,剛入行時,她們都想寫些搞笑的生活段子,到了後期,大家幾乎都會代入女性視角觀察和講述周遭的一切。
沒有任何一個女演員,拿了麥克風是隻為自己說話的,因為她們無法對同性的遭遇視而不見。

“失語的中年婦女”
2022年,說脫口秀前,餅乾處於漫長的“失語期”,沉默寡言,對旁人的否定逆來順受,連為自己說話都做不到。
少年時期,餅乾總是獨自一人躲在角落裡畫漫畫,她完全沉浸在漫畫世界裡,漸漸失去了與人交流的熱情。

餅乾小時候的漫畫
成年後,她去飯店吃飯,服務員少上了一樣菜,她也不敢出聲,這段經歷讓餅乾一度自嘲“是個失語的中年婦女”。
2018年,27歲的餅乾為了擺脫壓抑的工作環境,選擇和丈夫結婚,並來到丈夫的老家昆明。
在昆明,餅乾沒有朋友,丈夫是她唯一認識的人。
她試著透過找工作認識新朋友,但已婚未育的身份,讓有5年工作經驗的她,在職場處處碰壁,所有公司都預設她入職後會生孩子。面試後,沒有任何一家公司給她答覆。
這段求職經歷讓餅乾倍感挫敗,但她沒有反擊的武器,只能被動接受職場的排斥,試著隱瞞已婚身份面試,躲過hr縝密地偵查,才順利入職。
新職場並未給餅乾帶來新朋友。公司裡,每個人都在為生計奔波,疲憊而寂寞,無暇他顧,過多的交往顯得不再合時宜。
餅乾試著找老朋友傾訴,但卻發現,少年時期的、因愛好結交的朋友,或關閉朋友圈,或開起了“僅三天可見”,朋友圈一片空白。
哪怕是最好的朋友,各自也都有了新的生活和人生方向,很多事想傾訴又無處下口,她再也回不去與老朋友通宵促膝長談的日子。
在昆明的日子,餅乾狀態差到一度無法開口說話。
餅乾嘗試各種辦法讓自己打起精神來,她開始刷脫口秀的影片,然後看到了脫口秀演員石老闆。他擅長挖掘生活中的細微末節。
例如講到北京開計程車的司機大爺,石老闆學著司機的樣子,手握方向盤、用不耐煩的京腔問:“去哪兒呀?”,一比一復刻出了觀眾們平時遇到的司機大爺,就連車內擺放的物件,石老闆也記得一清二楚。

石老闆的演出
餅乾從沒想過,如此生活化的場景,也可以被演繹得如此生動有趣。
一潭死水的生活蕩起漣漪,她開始看更多的脫口秀影片。
顏怡、顏悅把職場女性遇到的歧視搬上舞臺,吐槽“如果第一個登上月球的是女性,她可能也要穿高跟鞋”;
梁嬌穎把和前夫離婚吵架、產後抑鬱的經歷,當成段子講得大開大合“有人勸我打小抄放臺上,以免忘詞,不用,真的,我有多恨我前夫這事根本不用打小抄”……
餅乾發現,許多她曾經歷過,但從未和人提起過的歧視、委屈,經臺上她們之口,變成了可以取悅自己和更多人的段子。
而且這個舞臺,不在乎一個人的性別、年齡、相貌、婚育狀況,只要你是一個好笑的人,都能上臺。
任何糟心事,都能成為在臺上抖的包袱,用幽默消解悲傷與痛苦。
餅乾嘗試寫段子,給當地喜劇俱樂部組織的開放麥投稿。餅乾在臺上講的第一個段子是她相親的經歷,臺下的觀眾聽得很開心,但餅乾依然不自信,她留著齊劉海的學生頭,看起來很乖巧,她一手拿著麥克風,另一隻手總是插進兜裡,講話聲音溫吞而小聲。
很快,她遇到了第一次冷場。轉向更大的舞臺後,上臺五分鐘,她覺得臺下的觀眾都在用仇恨的眼神瞪她,開弓無回頭箭,餅乾只能硬著頭皮講下去,越講越心虛。
餅乾意識中“那個人”再度出現,不停地否定她“你有罪,你對不起觀眾在花的門票錢。”

當“媽媽”變成“梁工”
從青春期開始,餅乾開口說話時,身邊總會出現一個人,她冷靜地看著餅乾,對餅乾的所有發言指指點點,漠視餅乾的悲傷,要求餅乾事事周全。
被意識中的人格操縱的感覺很痛苦,餅乾不喜歡她,想讓她消失,開口講脫口秀,或許能讓她消失。
這個人是媽媽“理想中的餅乾”,成績優秀、舉止優雅,最重要的是,她從事對社會有貢獻的工作。
某種程度上,餅乾媽媽只是在用要求自己的標準,要求女兒。
媽媽是工程師,負責修繕軍工裝置,由於交通、資訊不便利,從餅乾初中起,她便經常親自到外地拿紙質的圖紙,坐火車回單位。
圖紙的資訊涉及部門機密,一旦丟失,後果不堪設想。擔心圖紙丟失,媽媽睡覺也抱著裝圖紙的鋼桶。
媽媽工作的三十多年裡,從未請過一天病假,有時生病了,也只是中午休息一小時,院裡鈴一響,又馬上趕回去上班。
當“梁工”的壓力很大,所有人都盼著她能早日攻克技術上的難題,為保衛邊疆事業添磚加瓦,但“梁工”是人,不是“神”。
被壓力淹沒時,絕望的梁工站在辦公室的窗戶前,一度想跳下去。
如此高壓的狀態下,她還要兼顧餅乾的教育。
餅乾爸爸是個溫和的人,但在這段婚姻中,他似乎在家庭生活之外,有一個更安全的世界。
爸爸每天下班回家,就把自己關在房間裡看書。雙休日時,他早上八點帶女兒去圖書館,直到閉館再一起回家。但生活不只有看書。
餅乾很難判斷爸爸在這段關係中真正的位置。但生活裡、家庭中,許多問題最終似乎只能指向媽媽。
有時媽媽加班到凌晨兩點回家,也會衝入臥室,把睡夢中的她從床上拎起來,劈頭蓋臉地罵她,只是因為她作業本上的幾道錯題。
更讓餅乾委屈的是,媽媽成為梁工前,她本擁有另一種人生。
那時,餅乾留著比寸頭長一點的短髮,個子不高,身型健壯,什麼都不怕。
上小學時,餅乾因為好奇,把蓋子丟進取暖的暖爐裡,塑膠遇高溫迅速熔化,整個教室都瀰漫著塑膠燒焦的刺鼻氣味。

童年時期的餅乾(左)
老師發現後,擰住餅乾的耳朵。她不服氣:“憑什麼說我故意擾亂課堂紀律,我就是好奇啊!”
生氣的老師拽著餅乾的耳朵,把她拖出教室。逆反的餅乾,反手抓住老師的衣服、褲子,像狗皮膏藥一樣纏在他身上。
即便如此,媽媽被喊來學校後,依舊護著餅乾,她低頭跟老師不停道歉,回家後,也沒有罵她,只是溫柔詢問原因。
那時的媽媽,還不是單位上雷厲風行的“梁工”,她喜歡穿裙子,會抱著餅乾跳舞、拍照,誇餅乾是個“聰明”的孩子。
當媽媽變成“梁工”後,媽媽再也沒有穿過裙子,也再也沒有抱過餅乾。餅乾快樂的童年結束了。

《俗女養成記》中,陳嘉玲抱怨媽媽在她上國中後變壞了
驟變的家庭理念,讓原本開朗活潑的餅乾,越來越沉默。
丟掉開朗沒多久,餅乾又丟掉了一頭利落的短髮。
高中的餅乾告白失敗後,詢問朋友:“為什麼他不喜歡我?明明我們每天一起看書,一起聊天,又那麼懂對方。”
朋友說:“有沒有可能,他喜歡女人?你站在他旁邊,跟他長得一模一樣,你就像他的弟弟,只不過你更矮一點,比他壯一點。”
餅乾愣住了,朋友的話激發了她想要“當女人”的慾望,她開始留長髮、學化妝,把腳塞進窄一號的高跟鞋裡,腳上凸起的骨頭在緊緻的包裹中變得疼痛。
18歲的餅乾想當一個美女,她渴望被誇漂亮,渴望被追求,渴望被愛,這些渴望,讓餅乾把自己一步步塞進了社會規訓下的女性形象。她一味地改變,卻從不將自己的失意與渴望,宣之於口。

《My 盛 Lady》中,女警的朋友教她做“女神”,追男仔

“男人,你吸引了我的注意”
進入脫口秀行業後,餅乾發現,她的怯懦,在一群勇敢的女性同行中,顯得有些突兀。
餅乾認識的人中,朱大強是最勇敢的。公共場合中看到有人抽菸,如果是餅乾,她會糾結一番,要不要阻止,朱大強沒有猶豫半秒,上去讓人“把煙掐了”;有人在朱大強面前罵“辱女詞”,她也會直接說出對方的問題;有人把小男孩帶進女廁所,也會被朱大強“請”出去。
起初剛認識朱大強,餅乾覺得跟她走在一起很危險,她害怕跟人發生爭執,也擔心朱大強的直率會激怒對方,發生更大的衝突。

水手服的是餅乾;粉色衣服的是朱大強
和朱大強相處久後,餅乾發現,勇敢對冒犯自己的人出擊並不會怎樣。
有一次,餅乾開電動車經過立交橋,又看到了“野尿男”,她站在他身後,停下車,大喊“有人尿尿啦!”只見他揹著餅乾,手忙腳亂地拉褲子,餅乾的笑聲在橋洞下回蕩,她騎車飛快地離去。
原來,向世界大聲表達自己的不滿,是那麼的痛快。
她們勇敢堅定地向世界宣洩不滿,卻溫柔對待身邊每一個朋友。
餅乾說脫口秀後,遇到了各種各樣的女性,她們來自各行各業,出身、年齡、籍貫、經歷各不相同,但彼此尊重,從不以身份、地位、名氣劃分等級。
有一次,餅乾和顏怡、顏悅、步驚雲、山河等女性一起吃飯,按照行業的標準,她們已是頭部演員,可是大家座位排布完全沒有咖位主次之分。
線下對稿時,頭部演員也會坐下認真聽完每一個籍籍無名的小演員的稿子,在搞笑部分,不吝嗇掌聲和誇獎,不好笑的梗不僅不會打斷,還會在聽完後,幫忙改稿,並聽取小演員給自己的建議。
讓餅乾印象最深的朱大強,是昆明第一個登上《脫口秀大會》的演員。她是當地名副其實咖位最大的脫口秀演員,但她的字典裡不存在“咖位”。
只要有時間,朱大強不會錯過任何一場開放麥,不論是新人還是老演員的表演,她都會全程聽完,認真幫她們覆盤、聊段子。
這些女性從業者,讓餅乾覺得,之前經歷職場歧視、舞臺上的冷場,好像也沒那麼可怕。
講脫口秀第三年,餅乾重新留回短髮,她不再插兜講脫口秀,嗓門響亮,語氣篤定,颱風越來越穩健。她開始在臺上客串主持人,鍛鍊自己的臨場反應能力。
楊梅來昆明開喜劇專場時,餅乾再次擔任主持人,專場主題為“命中註定我愛我”,講述了楊梅從想成為偶像劇中的女主角,期盼一場浪漫的愛情,再到經歷各種遭遇後,決定成為自己人生劇中主角的故事。
演出結束後,餅乾看到一位女觀眾抱著楊梅,她們彼此摸著後腦勺,邊哭邊互相說:“會好的,會好的,你很好,非常好。”眼淚模糊了她們的雙眼,她們卻不忘給對方擦眼淚。

圖源《俗女養成記》
楊梅哭,觀眾哭,餅乾在她們身後也跟著哭,這是她在現實生活中第一次看到如此炙熱真誠地擁抱,儘管她們初次相遇。
餅乾再次回想起她的少年時代,她也曾像楊梅一樣夢想找到“真命天子”,“女性被愛的前提是漂亮”將她徹底洗腦。如果有人說她長得不好看,她會難過很久。
當主持人的那段時間,她試圖活躍現場氣氛,被臺下的大哥罵“你長得太醜了”,餅乾先是開玩笑“我長得跟劉曉慶一樣”,又把話筒遞給臺下的女觀眾“你覺得我長得好看嗎?”
女孩笑著答:“你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全場觀眾大笑起來,氣氛瞬間被點燃。
大哥見外貌羞辱無法傷害餅乾,便換了種挑釁手段,每當演員抖包袱時,他發出各種聲音接梗,影響演員的表演。
餅乾看不下去了,她決定“剛”一下:“這位先生,請你不要再接梗了,你再這樣你會吸引我的注意,你就要當我的小妾。”
這次,大哥終於閉嘴了。

34歲的餅乾,敢直視自己的外貌、身材,敢開口為自己說話,敢為她者仗義執言。現在,也終於有了勇氣,去面對那個曾讓她害怕、讓她逃避的人,她的母親。
2025年,餅乾給生殖科的醫生寫稿,醫生的話讓她震撼:“女性一出生就擁有她一生中將擁有的卵母細胞,當我們的姥姥懷著媽媽的時候,我們是媽媽卵巢中的卵子。”
餅乾忽然意識到,她成年後一刻不停逃離的人,到頭來,是世界上與她最親密的人。
2009年,18歲的餅乾為了逃離媽媽的掌控,把高考志願填到南方,從西北一路向南,來到廣州。
可餅乾並未過上她想要的生活,那時的媽媽已經退休,一週4天和她通話,向她傾訴所有煩惱和委屈。退休前的媽媽終日忙於家庭和事業,沒有朋友,如今,女兒是她唯一的慰藉。
為了逃避與母親每天事無鉅細的電話,餅乾隻身一人,騎腳踏車前往川藏線,高原上訊號不好,每次打電話,巨大的風聲在話筒迴盪,母親很生氣,叫她趕緊回來,餅乾說:“你管不了我,我馬上要到拉薩了。”
再後來,為了脫離母親的控制,她快速結婚,從廣州繼續西行,定居完全陌生的昆明。

在昆明生活的餅乾(右)開始有了新朋友
母親又搬到了餅乾所在的小區。
餅乾試著不再逃離。
後來,她聽母親聊起自己年輕時的人生軌跡,才發現,母女的經歷高度相似。母親也一生都在逃離。
姥姥對母親要求很高,會用冷暴力的方式對待她。一次,姥姥冷著臉不說話,母親怎麼問也得不到回應,直到母親急哭了,姥姥才告訴她由頭,但也只是因為母親出門玩前沒擦乾淨桌子而已。
壓抑的家庭氛圍,讓母親從小萌生逃離的想法,高考填志願時,生在東北的母親,選擇了北京。大學畢業後,又透過分配、結婚,定居甘肅,再用無休止地工作逃離原生家庭。
毫無準備地矇昧逃離,很容易讓人掉入另一個陷阱,但有逃離的念頭,才能讓逃離擁有無限可能。

《出走的決心》中,李紅嘗試遠嫁逃離殘酷的原生家庭
長大後的餅乾,嘗試理解母親,畢竟她小時候也是沒有被姥姥好好愛過的孩子。
更重要的是,母親也不再逃離。
退休後,為了擺脫工作帶來的陰影,她考取心理諮詢師證以自救。
隨著許多問題少年的家長向媽媽求助,媽媽開始反思餅乾的親子關係,並向女兒道歉:“我以前給你打電話說那麼多事情是不對的,孩子就是孩子,不能把孩子當朋友,你不是我的同輩。”
餅乾記憶中的那個女強人越來越模糊,和媽媽一起買衣服,她不再買年輕時喜歡穿的衣服,她開始買老年女性穿的版型,樣式誇張,但布料很舒服。
餅乾問她:“怎麼不買以前那種墊肩的西裝了,看起來很精神。”媽媽說:“我現在又不上班了,穿那個幹嘛。”
回家路上,她們走在滇池邊上,有隻小蝴蝶飛過來,媽媽興奮地追著蝴蝶跑。看著媽媽遠去的背影,餅乾突然意識到,媽媽壓制她的時間已經過去了。
2025年6月,餅乾再次站上脫口秀的舞臺,這一次,餅乾腦子裡對她所有發言指指點點、要求她事事周全,操縱她人格的“那個人”,消失了。

2025年講脫口秀的餅乾
除標註外,圖由受訪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