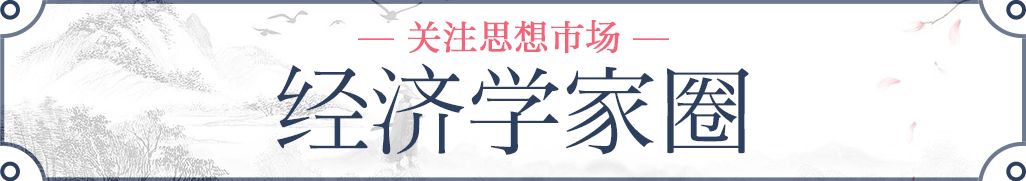褐石培心幼兒園鉛中毒事件。
園長朱某琳、投資人李某芳等人被調查。
公安機關查獲剩餘顏料,確認含鉛成分。

然而,官方通報並沒有一錘定音。
疑問更多了。
為何會為了食物外形美觀,去冒兒童食品安全的巨大風險?
為何不使用價格相對低廉,且更易獲取的食用色素?
所新增的顏料又是哪種顏料?
在僅有一份官方說明,且在無其他深度報道的情況下。
網友開始自發推測“真相”。
還有人以身試毒,親自試驗——
用麵包蘸取顏料食用,表示口感酸澀,排便也會帶有顏色,很難不被發現。

有人發現,那份官方通告也存在錯誤。
將原本的涉事方“褐石培心幼兒園”寫成了“培心幼兒園”,而這一錯誤,也延續到了新華社、央視的報道中。


事故乃因拆遷糾紛和生活壓力,涉案司機張某所採取的極端行為。
案件定性:
蓄意報復社會。

當時大量網友表明態度:
拒絕以任何方式為兇手“洗地”。


理解不等於寬恕。
——這一基礎常識並不被網友所接受。
若有人追問這件事情的始末,則會被視作為兇手“洗白”,是對死難者的漠視,是和這個司機一樣沒人性。

在還沒有深度報道的情況下,網路上就已經充斥著對深度報道的敵意態度。
整個事件傳播過程中,僅有一篇報道(後被刪除)。
其他深度報道數量:零。
02
“人血饅頭”
被認為採訪受害者及其家屬、親友,給他們帶來了二次傷害。
“揭瘡疤”、“消費苦難”、“吃人血饅頭”、“侵擾悲痛”。


接近核心當事人,還原事件過程,豐富事件背景。
這些本就是記者的職業本分。
當“人血饅頭”的指責蓋過對真相的呼聲,《人物》主動刪除了這篇文章。

一個業內共識:
任何關於新聞倫理的討論,都應建立在支援媒體到場的前提之上。
然而,如今這樣的討論越來越少。
因為另一個前提已然缺失——新聞本身。
2011年11月17日,山西太原部分群眾自費購買大量報刊,公開焚燒。
並打出橫幅:
“為了中華民族,火燒漢奸媒體。”

次日,河北石家莊有人響應,將數百份“漢奸”報刊在郊外垃圾場焚燒填埋。
《中國青年報》對此評論:
現代社會,價值多元是常態。從喻權域提案“懲治漢奸言論法”,到火燒“漢奸報系”,再到動手打人,都是對言論自由的侵犯。
最早丟擲“漢奸媒體”說法的,是北大教授孔慶東。
他曾多次公開表示:
“記者現在是我們國家一大公害。”
“這些記者排起隊來槍斃了,我一個都不心疼。”
“我覺得全國人民應該起訴。”

彼時曾有記者向孔慶東邀約採訪,遭拒。
事後孔慶東自己將這事發到了微博上。
一分鐘前,漢奸刊物電話騷擾要採訪我,態度很和氣,語言很陰險。孔和尚斬釘截鐵答覆了一個排比句:去你媽的!滾你媽的!操你媽的!

網友戲稱“三媽事件”。
後續網路輿論大致分為“教授不該罵人”,和“記者該罵”兩派觀點。
但當幾乎所有媒體,包括新華社在內,均對孔慶東的言論提出批評:
我國實行教師資格制度,教師有“品行不良、侮辱學生,影響惡劣”的情形的,應由所在學校、其他教育機構或者教育行政部門給予行政處分或者解聘。

而如今。
“文化漢奸”這一說法,幾乎不會再招來駁斥。

04
那個手裡拿著糞耙的人,目光只向下看;有人為他的糞耙獻上一頂天上的王冠,但他既不抬頭,也不理會別人給他的王冠,而是繼續耙著地上的汙穢。始終拒絕看到任何崇高的東西,只將目光凝視著卑鄙墮落之物的人。
好難聽的話,又是好崇高的敬意。
“扒糞人”這個詞被記者群體自己留了下來,是自嘲也是自勉,是一個相互認同的身份標籤。
但時過境遷,一些新的罪名被編織羅列——
是“沒有大局觀”。
是“屁股坐歪了”。
是“遞刀子”。
去年,揭露油罐車混載新聞爆出。
沒想到最基礎民生問題,竟然也能涉及屁股問題?

這已經不是在討論肉要不要爛在鍋裡。
罵跑了扒糞人。
糞去哪了?
寫到這有點反胃。
05
“自媒體時代”
2017年,新京報《局面》欄目釋出了25條,對江歌母親與其室友劉鑫的採訪影片。
節目上線引發輿論熱潮。
《局面》節目發文《多餘的話》,解釋節目初衷:
我們希望,《局面》的每一次專訪,都是在促進溝通,彰顯理性。我們更希望,各位能夠收斂起憤怒的情緒,儘量不給新聞當事人施加額外的傷害,用善意來理解這個複雜的世界。
“不要簡單辱罵劉鑫和她的家人。”
在這條勸說下,點贊最多的評論是:
“不要簡單辱罵,要複雜辱罵。”
在採訪影片釋出後,一大批公眾號爆款文章應運而生——
《為閨蜜擋刀而死的江歌,你媽媽終於當面問了那個人:還有良心嗎?》《劉鑫,江歌帶血的餛飩,好不好吃?》《劉鑫江歌案:法律可以制裁兇手,但誰來制裁人性?》《江歌,你替劉鑫去死的100天,她買了新包包染了新頭髮》……
探討不多,煽動更多。
批評不多,謾罵更多。

一個複雜事件,被砸平為絕對的惡與絕對的悲。
在這片制裁人性的浪潮裡,“促進溝通,彰顯理性”的初衷幾乎完敗。
“事實已死,情緒為王”。
——成為了新的遊戲規則。
而傳統新聞記者,仍在堅持媒體底線。
鳳凰記者李淼在轉發庭審錄影時,僅僅留下一句——
“我們只記錄還原事實。”

當傳統媒體所堅守的事實、理性、公共利益,開始慢慢滑向謊言、情緒、商業利益取代。
於是,等翻轉。
——成為了保持理性的必要手段。
06
“沒事可以不發”
沒有新聞了嗎?
現在所謂新聞,更多是這樣的——
狗,被風吹跑。
貓,上課打盹。
老虎,看著你撿手機。

看著像鬧著玩。
但都是由認證過的藍V新聞平臺釋出的。
“當時看著很有意思,於是就用手機記錄下來”,是這個時代黃色新聞的起手式。
標題誇張、描述膚淺、語言情緒化。
客觀理性?
它本身就沒有任何內容可言。
卻以排山倒海之勢劫持著公共注意力。
最極致的案例,莫過於貓一杯的“秦朗巴黎丟作業事件”。

一個擺拍影片。
因內容太扯淡,迅速走紅,並被各大新聞平臺轉發,成為毫無營養的熱點。
這是第一次。
隨後在網友的質疑浪潮中,自稱“秦朗舅舅”賬號高調現身,進一步引發熱度。
這是第二次。
最後,推動了官方通告發出:一切系偽造。

跟風轉發,至於嗎?
段子被轉發成新聞,再被當成“假新聞”嚴打。
貓一杯被封號。
那些以為自己捕捉到了“新聞”而四處轉發的賬號呢?
變假為真,變輕為重,變無聊為熱點。
Sir覺得,我們此刻需要的深度報道,就被淹沒在這一個又一個注意力陷阱裡。
不只是注意力。
資訊泡沫中的我們,也在慢慢失去面對社會癥結的能力與勇氣。
據《全球調查記者網路》(GIJN)2015年報道,中國調查記者數量在2010年代初達到高峰。
但所謂的“黃金時代”。
也是一個個普通人,用勇氣與良知拼出來的——
李翔,中國洛陽電視臺記者,經常報道社會議題,最後一條微博是關於當地地溝油報道。
2011年9月18日,被發現其回家路上被兩名殺手搶劫,身中十餘刀身亡。
朱文娜,原《法人》雜誌記者,2008年發表《遼寧西豐:一場官商較量》,該報道涉及某縣委書記的違規行為。
之後該地區警方以“涉嫌誹謗罪”對朱文娜立案調查,並進京拘傳,最終警方對朱文娜正式撤銷立案、撤銷拘傳。
簡光洲,前《東方早報》首席記者,2008年以一篇《甘肅14名嬰兒疑喝“三鹿”奶粉致腎病》,首次直接點名三鹿品牌。
發稿後,三鹿多次聯絡簡光洲要求其撤稿,簡光洲自己緊張得睡不著覺。

後來呢?
4年後,他從《東方早報》離職。
在社交媒體上留下一句“理想已死,我先撤了,兄弟們珍重”。
因特殊環境、新媒體轉型與輿論的影響。
調查記者正逐漸成為歷史。

坦白講,記者無非也是普通人,有失誤、偏見,甚至偶爾被情緒裹挾。
但他們來自專業制度性的嚴謹客觀,來自人性的善良勇敢,構成了現代社會良心的底線,也是真相的最後防線。
而如今。
“扒糞人”被汙名化,當“人血饅頭”的指責淹沒理性,當自媒體的喧囂取代深度報道,新聞的天平已悄然傾斜。
能怪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