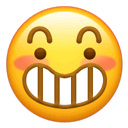“一切不利於我睡覺的事,我不做。
一切不利於我睡覺的人,我不交。”
——南懷瑾
去年,這句話在社交網路上悄然流行。當人們越來越關注自我感受,“睡得好”,在很多年輕人心中的分量不亞於“賺得多”。曾被視為懶惰象徵的睡眠,如今成了珍貴的自我關懷標誌。
而硬幣的另一面,“失眠”這個問題早已是現代人的時代症候,不斷激起人們的焦慮。在作家、心理諮詢師張春看來,失眠不是問題,而是一個訊號,一種問題的表現形式。“你覺得失眠是一個問題才是需要談論的。”
今天是世界睡眠日,關於“如何好好睡覺”,或許我們聽得太多,但很少有人告訴我們怎樣與睡不著的時光和平共處。這期我們與女性貼身衣物品牌ubras一起製作的“呼呼枕邊電臺”,邀請了心理諮詢師張春與單立人喜劇簽約演員賴銘佳,想陪你聊聊,什麼是真正的睡眠自由?
點選觀看影片

“我不是失眠,
是沒在規定時間睡覺”

在當代文化意涵裡,“睡得好”往往意味著沒有心事、健康的身體、良好運轉的生活系統,是一個相當奢侈的存在。但現實情況是,人們睡得不好。《2024中國居民睡眠健康白皮書》顯示,每一萬人中,59%的人存在失眠症狀,完全無睡眠障礙人群僅佔19%。
過去,人們會問候對方“吃了嗎?”而如今,“最近睡得怎麼樣?”則是一個萬能話題——無他,夜晚的睡眠像是白日的倒影,和我們的生活有著諸多方面的連線。
張春不愛用“失眠”這個詞,她說自己只是“沒有在規定時間內睡覺”。就像貓狗不會覺得自己“失眠”,它們只是按照自己的節奏“亂睡”,困了就睡,醒了就玩。只有人類,才會把晚上不睡覺當成問題。畢竟,“人是不可能真的不睡覺的”。
在她看來,所謂失眠,是被社會構建出的一個概念。理論上,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節奏去做各種各樣的事情。但社會勞動的高度整合,使得人們需要統一睡覺、統一工作,一旦偏離這個節奏,就被貼上“失眠”這個自帶焦慮感的標籤。這種社會規訓讓我們不自覺地與自己的自然節奏較勁,試圖強迫自己符合所謂“正常”的作息。

所謂“失眠”,是社會構建出的概念
對有些人來說,“不在規定時間內睡覺”是在為自己爭奪一些時間的主權——“時間很珍貴,我們想要壓縮出新的時間,而最好壓縮的就是睡眠時間。”所以哪怕再累,很多打工人也忍不住要熬夜刷劇、發呆,從睡眠裡偷出一些獨處時光。
張春有一個非常“卷”的朋友,不僅要照料兩個快10歲的雙胞胎孩子,還希望自己保持職業、獨立的形象,同時還要寫字畫畫,把所有的事情都打理得井井有條,以至於每天都兩點才睡覺,日復一日,年復一年,“這就不叫失眠了,而是能量很高,她已經進化了。”
而對於另一些人來說,失眠則是一種失權的表現。就像小孩子要去上學前說自己肚子痛,失眠是成年人讓別人看見自己需求、為自己爭取喘息的空間的一種方式。
其中,女性的失眠狀況更為突出。無論在外擁有怎樣的職業身份,在傳統的家庭分工中,女性常被賦予“服務者”和“照顧者”角色。這種角色要求她們隨時待命——衛生紙用完了要補、冰箱裡過期的食物要清理、孩子考試失利要溝通。即使沒有緊急事務,那種“需要把一切安排妥當”的責任感本身就是沉重的情緒負擔。失眠背後,往往隱藏著這些無處排解的情感反芻。

隱形的“情緒勞動”正在越來越被看見
而對許多承擔了這部分職責的人來說,回到家並不意味著休息。公司裡的工作結束了,家裡的工作卻沒有結束。“我怎麼能躺下?還有這麼多事情沒做。”在這樣的日常裡,他們潛意識會覺得,自己在道德上似乎是沒有權利休息的。
而生病、抑鬱、焦慮或是一些軀體化的症狀,反而成了獲取休息的間接出口。“我失眠”“我頭痛”總比“我需要休息”更容易被接受。
諮詢室裡,張春有時會建議一些失眠的來訪去醫院尋求醫生幫助,而這時會出現兩種截然不同的反應:一種是生怕醫生說自己有病,“精神病人”這個標籤可能意味著某種社會身份的失權;另一種卻是生怕醫生說自己沒病。當在醫生那裡確診時,後者反而鬆一口氣,“原來我是病了,那我現在應該能夠說服別人讓我休息了吧?”
這種現象恰恰反映了當代人所面臨的困境——似乎只有在“不能”工作時,才被允許不工作;只有在“生病”時,休息才成為被認可的選擇。

據2020年至今的臨床就診資料,全國臨床就診的抑鬱症、焦慮症患者中,有80%左右的共病是失眠
失眠早已不只是一種生理現象,它已被賦予了深刻的社會建構和意義。表面上我們在談論失眠,背後則是形形色色亟需被看見的需求。

最難說出口的一句話:
“我需要休息”

想要理直氣壯地表達“我需要休息”,為什麼這麼難?
Gap year也許算是最典型的案例之一。與西方側重體驗的Gap year不同,中國式Gap year往往有著明確的學習目標,比如考公、考研、考雅思。但實際上,很多年輕人看似在備考,背後卻是對休息的渴望。“說自己在備考,親戚才會停止追問‘為什麼沒工作’。”為了避免被貼上“躺平”標籤,年輕人需要為休息尋找合理化的藉口。
如此迂迴的方式,很難真正達到休息的目標,反而增加了內心的負擔。然而在我們的環境中,對於“我需要休息”,每個人都有太多正面表達時不被看見或接納的經驗,以至於需要另闢蹊徑。說得更直白一些——作為一個個體,“我的感覺”常常被界定為不重要的。
這聽起來有點悲傷,但深入習以為常的生活細節就會發現,現實中有著大量這樣的現象。
張春最近和母親久違地住在一起。有一天她問母親,“吃飯用的這些椅子,你喜歡哪一個?”因為母親的膝蓋有些傷病,張春想把母親最喜歡的椅子讓給她坐。結果母親說,“哪個都喜歡。”無論張春怎麼追問,母親始終不願表達自己的偏好。

當下的環境中,人們習慣了迴避自己的需要
最後,張春只好根據平時的觀察強行“讓”給母親一把椅子。她意識到,母親這代人,可能很長時間以來經歷的都是,說出自己的要求就會被冠以矯情和挑剔之名,以至於習慣了說“我什麼都可以”,就像我們常聽到的,“媽媽不累”“媽媽喜歡吃魚尾”。而這些被壓抑的需求,常常透過失眠等方式表現出來。
三聯記者魏倩走訪醫院時曾注意到,失眠門診裡擠滿了各個年齡層的女性,她們手裡攥著化驗單和藥袋,眼底泛著和黑眼圈一樣深的疲憊。失眠在醫學上有諸多解決方案,但在心理層面,它很容易變成新的自責源頭:我為什麼睡不著?我是不是太焦慮了?這樣下去會不會影響健康?
想要快速入睡的努力,變成了維持失眠的驅動力。於是,一個惡性迴圈形成了:睡不著→焦慮→更睡不著。這正是“與自己較勁”的典型表現——我們對失眠的焦慮與抵抗,反而成了失眠的幫兇。

對睡不好的焦慮,反而容易成為睡不好的原因
有趣的是,很多人反而在旅途中睡得很好。“在車上或飛機上,那麼不舒服的姿勢、那麼嘈雜的環境,人們卻能呼呼大睡。”張春推測,是因為旅行給了人一種“被允許”的自由——此刻我們允許自己放下責任,沒有事情需要掛念,這種心理狀態讓我們放下緊繃的神經,自然而然地進入夢鄉。
在關於睡眠障礙的詞雲分析中,有兩個有意思的高頻詞——“非得”“才能”。這種強制性的思維方式,是我們與自己較勁的核心。睡眠專家溫迪·特羅克賽爾(Wendy Troxel)指出,“我們的大腦必須感覺世界是安全的,才能入睡。”面對失眠,我們需要的不是更多的自我苛責,而是更多的允許,更多的接納——允許自己睡不著,接納自己獨特的節奏,反而是通往睡眠自由的必經之路。

來源:《2024情緒與健康睡眠白皮書》
2024年1月1日-1月31日,來自短影片、微博、微信、新聞、論壇等網際網路主流資訊渠道資料
常見的案例是,很多上班族熬夜,是因為工作太累,需要休息和娛樂,需要用熬夜贏回自己的空間。那麼,“睡不著就別睡,睡不著就起來玩。”當有一天這個人體驗夠了這樣用熬夜代償的狀態,就可以去分辨自己到底想幹什麼,自然會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
停止與自己較勁,溫柔地對待身體真實感受,尊重自己作為獨特個體的差異,是真正睡眠自由的開始。這一理念與ubras長期以來對女性的關注與呵護不謀而合。三年來,ubras不僅持續關注睡眠議題,更重視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的身體自主與舒適體驗。

真正的治癒
始於微小的改變

“變好不是一個按鈕按下去,魔力全開的過程,變好就是一丁點一丁點地變好。”張春說,“以區域性的改善來讓自己的生活多一點盼頭,也是值得的。”

用微小的改變,讓生活多一些盼頭
比如,睡不著時,你可以為自己找一個充分的失眠理由——無論是換季、水逆,還是因為你的祖先值夜班,你繼承了強韌的“守夜人基因”。也可以與地球另一端的朋友組成“失眠搭子”,讓曾經孤獨的夜晚變成另一種形式的相聚與交流。
當類似“打破睡眠節律會影響褪黑素分泌”等專家的發言讓你感到焦慮,你既可以取消該專家對你的權威性,也可以看看“躺著就是休息”等其他專家發言來對沖。挑一個喜歡的理論用在自己身上,而不是責怪自己。
對於那些被家庭和工作雙重壓力壓得喘不過氣的女性,張春建議,即便只是去家附近的酒店睡一晚,或是給自己開個鐘點房,也是一種修復。“哪怕只是二十四小時中的兩個小時是在酒店裡獨自度過的,那麼這一天就已經變好了,而這種變好是不會被抹去的。”

即便只是給自己開個鐘點房,對很多人來說也是一種修復
(《重啟人生》劇照)
改變,既可以從內在環境開始,也可以從最貼近我們的物理條件出發。尤其對女性而言,這種微小卻重要的變化,往往能帶來意想不到的改變。夜深人靜時,打敗睡眠的不只是萬千思緒,還有可能是深夜的窗外噪聲、身旁伴侶的翻身聲、寵物輕盈的跳躍,甚至是身上那件總往上卷的不合適的睡衣——這些看似微小的物理因素,常常成為良好睡眠的隱形阻礙。
為了提升自己的睡眠質量,許多成年人已發展出自己的“睡眠儀式”——一條蜷縮時剛好合適的毯子,一個可以抱在懷裡的抱枕,或者一件穿了多年的舊T恤。這些成年人版本的“阿貝貝”,給予我們童年時那種純粹的安全感。

成年人在“阿貝貝”中尋找安全感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小毯子’,”張春這樣形容,“那個能讓我們安心入睡的東西。對某些人來說,這可能是一種氣味,對另一些人來說,這可能是特定的觸感。關鍵不在於它有多高階,而在於它能否讓你的身體記起‘現在是安全的’這一資訊。”
我們與世界相觸的方式,決定了世界如何觸碰我們。在照顧情緒的同時,貼近肌膚的那層“第二皮膚”——睡衣的選擇,也成為影響睡眠的重要一環。ubras在睡眠領域的探索,正是基於這樣的理解。
透過持續研究女性睡眠需求,ubras將對女性舒適的理解轉化為實質性的產品體驗。研究表明,舒適睡眠的被窩溫度應保持在27-32℃之間,這正是深度睡眠的溫度敏感區。基於這一科學發現,她們的睡衣設計特別關注了女性睡眠過程中的溫度變化需求,並將睡眠舒適被拆解為輕、柔、透、彈、香、潤、防等關鍵要素——輕盈的質感讓人感覺不被束縛;柔軟的觸感像是“躺在雲端”;而特殊的織法則確保了睡姿變換時面料能自由伸縮,不會在翻身時纏繞身體。





滑動檢視更多
過去很多內衣設計強調“如何被看”,而ubras更關注“如何被感知”,以舒適與自由代替了傳統設計的束縛感。這些從“外在評價”到“內在感受”的價值轉變,正是一步步溫柔地找回身體自主權的過程。
ubras想傳達的,不僅是一件衣物的舒適,更是一種讓人安心自在的生活態度。新推出的呼呼睡衣正是這種理念的體現——每個人都有權利卸下情緒包袱,擁抱屬於自己的舒適與安寧。
這種對女性日常需求的深度理解,體現在ubras幾年來對睡眠的持續關注上。從療愈線下活動,到睡眠白皮書,再到影片播客……我們看到的不僅是一個品牌在講故事,更是一種對女性生活的深度理解與長期陪伴:選擇善意發聲,溫柔託舉,而非製造焦慮;選擇用產品帶來實質性的改變與修復,而非空洞的口號。
在當代人為睡不著而焦慮時,ubras看見了失眠背後隱藏的深層需求與困境。雖然一件呼呼睡衣無法直接解決失眠的問題,但真正的治癒往往始於微小的改變。當白天的面具被卸下,當世界的喧囂被關在門外,我們總該擁有一個柔軟的緩衝帶,讓自己在自我與外界之間找到更自在的平衡。一個更輕鬆看待失眠的視角,和一件更裸感舒適的家居服所承擔的,正是這樣的角色——它不承諾帶你去往夢鄉,但保證你在睡著或清醒的旅途中,感受到最具呼吸感的自洽與自由。
點選觀看影片
在這個輕柔的緩衝帶中,無論你是暢快地玩手機,和“失眠搭子”聊天,還是做任何你覺得有意思的事情,如張春所說,“我們這個世界的確變得更大了,不管是失眠、抑鬱還是焦慮,今天已經有了更多的選擇,能夠更好地、更多地照顧自己了——照顧自己這件事情,做得再多都沒錯。”
祝你今晚睡個好覺,睡不好也沒關係。
如果睡眠能夠給你帶來慰藉,那就安心沉入這一枕黑甜。如果今夜註定無眠,不妨理直氣壯起來玩兒。
畢竟,我們真正想要的,從來不只是“一夜好眠”,而是讓醒著的時光,同樣柔軟。

#說說睡不著時你最愛做的事#
策劃丨三聯.CREATIVE
編輯 作者 排版丨毛思雨
圖片來源丨ubras 視覺中國
出品人|李偉
監製|劉剛 宋彥
策劃|石書蘊 rolling 丸子 尹濟男
專案統籌|殷佳婷
商務製片|韋韋
藝人統籌|羅啟宏 邢宇 張鼎堃
導演|昌禾
製片|木籽
攝影|韓逸 魏佳煒
燈光師|劉歡
美術|陳楚儀
道具師|曉雨
妝發團隊|Freya-studio
錄音師|曹旭龍
剪輯師|昌禾 白勇剛
混音|肖玉倩
調色師|王宇浩
包裝|大蒜糖

*文章版權歸《三聯生活週刊》所有
歡迎轉發到朋友圈,轉載請聯絡後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