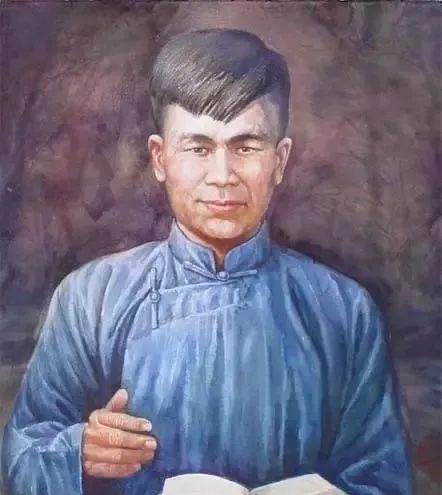問月生的開場白:
我最近關注到了“自我有罪建構”這個現象,引發了一些思考,並引出了一個問題,想聽一下真實的基督徒對這個問題的感受和想法。為了引出這個現象和這個問題,我先舉兩個真實的例子:
第一個例子:我高中時候的班長,考試總分數總是高我至少20至40分。我呢,數學和物理可以高他5至10分,但他的語文和英語碾壓我30至40分。後來發生了一些事情,我的老師,也包括我自己,會覺得我是在嫉妒他。
我當時認真琢磨了這個事情,好像真有。首先,“人皆有貪嗔痴”,人皆有嫉妒。其次,我只要一想到自己的數學和物理總是高他那麼幾分,就超開心,但視而不見我的語文和英文被碾壓的事實,還會自我辯解:“不就是因為……”第三,我問自己:“有沒有?”感覺了一下:“好像真的有!”於是,我內心就篤定了,真的看到了自己的嫉妒。之後,年輕的我就開始調整自己的心態,畢竟嫉妒不好嘛;並且與自己和解,畢竟“嫉妒也是人之常情”,只要不過分。
上面的回憶,我的表述帶著現在的痕跡,但記憶中的感受非常清晰。因為在當時,我對於這個事情是比較敏感的:我不喜歡自己不好,不喜歡自己真的那樣。
回到現在,我重新回顧這個事情,心裡卻非常清楚:我完全沒有嫉妒,反倒是,我很喜歡他。他就是一種“老好人”的性格,對我還噓寒問暖的。有一次他還專門告訴我:“你不要那麼貪玩,你數學和物理那麼好,肯定比我聰明,如果下點死功夫,語文和英文肯定上來。”這人真的非常好的性格。所以,我壓根沒有嫉妒的心思。這件事其實很簡單:數學和物理考得好,我當然開心,這很正常啊!我就這兩個拿得出手的東西,當然會開心。這個事情,當我回顧清楚之後,心裡通泰得很。
第二個例子:這是昨天我在琢磨問題,突然內心冒出來了這個事情:我長期“瓜田李下”。這是我高中語文班主任告訴我的,即:人不要在瓜地繫鞋帶、李子樹下整衣冠,別讓人誤解你要偷東西、做壞事。我當時對這位班主任很有敬意甚至有點“崇拜”,他是一個學問高、非常儒雅的老師。我就記了一輩子這個做人原則,基本上都刻在骨子裡面了。很多時候,我都會不自覺地“瓜田李下”,就是本能地會注意。
昨天下午,我突然發現:這個事情,很多時候隱含了一種“自我有罪建構”。至少其中一種情況會如此。
例如,當我擔心別人會懷疑我會做什麼不好的事情時,我會順著別人的擔憂目光去感受自己。於是,我有時會發現自己還真的有那個心思。我小時候真的偷過四次東西:在菜市場偷過一顆糖,偷過家裡一毛錢,還偷過兩次郵票。前兩次被逮著罵慘了,一直罵到我哭哭啼啼地自己放回去。所以有時我會懷疑自己有想偷的心思。然後,在“瓜田李下”的狀態中,我有時就會發現自己好像真的有想偷的心思。
你擔心自己有什麼不好的心思,然後你去預防,結果你發現你好像真的有那個心思。你試圖證明自己不是什麼,但結果“證明”了自己就是什麼。
這兩個例子,我都是想呈現這麼一種現象。我少年時代,如果我的記憶沒出錯,當時的我實際上做了一個“自我有罪建構”:本來沒嫉妒心思,結果自己建構成了有嫉妒心思。在某些“瓜田李下”的情況中,我實際上也對自己做了一個“自我有罪建構”:本來沒有偷東西的心思,結果自己建構成了有偷東西的心思。
在這兩種情況中,如果換一個場景,很可能我真的會有不好的心思。例如第一個例子,如果不是那個“老好人”,而是換一個人,我就可能真的會嫉妒。例如某些“瓜田李下”的情況,我也可能真的會有偷的心思。問題在於,這兩種場景從表現上看是一樣的,而我的內心其實也有這種可能性——但具體是不是,則需要具體情況具體去看,沒法一概而論。
於是,結合這種現象,再設想另一種“生成現象”。例如,昨天我確實沒有嫉妒,但今天我真的嫉妒了——假設這裡沒有建構,就是自然而然的、不知怎麼的就自己長出來了。所以,可以區分三種“是不是有某種心思”的存在情況:
(1)“存在”(be):確實有。
(2)“生成”(become):過去沒有,但現在有了。
(3)“建構”(constitute):本來沒有,但被建構成了有了(尤其是:試圖證明自己不是,卻證實了自己是)。
我據此進行反思,得出的結論是:
(1)人不要給自己做“有罪建構”或“罪感建構”,尤其“瓜田李下”的那種“試圖證明自己不是,卻證實了自己是”的有罪建構。
(2)人對自己不要預持負面評價(包括可能擔憂的他人評價)。
(3)但人不是聖人,所以,在不預持負面評價自己的前提下,後續發現了自己的負面東西(例如惡、壞、錯等)。這個發現或者是本來就有,或者是後來長出來的。然後,發現一個改一個。
(4)“存在”情況和“生成”情況都不挑戰主體,不會對主體形成異化壓力,都只是主體正常的情況,只需正常地去面對、應對即可。
(5)但“建構”情況直接挑戰了主體,對主體本身是一種壓制,具有異化的朝向。
我就開始想到:基督教式的原罪,即人皆有“罪感”,但這個事情與我對人“不要預持自己有罪、不要預持罪感”形成張力。人預持自己有罪、罪感,豈不是對主體形成了異化壓力,形成了預持壓制?於是我發問:如何協調“基督教式的罪感”與“預持無罪、無罪感意義上的自得生活”?我也對帶著基督教式罪感的生活很好奇,這究竟是一種什麼感受?在我自己想象中,這種生活會讓人感覺有壓力。但看到那些基督徒非常陽光,這是怎麼回事呢?
有了疑問,我就想找我身邊真實的基督徒問這個問題。
約翰的發言:
我的基督教信仰,不光是個人的經歷和體驗,更重要的是聖經文字。所以,我會對應一些經文來回復。
首先,對於第一種情況——“我確實嫉妒了、自己也覺察到了”。這個我想到《羅馬書》第一章18節開始的一段經文,那裡講到人的罪。保羅在此區分了猶太人和外邦人(非猶太人)。對於當時的猶太人來說,一個人有沒有罪,是透過舊約聖經、透過律法:違背了上帝的律法就是有罪。例如,嫉妒,就是違背了“摩西十誡”中的第十誡:“不可貪戀人的房屋,也不可貪戀人的妻子、僕婢、牛驢,並他一切所有的。”
猶太人有舊約聖經(律法),所以,當他們犯了罪,對照聖經中上帝的律法,就知道自己犯了罪。但外邦人,沒有讀過聖經,沒學過“十誡”,怎麼知道自己有罪呢?《羅馬書》第二章14—15節說:“沒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順著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們雖然沒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這是顯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們心裡,他們是非之心同作見證,並且他們的思念互相較量,或以為是,或以為非。”也就是說,外邦人也能知道自己的罪,就是透過他本性中的“律法”,就是刻在自己心裡的道德律,即是非之心,就是我們說的良心。
例如嫉妒,我們不需要學習、討論,不用學習“十誡”,心裡面就像刻著律法一樣,知道嫉妒是不對的。我們有某種內心的善惡標準。就好比在日常生活中,你知道行事為人應該這樣、不應該那樣。有這樣善惡標準在,我們才能評判自己和別人。這個標準對我們來說就像人所共知的法則一樣。絕對不只是我以為如此,而是大家都應該如此才對。
第二種情況,就是生成、發展出來的罪行,可以提出這麼一種問題:如何解釋這個世界當中的人(包括我們自己)會有那麼多作惡的情況呢?世上為什麼會有那麼多惡行呢?比如一個小孩子天真可愛,長大後怎麼會做出那麼邪惡的事情呢?或一個老實巴交的人,結果發現他那麼邪惡。或者一個表面上人畜無害的人,最後變成那樣,等等。
聖經的回答是:不是說人原本良善,然後因為莫名其妙的原因變壞了,而是說人的本性就是惡的,只是後來流露出來了,就表現為惡行。人的惡行是從惡的本性中生髮出來的。我們一開始可能還看不出來,但放在某種環境中,它就展現出來了。
舉兩個例子:第一個,我們總說貪官多麼邪惡貪婪,但如果把我們自己放到他們所處的地位和環境中——擁有不受約束的權力,身邊又有那麼多誘惑——我們很可能會跟那些貪官一樣墮落。第二個,如果對於一個小孩子,我們無條件地滿足他的一切欲求,那麼,這個天真可愛的孩子長大後會成為一個非常可怕的人。於是,教育的一個首要特徵,就是要抑制小孩子那些不正當的欲求。例如,教育小孩子,不要光顧自己吃好吃的,還要考慮弟弟妹妹,要考慮別人的益處。如果沒有給小孩子施加這種約束,他們長大後肯定非常自私任性。
這裡的主要觀點是:人生而有罪性,所以才會有罪行。不是說,人因為犯罪,所以成為罪人;而是說,人因為本身就是罪人,所以才會犯罪。
第三種情況,就是關於“有罪建構”這一點,它會涉及到我們和他人的關係。這裡,罪不光是一個自我的問題,它是在跟其他主體或者你所處環境的關係當中來呈現的。比如說,對方說你有罪,然後你去想自己有沒有罪——這裡就有一種影響與被影響的關係。
從關係的角度來說,聖經對罪的定義和我們一般的認識不太一樣。聖經認為,罪不是一個只關乎個體自我的問題,比如說我做了一件不好的事情,我產生了某種內疚或者一種罪惡感。不只是這個層面,而是說:人的罪根本是在關係中出了問題。這個關係,首先不是我們與他人之間的關係(這種關係是派生性的),而首先是人跟神的關係(這種關係是根本性的)。
比如,《馬可福音》第二章,耶穌赦免了一個癱子的罪。對耶穌那個時代的猶太人來說,一個人有殘疾(天生瞎眼之類的),肯定跟他的罪有關係。有人會認為這跟他個人的罪有關,有人可能認為人類普遍的墮落或罪性導致他們會經歷災難、疾病、死亡等等。現代人如果聽到耶穌對癱子說“小子,你的罪赦了”,可能會覺得耶穌心腸挺好,因為他赦免這個癱子的罪。但對於耶穌同時代的人來說,這是一個非常大逆不道的話。為什麼呢?因為,“除了神以外,誰能赦免人的罪呢?”
猶太人有個共識,一個人犯罪就是得罪了神,也就是說,他在跟神的關係當中做了不合乎神心意的事情,即反叛神、冒犯神、得罪神的事情,這叫犯罪。所以,你怎麼才能得到赦免呢?就是你得罪的這一位,他說要赦免你,你才能得到赦免。比如說,問月生得罪了我,然後旁邊一個人走過來對問月生說“我赦免你”。這話其實這毫無意義,因為問月生得罪的是我,只有我才可以對他說“我赦免你”或者“我饒恕你”。
所以,當耶穌對癱子說“你的罪赦了”,他周圍的人就立刻意識到,耶穌其實在宣稱他具有神一樣的地位。所以,對他們來說這絕對無法接受。最終耶穌是透過行神蹟的方式來證明他有赦罪的權柄,即他具有神性的身份。當然,這是後話。
不管怎麼樣,這裡很清楚的一點是:罪是在關係中呈現的。“十誡”就體現了什麼是合乎神心意的事,以及什麼是違背神心意、得罪神的事。例如殺人。為什麼殺人是罪呢?《創世記》給出了一個非常明確的理由,“因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這也就意味著:當一個人要剝奪另一個人的生命,其實是在破壞神的創造。所以說這其實是構成了一個罪。這不僅僅是從人與人的關係來講,而是從神的創造這個角度來講。
聖經當中,除了“十誡”,還有很多具體的律法誡命。這些律法,如果用一句話來總結,它的精髓是什麼呢?耶穌給出一個經典的總結,甚至他的敵人都說他總結得很好。就是:“你要盡心、盡意、盡力愛主你的神,其次是愛人如己,即愛別人如同愛你自己。”他說,這是律法的總綱。就是說,如果你完完全全按照這個標準去生活,你才是沒有罪的——只要能活出這樣的生命。或者說,如果你違背了這個標準,沒有做到它所要求的,那你其實就是罪人。律法的總綱主要有兩點:一個是愛神,一個是愛人如己。你會發現,第一點關乎最根本的問題,即人和神的關係,其次關乎的是人和人的關係。當然人和人的關係,也是建立在人和神關係的基礎上的。
人和神的關係,是縱向的關係;人跟人的關係,是橫向的關係。當我破壞了自己跟別人的關係,出現了傷害別人的問題,其實我也破壞了自己跟神的關係。就像我去殺人的時候,這個其實已經是得罪神了。
“十誡”有非常詳細的解釋,不單單說“不可殺人”——這是用非常簡略的方式表達出來的。耶穌解釋得非常清楚:如果一個人心裡面去怨恨別人的話,其實在神的眼中已經算是在心裡殺人了。比如說我看見女性心裡動淫念,雖然我沒有實際地犯奸淫,但是我已經在心裡犯了姦淫。嫉妒別人或者類似的罪,其實都是如此。
在這個意義上,如果按照聖經的這樣一種說法,它所揭示的情況,我覺得聖經沒有提到第三種層面(就是那種“有罪建構”的情況)。因為,聖經從一開始就在人跟神的關係當中來談論罪的問題。
即使你沒有讀過聖經,你也不可能否認神的存在。甚至你否認神的存在,你也無法否認,你會有內疚或者罪疚感。你也知道你有些事情沒做好、沒做對。然後聖經就會給你揭示:正因為你跟神的關係出了問題,所以罪惡的問題才會展現出來。在你實際的生命當中,你知道自己很多時候沒有按照自己所知道的那樣去行善,很多時候你也經歷行善失敗的情況,而且哪怕你很努力地想去改變自己,讓自己變成一個好人,但是你也會經常經歷非常多的失敗。可能你在某個時候會好一些,但是很快又會陷入失敗。
就比如,我知道刷手機不好,浪費時間,但是這個好像不是說我願意改就能改掉的。比如,對一個酒鬼來說,他可能知道酗酒不好,但他還是抑制不住自己。或者說對一個家暴男來說,他知道打老婆不好,他可能打了老婆之後,還跪在老婆面前痛哭流涕,但是他還是一次又一次地會打。
我們總是能見到這樣一種無可救藥的情況出現,所以說,其實聖經首先揭示:人的問題,遠遠超過我們所能感受到的程度。就像你去醫院看病,你去的時候只是感覺到自己胃疼,但是醫生會揭示:因為你得了胃癌,所以你會胃疼。當然這個時候,如果醫生給你開止疼藥,對你來說沒有任何幫助,只會掩蓋你的病情。那真正的方法是什麼?你需要立刻做大手術,你需要最好的醫生從根源上解決病根的問題。
所以說,人能感受到的是症狀,但其實最重要的是病根的問題。聖經首先是把這個病根揭示出來。人能夠意識到自己生命當中各樣的問題:人會作惡,人會有內疚和自責……而聖經把病根揭示出來了:人從生命的源頭上(或者人的本性上)就已經是有罪的或者是敗壞的了。
耶穌甚至用了一種方式,說人的心就像一個不斷湧出水的源泉。我們總覺得:雖然我可能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但我內心深處是個好人,或者說我內心深處是一個良善的人。但在耶穌那裡,他所揭示的恰恰相反。他說人的內心就像一個源泉,這個源泉本身已經被汙染了,因此只會不斷地湧出汙穢的水。你沒法透過“回到我內心的源頭”來解決這個問題,因為你本身恰恰是問題所在。
所以,人所需要的絕對不僅僅是某種外在的改良或改善,或者怎樣修身養性的問題。人最根本的問題是他這種罪的本性需要被扭轉,他的罪惡本質需要被改變。這個問題最終是透過“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來為我們贖罪,並從死裡復活為我們勝過罪和死亡”這樣一個拯救行動來解決。並且神也透過聖靈來實際地重生我們,即賜給我們一個全新的生命。最後,我們會復活得著一個永不犯罪、永不朽壞的新身體。
你會發現,即使已經接受耶穌的人,他在今生仍然會受到殘存的舊生命的影響。雖然他信耶穌之後生命經歷了很大改變,但是他仍然會時不時地犯罪,也會有軟弱犯罪的時候。但他裡面已經開始了一個新的生命、新的源頭,他存在的本質發生了改變。所以基督徒在今生活著,他裡面有非常大的張力和衝突。一方面,他裡頭的新生命讓他願意活一種良善的生命,他也實際能夠活出來;但是,他裡面還殘存著舊的生命,不斷地把他往下拉。
不過,因為耶穌基督已經死了,並且復活了,最終我們也要像他那樣復活,我們會獲得一個不再會犯罪的新身體,不再有死亡,不再有疾病,也不再有任何的貪念或罪行,不再有罪性。我們最終會帶著新的身體在新天新地中與神永遠的同在。
還是強調兩點:一、聖經揭示,我們的問題比我們所感受到的更嚴重;二、上帝對於這個非常嚴重的問題,他的解決方式也是最徹底的。他不是說只是外表上改良一個人,而是說他從內在更新你,給你一個全新的生命,最終給你一個全新身體,全新的存在狀態。所以,聖經是這樣揭示人有罪的問題,還有怎麼解決罪的問題。
再回到剛才提出的問題,就是:“基督教的原罪意識或原罪體驗下,一個人如何既持守住自己面對上帝的原罪體驗,又持守住自己在人世間不預先假設有罪,不預先假設自己有隱藏的、自己都看不到的惡意內心?”
這個問題也挺犀利,讓我想到馬丁·路德非常重要的一句話,就是基督徒“既是完全的罪人,又是完全的義人”。這句話表面上挺矛盾,既是完全的罪人,怎麼同時又是完全的義人?其實,按照我們的本相來說,或者說按照聖經所揭示的我們真實的樣子來說,我們確確實實是完全的罪人,我們從根本上就是有罪的,是敗壞的,我們裡面只能不斷地湧出各種各樣的惡,我們確實是完全的罪人。
但是,另一方面我們是完全的義人,因為什麼呢?因為神透過耶穌基督,他在十字架完完全全贖清了我們一切的罪,並且把赦罪的恩典、無罪的身份,賜給了我們。聖經當中也特別提到四個字,宗教改革的時候也強調這四個字,就是:因信稱義。就是當我單單憑著信心領受了耶穌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贖罪大工,神就會因著耶穌的緣故,算我是無罪的,因為我的罪債耶穌已經替我還上了,而且他也實際地代替我這個罪人承受了我犯罪該受的審判和刑罰。我犯罪該付的代價他都替我還上了,我欠的罪債他都替我還清了。
所以,當一個人憑著信心來到神面前,接受了耶穌基督贖罪的工作,那麼他的罪債就在上帝的法庭上完全清償了。這個時候,他就獲得了一個新的身份,一個稱義的身份。“稱義”什麼意思?就是在上帝的法庭上被宣告為無罪,我們被宣告為是正當的。
人最根本的問題在於,我們作為上帝的創造,我們在神面前是不正當的。為什麼?因為我們沒有按照創造我們的上帝的心意來生活,反而是按照不合乎他心意的方式來生活。所以,在這位上帝面前,我們是不正當、不合法的存在。但是,耶穌的救贖使得我能夠被賦予正當性。
這種正當性不是因為我改變自己的生命、把我自己生活改變得很好了才獲得的,而是說耶穌以他的贖罪工作來賦予我正當性,他還清了我的罪債,他改變了我犯罪的本性。但是,如果沒有耶穌的拯救工作,人會傾向於透過自己的某種努力來尋找正當性,或者是回到自己的本心去修身養性,或者去不斷地提升自己,或者透過理性反思、宗教虔敬、道德善行——人會透過這些方式來獲得自己存在的正當性,去消弭他心中的罪惡感。
但是,即便人做了這麼多的善事,仍然有一個問題,就是:“我做到什麼程度才夠呢?”比如說我傷害了一個人,說了一句傷人的話,要知道一句惡毒的話給人帶來的傷害可能會持續幾十年,可能讓他一輩子都深受其害。我曾經說過這樣傷人的話,很多年之後對方還仍然很難受、難以釋懷。你說我該怎麼彌補呢?那種傷害已經造成了,況且,這還只是從人的層面來講。如果是在跟上帝這個層面來說,那更是無法挽回,是我根本無法彌補的事情。即便在我自己內心,也時常為此感受到不安。因此,這條路即便在主觀上(就是人的感受當中),也沒法成立。
第二種就是,在於客觀上(就是在上帝的法庭上)也沒法成立。因為最終我來到上帝的法庭上,我不能說:“上帝,我做了10件壞事,但我做了100件好事,我這100件好事減去我這10件壞事,我還有90件好事——憑著這個,我有正當性,我是一個義人。”不是的,因為在上帝的法庭上,就像我們在人間的法庭上一樣,我不是因為自己做了多少善事接受審判,而是因為我做了惡事接受審判。一個人可能一輩子做了很多善事,但是他一輩子就偷了一次東西,他在法庭上就要被認定是小偷,他就要接受法律的懲處。
所以,就像一個殺人犯說“我建了很多座希望小學,我做了很多善事”,法官不會因此就不去審判他、無罪釋放他。他還是要接受審判和刑罰。所以,在我們自己裡面,我們沒有解決罪的根本問題的能力,也沒有任何出路。
但是,好訊息是什麼呢?就是神為我們預備了一條出路,而且這條出路是神完完全全地成就,現在白白地歸算給我們、賜給我們,就像一件禮物一樣送給我們。凡是願意接受的,就能得著。所以,如果有人真的接受了這個赦罪的禮物,他就會在上帝的恩典當中,獲得了這樣一種正當性,他也能實際地面對自己的罪疚。
基督徒在接受赦罪的恩典之後,他也會犯罪。但是在聖經當中,在《約翰一書》當中,提到:“若有人犯罪,在父那裡我們有一位中保,就是那義者耶穌基督,他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不單是為我們的罪,也是為普天下人的罪。”所以說,如果一個基督徒犯罪了,他在上帝面前承認自己的罪,即悔改,神就會赦免他的罪。這對基督徒來說是成立的,為什麼呢?因為耶穌已經為我們獻上了挽回祭。這樣的話,我們在神面前認罪的時候,神就會因耶穌的緣故,公正地赦免我們的罪。對於那些已經信靠耶穌的人,這是有效的,因為他已經接受了這個赦罪的禮物。
但如果說一個人沒有信靠耶穌的時候,即便他來到神面前認罪懺悔,也不會帶來赦罪。為什麼呢?就像一個罪犯,比如說他欠了1000萬,他還不起這個錢。他來到法庭上,跟法官痛哭流涕地認罪悔改,說“我許諾再也不欠錢了”,或者“我發誓要做個好人”,但是他的債務還在,法官仍不會宣判他無罪。但如果另一個人走進法庭,替他還上這1000萬。那麼,這種情況下,法官就可以公正合法地赦免他。即便他欠了這個債,他還是能夠獲得釋放。
所以,基督徒在面對自己罪疚問題的時候,就可以及時地來到神面前認罪,然後他也知道神必定會在耶穌基督裡赦免他的罪,因為正是神差遣耶穌來替我們贖罪。所以,這對於接受耶穌的人來說,就有這樣一種平安——良心的平安。所以,他就能夠在自己最敗壞的時候,因為神的拯救,他如今在神眼中是完全的義人。他擁有了這樣一個正當的地位。
約翰的分享回答了我好奇的那部分內容。因為我基於自己的一些思考,確實我的預持是:我不想持有罪感,對我來說,這樣才是愉快的。所以我就不理解基督徒的罪感,他怎麼能愉快呢?
我現在就理解了,基督徒的那種罪性是他底層的東西,所以他預持他有罪,就是有罪的那種底色。然後在這種底色下,他生活,就是一個預持有罪的狀態。這是很清晰的,都不一定是“我面對上帝我才有罪”,我面對任何人都有罪。面對這個生活世界,我生活,都有罪。體會到這個,我就清楚了:確實是帶著罪感或者是罪性在生活。哪怕我感覺不到,我也知道其實自己骨子裡是有罪的。
那麼這樣的話,我怎麼能夠在我的生活中“開開心心”呢?我又沒有真的犯錯,那為什麼自認“我有罪”的那種生活有一種無罪的自得感,兩者怎麼協調呢?約翰有一個很重要的分享,就是那個“完全的罪人和完全的義人”的協調。這就讓我有點兒體會到了他在一種罪與無罪中存在是協調的,完全沒有矛盾感。我覺得讓我看到了、體驗到了那個我之前好奇的東西。
然後就涉及到我分享的那三種存在方式。基於我最關鍵的一個觀察,在基督教的體驗裡,我就感覺到罪性很底層:有時候你感覺到有罪,有時候你甚至感覺不到有罪,但罪還是在那裡。它不會從無到有。所以在約翰的分享中,就沒有這個“從無到有”(生成)的事兒。
但是有一個地方,讓我發現:就是在舊身體換新身體的那種轉變中,不管是救贖還是因信稱義,其實也有一點從無到有的成分。但你只說罪性的話,它還是人裡面的東西;但當我們設想那種最終的拯救,人變成一個永恆完美的存在,那個時候他的罪性就徹底不在了。在約翰的分享裡面,通常的那種變化——像小孩子天真爛漫,長大之後變成一個可怕的人——這個不算生成(become),而只是罪性的顯露。但在最終的拯救那裡,是有一點生成的意味的。
還有一種情況:假如一個普通的基督徒,他裝作很虔誠。他知道人有罪性,他感覺到了;但是他在生活中也不是啥事都壞,他有些事情就真做得挺好。但是他就好像要讓自己體驗為“哪哪都有罪”。他就每件事情都讓自己體驗為“我是帶著罪性在做的”。他幫別人在路上撿了一隻掉了的筆,他沒有什麼罪,結果他馬上說“我是帶著罪性做”。這個時候他對自己就有一種虛假的建構。
我會問:對一個基督徒,如果這種虛假建構的內心感受存在的話,其實這是一種異化。因為他把自己往那種虛假的方向去壓,去鼓著自己裝成那個樣子。結果他裝成功了,搞得別人都以為他是世界上最牛的教徒,他也覺得自己是。但其實這是假的,和另外一個真正的聖人是兩碼事兒。他必須誠實。
對比一下我自己。我確實不是基督徒,我把生活的預持本身看得很重要。所以,我的那三種存在方式就真的很基礎。比如說,我本來沒有邪惡的內心,真沒有,我就是這樣傻呵呵的,但是別人告訴我那個是罪,我就真覺得自己有罪。就像我分享的那兩個例子(嫉妒和瓜田李下),其實也是一種虛假的建構。
從基督徒視角來說,我的生活其實是一種敗壞;但我卻會滿足,我很滿足。甚至會出現:別人說的十惡不赦的大罪,我就覺得沒罪。從約翰的視角,我就真的是個敗壞者,我都能感覺到那種敗壞者的感受了,但換我自己,我沒覺得我是敗壞者,反而還活得特真誠。
約翰的發言:
我回應一下剛才問月生舉的一個例子。就是那個冒充的聖徒。就是一個人覺得自己做的所有事情都是有罪的,努力去做一個更好的人,但是實際上他內心認為自己所做的所有事情都是有罪的。其實,我們能夠從現實當中找到這樣的例子,恰恰就是你說的這種情況。
但我對這種現象的理解不太一樣。這個例子就是我之前發言引用的馬丁·路德,他說“基督徒既是完全的義人又是完全的罪人”。為什麼他能說出這樣的話呢?是因為他自己從歸信之前到他歸信之後,有一個非常大的、非常戲劇化的轉變。
在他歸信之前,他大概是個什麼樣子的人呢?他原來是奧古斯丁修會的一名修士。他日常生活當中會定期去懺悔。就是為你過去犯的一些罪,找修道院院長去告解——就是一條條說你犯了哪些罪。一般來說,你想,修道院當中沒有那種很複雜的人際關係,你能犯多少罪?頂多也就是“我看到旁邊那個弟兄他的盤子裡面的菜比我多,我嫉妒了一下”。頂多就是這種事情,反正不會有太多的罪。
但是路德就特別奇怪,他在修道院的時候,曾經用六個小時來認自己過去24小時所犯的罪。他用六個小時的時間,以至於聽他告解的修道院院長都不耐煩了,他就對路德說:“你哪怕犯一個真正的罪來跟我告解,你說的那些事都是微不足道的事,然後你就說這是罪,然後你就在那裡難受得不行。”還有的時候,他花了兩個小時跟修道院院長認完罪,然後那個修道院院長按照聖經所要求的,對他說:“路德弟兄,神已經赦免了你的這些罪。”然後路德就開開心心地走了。但沒過多久,他突然想到自己還有一個罪忘了認,然後他就立刻變得愁眉苦臉,然後又灰頭喪氣地回去。
那個時候路德還沒有明白因信稱義,他也沒有真正體驗到上帝的拯救。那個時候,他就是這樣的一種狀態。當然這種狀態有個人的特殊性。在我自己的觀察中,我發現:人與人之間,良心的敏感程度是不太一樣的。同一件事情,可能對一個良心比較敏感的人來說,他會覺得特別內疚,內疚到他都睡不好覺。我真遇到過這樣的人,就是我們覺得無關緊要的事情,他就是過不去,他會特別糾結、特別自責。路德就屬於這種良心特別敏感的人,甚至到了病態的程度。
路德之所以如此,還有一個原因:他是學法律出身的,在去修道院之前,他原本是法學專業的學生。因此,他會帶著法學的訓練去讀聖經,因為聖經當中有很多神的律法——這關於什麼是合乎神心意的、什麼是不合乎神心意的。所以,當他以非常敏銳的法學訓練去讀聖經的時候,他對於罪的意識反而增強了。他這種對於罪的意識,或者說這種良心上的敏感,就導致他的那種情況——用六個小時去認過去24小時犯的罪。一般來說,我們一個星期犯的罪,可能五分鐘就認完了,但是他就特別誇張。結果他一直陷在深重的罪疚感當中出不來。其實,他在修道院當中是一位非常出色的修士。在宗教修行的各個方面,他都是出類拔萃的。
但是,如果讓晚期的路德看待他早期的這段經歷,他會覺得那其實不是一個基督徒該有的樣子。因為一個基督徒真正的樣子是:因為他知道不是靠著自己的虔誠,或者靠著自己認罪認得多徹底,而蒙神悅納,而是說神已經赦免他的罪,他就被算為完全的義人,即他已經被神賜予這樣一個稱義的地位,他在這當中去看待他自己,看待他自己的罪。
但是不可否認的是,罪的問題是基督徒信仰經歷的起點。就是說,基督教信仰開始於人意識到自己罪孽深重。這在聖經當中也能找到根據,甚至他們對於罪的認識已經到了本性的層面,大衛甚至說“我母親懷我的時候,我就有了罪”。我們論到原罪,一般就會講到這個層面。不是簡簡單單說我有具體罪行的問題,而是說我有與生俱來的罪性,就是原罪。
我們可能會覺得路德過於敏感,甚至到一種病態的地步。但是,就聖經來說,即便一個像路德這樣的基督徒,他對於罪這麼深刻的體會或感受,也與他實際的罪的嚴重程度,仍然是不匹配的。就是說,他實際的罪的嚴重性,也遠遠超出他所能感受到的那個程度。但是,上帝沒有讓我們以罪本來的程度去體驗它,這對我們來說是出於一種憐憫、寬容或忍耐。因為如果他真讓我們體驗到罪的真實程度的話,那麼人在這種重壓之下會被立刻壓垮、精神崩潰的。
我舉一個聖經裡的例子,就是先知以賽亞的蒙召經歷。先知以賽亞在一個異象中看到了神的寶座,他還沒有看到神本身,他看到神的寶座。又看到四周有天使在飛舞,每個天使有六個翅膀,兩個翅膀遮臉,兩個翅膀遮腳,然後兩個翅膀飛翔。那些天使都在高聲呼喊:“聖哉!聖哉!聖哉!萬軍之耶和華,他的榮光遍滿全地!”重要的事情說三遍,這是用一種重複的方式來強調上帝的神聖。
當以賽亞看到神顯現的時候,他的反應不像我們以為那樣——一個人如果看到神,他應該會很高興吧:“我終於見到神了,太好了!”不是,以賽亞的反應是一種極度的懼怕和驚恐。他說:“禍哉!我滅亡了!因為我是嘴唇不潔的人,我又住在嘴唇不潔的民中,又因為我眼見萬君之耶和華!”就是說一個汙穢的罪人,如果見到完全聖潔的神,這是一個非常可怕的事情。因為神沒法與汙穢的罪人相共存,他的榮光就會把汙穢的罪人消滅掉。以賽亞非常驚恐,他所表現出來就像一個精神崩潰之人的狀態。在上帝的榮光之中,他的罪被顯出來,可能也不是完完全全顯出來,但是顯出那個程度,就已經把他壓垮了。
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來說,即便是像路德那樣對罪的感受非常深、甚至到一種極端的程度,仍然不是對於他罪的真實程度的感受,他仍然只是部分地感受到了罪的實際嚴重程度。所以說,在聖經當中罪是一個非常根本的問題。如果罪的問題沒有得到確立的話,耶穌基督的救贖,他的贖罪工作、他上十字架、他的死和復活,這些都沒有意義。我們就會傾向於把耶穌理解成一個道德教師,就像孔子那樣,或者像雷鋒那樣,我們就會說“學習耶穌好榜樣”。我們就會學習像耶穌那樣做一個好人。
但是那完全不是聖經的意思。聖經就是在讓我們看到自己的罪如此深重的前提下,來告訴我們一個好訊息,即神要透過耶穌來解決這個嚴重的罪的問題。神要透過他的兒子耶穌來解決這個問題,而且確實已經解決了、已經還清了、已經勝過了。然後呢,他要把這個已經成就的福分白白地賜給我們。所以,對於一個合神心意的基督徒來說,他對罪的認識肯定是非常深的。因為只有對罪的認識非常深,他對神的恩典、神的愛的認識才能足夠深。否則的話,就是一種廉價的恩典。就好像我本來是一個挺不錯的人,然後信了神之後,他讓我的生活錦上添花了。但是那個絕對不是聖經裡的敘事,也不是真正的基督徒的體驗。
在基督徒的體驗中,我原來是在地獄的最深處,但現在我是在天堂的最高處。會有這樣一種反差。你可以看每個基督徒的歸信見證,都會有“從最低處到最高處”這樣一種經歷。
巴蒂斯新的發言:
以前我對於儒家的一些理念還是比較服膺的,我從小到大覺得自己應該是可以做一個比較正派(decent)的人。然後在好幾年前,因為有一段人際關係可能處理得不是很好(但那時候處在那個階段也沒有覺得不好,後面的結果就是不太好)。所以,當時給我造成了一些心理上的衝擊吧,就是有一些很負面的情緒。然後我有一段時間就會覺得有一些罪感。
既然有了罪感,我就想著基督教講到原罪的問題,然後我涉獵了一些基督教哲學的書,例如奧古斯丁的《懺悔錄》。那時候特別喜歡看《懺悔錄》,覺得它好像在說我自己當時的那種感覺。那種文學性的表達或哲學性的思考幫助了那個階段的我,使我的心靈達到了一種相對自洽的程度。那件事情過去很久之後,那種比較負面的情緒淡化了,我就逐漸走出來了,就沒再去看那些基督教的書了。到了今天,我看到這個話題,就覺得可以參與一下,也許可以幫助我回顧一下幾年前自己的那種狀態吧。
我提一個問題給約翰。其實我關於基督教也沒什麼特別好的觀點,就是有些疑問。因為我自身不是一個宗教徒,我並沒有什麼宗教信仰。但是我們今天講到“異化”這個話題,所以我想就“異化”問一個問題,就是:我們說到罪感或者說原罪,其實我們的現實生活中並不是每時每刻都有這種罪感。就我們這種沒有宗教信仰的人來說,我們有時候也挺快樂、挺輕鬆的。就是偶爾做了某些錯事或是傷害了某些人,或者傷到自己的時候,可能會有罪感。我只能就著我自己的生活感受來聊一下。
所以約翰剛才講到那個原罪,即便很多出色的宗教哲學家,他可能自身也沒辦法在生活感受中真正達到那種完全體會原罪的狀態。所以我就在想,如何跨越我們生存的感受與理論之間這道鴻溝,達到因信稱義這樣一種信仰?這對我這個沒有宗教信仰的人來說可能是一個問題。因為理論最高的程度,或者說宗教教義最高的程度,可能是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沒辦法完完全全感受得到的。
但是正如我剛才所講,就是我之前的那段經歷,讓我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產生了罪感。所以我當時就在尋找一些基督教的書籍去看,我覺得它好像可以解釋我當時的某些狀態。就是我做了什麼錯事,或者是說我犯了一些無心之過,然後產生了一些罪感。但是經過了一段時間,慢慢的調整過來了,我感覺我生活中還是有蠻多陽光的,我也可以做一些善事,或者做一些於人於己都有好處的事情。那個時候,這種罪感已經慢慢淡化了,就這種深層感受又把我從那種原罪的定義拉開了一段距離。
就從我這段經歷來看,我很難從自己的生活感受中真正跨越那道鴻溝、到達信仰的程度。所以我在想,真正信仰上帝的人是如何做到跨越這道鴻溝的?如果真正跨越了這道鴻溝,它是不是也是因為長期沉浸其中而被異化、被自我建構起來的?
約翰的發言:
謝謝巴蒂斯新的提問!從我的家境或者背景來說,我也沒有任何宗教信仰。我從小甚至可以說是一個自然主義者,就是我不光認為神不存在,我甚至還認為不存在超自然事件和超自然事物。有很長一段時間我都是一個挺自洽的自然主義者。但是後來,我是在學哲學的過程當中,有一些思考,當然會涉及到這個問題。你的這個問題,我覺得還是從我自己的經歷來回答可能會更好一些。因為這樣更加平易近人,而且我也比較有把握,因為這是我的真實經歷。當然,其中也會有一些理論性的思考。
在我開始接觸聖經、開始去教會的那段時間,我對宗教哲學特別感興趣。那個時候我就去聽了我後來碩士導師的課,他本身是一個基督徒,他也教宗教哲學。當然,我也看了很多宗教哲學的書,就是當代一些分析哲學的討論——比如說,關於惡的問題、上帝存在的論證、上帝全能的問題,包括宗教多元主義等各種各樣的問題。我還發現,關於上帝存在,有很多證明,也有很多反駁。我學了這些之後,仍然不確定上帝是否存在,我自己會傾向於不可知論。所以呢,我那個時候對於上帝和聖經的瞭解,更多是一種理論化的瞭解。就是說,我想知道基督教的思想是怎樣的,我想知道它是怎樣的一套觀念或理論。我也研究基督教,所以說我就把它當作一個研究物件來看待。
但後來,我在信仰上有了一些突破,或者說信仰上有一些轉變。當然,這有很複雜的原因,有個人經歷方面的原因,也有理性思考方面的原因。那麼,我的自然主義世界觀是怎麼破除的呢?其實不是在我學哲學的過程中破除的,而是在學習人類學和社會學的過程當中破除的。特別是那種做田野調查的人類學,即關於宗教的田野調查。我會發現一個很普遍的現象,就是在各個民族當中,甚至那些我們認為很“原始”的民族,都有關於超自然存在的信仰。在中國更是這樣,中國有很多的宗教或者神靈信仰。然後我就不得不面對一個問題,究竟存不存在超自然事件或者超自然存在?
而且我發現一個現象,就是:人類普遍相信存在某種超自然力量,或者超自然的存在、超自然的事件。這就讓我對於自己秉持的自然主義立場產生了一些懷疑和動搖。因為我好像還沒有思考過這個問題,然後我就來面對這個問題:究竟有沒有超自然存在?
但是在這之前,我會用某種象徵主義的方式來處理超自然的問題。比如,當我看到聖經中記載了很多神蹟,耶穌行了很多神蹟,包括耶穌從死裡復活這個最大的神蹟。我當時就很難理解:這種事情怎麼可能發生呢?肯定是某種謠傳或者是某種文學手法吧。
後來我發展出了一種自己比較能夠接受的解釋,就是說它是某種象徵。比如耶穌說過一句話,他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信我的有永生。”我當初讀到這句話,立刻想到了天安門廣場上的人民英雄紀念碑,那個紀念碑上寫著“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我就想,這肯定不是指那些人民英雄現在還活著,或者說他們真的永遠活著,這其實是某種象徵性的表達,表明我們紀念他們的精神。就像“某某永遠活在我們心中”,大概也是這個意思。我以為耶穌說的永生,就是這個意思。
後來我再去想這個問題。當時我在學習宗教社會學和人類學,接觸到很具體的田野調查,就是很具體的描述性材料。我發現自己不得不面對一個問題,就是耶穌在說這句話的時候,他先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當你在表達一個象徵的時候,你不會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就好像這是在說一個真實的事情一樣。然後我當時就面臨一個選擇:它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如果這是真的,那當然很不可思議;但如果這是假的呢,我真的沒必要太把聖經當回事兒,因為它就是在講一些很不著調、很虛妄的事情。所以我真正的思考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
在此之前,我是用一套象徵主義的方法,把我的既有認知與聖經之間的那種不協調給消除掉。但現在我發現,這種不協調沒法消除了,我必須得面對,作出明確的判斷和抉擇。要麼耶穌就是一個歷史上最狂妄、最瘋狂的人,因為他居然敢宣稱自己是神的兒子,能賜給我們永生。如果他實際上不是神的兒子,這樣的人該是多麼狂妄啊!但另一方面,如果他真的是神的兒子,那就沒什麼比這件事更重要。我這裡是從理性反思的角度來追溯這段往事,其實不光有理性思考的層面,我自己的生活也經歷了一些事情,比如說體會到自己裡面的空虛、內疚和失敗。
當我面對聖經所揭示的罪的問題,一開始我特別牴觸。別說原罪了,就是說人的罪行,我都不承認。我會認為自己在道德上不完善,比如說我做了一些不道德的事情,或者說我做過不好的事情,我在道德上不完美,我會承認這一點。但你要說我是一個罪人,我就覺得言重了。我覺得用“罪”這個詞來指我所犯下的錯,這就太嚴重了。後來看到聖經中說,你不光是個罪人,還是一個全然敗壞的罪人,這個對我來說更難以接受,因為這很違反我的常識。所以,大概在2012年的時候(那個時候我已經接觸聖經,在教會好幾年了),我就跟帶我去教會的師兄說,我沒法接受自己是一個全然敗壞的罪人。所以我就選擇離開了教會,我大概離開了四、五年。
罪是我很難接受的,那段時間也很糾結。但是,最終得出的結論就是:我不接受罪的這種“說法”。後來我進入碩士階段,有了更多的思考,包括也有了一些經歷,然後我又重新回到這個問題。那個時候我發現,聖經所揭示的罪的問題,不再是強加給我的一套解釋或者理論,而是實實在在就在我的生命中。就是,罪有實際的力量去摧毀一個人,就會讓你進入某種自我毀滅的狀態,我在自己裡面能夠感受到。當然,這些就構成了我信仰的一個起點——即對於象徵主義的破除,還有體認到自己的罪。當我開始去面對這個問題的時候,這些就成為信仰的轉折點。
所以,如果說你讓我現在來回答你剛才提出的問題,我不會傾向於說原罪是一種基督教的理論。我不會這麼說。因為在我的思考和體驗當中,或者說在聖經當中,它是一個很真實的事情,每天都在發揮著影響。其實,即便我成為基督徒之後,每天仍然要跟裡面殘存的舊生命、肉體在爭戰。雖然說我已經得到了稱義,得到了赦免,但是我只要在肉身活著,我還是要與罪爭戰。所以這是每天都在我裡面發生的,而且隨著我做基督徒的時間越長,我對於罪的體會越深。就我剛開始成為基督徒的時候,我覺得自己的罪挺嚴重,但是我成為基督徒很長一段時間之後,我發現原來自己的罪這麼嚴重!以前我會覺得我做的某些事情是罪,其他事情還是很好的,但是後來我發現,罪已經滲透到我生命的方方面面,我生命的方方面面其實都有罪,哪怕我在行善的時候,我也懷著有罪的動機。
舉個簡單的例子:在我研二的時候,有個師妹來找我幫忙。因為她要上一門香港中文大學老師開的課,這門課比較難。而我前一年上過這門課,並且成績相當好。然後,她就來找我,說她讀不懂材料,讓我幫忙輔導她。然後我就幫她做課堂報告,把文獻梳理清楚。她很感激,就對我說:“師兄,你這麼熱心幫助別人,你真是一個好人。”其實,如果我捫心自問的話,我這麼熱心幫助她,我的動機是什麼呢?我的動機是:因為這門課我學得很好,我考了第一名。然後呢,我在幫她梳理文獻的時候,可以顯示出我在這方面的特長,或者說讓我很有成就感,讓我很有自我價值感。
所以說,其實我並不太在意究竟能不能幫助到她,而是這件事能展示出我的某種能力、我的卓越之處。其實如果我現在來看的話,它是出於一種極為自我中心的動機。雖然外在上我確實行善了,但是我的裡面滲透了自私和驕傲。
後來,我來到北大,更加發現這一點。因為北大有很多在各方面都很聰明的人。但是,我在北大的人際關係讓我意識到:教育和知識沒法從根本上改變一個人,對於一個本來自私的人,良好的教育只能讓他成為一個更加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但不能讓他變成一個無私的人。我見到無數這樣的例子,就是那些非常有知識、有頭腦、很聰明的人,他們也受了非常好的教育,但是這好像並沒有讓他在人生的根本問題上有什麼轉變,反而會讓他更加陷入私慾之中。
我舉這個例子就是說明,當我在聖經當中來面對自己罪的問題,我也開始去面對聖經所宣告的那位上帝。為什麼我之前的發言特別強調罪是在關係中的,無論是我們跟別人的關係,還是我們跟上帝的關係?(當然最重要、最根本的還是我們跟上帝的關係,這個縱向的關係是最根本的。)我們可能會比較容易以為罪是在某種個人性的道德反省之中呈現的,但其實它是在關係當中呈現的,也脫離不了關係。所以,我面對這位上帝的時候,我看到自己在他面前真實的光景——他是誰,我是誰,他是怎樣的,我是怎樣的。罪對我來說就更加真實了。就像我跟師妹的關係一樣,我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其實我不是真的要幫助她,我其實只是來展示我自己的能力罷了。
所以,我理解罪的時候,就不是在一般的道德意義上,或者不只是從人的良心的角度來考慮。為什麼呢?我剛才也講過,人的良心敏感程度是不太一樣的,有程度上的差異。我瞭解過一些極端的案例,就是那些連環殺手,他們殘忍地殺害了很多人,但他們心裡沒有任何內疚。他們不像我們那樣會有悔恨或者自責。因為他們覺得殺人是很快樂的事情,讓他們很興奮,就像我們去喝酒或玩耍一樣。所以,這種情況下,因為我感受不到內疚,所以我就沒有罪責了嗎?其實我是有罪責的,很深的罪責。但是可能我的良心還沒有敏感到對於這些罪行有正確的反應。
我的良心很容易麻木,即便我不是一個連環殺手,即便我只是一個普通人,我也會發現自己的良心很容易麻木。比如當我做了一件錯的事情,傷害到別人了,我這時候很內疚。但我會刻意讓自己不去想這件事,然後過段時間我會發現自己不會太在意這件事了,然後就淡忘了,不再有罪疚感。
還有一個方面,就是我發現人有一個特點,這也是聖經所揭示的,就是人很會給自己找藉口。我自己在成為基督徒之前,經常出口傷人,所以我跟周圍人的關係特別緊張。我經常說一些很傷人的話,把別人傷得很重,但是我會給自己找藉口。我說:“我是一個很真誠的人,我有什麼就說什麼,我不虛偽。我不像你們,只說一些客套話,其實你們心裡不那麼想;而我是心裡想什麼,就說什麼。”
當然,我也會說自己是“刀子嘴、豆腐心”,就是說,雖然我是刀子嘴,但是我心是好的。我成為基督徒之後,有一次在讀聖經的時候,徹底顛覆了我的認知。耶穌有句話,他說:“你們心裡充滿的,口裡就說出來。”也就是說,我們總覺得“刀子嘴、豆腐心”,但耶穌向我們揭示:刀子嘴的人一定是刀子心!他根本不在乎別人的感受,他不在乎他的話傷不傷害別人。你裡面就是這樣的心,你說出來的話肯定也是傷害人的話。
所以,這又回到了我之前分享的那一點。我們為什麼會犯罪?是因為我們本來就是罪人,我們本性上就是一個罪人。而不是說:因為我犯了某個具體的罪,所以我是個罪人。這是根源上的問題,就是說,你裡面的源泉本身就已經是汙穢的,所以你湧出的水肯定也就是汙水,就像下水道一樣。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過程中,我發現原罪的問題,就是人的罪會到這樣一個地步。當我面對自己的罪,不再給自己找藉口,也按照自己所是的那樣去看待自己時候,我發現原罪就是一個非常真實的事情,它不是一種理論或者某種解釋的問題。
當然,這裡有一個比較麻煩的地方:即便一個罪人主觀上想去誠實地認識自己,他也不能真實地認清自己。其中一個原因是:人真實地認識自己,需要一個參照系,參考系就像一面鏡子一樣,他可以透過這個鏡子看清他自己。但這面鏡子如果是以人的標準或我自己定的某種標準,或者只是跟其他人作比較,你可能不會覺得自己是一個罪人。但如果你要是按照聖經所說,透過上帝所啟示的律法,比如“十誡”,來衡量你自己——比如,律法上說,看見婦女動淫念的,在神眼中已經是在心裡犯奸淫了——你會發現,罪是非常真實的。所以,關鍵在於你選的參考系是什麼。即便人所共有的良心可以讓我們多多少少意識到自己的某種罪疚感或者虧欠感,但是個人的良心不是一個客觀可靠的標準,因為我們的良心會麻木。
所以,在良心以外,上帝也特別啟示了成文的律法,就是一條條具體的律法誡命,用文字的方式確定下來。那麼,我既然有了成文的律法,那我去認真、誠實地面對聖經裡上帝的律法,那我能不能夠認識到自己是個罪人呢?或者像聖經所揭示的那樣,承認自己是有原罪的呢?其實也不一定。按照聖經所說,人沒法靠著自己的真誠和努力做到這一點。只有聖靈光照一個人的心,就像光進入黑暗的時候,在黑暗當中的人才能看清楚自己。
其實這是一種非常絕望的情況,也就是說,聖經把人一切的努力、一切可資依靠的東西,都給否定掉了。但是呢,如果不經過這種“殘酷的”揭示,就沒法做出正確的診斷。按照聖經來說,正確的診斷是:人感受到胃疼,但是他得的是胃癌,這個時候你給他開止疼片,他吃了之後可能會感覺好一點,但是病根還在那裡。聖經正是要徹底解決病根的問題,它把病根挖出來,讓我們看到這個血淋淋的現實。聖經的目的不是讓你難堪,它把這病根挖出來,是為了讓你能夠得到及時的救治。
耶穌他有一句話,他說:“健康的人用不著醫生,有病的人才用得著。我來不是要召義人,乃是要召罪人。”如果一個人不覺得自己是罪人,他覺得自己還挺好的,或者說即便他覺得自己沒那麼好,但是“內心深處是個好人”,他就不會去尋求和接受耶穌基督所提供的救治。他會採取某種自我改良、某種修身養性的方式。這個其實就是這個世界中人脫離神會採用的各種各樣的方式,比如某種修行、自我反思,或是某種道德改良。
問月生的發言:
我想對約翰的分享說幾句哈。約翰的回應非常真實,它不是一種理論,而是非常真實的經歷。約翰也分享了他在哲學或人類學方面的反思,包括對於象徵主義的思考。我有個呼應:就是我自己後來做“思修”,為什麼“思”還要加個“修”字?我真的在修,裡面好多東西都是未知的,都在探索狀態。很多都在探索以前,那些論證性的哲學都在,但一下子變成了人的具體修行,味兒就不一樣了。我後面還要很好地整理一下我那些真實感受到的東西。然後,我稱自己是“思修行者”,過去是“思修者”,現在是“行”。“行”就是更強調“一點點走”的意思。我就是分享一下“真實”的這個點,但是我們在覺得什麼真實的點上不一樣。
其次,對於一個基督徒張三來說,李四就是一個敗壞者。張三真正的那種感受,李四真的是個敗壞者。這個人會那樣看待自己過去的錯誤,一點沒有難受,還開開心心的,一點不懺悔那種,懺悔了也是輕飄飄的。所以,對張三來說,你李四就是個敗壞者。當然,張三很寬容,他不會去說李四什麼,但就是會這樣看他,他對李四的真實感受就是這樣。那李四呢,他覺得自己不是敗壞者,在他那邊,拔高點說的話,他甚至覺得自己是聖徒。即便面對強壓,他也要高昂著自己的頭顱。
這兩個人,張三真的會把李四看成是個敗壞者,而且是非常極端的那種;而李四真的會覺得自己不是,但也不認為張三是敗壞者。對李四來說,他可以容納這種可能性,但他自己不會那樣去說自己。嚴格說,他也沒辦法那樣真實地體會自己。像我體會約翰,其實是有點帶著想象的,我再怎麼代入基督徒,我也不可能是真的體驗那種發自內心的撕扯感。約翰分享的那些例子,我也就是代入一下、想象一下。我是沒有辦法真正體驗到的。
所以,很極端的一種情況是:這個張三對敗壞者是要去打擊的。那對方也肯定要反擊,就像“戰爭”一樣。那麼,這個“戰爭”怎麼解決呢?那就是兩個人必須面對的問題。因為張三真的覺得對方是個敗壞者,要把他置之死地而後快;那另一方是真的覺得自己不是,但是他又理解了張三,但是他不會讓張三搞死自己,還是要反擊他。如果我們預設了一種宗教自由,那期待的解決方案是兩方都能夠在自己內部容納對方,因為他們都是真誠的。
約翰剛才提到多元主義,我自己最開始讀的第一篇論文就是關於宗教哲學的。我就是中大讀書的時候,才進入哲學那兩年,讀了好多宗教哲學的書。我還記得好幾個理論,比如宗教多元主義。但這個問題不是理論性的,而是玩真的。所以第二點就是非常真實的一個“戰爭”狀態。就是說,這種真實的信仰者,我還是期待他是一種非常寬容的態度。就比如像約翰對我所表現出來的,就比較寬容。這種寬容強求不得,也無法變成指標。但是確實有那麼一個方向,就是我們現在預設的多元信仰的那麼一個方向。
約翰的發言:
剛才問月生這個探討,給我一個啟發。我之前的發言好像沒有從這個角度來討論,就是說:當聖經從如此深的層次來讓我們認識人有罪的問題,那麼基督徒如何看待非基督徒?如果一個人,假設他不是一個基督徒,他是一個無神論者也好,或者是一個世俗人士也好,或者是一個佛教徒都有可能——我們該如何看待他呢?
這確實是一個問題。我覺得這其實涉及到聖經所探討的一個非常核心的問題,我也簡單做一下分享。在我自己的信仰經歷當中,這也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是我成為基督徒之後的一個轉折點。我可以簡單總結說,就是法利賽人的問題。
在新約中,有一類人叫法利賽人。當耶穌去傳講天國福音的時候,有一類人對他非常敵視。倒不是說那些在社會中公認道德比較敗壞的人對耶穌很敵視。反倒那些人在聽到耶穌所傳講的福音,他們會被深深地吸引,因為耶穌所傳講的是赦罪的恩典。但是呢,有一類人,他們非常嚴格地遵守律法、非常追求敬虔、追求聖徒式生活的這樣一群人,他們叫法利賽人。
他們可能沒有很大的權力,或者沒有很高的地位,但是他們在道德和宗教追求上是一群很認真的人。就是有點像中國古代的君子和士紳。但是,他們確實非常反感耶穌。比如說,當耶穌去接待那些罪人的時候,他們就會說:“你怎麼跟罪人在一起?你怎麼跟罪人一起吃飯、一起交談?我們是追求聖潔的人,我們是良善的人,應該是遠離那些汙穢的罪人。這應該是我們追求的生活樣式。”所以他們對耶穌有很大的意見,甚至最終要殺害他,恨他恨到這個地步。
一個基督徒,在他得到赦罪恩典的那一刻,他會經歷到極大的喜樂和平安。因為他罪的重擔被挪去了。罪疚感不再來折磨他,因為他知道自己的罪債已經清償了。他的生命也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他切實地感受到一種根本性的改變。當然他不會變得完美,但他肯定有根本性的轉變。但在這個過程中,他會面臨一種試探或危險。這個時候,他會覺得:“之前因為我不信耶穌,那個時候我是一個很糟糕的人,跟世上的人一樣。但現在呢,我信了他,我罪已得赦免,我也確實感受到自己生命的改變。”這個時候,如果他再看身邊的人,他會有意無意地覺得:“我是個好人,我是個義人,而你們是罪人,你們是罪惡的。”他會以這樣一種心態來看待別人。
其實不光在基督教中會有這樣的問題。我一直在思考,為什麼中東會出現很多的極端主義勢力,比如哈馬斯。如果你仔細看他們發展的歷史,基本上都遵循這樣一個過程:一開始的時候,穆斯林世界經歷了某種世俗化,比如說大家不再嚴格地遵守宗教規條,也不去虔誠地禮拜,大家都變得很世俗。然後,在他們的群體當中,有一個非常為宗教熱心的人站出來,號召大家追求虔誠和良善的生活。他吸引了一批人跟從他,然後他們去埃及留學,接受更好的宗教訓練。他們的生活越發敬虔。但這個時候,這些虔誠人再去看那些仍然比較世俗的同胞——就是不那麼虔誠、在信仰上三心二意、也沒有很殷勤禮拜的人,就會對他們產生出一種深深的輕蔑,甚至是仇恨。
你會發現,這些宗教極端勢力幾乎都遵循這樣一個演進的模式,非常類似於法利賽人的生命樣式——他們追求敬虔,但他們看不起不追求敬虔的人,他們會覺得那些人是很敗壞的。對於耶穌去接待這樣一些不敬虔、很汙穢的罪人,他們是非常看不慣的。耶穌的做法跟他們所信奉的那套價值完全是背道而馳的。這在宗教當中一個非常普遍的問題。
一個得救的基督徒、一個信徒,當他以自己現在擁有的敬虔作為某種屬靈的資格或者作為“我是義人”的憑據,這個時候他恰恰否定了他所相信的那位耶穌,他恰恰否定了自己所領受的救贖恩典。因為這個時候他就不再說“我是靠著恩典得救”,而是說:“我是靠著我的虔誠得救——靠著我的虔誠,我獲得了我的價值,我的身份。”
我認為,對於任何宗教人士,都會有這樣一種試探和陷阱。我覺得,這個傾向其實是造成實際意義上的(不是理論意義上的)宗教不寬容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基督教歷史中也有很多這樣的例子,這被稱為律法主義。律法主義者會說:“你看!我現在成為基督徒,我現在嚴格地遵守律法,我是一個虔誠的信徒。”因此,他就會看不起那些世俗中的人,甚至看不起那些雖然也是基督徒、但是沒有他們那麼“敬虔”的人。律法主義不可避免地會產生這樣一種傾向。但是,如果一個基督徒陷入到這種狀態中,基本就可以判定,他可能並不真的明白那拯救的恩典。他可能已經回到了得救之前的狀態,甚至比他得救之前的狀態更加糟糕。因為,他會有一種靈性上的驕傲,或者一種屬靈的盲目。他處在極大的罪惡當中,但他還覺得自己很敬虔。這是人性中一件很弔詭的事情。
聖經還有一個方式來講罪,即說罪甚至會把人類最美好的東西,轉化成最邪惡的東西。比如說追求宗教、追求敬虔,這是人性中一種很美好的傾向。我不是說它最美好,但它至少是一種跟哲學或藝術追求不相上下的美好傾向。但是,人的罪甚至會把宗教性的虔誠扭曲成一種靈性的驕傲!由此催生出對別人的蔑視,甚至催生出無端的仇恨。
其實,我成為基督徒之後,也曾走過一段這方面的彎路。那個時候我已經得救了,但是我會覺得自己現在已經改變得很好了,所以當我看到那些現在還沒有信的、或者雖然已經信了、但是各方面都不太行的人,我對他們就會有很多的輕蔑。
正是在這個過程中,上帝也使用各樣的方式來擊打我的心。在這種驕傲當中,人是很盲目的、很狂妄的,他的心很剛硬、很冰冷,但是還不自知,還覺得自己很虔誠、很火熱。我經過很多破碎之後,才看清楚這一點,就是說:即便我已經領受了恩典,即便我已經得救了、有重生的生命在我裡面,即便我的生命有了根本的改變、並且有了永生,但是(用路德的話說)我仍然是“完全的罪人”。也就是說,我所擁有的新生命,我所擁有的一切改變,我所擁有的上帝兒女的身份,或者我所行出來的一切的善,歸根結底,功勞都不在我自己,而是上帝的工作在我身上所帶來的結果。
說到底,其實是神的工作。這就涉及剛才問月生提到的,就是說當基督徒復活獲得新身體,好像有一種“生成”,就是從無到有的生成。對,其實不光在那個時候。當然,那個時候是在身體意義上,我們獲得一個新身體。基督徒所說的永恆是新天新地當中的永恆,不是一種很虛渺的靈性狀態,而是一種現實的存在狀態。就像我們現在這樣,但是不會有現在身體當中會有的疾病、罪惡和死亡。
其實,基督徒他在得救的那一刻,就已經有一個“生成”了。這個生成,就是一個新的生命被放在他裡面——這就是“被重生”。重生很有意思,沒有哪個嬰孩是自己把自己生出來的,他甚至沒法選擇自己什麼時候出生。他完完全全是“被生”出來的。整個過程都是被賦予、被給定、被賜予的。所以,你沒有任何可誇口的,你不是靠著自己的努力獲得一種新的生命,包括你成長的過程也不是你努力的結果。不是說一個小孩努力長高,因為他很努力,他就長高了。不是。其實,那個生命已經給他了,這都是賜予生命的那一位給定的。所以呢,在他獲得新生命的那一刻,其實已經有了這種“生成”,而且這種生成不是因為他的某種努力或者原因所帶來的,完完全全是那位上帝賜予的。
所以,其實聖經也會用“新創造”來講重生的生命。就是說:“你們現在得到的生命,是新的創造,是上帝的新創造。”因為第一次創造就是舊的創造,第一次就是上帝從無中創造宇宙萬有。第二次創造就在我們裡面,開啟一個新的生命,一個去愛人、去愛神的這樣一種生命。當然,最終這個新生命的成全,是在你獲得一個新身體、在新天新地當中那樣一種完滿的狀態。
那麼,我現在如何看待一個非基督徒或者說一個非信徒?
首先我會看到,我和他是一樣的,如果離開神的恩典、離開神所賦予我的新生命,我其實跟面前的這個人沒有本質區別。當然,我不否認在某種程度上,人與人之間會有差別。比如說,某些人更惡,某些人不那麼惡。但是從根本的意義上、從聖經所定義的罪的意義上,我們都是罪人。聖經上說:“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我們都沒有活出神讓我們活出的生命樣式,我們在各方面都有虧欠。所以在這個意義上,其實每個人都一樣:在罪性方面人人平等。
當然,基督徒在跟別人分享福音的時候,他不是用一套理論來說服對方。當然,他所分享的福音有說理的部分,比如講解救恩的意義,肯定有說理的成分。但是最根本的在於,基督徒是在做見證。比如,我在法庭上做證人,就只能說:我看到了事情如此這般的發生。那麼,基督徒見證什麼呢?他們見證神在兩千年前透過他兒子耶穌基督的死和復活,成就了他所應許的救恩。這就是對十字架這個拯救事件的見證。並且,基督徒也見證神如何將這已經成就的救恩施行在我身上。這就是個人的信主見證。所以,就是透過見證,不是透過強迫,也不是要給別人施壓。我就把福音見證出來,最終對方願不願意接受,就需要他自己來決定。他可能信任我,或者他透過自己的思考接受或拒絕,這些都交給聽眾自己來做決定。我不應該強迫,況且信仰這件事也強迫不來。
當然,不光如此。聖經中也提到,如果沒有聖靈親自光照或者改變人心的話,沒有人有任何能力或意願接受耶穌基督。這裡也涉及到原罪的教義,即人在罪中無法自拔、不能自救。他沒有辦法憑著自己的力量脫離罪,接近神。除非,神先改變他、先光照他,他才能夠對神有回應。
聖經裡用一個詞來描述人跟神的關係,就是在神光照人之前,“人是死在罪惡過犯中的”。倒不是說人此時是生物意義上的死人,而是說,在跟神的關係當中,人對神是沒有反應的,就像死人一樣,沒有任何反應。對於神的心意,他沒有反應,他看不出來,也不知道。甚至,即便他頭腦上知道了,他也會本能地抵擋。他也不會願意順服神或信任神。他充滿了對神的懷疑,或者說充滿了對神的不信任感。所以,如果不是神在他心裡主動工作的話,他是沒法改變的。
所以,當我們去跟別人分享我們的信仰,或者跟別人分享我們所信的福音,我們當然希望對方能接受,但是我們也知道這不是我們能決定的,不是我們的口才、我們的論證所能決定的,我們只是上帝拯救作為的見證人。我們只能祈求聖靈來工作,神去改變他,讓他能接受。
還有一個關於多元主義的問題,我也要回應一下。我認為,在這個世界當中,宗教多元性是一個事實。宗教多元性,我說的不是多元主義(pluralism),是多元性(plurality)——就是有很多宗教,甚至同一個宗教中也會有不同的宗派、不同的主張。基督教也會分很多的教派或宗派。宗教多元性是一個事實,這個沒有任何爭議。
宗教多元主義與宗教多元性不同,這裡需要區分和辨析。這裡需要明白:如果某個人堅持某種觀點或主張,也就意味著他不會接受與這個主張(在邏輯上)相矛盾的那些主張。這是一個很顯然的事情。
舉個簡單的例子。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著我,沒有人能到神那裡去。”這句話非常明確了,如果你(作為基督徒)接受耶穌這句話,你肯定不會認為透過穆罕默德能到神那裡去,或者說透過某種印度教或佛教的修行,你可以到神那裡去。肯定不行,因為這句話是一個排他性的宣稱。因為當你堅持某個命題為真,這本身就是排他性的,也就是說,與這個命題不符的事情就是不對的。你不可能同時堅持一個命題和它的否命題。在這個意義上,其實就不涉及寬容不寬容的問題,而是說,我相信這個,這就意味著我肯定不會接受與它相反的命題。這對所有人都是一樣的。
對我來說,我接受這樣一種排他性的信仰,並不意味著我在實際的生活當中會對別人採取一種不寬容的做法或態度。這個不是必然的。當然,我不否認有一些堅持某種排他性宗教宣稱的人,他們會在實際生活中採取強迫別人或者不寬容別人的做法或態度。但是呢,這並不必然如此。一個人完全有可能既堅持某種排他性的宗教宣稱,但另一方面他又極為寬容,對別人非常有耐心、很溫柔,不去強迫別人。這個完全是可以實現的。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