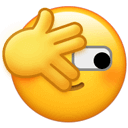作者:曾宇昕
來源:真故研究室
國內部分美髮店基本已經到了“進店不辦一張高價會員卡,就難以出來”的程度。當剪完發後,更有很多人想“哭著出來”。於是,一些厭倦了國內美容業風氣的顧客,將目光轉向了鄰近的日韓。
日本recruit旗下調查機構,於今年9月對936位訪日的海外旅行者做了一份“美容意向調查”。其中,50.2%的旅行者表示,想來日本體驗美容、美甲服務。當中又有80.1%的人最想體驗剪髮。理由是日本的理髮乾淨、技術高超、可信賴。57%的人準備的剪髮預算是5000到2萬日元(合243-972元)。其中,中國客人雖然沒有很確切的人數統計,但鑑於訪日中國遊客今年前10月已經突破580萬,人數位列各國第一,日本很多理髮店已經配置了能說中文的服務助手,想要賺中國人的理髮錢。
1
我去日韓理髮的理由
“把頭髮修一修,整齊點再去日本。”
今年7月底,正在籌劃去日本進行大學畢業旅行的小吳,在聽到媽媽的叮嚀後,轉而在行程里加上了一項——日本美髮。這也是小紅書#日本旅遊攻略#話題下被提及最多的一項體驗。
做了多方攻略之後,小吳選擇了在東京銀座的一家沙龍連鎖店,預約網站顯示,初次來店洗剪吹+染髮+深度護理:480人民幣。
與國內相對快節奏的美髮沙龍不同,店內安靜而溫馨,進門就有中文翻譯接待,全員都是女性的髮型師們在顧客耳畔輕聲確認著下剪的每一刀,沒有推銷,小吳感覺從細緻服務中,收穫了滿滿的情緒價值。
從美髮沙龍走出來的時候,小吳感覺“整顆頭都在閃閃發光”,服務她的託尼姐姐一路送她到計程車上,她們互相交換了聯絡方式。
3個月過去,除了顏色變淺了一些,髮根長出了一些黑髮外,保持的效果很好,“下次去日本還會找那個姐姐做的,特別有耐心。”
與之相比,她此前在國內理髮店的遭遇,只有“痛苦”的記憶。
小吳是淺髮色重度愛好者,亞麻灰、白金色、蜜桃粉、霧霾藍,大學四年,幾乎每個學期她都會換一個髮色,對她而言,這也是和託尼哥鬥智鬥勇的四年。
一次她要求理髮師,“修短一點,前面剪一個八字劉海”,還將自己在小紅書儲存的髮型樣式圖展示出來要求同款。理髮師信誓旦旦,“還原90%沒問題。”
可她看見,理髮師挑起發片,一刀裁去了四分之一長度的頭髮。“128元一次。八字劉海剪得像個鬚鬚。我要他重新改一下,你猜他說什麼?”小吳有些激動,“他說,我是專業的,可能是你現在還沒有看習慣。”小吳覺得和理髮師的溝通,中間隔著一道馬裡亞納海溝。
同樣是年輕人的小江,是到韓國的交換留學生。今年3月春季學期時,她在韓國首爾體驗了一把韓國特產“三件套”:剪頭髮、化妝、拍證件照。
小江從下午到晚上,剪頭、染髮、護理,一個系列下來,這位託尼老師為小江單人服務的時間超過了6個小時,
96290。
這是結賬時的韓元數字,摺合人民幣只有500元左右。
“在家裡(國內)找個沙龍,隨隨便便就上千塊了,能讓我笑著出來的也很少。”
更讓她驚呼的是,望著剪完後鏡子中的自己,她只蹦出了一句話:“너무아름다워!”(太美了!)
曾在日本工作過的北京上班族李哲表示,其實中國人去日本理髮,2018-2019年就已經火過,現在隨著中國人旅行方式從物質消費遊轉向生活體驗遊,日本洗剪吹又迎來了中國新客。
他這樣介紹中日兩國美容理髮業的不同。日本理髮店的氛圍感是:你可以很安心地在店內翻閱時尚雜誌,溝通之後,其餘交給理髮師。但在國內,需要不斷應付推銷辦卡,鬥智鬥勇,關鍵花高價剪出來的髮型,常讓人想哭。
令他印象最深的是在北京體驗某北造型,第一次去,被遊說充值1000元有折扣;第二次去,又被遊說充值2000元,說能打6-7折。但無論充多少,理髮師都先是對你的頭型進行“一輪暴擊”,再“很自然”地向你推薦高達7、800元的燙髮專案,關鍵是燙完,李先生每次都感覺一言難盡。
還有一次,李哲被哄到二樓的某北造型護膚部,說是進行剪髮前的松肩按摩,當自己光著上半身躺在那時,護膚部的疑似主管兩次闖入,對著李先生進行遊說辦卡。“每次一進店,就一堆人圍著你,感覺理個髮都要打攻防戰。”
在北京經營一家日式美髮店多年的日本女老闆,這樣總結中日兩國的理髮業。日本理髮受到中國人歡迎的理由是:剪髮技術的高超和細緻的服務。而中國的理髮店十足熱衷於銷售,不斷遊說辦理數千元的會員卡,推薦高價商品,顧客享受不到放鬆的時間。
2
國內tony哥揭露行業內幕
從消費者立場看到的中國美容業問題,歸根結底來自於中國tony哥的養成和生存模式,發生了偏差。
如果要問什麼世界上最會起頭銜的行業,美髮店絕對擁有一席之地:設計顧問,設計督導,設計大師,資深設計,設計總監,創意設計,高階設計。頭銜的響亮與否並不直接連結著理髮師技術之高下,但絕對與價格掛鉤。
在美髮行業摸爬滾打了6年的髮型師小靖表示,他也分不出來區別。他透露這就是行業裡包裝自己的一種方式。頭銜足夠花哨,先把顧客震撼住,掏錢的時候也就心甘情願了。想簡單粗暴地去評判一個人的剪髮水平,不用看頭銜,主要看價格。
比如,在小靖剪髮的髮型店,最便宜的是高階設計師,129元,其實是剛剛從助理升上來的新手。接著是239元的資深髮型師,339元的技術總監,580元的沙龍總監,一直到888元的藝術總監。如果是專人服務,普遍在1000元以上,業內最高能到6000多元一次(僅剪頭髮一項)。
去首爾理了發的小江表示,在韓國,除了愛豆同款“明星妝造師”,不太會有髮型師包裝自己,等級最多隻分三級,但大部分的髮型師價格、水平不會差異太多。
在日本東京銀座最有人氣的美髮沙龍里,髮型師只有兩種等級,“造型師”和“高階造型師”,但價格不是根據等級來規定的。宣傳頁面極其簡單,只介紹髮型師的基本履歷和擅長風格。一些店鋪的預約條件甚至是,請不要指定髮型師。就算指定人選,店長和造型師的價格相差也不會超過600元。
“說實話,染料、藥水,成本並不高。但我們這個行業,技術就是最貴的成本。”小靖回憶起,“就算最好的產品,價格一千多,成本也就兩百多。”
在國內,十七八歲的年輕人們從職業技術學校畢業後,通常只能應聘理髮學徒(也稱助理),在一位髮型師的手下,反覆練習洗頭、按摩、捲髮、刷料。
他們工資不高,洗髮的錢只從從屬髮型師的工資里扣,一月下來,底薪加提成往往不超過兩千。而一次自費的技術培訓,卻可能花掉他們一半的收入。半年之後,學徒們才被“允許”學習剪髮。
“你可以加我微信,來找我做造型,除了剪髮,燙頭髮染頭髮我都會,全能。”為了增加客源,縮短“實習期”,學徒們在洗頭時往往會這樣告訴來消費的人們。
17歲在技術學院美髮專業畢業,小靖拿到了美髮資格初級證書,以助理的身份進入這家店,一待就是5年。“開始非常無聊,主要就是洗髮、跟單、接待客戶。如果做得好,髮型師會給你分配一些調配染髮顏料的活兒,做得不好的話,就只能一直洗頭髮。”
美髮行業依照傳統慣例,遵循學徒制,但實際上,很長一段時間,沒人告訴他,怎樣才能往上升,一切都得靠自己觀察。
“技術是吃飯的東西,怎麼可能輕易教給別人。”
小靖默默觀察著,他發現調配染髮顏料,是一個很重要的階段,這個工作可以讓他從洗髮的後臺進入理髮的前臺。在一個100多平米、雙層甚至三層的店裡,如果只是在後臺打轉,那就永遠接觸不到理髮。他一邊調色,一邊看髮型老師的動作,看他如何基於不同的臉型做各種髮型,也看他如何接待不同消費水平不同性格的顧客。他牢牢記住,下班後慢慢琢磨。
一年多時間後,小靖開始接觸燙染。因為前期基礎打得好,加上助理時期服務得體,積累了不少潛在客戶,他如魚得水。開始獨立操作後,他愈發小心,同事閒暇時間刷抖音不過消遣娛樂,他卻關注了全國各地的髮型師賬號,在影片裡反覆琢磨人家的技巧。
不過,技術的躍遷並沒有徹底改變小靖的處境,對於髮型師而言,收入來自底薪+提成,而這又與頭銜等級相關,等級越高,提成拿到的錢也越多。每月店內考核,取得優秀的人才有機會提升。這種考核不限於髮型技術,還會考核行為舉止、為人處事、儲值推銷。
短暫的幾秒接觸,你能不能分辨出客戶的身份背景,以怎樣的方式開啟聊天讓他不反感,怎樣把他們轉化為熟客,願意儲值,願意做漂染接發之類的昂貴專案。
可以說,中國理髮師是技術力+銷售力結合的一個物種。
為了增強員工壓力,店裡常常組隊PK業績,單人對單人,或多人對多人,久而久之,彼此之間開始勾心鬥角。只有把新客變成熟客,讓人願意付費,髮型師才能維持穩定的收入。
一定程度上,傳統店對現金的渴求,和傳統健身房相似,即提前收取大量資金,回籠投入的成本,繼而用下一批資金去支撐當下的支出。
根據中國商業聯合會和美團共同釋出的《中國生活美容行業發展報告2020》,主要包含門店租金、人工工資、水電費和物料費在內的經營成本,是這類店鋪面臨的最大問題。有一半以上商戶的經營成本佔門店營業收入的40%~50%,還有三成商戶佔比達到70%。
壓力反噬到普通顧客身上,他們一方面要承受店員的推銷之苦,另一方面還有不斷上漲的價格。
3
“望聞問切”——
中國美髮業何時從手工業轉向了資本型理髮
二十世紀後期,隨著1988年漢城奧運會的成功舉辦,韓國服務業下細分領域開始蓬勃發展,特別是美髮行業不斷擴大其店面數量,從而帶來了質的飛躍。
二十一世紀初,中國也很快也打開了美髮行業的豁口,連鎖理髮店異軍突起。
2003年以前,中國理髮行業從業人數在100萬左右,到了2004年-2008年陡然暴增至600萬。“xx剪藝”,“xx造型”在這片土地上遍地開花,無數“想學一門好技術”的年輕人搭上理髮這列黃金快車,向著充滿期望的未知駛去。
也就在這一年,中國理髮業開始從傳統手工業,轉向資本型理髮。儲值卡的風口從中國臺灣吹到了大陸。大陸美髮師恍然大悟:原本剪一次頭髮收幾十,一天下來最多千把塊流水;現在一天賣幾張儲值卡就可以進賬幾萬。
而中國理髮店的經營模式,也變成了:高昂的會員充值卡——高價格的洗剪吹消費——繼續鼓動顧客連續高額充值。
這一模式讓這個小而分散、極難融資、迄今沒出過一家上市公司的行業,突然擁有了融資能力,直接起飛,美髮店老闆也膨脹了:一條街上不停有新店開張,一家店開半年老闆就能在當地買套房,門店裝修越來越浮誇,花樣也越來越多,“充值2000元打6折,充值5000元打骨折”。
美髮師花在手藝上的時間越來越少,花在套路上的時間越來越多。每個從業者都從中看到了致富的可能。如果沒有,那就是賣的卡還不夠多。
從業20餘年的李叔對當年話術的傳播印象深刻。憑據外貌、衣著、舉止判斷顧客的薪資、階層、消費能力,從而更好的推銷,這便是“望聞問切”的要領所在。
“一進連鎖店,從頭到尾,基本每個人都會跟你說一件事:辦卡。”
“顧客一進來,背了個兩萬多的包,你就想想給她推這個燙頭得推一千多,兩千的都很正常。有的人開一輛車一百多萬到你這,也不會只剪一個二十多塊的頭。”
話術和辦卡的思維傳播開後,越來越多的理髮店極力宣揚之,理髮店從“一人獨大”式的經營過渡到股份制經營。
推銷辦卡成功後的“卡金”存在老闆和股東們的賬戶裡,技術越高的髮型師拿的股份越多,這也成為連鎖理髮店拉攏高精人才的一種方式。“這錢已經不在老闆手裡了,顧客要追,是追不回來的。”
當資本之風吹向急速發展中的理髮行業,傳統市場模式被打破,利益伴隨著風險如破堤之潮般向投資者們湧來。大額儲值卡就是連鎖店們的“移動銀行”,卡金是蓄在裡面的水。老闆用這筆錢不斷擴店,就像錯落有致的梯田,上一階蓄積的水流淌入下階,消費者的資金最終在不斷迴圈往復中灌溉出一整條連鎖的土地。
連鎖辦卡的模式造成了競爭的惡性迴圈。“所有店都在辦卡,你不辦,客源便會被辦卡店‘吸‘走。你不辦,你的牌子就做不成,你就無法成為連鎖。”
當髮型師們不再專注於業務提升而是辦卡業績,顧客滿意度下滑,客源像水源一般流逝極快。一旦業務不達標,水源便會截流。
一些連鎖店倒閉時,欠了顧客七八百萬,而當責任人消失,這筆錢將永遠不會回到客人手裡。負面新聞頻見報端:卡在,店沒了;店在,名字換了;名字沒換,老闆沒了……美髮業信譽一度成為投訴率最高的行業。
“儲值卡的出發點是好的,既幫美髮店留住長期顧客,又幫客人省了錢。只是後來跑偏了,大家聽到充卡就害怕。”李叔嘆道。
手藝人的時代在老師傅一代的退隱中緩緩拉上帷幕,在做大“理髮資本”的驅利動機下,曾經的“剃頭師傅”走向嚇唬人的“總監老師”。
為了吸引客源,理髮資本們還用上了一種名叫“髮型變裝”的短影片來種草引客。在這類影片中,我們時常能目睹到這樣的劇情:一位原本邋遢平凡的女孩,在髮型師的巧手下,鏡頭一轉,瞬間蛻變成為一位時尚精緻的都市麗人。
然而,現實往往與理想存在著不小的差距。據多位資深髮型師透露,那些在網路直播或短影片中驚豔亮相的變身女孩,其實都是經過精心挑選的髮型模特,她們是髮型師為了吸引流量而特意培養的“種子選手”。當滿懷期待的觀眾沿著影片中的連結找到這些髮型師時,卻發現實際效果與影片中展現的大相徑庭。
從“剃頭師傅”到“網紅託尼”,變化的過程中,不變的是什麼?
理髮師曉華在直播中給出了自己的答案:“(爆火)之後的打算嗎?繼續剪頭髮。”身處其中,美髮行業需要想好如何分蛋糕,更要回歸美髮的本質——憑手藝吃飯。
而這也正是如今日韓這種相對成熟的理髮市場追求的目標。在日本,全網經常有如何開好一家理髮店的貼文。幾乎沒有誰在教:如何透過辦卡來生存,而是如何滿足顧客的需求,創造一個讓顧客下次還想來的服務環境上,大家在集思廣益。
中國理髮美髮業,市場一定是億級水平,但現在缺了一個迴歸行業本質的初心。
– END –
CEO企業家微信群

掃碼申請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