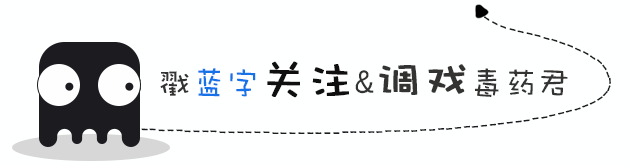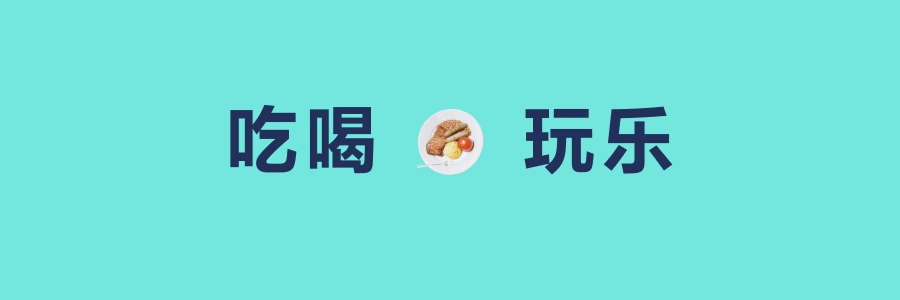改編自李娟同名散文集的迷你劇《我的阿勒泰》近日收官,豆瓣評分達8.7分,成為2024年國劇評分第一。
無論是全電影班底的主創團隊、業內首次嘗試“原生HDR”拍攝製作,還是精緻又適度留白的鏡頭語言……幕後製作團隊如工匠般,對鏡頭、聲音、色彩每一處的精雕細琢,讓這部愛奇藝出品的迷你劇收穫大量觀眾“畫面精美 ”“每一幀都是電影質感”的評價。
《我的阿勒泰》在愛奇藝將以杜比視界和杜比全景聲呈現。在透過“幀綺映畫MAX”認證的終端裝置,可觀看到這一最高的視聽版本,原汁原味地感受主創在視聽設計上的細緻用心。
本期「桃的視界」&「桃廠藝術家」聯合介面文化,一同走近《我的阿勒泰》的拍攝幕後——李娟筆下的“彩虹布拉克”,如何以一種“非遊客化”的視角呈現“雲淡風輕”的質感?阿勒泰夏牧場上,那些“散文詩碎片”一般的生活故事,怎樣透過視聽語言直擊心靈?
攝影指導劉懿增、聲音指導張楠兩位主創,將帶來他們的第一手創作筆記,以及部分未公開的創作花絮。帶著他們的分享,“二刷”時或許會發現更多意想不到的驚喜。
劉懿增
《我的阿勒泰》攝影指導

勘景、拍攝:克服險峻,
呈現“美好”又“善變”的北疆生活質感
“我們就像一群‘城市動物’,時時刻刻都想拿出手機瘋狂拍照。”劉懿增回憶,初到新疆,所有人都被眼前的“極美之地”震撼。但對於生活在那裡的哈薩克族人來講,這一切美景不過是他們無比平常的日常而已。
《我的阿勒泰》作為一部展現了遊牧民族深遠豐富生存景觀的作品, 想要把這種“日常化”、雲淡風輕的質感用鏡頭語言呈現,關鍵在於去除讀者化、遊客化的視角。在勘景和拍攝時,劉懿增和劇組便試圖以當地人的視角,展現出最自然、質樸的北疆生活風貌。
然而,想要實現這種生活化的質感,過程卻並不簡單。
“都說‘無限風光在險峰’。由於新疆的溫差大,天氣狀況多變,在現場的拍攝就像帶著攝影機來‘打仗’一樣。”除了天氣,劉懿增還要關心的是,馬和駱駝有沒有彼此熟悉,會不會鬧情緒;羊群能否穩定在一個區間吃草不走散;狼在到場前有沒有時間熟悉環境和人物,天氣會不會不按常理出牌;看似秀色可餐的草地很可能是沼澤……
為了儘量利用好每一個短暫的“最美時分”,在勘景時,劉懿增會用APP提前算好太陽角度與時間,拍下示意。鏡頭裡雲淡風輕的從容背後,有嬌豔的鮮花草地,也有走丟的駱駝馬匹,有李娟筆下穿過樹林的風,也有導演組嘶啞的喉嚨。“最美的時刻,都是稍縱即逝。轉場要時間,動物要控制,演員要就位,如果不計算好時間,很難拍到預期的畫面。”

勘景

成片

勘景

成片

鏡頭測試

大結局巴太射箭名場面
除了提前做好勘景和鏡頭設計,劉懿增和劇組也時常需要隨機應變。
拍攝期間劇組經常遇到太陽雨,太陽雪,太陽冰雹,颶風等,劉懿增說:“有的時候一片雲飄過,畫面就會一下由晴轉陰。”(下圖)


愛奇藝劇集截圖
但劉懿增認為,恰恰是這種“說翻臉就翻臉”的天氣,給劇情增添了一絲靈動鮮活。他說,新疆的天氣非常考驗演員,比如猛烈的陽光會晃得周依然睜不開眼,就連於適這樣的“草原猛獸”也在賽馬會的時候,被颶風吹得眼睛發紅流淚。
拍攝文秀坐車回小賣部那場戲時,劇組突然遇到太陽雪,劉懿增特別抓拍了一個太陽雪的空鏡。“我和導演說,咱們把這個空鏡剪進去吧,讓觀眾體驗一下真實的新疆是怎麼‘美好’又‘善變’的。” (下圖)



愛奇藝劇集截圖
令劉懿增印象深刻的一場戲,是張鳳俠的出場。“那天風捲狂沙,基本一張嘴就會被灌進去一口沙子,而馬伊琍老師就像長期生活在這種環境的人一般,絲毫沒有一絲在意。”(下圖)


愛奇藝劇集截圖
劉懿增回憶,一次,巴太父子的情感戲被颶風“打斷”,氈房周圍突然颳起颶風下起冰雹,劇組帳篷被風颳向不知何處,車隊陷在草地裡無法動彈。

巴太父子情感戲及氈房周圍散景戲拍攝背後
劇組遭遇颶風


有時,劇組還會遇到沙塵,有時候風甚至大到聽不清聲音。而在這樣的環境中,於適不但要騎馬射箭,還要表現得雲淡風輕,蔣奇明的頭髮被風吹得一刻沒有整齊過(下圖)。


可正是這種凌亂的質感,讓劉懿增覺得“十分動人,會忍不住想要多拍”,“雖然攝影機連保持穩定都困難,但是特別有幸能夠與各位演員老師們一起‘風中凌亂’。”劉懿增笑道。
光影設計:曝光控制與攝影留白,
呈現北疆的最美時分
劉懿增坦言,能夠用鏡頭靠近《我的阿勒泰》中的故事與人,是非常榮幸而愉快的一場旅行。
無論是愛奇藝平臺,還是主創團隊,都對高影像質量有著“死磕到底”的追求。《我的阿勒泰》是愛奇藝首部打通“原生HDR”拍攝製作流程的迷你劇,現場特別配置的HDR監視器,可以讓團隊在暗部和亮部看到更多細節,色彩更豐富,對於攝影師精準曝光非常友好。
劉懿增介紹,很多逆光拍攝的最佳時間點就是太陽剛好要落山前的那一刻,此時天光不會太亮,雲層依然有層次,太陽的光心不至於炸裂。



在日落前,劉懿增會以側光角度,選擇影子能拉到最長的那一刻來安排拍攝的全景。

在日落後,雪山已退去刺眼的明亮,前景的人物更容易被突出拍攝。

巴太作為導演筆下的原創角色,既代表了新生代和傳統文化的碰撞融合,又是人與動物,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的完美表達。劉懿增提到,在讀劇本時,他腦海中想到了一則Burberry Hero香水廣告裡的畫面,“其中有一個半人馬的模糊剪影令我印象極為深刻”。


畫面出自廣告截圖
在《我的阿勒泰》拍攝時,劉懿增一直在想,是否有機會把“半人馬”這個意象表達在合適的場景裡。直到“賽馬會”那場戲,巴太要親手弒殺愛馬,這場戲張力很強,並和馬頭樹那場戲形成劇作閉環。“於適本身極佳的騎射表現力,與天時地利的光線機會,‘半人馬’的這個意象得到最佳表達。”

最終“賽馬會”“半人馬”形象呈現效果
劉懿增說,在導演的劇本和作者李娟的世界觀裡,世界和自然是很大的,人很渺小,所以在整部作品的構圖上,他都會用留白和大環境去壓住人物。





或者,劉懿增會選擇讓環境包裹住人物。“只緣身在此山中”的留白,可以讓觀眾自行腦補山的高遠與層巒疊嶂。



鏡頭推動情緒昇華
為觀眾提供一個靠近角色的“觸點”
劉懿增說,文秀(李娟)作為一個作家,她手中小小的一杆筆,一瓶墨水就可以是她的整個世界。因此,為了營造一種寫作的“宏大感”,劉懿增希望能有一個距離筆尖非常近的透視感鏡頭,特別讓道具組做了一個特殊墨水瓶,呈現出鏡頭就在墨水瓶裡的世界觀感。
“文秀提筆吸墨的那一刻,墨水的漣漪輕翻,就是攝影機靠近角色的最佳觸點。”



在哈薩克語文化裡,人與人之間產生友情或者愛情,是由於被看見。所以哈薩克語中,表達“我喜歡你”的意思是“我清楚地看見你” 。
文秀對巴太的感覺,是有一個“看見又沒看清對方,所以更加要去探索對方,同時也看清自己”的過程。

文秀在草原上看到巴太的輪廓時就已心動,雖然只是輪廓;她在月光密林中試探巴太的心儀物件時,也還沒有把巴太的心看得那麼清楚;她和巴太分開的時候,即便瘋狂想念,但也不確定能否再見到巴太,以及釐清巴太對自己的情感。
劉懿增說,為了貼近文秀的內心,貼近這種看見和探索中的狀態,特別在攝影的光線控制上做了收斂,讓畫面處在一個能看到,但不能一眼就看清的狀態。“希望觀眾也像文秀一樣,更願意在這種氛圍中去探索這部劇的情感表達。”



張楠
《我的阿勒泰》聲音指導

收音、混音:
讓人與自然“再近一步”
《我的阿勒泰》與其他劇集不同,有大量的自然風光外景,有森林、草原、湖邊的環境。因此,張楠和團隊會在前期收音和後期的環境聲製作上,去特別體現阿勒泰的自然特點,藉助聲音去增加劇集中人與自然的連線。

“我們在聲音上做了杜比全景聲設計,就是為了讓聲音從二維提升到三維,希望讓觀眾有更強的環境包容感。”為了讓觀眾在聽覺上感受到自然聲音的真實還原,在前期收音時,張楠和團隊著重錄製了“安靜”的環境音,如雪後的安靜,樹林中的安靜,草原的安靜,以及有特點的環境聲,如牛群羊群的活動聲,草原的溪流聲,樹林中的雨聲等。
“後期混音時,我們以動靜的反差對比,儘可能地還原出我們身處阿勒泰時真實的聽覺感受。”張楠提到,有一場三個姑娘割木耳的戲,導演說木耳好像缺了一點溼潤的感覺,於是團隊就錄了很多水的聲音疊在一起,大概七八種聲音。“這樣,後期呈現出的效果是,只割了一下,就能感受到木耳Q彈的質感。”
聲音傳遞情感連線
藉助“弦外之音”烘托故事表達
和很多人想象中的“文藝片”不同,輕喜劇的元素貫穿於《我的阿勒泰》整部劇的始終。張楠表示,在後期混音時,團隊選擇有意放大具有喜劇元素的聲音音量。“比如雞叫、床塌、摔倒等,我會讓這些聲源大於常規中我們熟悉的音量比例。”
張楠舉例,實際拍攝中,馬其實不會有那麼多聲音互動。所以在後期製作中,張楠設計了很多“踏雪”與男女主角的互動音效。“比如馬感受到了巴太的悲傷;在巴太深夜與馬談心時,馬兒會給予巴太回饋的聲音;巴太與文秀在樹林裡交流時,馬兒會‘調侃’二人的青澀狀態。” 張楠說,“踏雪”與巴太之間親密的情感連線,此時都能透過聲音做更為直觀的呈現。
馬匹對巴太和文秀的調侃聲


文末福利


在文章下方留言及轉發本文至朋友圈
分享對這部劇印象最深刻的一個畫面
或其他感受
留言點贊量最高的前1-5名
將獲得5月17日晚19:00
《我的阿勒泰》北京國貿
百麗宮影城杜比影院
主創交流觀影沙龍電影票1張
留言點贊量最高的6-9名
將獲得《我的阿勒泰》原著1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