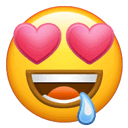近期,北京兒童醫院的
“拒絕上學門診”再度引發熱議。
開設一年來,
就診人數常常爆滿,一號難求,
厭學、休學逐漸成為普遍現象和社會話題。
任竹晞,37歲,北京人,
從2019年至今,
她創立了“一齣學社”,
在6年間陪伴過150名休學的青少年,
幫助他們或重新回到校園,
或找到新的人生目標。
她從小就是“別人家的孩子”,
高中考入人大附中,
又透過高考進入清華大學,
但是步入大學之後,她休學了。
她與這間學社的故事,
正是在休學之後開始的。

“這學/這班 咱是非上不可嗎?”

6月下旬,一條在北京與任竹晞見面,
與她聊了聊她如何對“名校光環”祛魅,
以及休學期間的自我探索。
我們也拜訪學社,
看課堂如何運轉,聽到孩子的聲音。
“休學更多是一種處境,
就是你在原來設好的軌道上、
單一的標準下產生疑惑了,
你想停下來,
思考一下自己的路怎麼走。”
編輯:藍雨約
責編:魯雨涵


一齣學社的牆上,貼滿了孩子們的心得感受和遊學照片
上午9點半,敲開一齣學社的門時,任竹晞已經到了。
她是今天第一個到的人,也是學社的創始人。過去6年間,任竹晞總共陪伴了150名13-20歲的休學少年,幫助他們重新邁出人生的下一步。
2019年創立以來,學社搬過好幾次家。去年10月份,任竹晞和老師、孩子們來到了這裡。
這是一間坐落於北京四環的140平三室一廳。屋內的牆上,張貼著師生共同繪製的卡通課表,學生們對學習、生活的困惑與感受,以及過往去到杭州、上海、雲南、貴州等地遊學的合影。
這裡沒有嚴格的時間表。上午11點,莎士比亞戲劇課開始了——這是一個喜歡戲劇的孩子提議的課程。三個孩子選擇去上課,也有孩子選擇一個人去另一個房間自習。
“選擇不上課還挺常見的,他們可以約導師聊天,自己發起一個學習課題,也可以什麼都不做。上課也有不同的方式,可以參與其中,也可以圍觀。”

學社老師和孩子們圍坐在一起
老師來自各行各業,其中不乏海內外名校出身。他們都或多或少地經歷過生命中的“休學”:有人放棄了中科院博士,北師大碩士的學位;有人下過工地,做過商業地產白領、博物館運營,在不同行業間走走停停。
學社幾乎不教具體的學科知識,比較常見的上課形式是師生圍坐成一個半圓,對選定的議題展開討論。主題多種多樣,有關於教育公平、社會熱點的看法和感受,有對性別教育、生死觀的探討,也有日常生活中人際關係的煩惱和反思。
任竹晞教的是批判性思維,她會帶著孩子們去思考自己不想上學的原因,以及上學到底是為了什麼。“我們天然地就會認為一個孩子應該上學,應該聽老師的話,但是為什麼是這樣的?”

社群會議則是大家出席率較高的活動。“在學社門口的樓道里聞到二手菸怎麼辦”,“我可以帶小貓小狗來上課嗎”,這些都是師生們一起討論過的話題。
“他們能夠對於影響自己的事情有知情權、發言權,然後也可以去理解每一件事情是怎麼發生的,這本身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學習過程。”

學社老師會帶著孩子們外出遊學
還有些學習經歷,發生在學社空間之外。
他們去電影院看《初步舉證》和《好東西》。影片結束,一位13歲的女孩告訴竹晞,“我想到平時看的言情小說,現在不忍直視了”;有個男孩則問一位男老師,“什麼是結構性壓迫?”
他們也去北京的公園觀鳥、綠道騎行,逛書店、攝影展和博物館;在進行死亡主題的課題學習時,他們還拜訪了殯儀館。
任竹晞喜歡把學習比喻成一棵樹的主幹長出不同方向的枝椏,是一個主動探索、旁逸斜出的過程。“很多時候我們覺得只有在刷題才是學習,在備考才是學習,但學習是無時無刻不在發生的。”
對於休學的孩子而言,他們最主要的訴求往往不是如何應試升學,而是找到學習和生活的動力,得到理解和接納。換句話說,是到底怎麼找到生命的意義。


任竹晞(正中間)本科畢業於清華大學
任竹晞曾經也是休學者。
她是北京人,1987年出生。她高中考入人大附中,2005年透過高考進入清華大學的電子資訊工程專業。幾年後,她又去哥倫比亞大學讀了教育學碩士。
她承認自己有學習天賦。從小學到中學,媽媽常年在日本工作,她很長一段時間都在姥姥、姥爺的陪伴下長大。“我爸爸是個特別放養型的人,他堅信‘是金子總會發光的’。”
在學習這件事上,任竹晞有自己的方法和心得。她沒上過培訓班,也無需家長督促和操心,成績總是名列前茅,是不少家長口中的“別人家的孩子”。
在高一下那個學期,學校因為非典停學了幾個月,任竹晞把這段時間稱之為“特別快樂的日子”。那時沒有網路教學,她按照自己的節奏自學,上傳老師佈置的作業,回學校後她的成績排名反而更好了。

她也有小小的“叛逆”。她反感形式化的學習,高二時她覺得高考議論文就像模板化的八股,就寫了一篇“為什麼不應該寫議論文”的議論文,交給了老師。“我一定得找到一個方式,讓我覺得學習這個東西是不違心、有意義的。”
這種對學習意義感的叩問在大學時期愈發強烈。
她記得剛進清華的第一週,就有大四學長來做分享,說每門課都要追求95分以上,不擠進年級前20就會很糟糕。在平時的學習生活中,她觀察到許多同學除了上課就是泡在自習室,討論的也更多是哪門課更水,更容易拿高分,而不是哪位老師講課更有吸引力,更能學到東西。
“我好像沒有辦法投入我的全身心去追求一個績點和排名,我不明白我為什麼要這麼做,但身邊更多的人是毫無疑議地就這麼做了。我特別不適,覺得清華的學生不應該是這樣的。”
入學的兩年間,任竹晞把更多的時間花在了社團工作和校園活動上,成績基本在85分左右。現在回頭看,她覺得這其實算一個不錯的分數,可是當時的自己覺得很差,總是感到焦慮和迷茫。


本科休學期間,
任竹晞在美國紐約的大學生社團工作了一年
到大三,她申請了休學。
她分別去到自己大一時加入的大學生社團的北京分部、美國紐約總部各工作了一年。在紐約期間,她負責對接西海岸的幾所大學,幫助當地大學生參加海外的志願者或是實習專案。
在和美國學生交流的過程中,她發現自己會真心地為他人找到目標、做出成就而感到開心和興奮,很享受這種支援他人的感覺。她也從對方身上收穫鼓勵,意識到原來他們也曾感到迷茫,會停頓,而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它讓我激動,我覺得這就是我想做的事情。”休學兩年後,任竹晞決定要做教育。


本科畢業之後,任竹晞去了哥大讀教育
在學社成立的前一年,任竹晞和畢業於北京大學的朋友進入一所中學,與學校合作做全人教育中心。在那裡,她看見一些因為跟不上學習進度被停課的孩子,便開始帶著他們自學。
“一些學生不能上學了,這不是極少數,是存在這樣一個群體的。”
陪伴休學少年6年來,任竹晞感覺休學正變得普遍。她觀察,尤其在疫情之後,休學者的人數有一個絕對數量的上升。在她接觸的學生裡,有抑鬱、焦慮傾向的孩子始終佔據一定比例。
根據《2024兒童青少年抑鬱治療與康復痛點調研報告》,在1232個家庭樣本中,超過一半的孩子經歷過休學,首次休學的平均年齡不到14歲。

15歲的繁繁在去年9月選擇了休學,彼時她剛剛經歷了中考,覺得“再撐三年真的撐不動了”。
還在上學時,她因持續的失眠、胸悶等症狀跑了好幾次急診,最終在心理科被診斷為焦慮狀態。她還記得在一次物理課上,她漸漸聽不懂老師在講什麼,也聽不清,嚇得哭出來。
“我學校的人都對自己有很高的要求,你就被推著往前走,沒有辦法停下來。”為了不被同輩甩下,繁繁每天會給自己佈置額外的學習任務,一度熬夜學習到凌晨,再定好5點的鬧鐘起床。
“我那時會想,如果我中考的時候發揮失常了怎麼辦?我就給自己定更高的目標,這樣失常了也還有餘地,結果是把自己的身體和心理都拖垮了。”

除了難以承受的學業壓力和抑鬱、焦慮的心理狀態,任竹晞看到休學背後還有其他複雜原因。
一個普遍的原因是認知上的喪失意義感。任竹晞曾遇到過一個“特殊”的孩子。她積極懂事、考年級第一,是學校老師眼中的“完美學生”。
觀察了幾天,任竹晞髮現這個女孩“停不下來”——“什麼課她都要參加,什麼事她都要幫忙,其他同學吃飯剩的碗在那兒,她還要去替別人洗”。
後來女孩告訴竹晞,其實她的身體已經很累了,但是大腦不允許她休息,要一刻不停地做一個好孩子。她害怕失去旁人的喜歡,同時覺得大家是因為她的優秀和積極才喜歡自己,她問竹晞:“萬一我停下來,不做了不學了,大家是不是就不喜歡我了?我的人生就沒價值了?”
任竹晞覺得,應試教育讓不少孩子對自我價值的判斷標準比較單一,彷彿一個學生成績不好,他就過得沒有意義,前途會一片灰暗。她感到一些休學的孩子就像大學時的自己,他們覺得迷茫、不對勁,就發出訊號,“我這麼做是為了誰,好像不是為了我”。

另一個常見的原因是不舒適的人際關係,比如過於不平等的師生關係和同伴關係。
任竹晞想起自己小學時每年放完暑假,回校的第一件事是和同學們去操場上拔草,“就是一個土場子,草都長到齊腰高”。放學之後,她會很自然地去附近的朋友家串門,或者約好在外面玩。
然而,這一代孩子從小上課後延時班和各種培訓班,自由玩耍的社交時間變少了,“在遇到人際上的困難的時候,他們不知道怎麼修復或去面對,容易變得比較極端,一言不合就拉黑了”。


現在,繁繁最常做的事是躺著。她還在吃調節焦慮狀態的藥物,但當軀體化的症狀到來時,她不再恐懼,而是坦然接受它的來臨。
任竹晞和老師們會鼓勵孩子去關注自己的感受。而這在過往的教育經歷中經常是被忽視的。
“我們最開始想要去請一個人描述你的感受是什麼,很多人會說我不知道,或者有時候他說是感受,其實他說的是想法。”
在學社,情緒得到了更自然地安放。一次,一個學生突然在房間裡放聲大哭,沒有人感到奇怪或是上前強行安慰,只是有人輕輕地去把門帶上。
有一位已經從學社“畢業”的孩子曾寫下一句話:覺得情緒來了,就像是有人給你送快遞了,你只要開啟門讓ta放下。

任竹晞在“休學”主題展覽現場
與一位成年女性交流
休學不僅是孩子的事,也是家長的事。
找過來的家長多數來自如體制內的老師、醫生等循規蹈矩的職業;超過90%是媽媽,她們基本都非常焦慮。“爸爸很多時候是隱形的。夫妻是同時出現的,其實孩子的狀態也會更好一些。”
任竹晞觀察,不少家長對休學帶來的不確定性感到非常難受,有些爸爸一上來就問結果,想知道孩子什麼時候能離開這裡,重新回去上學。
“就像在一個高速路上行駛,本來一切都很明確,突然有一天被甩下來了,開始懷疑是不是過往所有一切都做錯了,又想趕緊回到高速路上去。”

任竹晞的女兒參與佈置展覽現場
8年前,任竹晞成為了母親,現在有一個上小學二年級的女兒和上幼兒園的兒子。女兒幾乎與學社同步成長,她常常能和一些媽媽感同身受。
女兒是高敏感人格,對情緒的感知和表達異常敏銳,也更容易接收到來自學校、生活的各種各樣的壓力。
有時候,這種情緒會過載,女兒會說自己不想上學了。竹晞和她聊才知道,女兒不想上學的原因是許多個細碎時刻的累積:怕疊不好教室櫃子裡的衣服,擔心英語考試考砸,被弟弟吵得沒睡好覺……
後來,任竹晞和丈夫會主動和女兒約好一週裡在家休息的時間。

“人生就是走走停停”
任竹晞覺得現在大眾對休學還是存在很多誤解,她曾經也質疑過自己是不是不夠標準,為什麼別人都能按部就班地選擇,自己就總是卡住。一些休學者甚至會自我汙名化,說“這就是一個精神病院,一個躺平的大本營”。
“不上學不代表什麼,只是停下來,調節一下,思考一下自己的路怎麼走。”


多數孩子會在學社停留一年左右離開。竹晞做過統計,超過一半的孩子會繼續去上國內外的中學,也有一些會選擇讀大學預科,去做實習,去創業。
曾有一個孩子透過高考考上了一所不錯的國內大學,又在本科期間退學,選擇去日本讀書。“生命變得更有彈性了,不是說一定要按照這一個時鐘去走,方式是多種多樣的。”
部分孩子迴歸學校後又會聯絡竹晞,說自己最近狀態很不好,不喜歡哪個老師粗暴的管理方式。但孩子的處理方式會發生改變,過去可能是不上學,現在會嘗試和老師溝通,比如作業交不上了,問老師能不能寬限幾天。

學社的孩子和老師一起大笑
任竹晞覺得,孩子聯絡的支點變多了,自己、曾經認識的老師和同學都組成了他們的支援系統。
“他們知道會有困難,不能期待說一條完美的出路,主動選擇和被動接受是不一樣的。”
6月下旬,任竹晞組織孩子們舉辦了一場面向公眾的休學主題展覽。展覽的展品是許多個不同的紙箱,上面貼滿了孩子們分享的休學故事、情緒感受和支援的話語。
竹晞與前來觀展的人群交談,聊休學孩子分享的故事。人們在不同的紙箱前駐足、坐下,仔細閱讀孩子們手寫的字跡。

“休學”展覽上孩子們分享的故事
“最終教育反映的是我們社會怎麼去看待一個人,現在大家把自己戲稱牛馬了,我們這個社會沒有把大人當人,所以我們的學校也很多時候沒有把孩子當成一個人去對待。
休學是一種處境,在孩子身上是休學,在職場人身上可能是GAP。我覺得如果每一個人能努力去把自己身邊的小系統營造得更有活力的話,孩子的問題自然而然會解決的。
孩子怎麼走出來,他們的故事也可以激勵到更多成年人。”
注:繁繁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