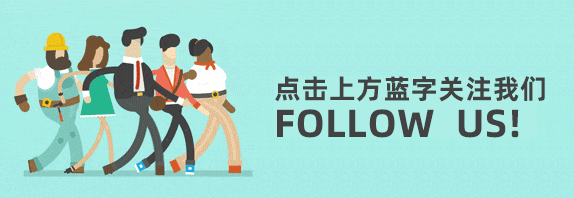提到這所曾一度位居QS全球排名第一的知名大學,不少人大概第一時間會想到“炫酷”,“天才瘋子”,“惡作劇”這些關鍵詞。
怎麼回事?原來,MIT的校訓,是拉丁文“Mens et Manus”(Minds and Hands 手腦並用)。所以,不少學生,都會以成為聰明而且動手能力極強的工程師為目標。那麼,如何體現這一點?實現一個充滿奇思妙想,但又難度極高的惡作劇,無疑是方法之一。
像這樣,把校長的辦公室用佈告欄偽裝起來,只是小兒科。

(圖片來源於網際網路)
更離奇的惡作劇,還有花了七天,把遠在四千多公里之外的,加州理工學院的鎮校之寶一尊大炮偷走,運回麻省理工。麻省理工標誌性的建築“大圓頂”上,更是留下了前輩們的無數“花活”:把它裝扮成萬聖節的南瓜,把警車、消防車搬上了圓頂……



(圖片來自網際網路,可上下滑動)
有意思。那麼,MIT的學生們,到底是什麼樣的一群人?這所學校,到底藏著怎麼樣的秘密?
帶著這樣的好奇,我們來了。


來到這裡,一種感覺油然而生:還好,當年沒有被哈佛收購。
為什麼這麼說?
早在上個世紀初,因為戰後經濟疲軟,麻省理工學院支付不起擴建校園的費用,而學生的數量又在逐年上升,所以一度陷入了財務困境,面臨被哈佛大學兼併的局面。哈佛開出的條件,不可謂不優厚。麻省理工可以獲得更多的資金支援,共享教育資源。
這聽起來很好。但是,MIT的教職工和校友們,都強烈反對。
因為他們,可能不太認同哈佛的理念。
啊?哈佛這種頂級名校,還不認同嗎?
還真不認同。你看啊,哈佛的校訓,是“Veritas”(真理),強調追求真理。而MIT的校訓是“Mens et Manus”(手腦並用),強調理論與實踐的結合。

這種不一樣的教育模式,可能要求它必須獨立辦學。最後,兼併的提議,還是被否決了。
而事實證明,這個決定是明智的。今天的麻省理工,已經發展成為全球頂尖的理工院校,擁有獨步天下的工程學和計算機科學學院,培養出了無數改變世界的科學家和工程師。
這裡,還誕生了無數創業公司。根據麻省理工學院釋出的報告,校友企業家的公司,年收入近2萬億美元——這一數字超過了世界第十大經濟體的國內生產總值(GDP)。
而如果你身處麻省理工,想要學習哈佛的課程,也有辦法。每個學期,你可以去哈佛選擇你喜歡的課程學習,也能獲得被麻省理工承認的學分,只不過,原則上不超過50%。
有時候,拒絕一個看似誘人的機會,堅持自己的與眾不同,反而能走出一條更精彩的路。
MIT不光是這麼要求自己的,也是這麼期待學生的。


鬆弛,但雞血
在MIT的Media Lab,我遇到了一位劉同學。
他22歲,剛讀研究生,雖然年齡並不大,但你卻能從他身上感受到一些特別的東西——不光是從容,還有一種飽滿的,對自己正在做的事情的自信和熱愛。
“我在MIT學習的一個重要收穫,就是找到了自己想要什麼。”劉同學說。
聽到這句話,我特別有感觸。
過去,我們一直在被告訴“該做什麼”,但卻很少有人問“想做什麼”。考個好學校、找個好工作、升職加薪,這似乎就是我們追求的全部。
但是,人生或許還有別的活法。如果有天,你能夠以熱愛為驅動做事的話,生活大概會變個樣子。
就像我遇到的另一位前阿里員工一樣。這位朋友,正好在MIT讀書,知道我來了波士頓,就邀請我一起吃早飯。他說,來MIT讀書之後,做自己喜歡的事,整個人都變鬆弛了,像打了雞血一樣。
嗯?不是在大廠的狀態,才更像“打雞血”嗎?
不是的。當你真的在做自己喜歡的事情的時候,你是能從床上彈起來的。這,才叫真打雞血。
不過當然,當你要為活著而奮鬥的時候,追求熱愛就成了奢侈品。但我還是祝願你能有一天,也可以做熱愛的事情。因為這世界上,還有很多事情的發生,不太能用錢驅動。
比如說,科技的發展。



在Media Lab,最重要的是找到熱愛
如果以錢為目標,那麼一門新技術,大概很難被開發出來。
因為,對於一項科學技術來說,想要轉化成產品,被人買走,產生商業價值,獲得回報,往往要隔上很長一段時間。
從被髮明出來,到人人手機上的應用,鋰電池花了十幾年,觸控式螢幕花了幾十年。無線充電技術,從提出到應用,更是花了一百多年。
如果發明觸控式螢幕的科學家們,只想著“這玩意兒能賺錢嗎”,那今天的iPhone可能就不會誕生。如果發明電子墨水屏的研究員,總想著“這東西有市場嗎”,那今天的Kindle也不會問世。
那怎麼辦呢?關鍵還是,熱愛。熱愛,是最好的老師。
當你真正找到自己熱愛的事情時,你就不會再把它當作工作,而是會把它當作使命。
所以,你能在MIT Media Lab聽到一個特別常見的問題,“你到底想做什麼?”
Media Lab成立於上世紀80年代,是一個為了打破傳統學科之間的壁壘,而成立的跨學科研究平臺。雖然Media Lab被譯作“媒體實驗室”,但它的本意,卻並非“媒體”,而是來自英文單詞 medium,有“跨界”的意思。

(圖片來自Media Lab官網)
當時,很多人不理解。MIT這樣一所嚴謹的工程學校,怎麼會去搞數字藝術、互動設計這些“不務正業”的東西?
但讓大家沒想到的是,正是這個“不務正業”的實驗室,開發出了一系列改變了世界的成果。
比如,著名的Scratch程式語言。它以圖形為主,孩子們無需背誦程式碼,只需將圖形拖放操作即可。到現在我才知道,這個小米同學從小就開始學習的程式語言,是從MIT出來的。又比如,家喻戶曉的電子墨水屏,樂高機器人,都是出自於此。
而這天,我們還在這裡看到了為可穿戴裝置打造的柔性纖維研究、音樂和人神經的研究、神經元植入式腦機介面的研究……
或許,這就是科學的魅力:在商業價值之外,追求人類認知的邊界。
在這裡,眾多大公司匯聚一堂,提供每年高達10多億美金的預算,供研究人員自由探索創新。這些公司,僅提供經費,以便前來交流學習,看看研究成果能否應用於自身業務。
所以,當我們說“不能用錢衡量”的時候,不是說錢不重要,而是在說:一個真正文明的社會,應該為那些無法立即產生經濟價值,但對人類發展至關重要的事業提供土壤。
而能讓這裡源源不斷產出新成果的原因,鼓勵學生去做自己真正熱愛的事情算一個,還有一個,可能是:思想上的集體主義。


美國人,在思想上可能更集體主義
MIT的一位同學,向我們提到一件很有趣的現象。
在MIT的課堂上,華人的學生喜歡往後排坐,不怎麼參加討論。即便是這裡上課有強制要求,必須舉手發言,否則拿不到參與分。可即便如此,有些華人同學寧願不要參與分。而其他國家的學生呢?就坐在前邊,經常舉手,參加討論。
是他們水平更高嗎?能一下子就輸出很厲害的觀點嗎?
不是的。而且,會產生這樣的疑問,說明你和這些華人的同學一樣,掉進了一個誤區裡。那就是:一定要等想好了再說。
但很多來自其他國家的同學,可能不這麼覺得。沒想好就說,也不要緊。因為雖然你說的不一定對,但這一句話,可能會激發集體裡的另一位同學,讓他產生一個厲害的觀點。
有意思。我們常常說,中國人更集體主義,而美國人更個人主義,但在思維方式上,可能恰恰相反。
或許,真正的集體,不是每個人都追求完美,而是每個人都勇於貢獻自己的不完美。
在MIT,學生們更在意的不是“我說得對不對”,而是“我的想法能否幫助團隊前進”。這種集體智慧的碰撞,才是創造的源泉。
而只有參與創造,才能真正進步。
劉同學說,我們這裡有一門課,大受歡迎,就叫做“How to make almost everything”(如何製造幾乎一切東西)。


他們的吉祥物,是河狸
製造一切?好大的口氣。我倒要看看,你們是怎麼製造的。
不聽不知道,一聽嚇一跳。要修這門課的,你要學習和掌握雷射切割,CAD(計算機輔助設計),電子電路設計和製作,3D掃描和列印……把這些學完,好像還真的“什麼都能做”。
劉同學介紹,這個實驗室的特別之處在於,任課的工程院院士尼爾·格申菲爾德,凡事都願意親力親為。正常情況下,學生往往是自行設計,然後交給工廠打樣,但他更希望學生掌握全流程技術。他們甚至與機床廠商合作,協助更新、研發運動控制系統。

(圖片來自:makerlog)
這門課體現的,就是MIT的創造精神。
同樣體現MIT創造精神的,還有他們的吉祥物,河狸。

(圖片來自網路)
河狸是大自然的頂級建築師,勤懇、努力、不知疲倦。它們能夠透過被咬斷的樹木,樹枝和泥土,建造起復雜龐大的水壩,為自己提供安全的棲息地。

(圖片來自網路)
選擇河狸作為吉祥物,也寓意著MIT希望從這裡走出去的學生們,能像河狸一樣,勤懇、努力、並有著強大的創造能力。

於是,在MIT的很多實驗室裡,透過透明的玻璃,你都能看到學生們在裝置前動手做東西。
所以,很多MIT學生的學習,就並非僅僅基於考試,而是基於專案。就像很多關於電機控制的問題,他們都是自己查閱資料,向其他研究員請教,自行設計方案。而當你親自做東西時,內心會強烈渴望它最終能夠成型,目標感十足。
這種狀態,就讓我很羨慕。
我是學數學出身,哪怕做過一段時間技術,也是計算機相關。這些學科,就有一個特點:沒有實體。所有的試驗,也都是在大腦裡,紙上,電腦上進行的。很少能體驗到,在物理世界中做出實體的成就感。
而這,就又帶給MIT的學生們一種,理工科的浪漫。


理工科的浪漫
什麼叫理工科的浪漫?
在MIT,你有可能會收到這樣一種禮物:你的大腦模型。先掃描,再用3D列印技術,1:1打印出來。
有點意思。不過,打印出來又能怎麼樣呢?
哎,不一樣。一位女同學說,當他們把我的大腦打印出來之後,我發現自己的左半邊大腦比右半邊大腦大一些。這感覺,很奇妙。
把大腦打印出來送你,這就是理工科的浪漫。
雖然這在很多人眼裡有點“直男”,甚至有點“驚悚”,但他們樂此不疲。
類似的例子,還有:MIT特地把三十多萬學生的名字,用奈米技術刻在了一個晶圓上。對,就是那個做晶片的晶圓。

(圖片來自網際網路)
又比如,這個杯子。
你知道,這個杯子上的複雜公式,是什麼意思嗎?



從他們身上,我看到了優秀的人應該有的模樣
在接待我們的3位來自MIT的年輕中國學生身上,我看到了真正優秀的人,應該有的模樣。
要知道,能考入麻省理工或者哈佛的學生,都是中國最頂尖的人才。每年,想要去這兩所高校求學的中國學生數不勝數,但這兩所高校,每年在中國大陸招收的學生,可能還不到10個人。
那麼,我從他們身上看到了什麼呢?
這首先,就是使命必達。這一點,從一路帶領我們講解的女同學身上,體現的淋漓盡致。
既然來帶領我們參觀MIT,那麼就要能講解的地方都儘量講解。哪怕嚮導不斷催促,說時間來不及了,但她還是說,這個地方不能錯過,那個地方也要說明白。正門入口的一段話,是哪位負責人寫的,這裡的海報,又有什麼故事……
雖然這可能只是她的兼職,甚至是幫忙,但你絲毫見不到敷衍。
還有,就是知道自己想要什麼。
劉同學說,在求學的過程中,不斷地有人問他,你到底想要什麼?你到底喜歡做什麼?熱愛什麼?
幸運的是,他找到了。就是動手做出東西,就是和這些裝置和機器打交道。所以,他選擇本科畢業之後,繼續在這裡攻讀合金和陶瓷材料領域的碩士學位。每天回宿舍睡一覺,睜開眼睛就立刻返回實驗室,爭分奪秒地投入。
他還和我們分享了另一位MIT學生的故事。他創業的專案,就是3D印表機,目前這家公司的估值,大概有50億美金,很多航天領域的著名企業,比如NASA、Space X,在3D列印火箭發動機的時候,都會用到他們的裝置。
本來,劉同學以為他只是一個到處拉投資的人,但沒想到,他對技術的熱情堪稱痴迷。每次前來交流,都會和研究員們聊個不停。
此外,我們還見到了另外一位女同學。在她身上,我看到了目標感和強大的洞察力。
高中時期,她就在USACO(美國資訊學奧林匹克競賽)裡,取得了全球前五的水平。並以全年級第一的水平考入了MIT,可見其智商超群。
而提到自己被錄取的原因,她也很謙虛,說自己可能就是擅長考試。但實際上,她很懂得在做事之前,看清楚底層邏輯。比如,SAT考試。SAT考試由ETS負責,ETS雖然是非盈利機構,但也需要考慮成本收益,所以不會經常去更新題庫。所以,她在花了一週刷完舊題之後就去考試了。
此外,作為一個20歲出頭,剛剛進入CSAIL(計算機科學與人工智慧實驗室)的學生,她居然已經開始創業了。
她說,我們做出了一個比現有的Chat GPT更精簡的模型。ChatGPT3.5的引數,當年足足有1750億個,但每次訓練,都需要重新把所有引數調整一遍,我們用了更高效的方法,需要幾千萬個引數,就能滿足一些企業的需求。目前,她已經有了一些簽約客戶了。
太厲害了。
看著這群朝氣蓬勃的年輕人,我忍不住說,人工智慧正在爆發前夜,你們遇到了好時代。真羨慕。



每個人的時代,都是最好的時代
我知道,我知道。
“每個人的時代,都是最好的時代”這句話,其實很多時候,是被用來安慰現在的年輕人的。
什麼意思呢?這幾年,我不止遇到一位年輕人這麼說,機會都被上一代人拿走了,然後老人就安慰他們,說哎呀,每個人的時代,都是最好的時代。
可是在MIT,我看到了這些優秀的中國年輕人充滿朝氣,全神貫注去做自己熱愛事情的樣子,一種羨慕就油然而生,所以說出了“你們真是遇到了好時代”這句話。
但沒想到的是,他們居然反過來安慰我,說,每個人的時代,其實都是最好的時代。
這一方面,可能意味著,他們也同意,今天這個時代,確實是對年輕人來說是個好時代。
另一方面呢?或許,對真正願意改變世界的人來說,無論什麼時代,都是好時代吧。



這裡,有著改變世界的力量
是的,改變世界。
不光是我們前邊提到的Scratch程式語言。從曼哈頓計劃早期的技術成果,再到微波雷達,電子郵件(E-mail)、電子表格、乙太網、全球資訊網、滑鼠、可消化的膠囊機器人……
在MIT,誕生過太多能夠改變世界的東西了。
不少人,傾盡一生只是在研究一個看起來很小的課題,比如某種特殊的疾病,像阿茲海默症。這可能要花上幾十年才能看到研究成果,但他們依然在堅持。
或許,在MIT,創新不是為了賺錢,而是為了實現改變世界的夢想。
這就是為什麼MIT的校訓是“Mens et Manus”(手腦並用),為什麼他們的吉祥物是河狸。
因為在這裡,每個人都在用雙手,把想象變成現實,把創意轉化為改變世界的力量。



真正想改變一個國家,最重要的是教育
最後,和你分享一個我在MIT聽到的小故事。
某天,當尼爾·格申菲爾德院士在國會聽證的時候,提到自己的小型實驗室遍佈全球,而這對美國未來國家安全至關重要,甚至涉及國防領域。有人質疑:為什麼要在教育上投入這麼多?這和國家安全又有什麼關係?
另一位議員拍案而起:你知道嗎?對於一個國家來說,真正的核心就是新一代的教育!
是啊。如果想改變一個國家的未來,最重要的不是GDP,也不是軍事力量,而是教育。
這一天,我看到了一個完全不同的教育生態。這裡的學生,不是為了分數而學習,而是真正以做出專案為樂趣。這裡的課堂,不是我說你聽,而是互相探討。實驗室裡呢?也有很多專案,一會做材料,一會又轉向了機器人,接著又去做晶片了,你可以自由選擇,怎麼切換。
這種教育模式,培養出了什麼?
有的同學,剛入大學,就致力於革新大模型技術,創業並簽約客戶。有的同學,要做什麼就要做好,使命必達。有的同學呢?更是找到了熱愛,天天像打了雞血一樣,眼裡有光。
但更重要的是,在這裡,我看到了一種永遠保持好奇、熱愛學習的精神。
或許,這就像這裡的一所實驗室名字一樣:Lifelong Kindergarten(一輩子的幼兒園)。學習,不應該是痛苦的負擔,而是充滿樂趣的探索。創新,不是完成任務,而是實現夢想。研究,也不是為了晉升,而是為了改變世界。
又或許,在一個好的教育制度裡,孩子們應該把科學當作興趣,而不是把科學當作賺錢的工具。教授們,能在這裡賺到錢,而不是必須去外邊去賺錢。發論文,也應該是自己的榮耀,而不是拿職稱的工具。
因為,一個國家最寶貴的資源,不是礦產,也不是資料,而是年輕人的創造力。
而教育,就是激發這種創造力的關鍵。
P.S.
坐在家裡,只能揣測。去到現場,才有答案。
2025年,我們會繼續走在問道中國、問道全球的路上。
去年1月,我們去到了中東(沙特、阿聯酋)。6月,我們去到了日本。9月,我們去到了美國、墨西哥。12月,我們去到了東南亞(越南、印尼)。
此刻,我們正在美國東岸,看文化與創新,碰撞出了什麼樣的火花。
然後,2月7日晚上19:00,我會在劉潤影片號直播間,與你毫無保留地分享我在美國東岸的所見所聞。
歡迎你點選下方“預約”按鈕,來直播間坐坐。

接下來的3月,我們還會去到新加坡。看看這個地域狹小、天然資源匱乏、人口不到600萬的小島國,是怎麼在世界舞臺上脫穎而出的?

6月,我們要去英國。看看“世界第一城”的美譽,究竟從何而來。

之後的8月,我們要去非洲。看看那片最狂野的土壤裡,開出了什麼樣的花。

現在,我也想邀請你,與我同行。
一個人,要讀萬卷書,也要行萬里路。因為,一個人的成就,大不過他的夢想。一個人的夢想,大不過他的所見所聞。
如果,你也對這樣的一線遊學感興趣,歡迎你加入我們。
讓我們一起,行萬里路,問道中國,問道全球。

*個人觀點,僅供參考。
參考資料
-
自然界中真正的“建築大師”:強者從不抱怨環境!
https://www.kepuchina.cn/article/articleinfo?business_type=100&ar_id=531492
-
Twenty-five ways in which MIT has transformed computing
https://news.mit.edu/2019/25-ways-mit-has-transformed-computing-0225

觀點 / 劉潤 主筆 / 景九 編輯 / 二蔓 版面 / 黃靜
這是劉潤公眾號的第2499篇原創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