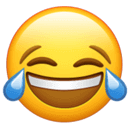本文轉自:北貝BOOK

“生下你,是我為數不多的正確選擇之一。"
我們總在意外中與命運狹路相逢,在掙扎中與苦難握手言和。樹兒,是一位平凡女性體內原始母性的衝動與勇氣所結出的果實,這果實,也是一道溫柔又刺痛的遙遠星光。
《樹兒:我的女兒來自星星》的作者朱矛矛以坦誠細膩的筆觸,記錄下了與孤獨症女兒同行的十年,敘述了愛與磨難交織的日常。她感受過絕望,因此更願意散播絕望盡頭綻放的希望。
她是樹兒的世界起點,樹兒是她來自星星的荊棘冠冕,這人間,因羈絆與連線而變得值得。或許我們每個人,都能在這裡找到自己與世界和解的影子,領悟到生活不過是笑有風沙,淚有鹽巴。

樹兒的照片
我的女兒來自星星,也帶我回到人間
文/朱矛矛
我的孤獨症女兒樹兒已經11歲。她現在成了一個微胖的、身高一米五的大高個小學三年級生。她的眼神依舊百分百清澈,肉乎乎的臉蛋笑起來依舊百分百治癒,說起問句來總是瞪圓了眼睛、撅起小嘴,面部表情略顯誇張。她已經成了我的生活小助手,收拾碗筷、洗衣晾衣、倒垃圾、掃地、下樓打醬油樣樣行。她特別享受乘坐交通工具的過程,我們會趁週末來一場說走就走的短途旅行,私家車、公交車、輕軌、動車、渡輪,全都坐過。她經常會明知故問,或者問些在我看來莫名其妙的問題,我們的對話依舊存在大量對牛彈琴的情況。每天晚上熄燈後,我依舊習慣進她房間,親她的臉蛋,跟她道晚安。
她的世界早已不再只有我一個人,還有爸爸、外婆、學校裡的老師和同學、康復師、美術老師、音樂老師……曾經,我深陷於生下一個孤獨症女兒的不幸泥沼中。樹兒確診已經五年了,日子依舊在過,我已經與這百分百的不幸和解,我付出了百分百的愛,這愛塑造了女兒,同時更新了我自己。
千萬分之一的機率,百分百的不幸
據中國殘聯2023年釋出的中國殘疾人普查報告資料顯示,中國孤獨症患者已超1300萬人,且以每年近20萬人的速度增長著。現在孤獨症孩子的出生機率已經達到近1/100。在普通學校,一個年級段裡面起碼有一兩位不同障礙的特殊兒童。
對於國內數量龐大的孤獨症群體來說,樹兒只佔比千萬分之一。但這千萬分之一的機率實實在在落到我家裡,就成了百分百的不幸。“孩子患孤獨症是個機率問題,它既然可以發生在別人身上,為什麼不能發生在你身上?”精神科平醫生反問我。
每個孤獨症孩子的父母接受自己的孩子是個孤獨症孩子的時間長短不一。我從得知樹兒患孤獨症的噩耗不知所措,到釋懷坦然,花了近一年時間。這在我周圍的孤獨症家長群裡算短的。因為我的家族有精神病基因,我母親和我都是雙相情感障礙患者,我的內心深處可能早就做好了生出一個“不正常孩子”的準備。甚至為了杜絕“瘋血”代代傳的悲劇,婚後五年內,我經歷了一次自然流產(胚胎卵黃囊停止發育),又近乎偏執地選擇了三次人工妊娠流產。這樣算起來,樹兒算是我第五個孩子,命中註定是“吾兒”。

我的人生是錯題集,生下你是我為數不多的正確選擇之一
懷上並決定生下樹兒是一場意外。2014年春節,我和樹兒爸坐了三十幾個小時的綠皮火車去四川榮縣探親。我意外懷上了樹兒,而這趟旅程,改變了我對於是否要當媽媽的想法,解開了我一直排斥擁有一個自己的孩子的心結。
在樹兒爸老家,我和7歲的侄女奇娃一起玩地理拼圖遊戲。
“奇娃,你長大了想幹什麼?”
“像媽媽一樣,生個小奇娃,把她養大。”
我被奇娃的回答觸動,一瞬間萌生了生一個像奇娃一樣的,以媽媽為榮的孩子的想法。從四川省親回來,我想要當母親的慾念再一次蠢蠢欲動,我最終做出了一個或許會被認為自私的決定——我要生下我的第五個孩子。
懷孕期間,我就為孩子取好了乳名——樹兒,取其平穩、正直長大的寓意。2014年10月18日晚上七點,樹兒出生了。
被貼上孤獨症標籤之前和之後,你始終如一是我親愛的女兒
在樹兒五歲前,全家一直把她當成一個普通孩子看待。她天生捲髮,出汗後,頭髮會變成羊毛卷,尤其到了盛夏,她經常熱得像鍾馗一樣。她很愛哈哈大笑,笑起來像只招財貓,笑點低且莫名其妙,一不留神就會觸發大笑開關。
除了身高體重發育偏快,其他各方面她都算是發育偏慢的。三歲斷奶,四歲戒斷尿布、牙才長全,說話一個字、一個字往外蹦,很難說出一句完整的話,從1數到100學不會。當全職媽媽的頭五年,我時常感到精疲力盡。樹兒一直精力旺盛,幾乎不午睡,而我因為服用精神類藥物,經常出現嗜睡的副作用。我和她之間很少有語言交流,大多靠肢體語言溝通,每次說一個指令,我需要重複喊她的名字三四次,她才會跟我眼神對視。

樹兒的畫《到月亮上滑滑梯》被法中促進友好協會收藏
隨著樹兒慢慢長大,我發現她從不跟別的同齡孩子玩,比如在小區樓下花園,假如有其他孩子在場,她會立馬躲開。我慢慢意識到她的“朋友”都是成年人,這並不正常。不和孩子玩,這在我和樹兒爸看來是比較糟糕的事。因為孩子的成長、學習,都需要依靠同伴的幫助。2018年,我每週六帶樹兒去參加一個名為“親子開放空間”的兒童遊戲、心理諮詢公益專案。連續參加數月後,專案負責人Lisa告訴我,她擔心樹兒有孤獨症趨勢。
2019年12月,樹兒五歲零一個月大的時候,被確診為典型孤獨症並伴隨輕度智力障礙。“你的孩子現在干預已經有點晚了,如果不好好幹預,她將來可能沒辦法正常上學,沒辦法正常工作。”
我的天塌了。
從確診那一刻起,樹兒就不再是個普通的活潑好動的孩子了,她曾治癒我們的哈哈大笑,一下子變成了孤獨症兒童的刻板行為。樹兒成了孤獨症譜系障礙兒童,我成了一位孤獨症譜系障礙兒童的家長。
而後,我花了近一年時間才從“殘次品思維”中擺脫出來,意識到樹兒本身的珍貴。我放棄了追求“正常”的執念,慢慢接受樹兒患孤獨症這一生活中的非正常因素。我不再帶著自責去幻想:要是不是她,或者她是個普通的小姑娘該多好。我內心那些複雜糾結的情感漸漸消退了,被貼上孤獨症標籤之前和之後,她始終如一是我親愛的女兒。
但樹兒爸很長一段時間都未能從樹兒患孤獨症的打擊中走出來,心情煩悶喝了酒,就會罵我,怪我懷孕期間喝咖啡喝酒亂來,才把孩子“生壞了”,怪我毀了樹兒的一生——“你欠樹兒的,一輩子都還不清。”

樹兒一家
當然,樹兒爸也是深愛著樹兒的。從樹兒剛出生,他就是一個稱職的奶爸,給孩子換尿布、餵奶、洗澡、剪指甲、梳小辮,他樣樣都手熟。他和樹兒之間有他們獨有的溝通語言,兩個人會玩在我看來挺無聊的遊戲,並樂此不疲。現在他仍像樹兒小時候那樣陪她玩耍,陪她追動畫片,不厭其煩地回答樹兒機械、重複、刻板的有關劇情的提問。
樹兒爸的自律和務實,也成了維持這個家不散掉的關鍵因素之一。有困難時他能夠託底,“我們自己先把自己保好,等她長大了,給她辦低保。情況再好點,還能找到一份簡單的工作。或者我退休在廠裡當保安,讓她進廠,我帶著她幹活,這樣生活問題就能解決了。腦子有點不好不要緊,關鍵是學會節省,肯幹活,性格不悲觀,才能活得好”。這種對樹兒未來樂觀的看法與孤獨症家長圈裡流行的“爸媽走出來,孩子有未來”的觀點不謀而合,多少撫平了我一貫的焦慮。
康復五年,樹兒終於不再是個對人類不感興趣的“人機”
孤獨症早就被列入了國家特病醫保目錄,但真正能在全國範圍內的一些省市普及推廣刷特病醫保,則是2023年以後的事了。
拿到評估師的“死刑判決”不久,我們就開始找康復干預機構,一打聽康復費用,一個月如果純自費需要六七千,我們手頭拮据只好去找親戚借錢。
對於佔絕大多數的普通孤獨症患者來說,孤獨症的標籤意味著你將與其抗爭終身,你必須學會與這個病共存,你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才有可能“高度隱藏”在普通人群中。這終身的抗爭不僅需要樹兒自己付出努力,更需要全家的參與,從物質費用到精神陪伴,這是一條一旦走下去就沒法回頭的路。

2020年樹兒開始接受康復訓練。2021年,我們選擇讓原本已達入學年齡的她,緩學一年,全天候在某精神病院下屬康復機構康復。經過兩任康復師的教育打磨,樹兒逐漸從一塊頑石被打造成一塊初具雛形的璞玉。我親眼見證到,樹兒說話的句子長度越來越長,她學會了識別喜怒哀樂等基本面部表情,她有了日月年、分秒時的時間概念,她能參與主題聊天,她能看片子猜測劇中人物的想法(心智解讀對於孤獨症孩子來說是尤為困難的),她原先的不停自轉、轉動手腕的刻板行為消失了……可能只有孤獨症家長才能懂,看到孩子一次次對普通人來說小到幾乎不存在的進步時,喜悅到底能有多大。
語言能力得到提升後,她的世界拓寬了,她有了強烈的聊天慾望,進而衍生出一點點的社交動機。作為孤獨症核心障礙之一的社交障礙,正在一點點被消除。參與康復近五年,樹兒終於達到了對於普通孩子來說理所當然的社交水平,她變得不再懼怕同齡人,能夠被動參與同齡人的社交了。由於她心智發育偏低,她和低幼年齡段的孩子玩耍更容易,鄰居家上幼兒園大班的男孩成了她的朋友。
在得知她患孤獨症後,我一度以為她不會在意別人的情緒,便把她當樹洞,隨時隨地向她傾倒各種負面情緒的垃圾。那時候的她,看著我痛哭流涕也無動於衷。樹兒七歲時,有一回我崩潰大哭不止,她凝視了我幾秒,說“媽媽不哭”。那是她出生七年來,第一次和我有了明確的情感互動。從那時起,我再也沒有把我的女兒當成“樹洞”。我的女兒,終於不再是個對人類不感興趣的人機了,而我也被她拉回了人間。

重生之和女兒一起上小學
雖然我和樹兒爸都不太懂孤獨症康復理論,但我們有一個樸素的想法:一個孩子從同齡人中學到的,一定比跟著大人學到的更多。會玩、肯玩的孩子,不至於太糟糕。
樹兒的康復一直比較順利,2022年9月,她成了一名普通公辦小學的小學生。我也成了全班唯一一位陪讀家長。一年級整個學年,我都可以自由出入學校。從現實情況而言,現在一所普校肯讓家長陪讀,已經是最大的開放尺度了。陪伴樹兒的同時,我還扮演了“講解員”的角色,回答孩子們層出不窮的提問:“什麼是孤獨症?”“樹兒的病能治好嗎?”“樹兒為什麼會得這個病?”“她是傻子嗎?”……
上小學前,我一直擔心樹兒無法適應普通學校的生活,害怕她遭受校園霸凌。親身經歷陪讀後,我打消了許多疑慮。作為旁觀者,我看到了樹兒和普通孩子的真實差距,感受到了現行教育體制下老師和學生的內卷壓力,發現了普通學校開展融合教育的缺陷。同時我欣喜地記錄下,班裡其他普通孩子對樹兒從好奇、不理解到接納、包容、共處的全過程。我珍惜現在樹兒擁有上普校還是上特校的自主選擇權,我會陪伴她繼續探索融合教育的方方面面。

樹兒畫作《生氣的媽媽》
普校融合為主,孤獨症康復為輔,在我看來是目前最適合樹兒的教育。我期待經過後續康復,樹兒的語言準確度能越來越高,詞不達意的情況越來越少。期待有一天,她能夠不用再牽著我的手過馬路,獨立上下學,獨立坐公交去想去的地方;能夠學會量入為出的生活,找到興趣點並將其發展成職業。
養育樹兒,不是我單向的付出。透過與樹兒朝夕相處,我從朋友、普通孩子家長、老師們的肯定中找到了嶄新的自我價值。樹兒的孤獨症成了治癒我雙相情感障礙的良藥。我和她之間是共同成長的師友,她不是我的翻版,她有屬於她自己腳下的路要走。
揭開傷疤的寫作是一場治療,《樹兒》讓我找回自己
2023年12月,我經歷了較為嚴重的躁狂發作。幾乎每天白天泡咖啡館、夜裡熬夜到兩三點,鍵盤敲得像彈鋼琴,一個月內寫出了四萬字的《陪讀日記》。經朋友推薦,這部作品被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旗下的北京貝貝特出版顧問有限公司發起的2024年第四屆“不一樣的社會觀察”論壇看中,而後我決心把這部稿件擴充成一本書。我努力回憶樹兒小時候的樣子,翻找留存下來的各種記錄,寫下我這十年養育她的經歷。
過去十年,我雖然是全職媽媽,但我沒有虛度光陰。揭開傷疤的寫作本身就是一場艱苦卓絕而又痛快淋漓的治療,透過寫作《樹兒:我的女兒來自星星》,我找回了自己。但願這本小書能給更多人帶去對生活的希望。



凹凸鏡DOC
ID:pjw-documentary
微博|豆瓣|知乎:@凹凸鏡DOC
推廣|合作|轉載 加微信☞zhanglaodong
放映|影迷群 加微信☞aotujingdoc
用影像和文字關心普通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