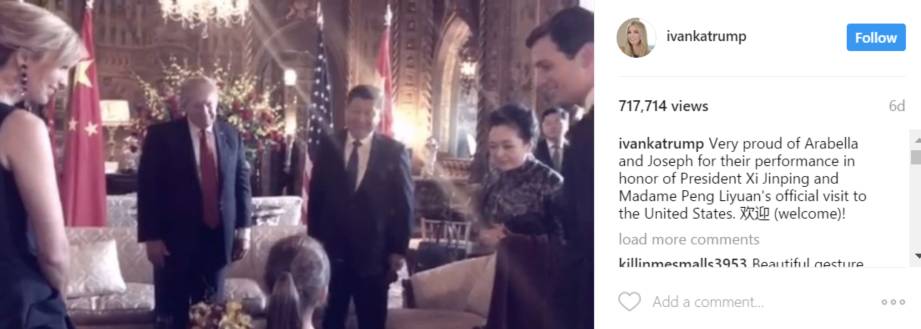前兩天在辦公室和同事聊天,有個同事說:
你們知道嗎?從明星的名字裡,也能看出重男輕女。
大家紛紛七嘴八舌討論起來——
小S的本名就是
徐熙娣
,歐陽娜娜的妹妹
歐陽娣娣
…

歐陽娜娜一家上《康熙來了》截圖片段
其實,給女兒的名字中帶「弟」、「娣」只是最有代表性的性別歧視。
今天,我想從名字入手,帶你們認識一群被名字詛咒的女孩。

2022年,央視網、人民日報等官媒,都報道了一群為自己改名的女孩。
來自河南的招弟就是其中之一。

懂事後,她才意識到自己名字的含義是“給家裡招一個弟弟”。
從此以後,名字就像一個咒語。
一有人叫起,自卑感就撲面而來。

每次自我介紹、上臺發言,她都不好意思說出自己的名字。
哪怕成績優異在學校表彰大會上演講,她依舊會因為名字無所適從。
自我懷疑伴隨她度過整個青春期。
終於,20歲這一年,恰逢《民法典》在同年正式生效,她不顧周遭的勸阻,經歷道道程式,成功改掉自己名字。
新名字她挑了一個自己喜歡的字——
“芃”
。

一個寓意十分美好,生命力很旺盛的名字。
改名後的芃芃,用涅槃重生來形容毫不為過。
她的故事,背後代表的是活生生的,數以萬計的女孩。
名字背後的歧視,也往往比我們想象中要沉重很多。
知乎有個老師,班裡有個叫“夢弟”的女孩子。
有一次跟班裡同學吵架,對方直接對她說:“你爸媽是不是做夢都想要給你生個弟弟”。
夢弟直接傻了,當場崩潰哭了。

孩子的名字,本來承載著父母對孩子的美好祝福。
而招娣這樣的名字,天生就攜帶著不被期待:我的出生是錯誤的,是不應該的,我出生的意義在於召喚下一個男孩。


類似招弟這種名字,隨處可見。

我試著用廣東省政務小程式【粵省事】搜了一下省內幾大姓氏名字叫招娣的重名率,映入眼簾的是4000多個女性。

截圖自【粵省事】小程式
這個數字如此龐大。
《人物》在一篇特稿裡提到,
還有大把令人窒息的命名方式:
有的隨意得讓人難過的:
很多女性的名字裡都有妹字。比如「夠妹」,就是「妹妹夠了,下一個希望是弟弟」,比如「篩妹」、「減妹」,意思是把妹妹篩出去、減掉。
有的表面看起來美好,實則隱藏著惡意的名字:
比如「燕」字,這個名字在當地也很常見,但一個名字裡有「燕」的女孩說,這個「燕」是厭棄的厭。此前在網上還有人說過,自己的名字叫美腰,但這個「腰」真正的意思,是夭折的夭。

脫口秀演員調侃自己的段子
波伏娃有句話是:“女性不是一種性別,而是一種處境。”
改編下這句話:
招娣不只是一個名字,而是一個符號,一個彙集了千萬女性一生縮影的父權符號。
這個符號天生帶著重男輕女的思想鋼印,所有聽到這個名字的人,第一印象都會是:她很可能來自一個重男輕女的家庭,她會不會是伏弟魔啊。

這些女孩,從出身開始,她就註定不會很受父母待見。
她們的生命歷程,或多或少都逃不過被忽視、被嫌棄、被刁難…
辦公室裡有個來自廣東潮汕的同事跟我說,老家那邊還是有大把跟她一樣大的女孩子,只讀到小學或者初中,就要離開家,去廣州深圳看檔口,或者去珠三角的工廠打工…
家裡幾個小孩,
只有男孩有機會讀書上大學,是常有的事。
她還跟我說她一個小學女同學,家裡在當地家裡算蠻有錢的,她自身成績也不錯,讀到高中家裡就不讓讀了,理由是反正要嫁人的,別浪費那個錢。

聽完,我震撼得說不出話來。
比赤裸裸的歧視更虐心的是,這種環境下長大的女孩子,有些也被迫成為這個系統的一部分,淪為
“拼男孩”
的一部分。
沒機會接受更高的教育,沒機會從這個系統逃脫。
家裡嫌棄她們多一雙碗筷,所以她們也普遍早早就嫁人。
在“母憑子貴”的氛圍裡,生出兒子的她們能尚且鬆一口氣。
生不出兒子的備受羞辱,立志“湊一個好字永久封肚”。

無數像她們一樣的女性生活在底層叢林中,受過我們無法想象的苦。
網友們嘲諷她們淪為生育機器而不自知。
而她們也許僅僅是憑藉本能地意識到了,換個性別,或許就能更輕易地活。

這才是現實的底層女性生存現狀。

張桂梅為什麼要創辦華坪女高?
她的出發點十分樸素,也十分偉大。
在資源匱乏的大山、農村和鄉鎮,女性作為底層裡天生的弱勢群體,過著一種像前面所說的惡性迴圈的生活。
所以她說:
“女孩子受教育,是可以造福三代人的”“我想讓我的學生都考上一本”“讓山裡的孩子飛得更高、飛得更遠”

她希望女孩們做的,是飛出大山不要再回學校。
她告訴女孩:作為一個女性,一定要堅強,要獨立,要讀書,用知識來改變命運。
張桂梅的話,也送給每個“招弟”們。
願你們人生不被名字所封印,活出自己最燦爛的樣子!
也願天下,再無“招弟”!

給我們身邊每個“招弟”們
點亮一個“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