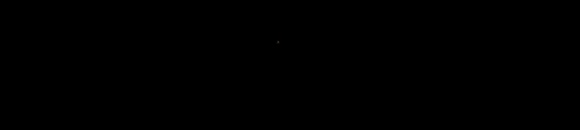撰文 | 尹清露
編輯 | 黃月
“以前我發表論文,但沒有人跟我站在一起,大家還是把假畫當真。”90歲高齡的美術史學者徐小虎身著一襲寬鬆的藍袍,在2024理想國讀者日的活動上這樣說道。
徐小虎的那本以元代畫家吳鎮為個案的研究專著《被遺忘的真跡》曾經震驚了藝術史圈,她的觀點認為許多現今被收藏的中國山水畫是偽作,而她也認為吳鎮現存的畫作中只有三幅半是真作。但是起初,並沒有人相信她,她不得不設計各種方法來測驗是不是自己出了問題,“不管是看筆墨還是結構,結果都是一樣的,我只得承認是沒人願意接受。我不傷心,只是為了他們傷心,因為他們缺乏了真實。”
在讀者日期間,徐小虎與上海大學歷史系副教授成慶在阿那亞進行了一場題為”何處是心靈的庇護所?自然,藝術與信仰“的對談,從兩人的童年經歷開始,談到如何在物質主義的今天保持心靈上的真實。

藝術史學者徐小虎(右),成慶(右)
被畫感動過後,
它就變成了心靈的一部分
徐小虎於1934年在南京出生,幼兒園到中學時期輾轉於南京、羅馬、重慶和上海。在徐小虎看來,在貧窮的重慶歌樂山生活比在富有的上海快樂許多,因為前者的生活更真:“那時揹著饅頭去上學,吃不完就分給野狗,滿路都是杜鵑花,下雨後的土地還有香味。在歌樂山我們和自然是合一的,太陽下山後也是人休息的時間,這些在都市裡都是沒有的。”成慶也回想起小時候回農村騎牛的經歷,要跟著水牛背上那根左右晃動的骨頭擺動屁股,找到韻律感,在他看來,這其實就是藝術。
兒時的經歷與徐小虎後來研究山水畫也有某種關係。在宋朝的畫中,她感受到了一種在畫面之外、無法被動搖的秩序,這在宋朝叫做“禮”,在佛教中叫做“法”,現代人稱之為“operating system”(作業系統)。徐小虎認為宇宙也有作業系統,正是在這個系統下,星星不再互相撞擊,水分蒸發變成雲再化作雨水,讓種子長成一棵大樹,也使得小小的人腦袋裡有那麼多思維。可是在徐小虎看來,人們經常會忘記這些,反而去煩惱物質。“如果你因為沒錢煩惱,那我可以恭喜你們,因為這是完全用不著的,可以放掉了。”看畫也是如此,別人問徐小虎是否收藏或擁有一幅畫更好,徐小虎覺得不用,因為被畫感動過後,它就已經變成了心靈的一部分。
成慶同樣談到物質與心靈的關係,對來到這裡的觀眾來說,阿那亞可能是一個能獲得愉快經歷的世外天堂——“可是阿那亞很貴誒!”成慶提到,“阿那亞”在佛經中翻譯為“阿蘭若”,也就是僻靜之處,以前的僧人要尋找到這樣的地方獨自修行,可是佛家還有一個說法:真正的僻靜並不在於環境,而是心靈的僻靜之處。
父母的責任是發揮孩子心裡的能量
兩位對談嘉賓也談到了教育的問題,認為如今的教育有許多缺失。成慶形容自己在大學上課的狀態,進入課堂就感覺“進入了一個古墓”,非常死氣沉沉,學生們是為了找工作才來到學校,也要承擔社會的期許。徐小虎則認為,之所以要為了職業上大學,沒有學歷就什麼都辦不到,是因為“大人僱傭你的時候,他們不敢用自己的心跟你說話,而要靠別人的打鉤認證”,這是完全不負責的。進而,徐小虎談到教育中的“填表思維”。在臺南藝術大學任教時,徐小虎曾因為太調皮被校長任命做學務長,學著怎樣管學生,學務處的秘書非常官僚,是“站著都在填表“的那種人。
在徐小虎看來,怎樣保護今天的孩子們,也是如今的她最想做的事。她說自己以前的工作是“保護死人”,也就是找幾個已經死掉的老畫家,把他們的真跡找出來,讓博物館不再騙人,《被遺忘的真跡》就是一本保護畫家吳鎮的書,而她現在的生命要用來保護孩子。
徐小虎還有一個理論,她稱之為公共的秘密——她認為大人都很笨,只為孩子的生活著急,卻不為孩子的快樂著急。父母只想讓孩子吃飽穿暖,彷彿這是做父母唯一的責任。徐小虎這樣問觀眾:“你還記得小孩子的時候嗎?那是最重要的時代,因為那時的你想的是什麼能夠讓自己快樂。所以麻煩爸爸媽媽們,不要叫孩子去做牙科醫生或者律師,你要看他在做什麼,然後問問他,你畫畫還需要紙嗎?你要不要去外面走一走?你們的責任是充分發揮孩子心裡的能量,讓他們盛開心中的那朵花。”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撰文:尹清露,編輯:黃月 姜妍,未經介面文化(ID:booksandfun)授權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