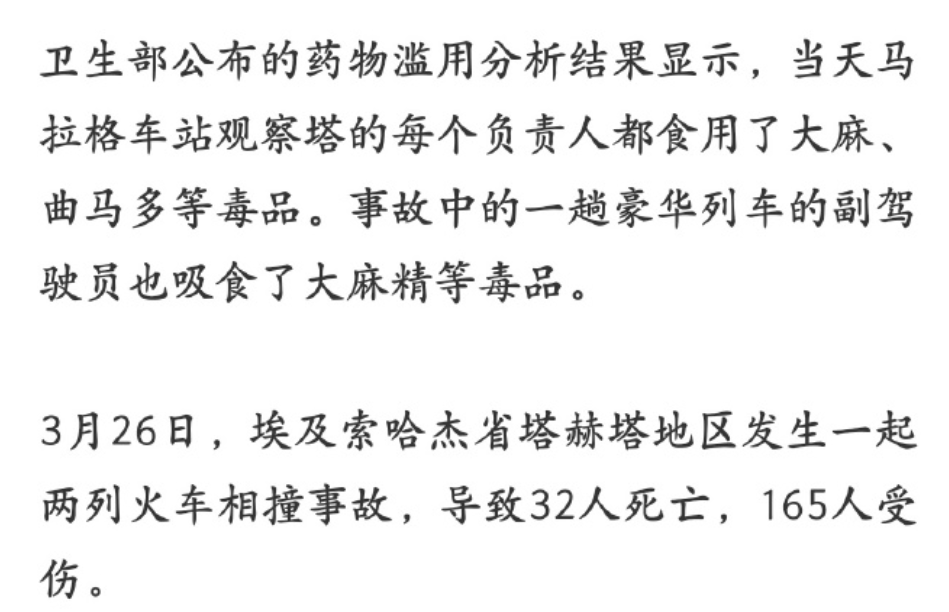如果沒有普京,也許俄羅斯離西方的距離會更遠而不是更近。
因為批評某地的防疫,被封號14天,今天滿血復活。附一下小號的連結。大家也可以去weibo搜同名《西西弗評論》
1、在西化和本土之間糾結的俄羅斯

俄羅斯的國徽是雙頭鷹。這個國徽的來源應該是東羅馬帝國拜占庭科穆寧王朝的國徽。拜占庭是一個橫跨歐洲和亞洲的國家,有人說,雙頭鷹國徽彰顯帝國是東西兩個方向的王者,要統治歐洲和亞洲的領土。俄羅斯,同樣也是橫跨歐洲和亞洲的國家。
雙頭鷹,同時也代表了俄羅斯文化上的糾結。一個鷹頭面向西方,面向西歐。另一個鷹頭面向東方,面向俄羅斯的廣闊無垠的腹地。在俄羅斯的歷史上,面向哪個方向的分歧產生了西化派(Západnik)和本土派(Slavophiles),
一部分俄羅斯人看向西方,希望成為西方的一部分,希望能融入西歐的文化。另一部分人堅持俄羅斯的本土特點。兩方針對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辯論。俄羅斯民族應該走什麼樣的發展道路,它在世界歷史上的地位如何?俄羅斯是應該全盤西化,接受西方文化價值觀?還是應該保留俄羅斯獨特的文化遺產,走具有俄羅斯特色的獨特道路。
這種分歧實際上從彼得大帝的時代就開始了。在十九世紀,當亞歷山大一世的大軍進入巴黎後,俄羅斯人親眼看到了西方的繁華,一部分精英因為看到了俄羅斯與西方的差距,而感到痛苦和反思。另一部分人則堅持俄羅斯的傳統和特點,最終這兩個派別形成並尖銳對立。
2、俄羅斯的歷史與幾次政變
彼得大帝的西化改革的故事,很多中國人都耳熟能詳。彼得大帝的改革也開始了俄羅斯西化派與斯拉夫派數百年的恩怨情仇。從彼得大帝開始,俄羅斯精英就深受日耳曼文化的影響。那時的西化派以德意志派為主。
彼得大帝於1725年去世後,他的妻子和孫子各當了兩年皇帝,1730年,皇位落入了彼得大帝的侄女安娜的手裡。而安娜的情人,德意志冒險家,恩斯特·約翰·馮·比龍握有實權。
比龍在俄國宮廷中大肆引入德意志人,以他為首的一批德意志人,操縱朝政,排斥俄國貴族,將反對他們的處死或流放西伯利亞。當時俄羅斯的軍隊總司令都是德意志人。
1740年,安娜去世後,任命比龍為攝政,輔佐剛剛出生的伊凡六世。伊凡六世與其說是俄羅斯人,不如說是日耳曼人。他的父親是布倫維克的烏爾裡希,母親伊麗莎白是克倫堡-施威林公爵卡爾·利奧波德與伊凡五世長女葉卡捷琳娜·伊萬諾芙娜的女兒。他有四分之三的日耳曼血統。伊凡六世即位僅三週,俄羅斯宮廷中的德意志人就開始內鬥,烏爾裡希聯合軍隊統帥馮·米尼赫推翻了比龍。
然而,俄羅斯本土派不甘心權力被德意志人搶走。彼得大帝的女兒,伊麗莎白聯合近衛軍發動宮廷政變,從德意志人手中奪回了權力,廢黜了伊凡六世。權力重新回到了俄羅斯人和本土派的手中。伊凡六世在位只有1年時間。
這只是第一次權力的輪迴。西方派(主要是德意志派)和本土派的鬥爭,還將一次次重演。
伊麗莎白執政20年,俄國國力大大增強,開始介入歐洲戰爭。1746年參加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1756年參加七年戰爭。聲勢顯赫的腓特烈大帝,屢屢被俄軍擊敗。1758年,俄軍佔領東普魯士首都哥尼斯堡,1760年10月,俄軍一度突襲攻佔柏林。絕望的腓特烈大帝幾乎要選擇自殺。
1762年1月5日,伊麗莎白女皇突然病逝,拯救了普魯士和腓特烈大帝。繼位者是伊麗莎白女皇的外甥彼得三世。
這位彼得三世是個神奇的人,他的父親是德意志人卡爾·腓特烈。彼得三世自幼在德國長大,不會說俄語,對俄羅斯的東西也不感興趣。彼得三世因為繼承俄羅斯皇位,失去了瑞典的繼承權。他為此憤憤不平。彼得三世即位前,曾經公開說:“把我拖到這個令人詛咒的俄羅斯,我簡直就是被逮捕一樣;如果當初我不來俄羅斯,我不就能成為文明國家的君主了麼。”
在七年戰爭期間,俄國和普魯士交戰。彼得仍公開對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大帝表示支援,毫不隱瞞腓特烈就是他的崇拜偶像,並多次向敵國普魯士提供軍事情報。這種叛國行為引起了女皇和俄羅斯人的不滿。但彼得三世是伊麗莎白女皇唯一的親人,女皇也別無選擇。
彼得三世即位後,立刻與普魯士談和,歸還整個東普魯士和俄羅斯在七年戰爭中佔領的全部土地。當時,普魯士派出了一個和談使節,彼得三世對這個談判對手是如此信任,以至於他委託這個談判對手直接同時代表兩國起草和約檔案。
俄羅斯人也是夠悲催的。自己帝國的皇帝,不把自己當成俄羅斯人,不會說本國語言,信任敵國的使節勝過自己國家的大臣,把敵國的利益置於自己國家的利益之上。
俄羅斯本土派自然不甘心自己的國家變成普魯士的附庸。彼得三世登基僅僅六個月,彼得三世的妻子聯合近衛軍再次發動政變。推翻了彼得三世。
彼得三世的繼承者,是他的妻子葉卡捷琳娜二世。這位女皇也是德意志人,是一個德意志小國的公主。但葉卡捷琳娜明白,她在俄羅斯站住腳的最主要條件就是要成為一個俄羅斯人。為此非常勤奮地學習俄語,徹底融入俄羅斯。
這是俄羅斯本土派第二次政變,再次推翻了親西方派的執政者,廢黜了沙皇彼得三世。葉卡捷琳娜二世統治俄羅斯34年,被稱為大帝。
葉卡捷琳娜去世前,本打算讓鍾愛的孫子亞歷山大一世越過不成器的兒子保羅一世直接繼位。但她還沒來得及實施就因為中風去世。
保羅一世和他的父親彼得三世一樣,也是一個德意志/普魯士的崇拜者。他要求俄羅斯軍隊改穿普魯士式樣的軍裝。保羅一世模仿普魯士的制度,進行了一系列改革,特別是軍事改革。他的改革很難說是正確還是錯誤,但短期劇烈的改革,讓俄國軍官階層對其非常不滿。同時,保羅一世和法國拿破崙議和,企圖與英國斷交,也遭到了貴族和商人的反對。
1801年,反對保羅一世的俄羅斯貴族和軍官發動政變,推翻並殺死了保羅一世。很多人認為,保羅一世的兒子,後來的沙皇亞歷山大一世也參與了這次政變。參與政變弒君的人,也沒有任何人受到懲罰。保羅一世的執政也只有四年。
這次政變,算是第三次俄羅斯本土派貴族推翻親西方的沙皇。
亞歷山大一世擊敗拿破崙,俄羅斯大軍進入巴黎,使俄國成為歐洲大陸上的頭號強國。俄羅斯終於建立了自己的民族自信,擺脫了德意志/普魯士的影響。亞歷山大一世統治俄羅斯24年。
亞歷山大一世之後就沒有再發生推翻沙皇的政變。尼古拉一世病死,亞歷山大二世被左翼革命黨暗殺,但不是政變。亞歷山大三世病死,然後就是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
1904年日俄戰爭俄羅斯戰敗後,爆發了1905年革命,但最終被沙皇鎮壓。在一次世界大戰中,俄羅斯軍隊遭受了慘重損失,1917年2月爆發了2月革命,沙皇被推翻。
從彼得大帝開始,被政變或者革命推翻的沙皇一共四位,伊凡六世,彼得三世,保羅一世,尼古拉二世。其中,前三位都是代表親西方(德意志)的勢力,在政變中被俄羅斯本土派推翻。只有尼古拉二世是因為戰敗而被推翻。
十月革命以後,布林什維克奪取政權。國際派和本土派的鬥爭仍然在繼續。列寧就是一個國際派的代表,他認為歐洲國家(主要是德國)必然會發生革命,最終的蘇聯將是一個世界各個無產階級國家的大聯合。所以,他制定的蘇聯憲法中規定,每個加盟共和國都有退出蘇聯的權力。列寧心目中的蘇聯,不是一個民族國家,而是一個超國家的聯盟。
托洛茨基也是一個國際派的擁護者,信奉的也是國際主義,全球革命。而斯大林雖然是喬治亞人,但他卻是一個俄羅斯情結很強的本土斯拉夫主義者。最終,斯大林贏了,托洛茨基輸了。斯大林基本幹掉了布林什維克上層的外族勢力。
赫魯曉夫1964年被搞下臺,取代他的勃列日涅夫也比赫魯曉夫更保守,更本土派。
1991年八一九政變,也是保守本土派發動政變,企圖讓改革派戈爾巴喬夫下臺,但八一九政變失敗了。
在整個俄羅斯的歷史上,政府精英比人民大眾總體上更傾向西方。普希金有一句名言“政府是俄羅斯唯一的歐洲人”
在俄羅斯歷史上,絕大多數政變都是保守本土派發動,企圖把親西方的改革西化派搞下臺。幾乎無一例外。(可能唯一例外是二月革命)
關於西化派對俄羅斯和俄羅斯文化的看法,有興趣可以讀一下十九世紀西化派代表恰達耶夫的《哲學書簡》。這些批判和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某殤》一派對中國的批判很類似。恰達耶夫在《哲學書簡》中這樣描述俄羅斯和俄國文化
“我們沒有給世界以任何東西,沒有教給它任何東西;我們沒有給人類思想的整體帶去任何一個思想,對人類理性的進步沒有起過任何作用…… 自我們社會生活最初的時刻起,我們就沒有為人們的普遍利益做過任何事情;在我們祖國不會結果的土壤上,沒有誕生過一個有益的思想;我們的環境中,沒有出現過一個偉大的真理。”
3、在西化派和本土派之間搖擺的普京
西方普遍認為普京是保守傳統的斯拉夫派。但是普京本人不是斯拉夫派提拔起來的,而是西化派提拔起來的。無論是早期提拔普京的恩師索布恰克,還是任命普京為接班人的葉利欽,都是西化派的代表。普京本人出身強力部門,是希拉維克集團的一員,但他並非一開始就是本土派。
2014年之前的普京,一直在西化派和斯拉夫派之間扮演調停的角色,如果說有傾向,更傾向西化派。
普京一直想融入西方,蘇聯解體後,俄羅斯一直也想融入西方。但如我前文所說,對於西方來說,俄羅斯太大了,太危險了,西方不敢接納俄羅斯。
西方認為,俄羅斯民眾在威權統治下敢怒不敢言。但實際恰恰相反,俄羅斯的精英親西方,而民眾反西方。(西方的這個誤判,在中國同樣存在)
“俄羅斯和美國對彼此的態度是顛倒的”,1990年代民主運動的前活動家、莫斯科俄美和解中心副主席Yevgeny Sevastyanov說。 “在美國,普通人或多或少地同情俄羅斯,但精英階層的反俄情緒卻很強烈。相反,在俄羅斯,精英們對美國和西方的普遍同情比普通公民要多得多。”
俄羅斯政治分析師Dmitry Babich把俄羅斯精英和西方的關係稱之為“永遠的單相思”。
這種精英“永遠的單相思”,也許不僅僅是在俄羅斯吧。
在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精英試圖兼顧俄羅斯的國家利益與西方經濟和政治的一體化。在1990 年代,這項任務似乎很容易實現,因為俄羅斯、歐盟和美國在地球上最不穩定的地區——中東、巴爾幹半島甚至高加索地區——的利益似乎沒有互相矛盾。
這種對西方的溫和態度(現在有人稱之為綏靖政策)主導了葉利欽領導下的俄羅斯外交政策,導致這位已故總統勉強默許了 1999 年北約擴張的第一波“浪潮”。
在他最初的兩個任期內,普京的大部分時間都保持著同樣的態度。2010-2011年反普京抗議活動“左翼”派的活躍領導人Sergei Udaltsov指責普京“出賣”俄羅斯的安全,2003年提醒公眾普京決定撤出古巴和越南的舊蘇聯基地。普京的這一舉動在俄羅斯引起了很多批評,但在很大程度上沒有引起美國和歐盟的注意。俄羅斯的讓步,就像葉利欽領導下的許多其他讓步一樣,並沒有起到期望中的”討好西方”的效果,沒有人向俄羅斯說一聲謝謝。
相反,北約一次次東擴,一步步擠壓俄羅斯的生存空間。俄羅斯與西方再次漸行漸遠。
喬治亞和烏克蘭(2003 年和 2005 年)的“橙色革命”,以及2014 年烏克蘭政權的暴力更迭,讓俄羅斯最終轉向。
在俄羅斯精英眼中,亞努科維奇並不是俄羅斯的傀儡,也並不反對西方。亞努科維奇拒絕過俄羅斯許多誘人的經濟提議,內心深處也希望烏克蘭最終能和歐洲一體化。他們無法理解為什麼亞努科維奇會被西方認為是“邪惡”的,並被暴力推翻。亞努科維奇只不過是在2013年11月要求推遲(甚至不是取消)與歐盟的結盟協議而已。
4、如果普京下臺,什麼人會執掌俄羅斯
2014年克里米亞頓巴斯事件的真相至今仍撲朔迷離,我個人的觀點是,這個事件其實是俄國內部強硬本土派策劃的,然後普京最後接受了事實。
當時,頓巴斯抵抗軍的領導人斯特列科夫當時要求擴大戰爭,打通克里米亞和頓巴斯的聯絡,被普京拒絕並強行召回俄國。這就是中國網際網路上“普構”這個外號的來源。(把普京比作十二道金牌找回岳飛的宋高宗趙構)
2014年因為克里米亞事件,俄羅斯被西方制裁。即使2014年以後,克里姆林宮的大多數高層人士的心態仍是西化派。他們認為歐洲最終能看到頓巴斯發生的悲劇,能理解俄羅斯在烏克蘭問題上的立場,而放鬆制裁。他們再次失望了。
2022年,為什麼普京會發動全面入侵烏克蘭,這個決策並不明智。我個人認為普京也受到了強硬派巨大的壓力,雖然他自己很猶豫,但最終還是決定發動戰爭以滿足強硬派的要求。真正對普京構成威脅的,並不是納瓦爾尼這樣的西方自由派,而是希拉維克集團內部的更強硬更本土的力量。
納瓦爾尼,與其說是一個不屈不撓,有廣泛影響力的可以取代普京的自由民主鬥士,不如說是普京擺在檯面上的一個構不成實質威脅的反對者。
今天,戰事進展並不順利,斯特列科夫這樣的本土強硬派已經在呼籲俄羅斯應該全國總動員,用調動全部力量一舉壓垮烏克蘭。而普京很顯然不願意這麼做。他還是希望透過談判,取得想要的東西,其後再努力和歐洲和解。也許戰事不利,會危及普京對俄羅斯的統治。但是想要撼動已經根深蒂固的希拉維克集團(Siloviki),比推翻普京難度大得多。
西方把普京描繪成魔王。但普京如果真的被政變趕下臺,也許更可怕的魔王會執掌俄羅斯這個超級核大國。畢竟,俄羅斯的全部歷史上,透過政變上臺的,基本都是更保守更強硬的本土派。
這將是西方乃至全世界的噩夢。
如果沒有普京,也許,俄羅斯離西方的距離更遠。
關鍵詞
俄國
葉卡捷琳娜
戰爭
普魯士
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