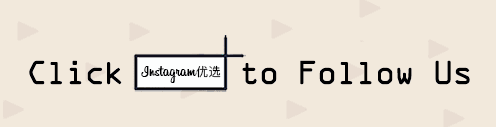圖片來源:unslpash
撰文|伊麗莎白·安妮·布朗(Elizabeth Anne Brown)
翻譯|林清
櫛蠶(Peripatus)屬於有爪動物門(Onychophora),俗稱天鵝絨蟲(Velvet Worm),是一種體表結構和觸感好似天鵝絨一般的蠕蟲,有著柔弱的外表,但它們屬於捕食性動物,且捕食方式十分奇特:透過噴射黏液來捕捉獵物。
天鵝絨蟲生活於熱帶和溫帶地區的林下落葉層,白天隱藏在落葉之下,夜間“邁”著幾十條胖胖的小短腿出來活動。它們體形較小,體長從1釐米左右到20釐米不等,視力極差,只能盲目地四處移動,全憑運氣撞見可食用的獵物,比如蟋蟀或潮蟲。一旦發現獵物,天鵝絨蟲便會利用頭部兩側的腺體向獵物噴射黏液。
加拿大麥吉爾大學(McGill University)的生物化學家馬修·哈林頓(Matthew Harrington)研究天鵝絨蟲已有十年之久,他表示:“這個過程發生得太快了,幾乎就像它們在打噴嚏一樣。”
起初,這種黏液是一種水狀液體,但在空中會轉變成凝膠樣絲狀物,纏住不幸被捕的獵物並將其牢牢黏在地上。隨著獵物掙扎,黏液會形成纖維狀細線,接著幾秒內就會硬化成玻璃態纖維。
一個多世紀以來,科學家一直對天鵝絨蟲黏液的黏性很感興趣。(19世紀70年代,研究者試圖弄清楚是什麼讓這種黏液很黏,就嚐了嚐它。結論是:味道苦澀。)根據哈林頓和同事近期在《美國科學院院刊》(PNAS)上發表的研究,這種會發生相變的黏液或許對研發新一代可回收生物塑膠具有啟示作用。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此前,研究者發現將這種纖維浸泡在水中可以使其恢復到液態,假如重新在指尖揉搓這些黏稠的液體,就會發現它們重新形成了像尼龍一樣堅固的纖維。這意味著,“關於製造這種纖維所需的一切資訊都編碼在自身的蛋白質中,”哈林頓說。
但科學家發現,分離這些蛋白質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卻很難。因為這種黏液對外部的接觸非常敏感,即便是移液這樣常規的實驗操作也會觸發相變。為避免陷入這種棘手的局面,科學家對採自多地(包括巴貝多、新加坡和澳大利亞)的天鵝絨蟲黏液中的蛋白質進行了RNA測序,然後將RNA序列輸入到AlphaFold3(由谷歌DeepMind推出的人工智慧模型,用於預測蛋白質結構)中。對於這三種天鵝絨蟲,哈林頓說,AlphaFold3“都輸出了一種馬蹄形”且富含亮氨酸的蛋白質。
儘管這種結構對材料科學家來說很新穎,但對演化而言卻早已司空見慣。比如有一類相似的蛋白質叫做Toll樣受體(toll-like receptor),是跨越植物、無脊椎動物和脊椎動物的最古老最保守的免疫系統的組成部分。這些受體位於免疫細胞表面,可以與入侵微生物的碎片緊密結合,隨後再將它們釋放。哈林頓和同事認為,這種馬蹄形的蛋白質可能採用類似的“主-客”動力學機制與黏液中的其他蛋白質結合,產生鍵合力強且可逆的鍵,從而形成強韌的纖維。
這對致力於開發塑膠替代品的材料科學家而言極具吸引力,他們的目標是製造易於分解並可重塑為新形狀的替代材料。
哥斯大黎加國家奈米科技實驗室(National Laboratory of Nanotechnology)研究天鵝絨蟲黏液的研究員揚德里·科拉萊斯·烏雷尼亞(Yendry Corrales Ureña,未參與這項研究)認為,這項研究發現的馬蹄形蛋白質很重要。
不過,她補充說,這些蛋白質並不能解釋天鵝絨蟲黏液的其他重要特性,如韌性或彈性。“它們只是揭開了層層謎團的冰山一角。”
哥斯大黎加大學(University of Costa Rica)研究無脊椎動物演化的生態學家胡利安·蒙赫·納赫拉(Julian Monge Najera)說,來自不同大洲的三種天鵝絨蟲噴射的黏液中所含蛋白質具有相同的形狀,這凸顯了天鵝絨蟲一直保留著這一非常古老的演化特徵。
化石記錄顯示,至少在3億年前,天鵝絨蟲就已經存在了,形態與現生天鵝絨蟲相似,比恐龍和現今大洲出現還要早。“如果我能搭乘時光機回到寒武紀之後的古生代,我在那裡捕獲的天鵝絨蟲會與如今生活在哥斯大黎加雲霧森林中的並無兩樣,”蒙赫·納赫拉說,包括它們分泌的、會發生相變的黏液。
哈林頓及其團隊正在努力從黏液中分離純化馬蹄形蛋白質,並透過電子顯微鏡確認這種蛋白質的結構。“我們不會為了替代塑膠而不斷提取天鵝絨蟲的黏液,”哈林頓說,“但我們希望能模仿它們的化學特性。”
本文選自《環球科學》7月刊“前沿”欄目。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環球科學”。如需轉載,請在“環球科學”後臺回覆“轉載”,還可透過公眾號選單、傳送郵件到[email protected]與我們取得聯絡。相關內容禁止用於營銷宣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