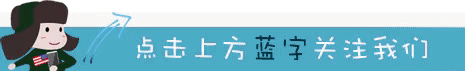譯者 | 黃昱翔 中國政法大學 本科
一審 | 左亦惟 康奈爾大學LL.M.
二審 | 郝林樺 西南政法大學 本科
編輯 | 田 悅 華僑大學 本科
蘇 桐 華中科技大學 本科
責編 | Susan 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

英文原文系中國政法大學“未成年人法學”課程(501100102.02)學習資料
授課老師:苑寧寧
授課時間:2024年秋季學期,32課時。
已獲得授課老師授權
譯者按:
《牛津兒童權利法手冊》是牛津大學出版社享譽世界的權威系列學術出版物“牛津手冊”在兒童權利法領域的最新成果。該書由佐治亞州立大學法學院教授喬納森·託德雷斯和佛羅里達大學萊文法學院教授沙尼·金主編,彙集四十餘位兒童權利法領域的頂尖學者寫作而成,旨在闡明兒童權利法的內容,剖析其實施的複雜性,並指出兒童權利發展所面臨的關鍵挑戰與機遇,填補了這一人權學術領域的空白。
兒童最大利益原則是《兒童權利公約》的核心原則之一,因其在兒童權利法中的重要地位而被稱為“帝王原則”。作為公約的締約國之一,我國在履行條約義務和實施我國《未成年人保護法》的過程中亦應當發揮這一原則的指導作用。該書在“最大利益原則的影響”一節中的“國家義務”部分即充分論述了各國法院在處理這一原則的實施問題,可為我國乃至世界各地兒童權利法律和政策的研究提供有價值的參考。

(圖片源於網路)
牛津兒童權利法手冊
Ⅲ. 實體法領域
第10章 兒童最大利益
4. 最大利益原則的影響
在解釋了歐洲法院如何理解兒童的最大利益之後,我們將注意力轉向國家義務。歐洲法院在解釋兒童最大利益原則時,已從單純定義兒童的最大利益,轉向強調國內法院在處理此類問題時應遵循的程式。例如,在有關父母誘拐兒童(譯者注:父母誘拐兒童(parental child abduction),指父母一方侵犯另一方監護權,將孩子帶離其祖國或將孩子留在國外。)的判例法中,這一點尤為明顯。在早期的判例法中,歐洲法院認為,兒童的最大利益在於“迅速回到其習慣的環境中”。然而,一些法官持不同意見,包括在對(兒童被)誘拐與遣返令被執行之間的時間差應當如何處理的問題上。這導致歐洲法院大審判庭宣佈,被訴請的法院必須“深入審查整個家庭的情況以及……事實、情感、心理、物質和醫療上的(因素),並對每個人各自的利益(進行)權衡和合理的評估,始終關注如何為被誘拐兒童找到最佳解決方案,尤其是在申請其返回原籍國的情境下。”如果兒童已經在新環境中定居滿一年,則法官不得下令遣返。此外,在有關驅逐外國公民的判例法中,可以找到判定兒童是否可以被視為已經定居的指引:法官必須考慮到兒童的最大利益和福祉,“ 特別是其在目的地國可能遇到的困難的嚴重程度,以及與東道國和目的地國之間的社會、文化和家庭聯絡的緊密性。”在隨後2013年的一項判決和此後有關這一問題的主要案件中,歐洲法院大審判庭再次採取了程式性方法,強調被訴請的法院必須切實考慮到(《海牙公約》中的)有關立即遣返兒童的例外情況,且其判決必須在這一點上充分說明理由。(被訴請的法院)必須根據《歐洲人權公約》第8條對例外情況進行評估,該條規定應當尊重私人和家庭生活。

(圖片源於網路)
歐洲法院有關非監護人父母探視權的判例法中也採用了類似的程式性方法,歐洲法院認為,應當根據專家建議(獨立心理報告)和是否授予探視權的決策過程中(非監護人父母的)參與來評估兒童的最大利益。同樣,在生父確認訴訟(paternity suit)中,必須為兒童利益的程式保護提供法律保障,法官需要考慮到兒童的最大利益。歐洲法院在最近的一起案件中還強調了採取個案分析方法的必要性,在該案件中,撫養孩子五年多的(前)丈夫在被確認他不是孩子的生物學父親後失去了所有的探視權。歐洲法院嚴厲批評了探視權的有關法律規定缺乏靈活性,並補充道:
“法院並不認為兒童在探視權領域的最大利益可以透過一般的法律推定來真正確定。鑑於可能涉及的家庭情況的多樣性,法院認為,要公正地平衡所有相關者的權利,就必須審查每個案件的具體情況。因此,《歐洲人權公約》第8條可被解釋為規定成員國有義務根據個案具體情況審查,以確定兒童與撫養過其足夠長時間的特定人保持接觸是否符合兒童的最大利益,而無論該人與兒童是否具有生物學關係。”

(圖片源於網路)
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根據其申訴程式作出的第一項決定重申了透過個案分析確定兒童最大利益的必要性以及對各國程式性義務的強調;該案件涉及丹麥的一項驅逐令,一位母親對此提起申訴,理由是她的女兒如果返回索馬利亞將遭受女性割禮。委員會認為,丹麥未能從程式角度確定兒童的最大利益,因為丹麥政府在評估兒童是否會受到不可挽回的傷害時“沒有評估母親及其女兒被驅逐出境的具體和個人情況”。只要最大利益的概念沒有被剝奪基於家庭紐帶、發展和需求等概念的更廣泛和實質性的含義,個案分析和程式性方法就是值得歡迎的發展。
努斯伯格法官(Judge Nussberger)在針對一起父子關係案件的反對意見中,就兒童最大利益的抽象概括定義提出了質疑。國內法院裁定,兒童的最大利益在於確立其真正的生物親緣關係,而不是維持與其母親的丈夫的父子關係。歐洲法院的結論是,國內法院沒有逾越其裁量餘地。努斯伯格法官在他的反對意見中對最大利益的主觀定義和客觀定義進行了區分,並否定了客觀定義。這一區別再次表明,兒童的主觀意見對最大利益的確定至關重要。從主觀定義上看,孩子並不想與推定的生物學父親重新建立聯絡。最大利益的抽象概括定義,即獲知一個人的身世真相,並未考慮兒童個體的具體情況。在該案中,孩子失去了他的社會和法律意義上的父親,而在青春期階段被迫去接受一個他被推定的生父作為他新的合法父親。

(圖片源於網路)
儘管如此,在某些領域,歐洲法院對各國應承擔的實體性(而非程式性)義務仍保留了更多的規定。例如,在一起涉及一位聽障父親的探視權案件中,歐洲法院認為,國內法院“應該設想更多的附加措施,以更適合案件的具體情況。”歐洲法院認為,他們應該研究可以採取的措施,“以消除現有的障礙來促進兒童與非監護人父母之間的接觸。”同樣,歐洲法院也強調,國家不應在未經適當的過渡和準備措施的情況下,強制要求長期與母系家庭居住的兒童回到父親身邊。這些(過渡和準備)措施應旨在幫助孩子和其疏遠的父親重建關係。根據歐洲法院的意見,只有在兒童面臨緊急危險時,安置照護才是允許的,因此(安置照護)不能僅僅基於物質需要。此外,歐洲法院還強調,國家有積極義務採取措施,儘快促進家庭團聚。從家庭生活的角度來看,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一義務變得更加緊迫,但也必須與考慮兒童最大利益的其他方面的義務相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