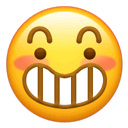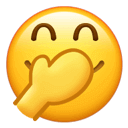作家張愛玲曾說:“對於不會說話的人,衣服是一種言語,隨身帶著的一種袖珍戲劇。” 服飾不僅關乎遮體與保暖,它還承載著文化、身份與個性。優秀的小說家們深諳此道,卡夫卡在隨筆中描述了一位女房東的穿著:“她身上的衣服打起矯揉造作的褶皺。”寥寥幾筆,她的性格與處境就被讀者看見了。
普通人在生活中選擇使用怎樣的物品,某種程度上就是對生活的道白。服飾工藝正是這種表達的外化——它不僅受到原料、審美、社會環境的影響,同時也承載著歷史與地域特色,為我們展現生活的廣闊與多樣。
時至今日,那些曾經根植於日常的服飾傳統工藝,是否仍能適應現代社會的需求?在日新月異的消費文化中,我們如何為這些“舊日的藝術”找到新的生命,使它們真正復歸今日的生活?

對「過去」的懷想
也許是自我幻想的浪漫

當人們在購物軟體裡挑選最新款的衣服時,「布盡其用」專案顧問、植物染藝術家林含正在海南東方的報白村跟當地的黎族人去附近的山上收集野板栗樹皮,這種樹皮可以染出潘通色卡上不存在的某種棕色。
至少在林含多年的田野工作經驗裡,已經沿襲了3000年的黎族紡染工藝有其特殊性:時至今日,他們依然使用天然植物染料染制所需的每種顏色。“一個民族有植物染色是不稀奇的,可是在現今社會來說,能全部使用植物染料完成一種工藝的所有顏色的民族是非常少見的。”林含解釋道。顯然,當地的黎族人並不認為這種經由手口相傳的傳統工藝有多麼神聖。他們無非是繼承祖傳的手法,就地取材,採用笨拙的工具和粗糙的材料,毫無困惑地製作出來而已。

黎族紡染工藝堅持使用天然植物染料染制所需的每種顏色
與高度標準化的現代工業體系相比,傳統紡染工藝有些過於“靠天吃飯”了。植物採收的季節、天氣、水的溫度,都可能影響最終的染色結果。黎族的“染匠”們心平氣和,罕見對“精確性”的焦慮——多年重複的染織過程中,他們早已習慣了接受各種可能。他們生產的這些被今天的我們稱之為傳統手工藝的生活物品,蘊含著某種不為環境所縛的趣味和創造力,以及被自然滋養的滿足。對這樣的工作用先進、落後的言語去評斷是不合適的,這裡隱藏著不為時間所左右的、生活的本質——單純的、樸實的、節制的、寬容的。
一些人對這樣的生活富有某種浪漫主義色彩的感傷,有時我們稱之為“懷舊病”。哈佛大學教授斯維特拉娜· 波伊姆(Svetlana Boym)坦言,懷舊病(Nostalgia)是“ 一種‘損失-替代’情感,也是某個人自己幻想的浪漫” 。
導演伍迪·艾倫(Woody Allen)用一部電影《午夜巴黎》戳破了這層“浪漫”:男主角吉爾在巴黎的一間酒吧裡遇到了已故的文化偶像菲茨傑拉德、海明威……當他沉迷於往昔世界時,舊友保羅毫不留情,“認為別的時代比自己現在生活的時代更好,這是那些無法應對當前生活的人,所產生的浪漫主義的缺陷。”

電影《午夜巴黎》劇照
實際上,“懷舊病”並不是最近才產生的一種集體情感。在十七世紀的西方,懷舊被視為一種可以治癒的情感疾病,當時的醫生推薦用山地旅行來“治療”。服裝設計領域亦未缺席過對這種情感的回應,畢竟,服裝與人有肌膚之親。出生於德黑蘭的伊朗裔德國設計師萊拉·皮耶達耶什(Leyla Piedayesh)童年時舉家搬遷到德國,多年之後,她從阿拉伯傳統的庫菲亞頭巾中獲得靈感,設計了一款的圍巾。英國社會學家伊麗莎白·威爾遜(Elizabeth Wilson)在《時尚的旋渦》裡指出,“快時尚工業將服裝變成‘一次性商品’,而傳統工藝的復興是消費社會對‘真實性’的集體鄉愁。”
當一個人難以在真實世界找到應對生活的方式時,任何一種形式的張望和尋找都是可以被理解的,畢竟,過去存在過的一切,要麼戰勝過時間,要麼就還在於時間纏鬥。於是,“過去”成為了可信的事實,也提供了接受現實世界的一種可能。

傳統不僅是一種工藝,
是某種生活方式的結果

至少在林含眼裡,黎族傳統紡染工藝並不是“舊”的。日本民藝運動的發起人柳宗悅明確提出,“無論怎樣古老的物品,只要有新的接受方,就會復活為新的東西。”
誠然,對傳統的“復活”有時看上去是對傳統的背叛。日本服裝設計師山本耀司(Yohji Yamamoto)不無刻意地將日本和服剪裁融入西式女裝結構,透過不對稱設計解構傳統,“傳統工藝是服裝的靈魂,但你必須親手‘殺死’傳統才能讓它重生。我的設計是用現代剪刀裁剪歷史布料。”
傳統工藝自身的危機在於,它是某種生活方式的結果而非原因。民間手工藝尤其如此,它伴生於當時當地的具體生活所需和審美要求,往往就地取材,普遍缺乏流動性,當一地的人們生活發生變化,存續就岌岌可危了。比如一個民族從山上遷徙到山下,這個過程中,他們失去了對山的掌控和對植物的採收能力,印染技藝可能就不復存在。隨之消失的,不僅是一種技藝,而是當時的生活方式和審美趣味。

民間手工藝依賴於某種生活方式
“現在的孩子其實很難看到真正的鵝黃柳綠這樣的天然顏色了”,林含有些遺憾,“我們今天看到的主流色彩體系,無論是基於RGB(指工業界的一種顏色標準,將紅、綠、藍三原色的色光以不同的比例相加混色)還是CMYK(指彩色印刷時利用色料的三原色混色原理,加上黑色油墨,共計四種顏色混合疊加),其實是針對化學染色的結果而產生的。”
尋找民間所用的日常用品,本身即是對傳統工藝之美的根本的探索。無論是由誰來收集、在何處收集,選擇都要充分顯現物品之美,並以此說明美的多樣性。由於這些傳統手工藝散落在民間,研究者除了要建立清晰的研究脈絡之外,往往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做田野調查。已經進入第三個年頭的「布盡其用」,是江南布衣的一個研究專案,最新的研究課題是印染,傳統手工藝如何從自然材料獲得色彩?如何透過浸、扎、折、畫、印等技法獲得豐富的色彩效果?研究團隊在浙江、上海、江蘇、廣東、貴州、雲南、四川、青海等8個省、自治區、直轄市,記錄了14種傳統手工藝,連結了30個手工藝傳承人、工坊或組織,親歷技法實踐,積累了大量資料。在染材的研究尤其側重於經典傳統天然染材如茜草、紅花,或是植物廢棄物如洋蔥皮、栗殼、茶葉梗、咖啡渣。這些草木染等傳統染色工藝,從某種角度來看,填補著主流顏色體系之間的縫隙。

「布盡其用」印染課題深入各個省市探訪傳統手工藝
用林含的話來說,“中國的植物染匠人,就像神農嘗百草。”當我們欣賞這些顏色時,會驚訝於傳統工藝對材料的充分應用,這種樸素的“物盡其用”,從未以“環保”的面目示人,卻早已憑藉傳統手藝人的才智,融入了普通人的生活。
如果僅僅將工藝研究的探索停留在收集記錄、抑或個人創作層面,這些工作從根本上來說有悖於民間傳統工藝的實質,即為人們的生活而創作。「布盡其用」專案團隊花了近一年的時間,使用四種材料的坯布作為對比,清晰地對比出同一染材在不同材料上的表現力;同時參考現代色卡的形式,設計了一套可以靈活拆用的色卡。「布盡其用」團隊對專案有更大的寄望,“我們希望這套色卡可以成為江南布衣的設計師在製作靈感氛圍版、對比色彩時能夠真正用起來的工具。”

「布盡其用」專案團隊設計了一套可以靈活拆用的色卡
LESS的主設計師張亞寧剛進公司就上了「布盡其用」的一些課程,如此集中深入地瞭解各地工藝,對設計師而言無疑是一種好奇心的極大滿足,也成為了她的靈感來源,雖然在嘗試將傳統工藝進行現代化演繹的過程中,大部分時間都是失敗的嘗試,“用現代的設計思維來解碼傳統,其實不等同於‘搬運傳統’這麼簡單的概念。”而每一次的成功,對他們而言都不僅僅意味著設計上的成功,而是從設計、材料到生產各個環節的進步。
常年在各地探尋傳統植物染色工藝的林含,對「布盡其用」專案與現代服裝產業的連線同樣報以熱忱,“哪怕最後不一定能得到一個很完美的結果,我也願意,只有在這樣的共同工作下,才能讓它不再成為一個收藏在博物館裡的遺產,而是進入人們日常的生活的實物。”

平凡地使用,
才能自由地使用

有野心的服裝設計師們從未停止過表達個人價值認同與社會生活之間的矛盾心理:青春與年老、男性氣概與女性氣質、工作與娛樂、從眾與反叛……畢竟,現代消費者購買的不只是服裝,更是附著於其上的文化敘事。準確的文化敘事可以產生文化認同,回應消費者不斷審視自身的幾個關鍵問題:我是誰?我從哪裡來?我應該過怎樣的生活?
對普通人來說,答案或許不來自哲學思辨,而在於生活中所做出的每一個真實的決定。文化敘事並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它來自於人自身的情感、物件背後的故事、人與人之間、人與物件之間的連線。這就是張亞寧在介紹LESS「精工系列」時所提到的“有故事感的衣服”。而那些經由口手相傳的傳統工藝,值得一說的故事實在豐厚。

消費者購買的不只是服裝,更是附著於其上的文化敘事
LESS品牌自2021年秋季推出「精工系列」以來,團隊長期研究傳統手工工藝如何經由現代服裝工業的技術發展和設計更新,運用於女裝成衣的設計和生產。前幾年用現代科技昇華近7000年曆史的嵌花工藝,把製作時間精煉到182分鐘。這極大地解決了傳統工藝的普及問題。那些對現代人來說過於“奢侈”的傳統工藝,在技術的煥新過程中,更有機會進入更多普通人的衣櫃,自由地出現在各種場合。
最近推出的夏季的「精工系列」,設計團隊跟隨「布盡其用」團隊去各地探訪和體驗不同工藝的在地生產過程。於是,這些隱於民間的工藝不再是辦公室裡的一塊樣布,而是某種生活結果的實證。當3000年前的黎族人染過的棕色出現在LESS辦公室的靈感板上,顏色不僅是一種顏色,而成為了一幅真正的生活圖景——南方遙遠的海風、夕陽、若隱若現的群山、田地間耕種勞作的人們……
仔細比較LESS2025年夏季的精工系列的吊染成衣,實際上不存在兩件一模一樣的衣服。這與成衣製作工藝的難度有關:“吊染”工藝要實現色階漸變的效果,在現有的技術條件下,仍然需要大量的手工參與才能實現。

LESS 2025年夏季精工系列
從「布盡其用」專案的植物染研究裡獲得的棕色靈感,還原顏色成為第一個要克服的難題——跟很多草木染形成的顏色一樣,這種棕色沒有現成的色卡可供使用。新染料的研發相當費時,但不得不做。畢竟,染制這種顏色的原材料野板栗樹皮,不僅數量不夠,材料質量也難以達到標準。如果堅持使用原染料,那麼成衣的數量就就無從談起了。現實告訴我們,從傳統工藝中汲取靈感,不應當將傳統工藝的生態代價被浪漫化遮蔽。正像林含所說的,“世界上每一株長得好好的植物,你把它砍伐下來去做染色,這也不是一個非常美好的事情。”
染制過程同樣麻煩。中間淺兩頭深的吊染工藝,儘管嘗試了多種技術解決方案,很多工藝環節仍需要手工參與完成。在反覆染色、滌洗、靜置的過程中,水的溫度和染料的時間控制極為關鍵,特別是當布料在沸水中染色時,沸騰的水泡會不可避免地飛濺到衣服上,一部分衣服就無法進入下一個環節了。並且,由於手工操作環節的誤差,每一件衣服最終的暈染效果,細看之下仍有細微的差別。

從還原顏色到染制,成衣製作工藝過程需要克服很多困難
然而,就是這些細微的差別讓每一件衣服都生動了起來:它擁有了機械複製時代天然缺乏的個性。在效率至上的時代,服裝設計是否需要為“舊”保留空間?服裝的“人性化”未來在哪裡?這不再是一個問題,而是“應當如何做”。日本服裝設計師川久保玲說,“我故意用粗糙的手工縫線,因為完美是工業的謊言,而不完美才是人的證據。”而消費者或許可以對“不那麼精確”的結果報以一種更寬容的態度,去觀察、瞭解,並與之相處。這是差別,而非差錯。
過去,年輕女性及其女性親屬一般會花幾年的時間來準備自己的嫁妝,這些應用傳統工藝製作的服裝在繁難之外,耗時費力的生產過程深度參與了生活,“惜物”是自然而然的情感。今天的消費者與衣服的關係通常產生於購買之後,已經很難與之建立情感聯絡了。但這並非成為了定局。經由設計創新、工藝改良,LESS的「精工系列」無疑以一種更具親和力的方式,將傳統工藝復歸了普通人的生活。當面對無窮的選擇時,也許可以參考張亞寧的購衣觀——買衣服應該是一種“我找到好朋友了”的感覺,它不應當是負擔,而是長久的陪伴。
點選「閱讀原文」,檢視更多新生匠意之美
策劃丨
三聯.CREATIVE
微信編輯丨毛思雨
作者丨張盼盼
設計排版丨熊清
圖片來源丨江南布衣布盡其用、LESS

*文章版權歸《三聯生活週刊》所有
歡迎轉發到朋友圈,轉載請聯絡後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