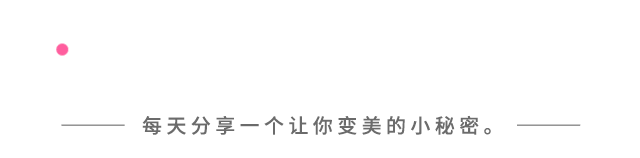又拍砸了。
自從2018年重啟版[月光光心慌慌]獲得巨大成功之後,一系列黃金時代的砍殺片(Slasher Flim,也被稱為肢解電影、血腥電影)被排上重啟序列。
剛在網飛上線不久的2022版[德州電鋸殺人狂]是其中之一。

新版[德電]口碑欠佳,豆瓣5.1,IMDb,5.0
劇情直接延續最經典第一部,第一代“最後女孩”莎莉迴歸,繼續和皮臉(Leatherface)“相愛相殺”。
噱頭給足。
但爛得也毫不意外。
全片看過之後,唯一的記憶點大概只剩下那一場狂躁巴士殺戮秀。

有趣的東西有,但不多,比如新世代們面對上世紀老牌殺手,第一反應是拿出手機開始直播。
讓人懷疑,老牌殺手仍能在今天大殺四方,是否和新世代更低的危機意識有關?

不過,這種古怪的幽默感和可能的趣味性總是稍縱即逝,在本片沒能延續下去。
這隻能是一部網飛大資料演算法下的撒血漿無腦爽片。
血漿撒得標準到毫無新意,莎莉迴歸噱頭多過內容,劇本潦草到像AI寫作完成。

更重要的,它沒能革新砍殺片對女性角色的“男凝”塑造。
不看也罷。不看毫無損失。

幾個年輕人駕車去荒漠中的德州,途中一個詭異自殘的搭車人勾起了他們的好奇心。
不久後,他們進入了一幢大屋,這裡充滿了陰森恐怖的氛圍,當這群年輕人不知所措時,電鋸聲驟然而起…….

希區柯克式的懸疑、詭異冷血的陳設佈置、真實陰森的謀殺場景、不可思議的攝影機排程,以及令人心悸的同期聲。
1974年,導演託比·霍珀將一切混合在一起,變成了一道動魄驚心的砍殺大餐。

而最重要的。
和[月光光心慌慌]邁克爾、[猛鬼街]弗萊迪齊名。
[德州電鋸殺人狂]的皮臉形象之成功,也讓它成為影史最成功的砍殺片系列之一。

奇妙的是,皮臉以白麵人皮臉和揮舞的隆隆電鋸的兇惡形象而聞名。
但他一定也是影史上“最具脆弱感”的惡魔之一。
皮臉對來自遠方的外來入侵者的第一感受是害怕的。

當年託比·霍珀選擇了冰島演員貢納·漢森來飾演皮臉,漢森在出演前,先去一所特殊學校,觀摩和學習了智力障礙者會如何移動和說話。
這也有了皮臉在兇猛的電鋸暴力以外會給出的最接近人類的反應。
電影中有一幕,當他先快速處理掉了闖入屋中的兩個年輕男女,後又一錘子砸死了前來尋找男女的第三人後。
皮臉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恐慌。

銀幕上的他扭動著肥胖的、笨拙的身軀,喉嚨裡發出“嗚嗚呼呼”的低吼,他跳到視窗,努力尋找著更多的可能的入侵者。
他的焦躁不安、悲傷害怕和嚴重缺乏安全感的心理脆弱,在捂著臉舔牙齒的一幕中到達了高潮。

所以有人說,託比·霍珀甚至是以一種悲憫的情懷在描寫惡魔的。
皮臉,某種程度上是70年代的弗蘭肯斯坦,殘暴混合著天真,讓人恨之牙癢之外多了些同情。
而相比他的“脆弱”,皮臉處理女人的手法,卻是全然屠宰場式的。
確切的說,在電影裡,不論男女,所有外來者對皮臉而言都不過“肉團”而已。
失落的小鎮,過時的屠夫家族設定,讓皮臉一家人砍人如砍肉,在他們那裡,並沒有道德可言。


可即使如此。
即使在三男兩女的主角團,死亡比率大致相等的剝削電影中,最終給觀眾造成巨大心理壓力的,還是來自對女性角色的暴戾行為。
一個證明是——
本片中的三個男性角色都是一刀致命、快速而沉默的被殺害。
而兩個女性角色,一個被緩慢的殘忍虐殺,透過掛在肉鉤的方式——透過對肉鉤和腳下血盆的特寫鏡頭。

曾有女性評論家在70年代將其一幕稱為“在所有商業發行電影中最殘酷的銀幕女性死亡”。
另一個女性角色,也就是女主角莎莉,負責在電影最後半個小時被皮臉追殺、被綁架、被恐嚇、被割血(給骷髏爺爺——男性父權家長食用,而來自幕後的剝削情形則是,這一幕是演員真的被割血)。


以及製造永無止境的、絕望至極的長達電影四分之一長度的尖叫聲。
有意思的是,飾演莎莉的演員瑪麗蓮·伯恩斯也因這一角色,獲得了“尖叫女王”的“美譽”。
甚至在恐怖片界,有專門的“尖叫女王”評選,來讚美女性角色受剝削之程度和尖叫表現力。
無怪乎連導演湯姆·霍蘭德都忍不住在1985年的[天師鬥殭屍]中吐槽砍殺片:“他們現在只想看神經病,戴著面具追殺處女!”
“處女”後文再說。
而有統計顯示,在砍殺片中,女性受害者處於恐懼狀態的時間一般是男性的5倍。
並且她們的慘死往往伴隨著被追逐、被拖曳的哀嚎和尖叫。

將赤裸和暴力混合在女性肉體之中,在緩慢而事無鉅細的虐殺過程,電影完成了對女性的剝削。
[德電]幾乎是此資料的完美例證。
更以負面的作用影響了之後數十年甚至一個時代剝削片的拍攝與流行。
強大而“脆弱”的惡魔皮臉成了銀幕另類“偶像”,源自他短暫的出場得到了細膩甚至是優美的刻畫。

可你要問女性角色呢?她們在乎什麼?擁有怎樣的性格?
在粗暴和功能性的展示後,觀眾對莎莉的印象最終無非停留在了超能叫的“尖叫女王”和最終倖存的“最後女孩”罷了。
你問肉鉤上的女孩?大家對她的印象,那可能是漂亮的裸背。


[德電]系列有“厭女”的內裡基因。
部分源自皮臉的真實原型——美國50年代人皮愛好者艾德·蓋恩。
著名的連環殺手艾德在犯案數量上比不了其他名人殺手,但他作案手法是其中令人格外毛骨悚然的一個。

艾德不是德州殺手,而是威斯康辛州人,從小與母親和哥哥相依為命。
艾德從小和母親發展出了一種畸形的依戀關係,並一直被母親灌輸一種觀念:性是邪惡的,除了母親之外的所有女人都是妓女。
在艾德的世界,沒有同齡朋友,更沒有喜愛的異性(可能有過,但也被母子關係打敗了),只有母親是絕對的中心。
人到中年,艾德仍是乖乖聽話的“媽寶男”。
一直到他39歲那年,母親因病去世,艾德內心深處的扭曲因子終於被點燃。
他先是將母親的屍體保留在家中,隨後開始為了滿足對女人的慾望而去盜墓。
他後來承認至少殺害了2人,並盜墓了9具女屍,並將其肢解、剝皮,並縫製成各類人皮臉、人皮碗、人皮燈具和人皮服。


[德電]裡的盜墓案和人皮燈具
他會穿上這些人皮女裝,假裝自己是自己的母親,遊蕩在月光下的農場附近。
說到這裡,恐怖片影迷應該對他的銀幕形象並不陌生。
除了[德電]系列皮臉。
[驚魂記]裡的“戀母”殺手諾曼、和[沉默的羔羊]的反派水牛比爾,原型都來自艾德·蓋恩。


[沉默的羔羊]另說,[德電]幾乎可看作是[驚魂記]同個故事的另一種開啟形式。
一般認為,希區柯克的[驚魂記]挖掘了蟄伏於浴室的恐怖,帶領恐怖片“走入了新世紀”。
他的浴室謀殺一場戲被反覆描摹、重演,取得了巨大的聲望和影響力。

從六、七十年代的義大利鉛黃電影。
到八十年代的美國殺人狂砍殺片。
都從浴室謀殺一幕取得靈感,將對女性的暴力虐殺變成一種“恐怖片賣點”和“銀幕奇觀”。
在其中,女性角色常被貶低以“引誘者”形象出現。
一如[驚魂記]裡投宿旅館的女主,因為引起了諾曼被壓抑的性慾,隨後被嫉妒的“母親”(諾曼扮演的母親)謀殺。
而從[德電]到[月光光心慌慌],再到[13號星期五]和[猛鬼街],與倖存的“最後女孩”相對的——
總是因為慾望而被“懲罰”的女性配角們。
邁克爾初登場,殺害了剛和男友親熱完、赤裸著身體的姐姐;

隨後,當他15年後迴歸、大開殺戒之時,乍看的挑選受害物件都是隨機而毫無緣由的。
但那些女性角色卻常常是與男友在雙人運動完之後,隨即被殺害。
所以[驚聲尖叫]裡才會吐槽道:恐怖片生存法則第一條——絕不做·愛,做·愛必死。


除了視覺上的考量,這類設定也是公開的“性懲戒”:
女人,因擁抱慾望而被謀殺;男人(常常是殺人狂),因為“被引誘”而謀殺。
於是,但凡倖存者女孩,也有其倖存的固定正規化。
當她的姐妹們因“放浪形骸”遇害時,她們往往靠著“潔身自好”和“傳統本分”笑到最後。
無論[13號星期五]的愛麗絲,或[月光光心慌慌]的勞瑞,禁慾的、中性的(更偏男性氣質的)更容易存活。

但她們的短暫存活,也不意味著對怪物的最終勝利。
比如第一部活下來的愛麗絲,在第二部一開場就被殺害。
重啟版[德電]打上了第一代“最後女孩”莎莉迴歸的標籤,你以為“最後女孩”化身“復仇女王”歸來?

實則只是純純工具人。
[德電]註定成不了[異形]那樣的“大女主”恐怖片。

重啟版[德電]有迷惑人的“假象”:
比如時隔半世紀,老牌電鋸殺手和“最後女孩”的再對決;
比如,這一部劇情有對皮臉和其“母親”關係的描繪,讓人想及艾德·蓋恩的戀母情結。

皮臉迴歸的新皮來自死去的母親
50年後,在皮臉隱身50年後,他的故事已經成了一種近乎都市傳說般的“德州傳奇”。
一群年輕的“網紅”vlogger駕車來到荒蕪偏遠的小鎮,打算在這裡開一間餐廳,開展返鄉新事業。

沒成想,他們闖入的“荒屋”,還住著殺人狂皮臉和他的母親。
年輕人的闖入讓年老的母親犯病,死在了開往醫院的路上,這也喚醒了沉睡的皮臉和他的電鋸,讓他再次大開殺戒。

50年來一直在追殺皮臉的莎莉,收到了求救資訊,也來到了小鎮,意圖復仇。
但莎莉的出場實在是傻透了。
她將求救的重啟版新女主鎖在了車間,自己一把長槍闖入巢穴,對著皮臉,先來了一把子淚眼無語凝噎的懷舊三連:
“你還記得我是誰嗎?記得殺了我的朋友嗎?說出我的名字。”

瞬間讓人誤以為打開了某三流愛情片?
那問完了你倒是開槍啊。就不。非要等到之後不得以的赤身肉搏戰,兩下又被皮臉虐殺了。

請問,莎莉這樣的迴歸又有何意義?
誰想看“傻白甜”時隔50年還是“傻白甜”?
以多年復仇者之姿登場,以傻得冒泡的白髮阿嬤再次被殘殺結束,重啟版,你可真會氣人啊。
而本片對皮臉和其母親關係的描畫,也只是淺嘗輒止,引出了之後皮臉的甦醒與暴走。
並沒有在真實原型基礎上,有任何更深入的挖掘和討論。
希區柯克拍[驚魂記],停留在了諾曼因為戀母而假扮作母親殺死其他(引發性慾的)女人。

沒有再問一層,母親為何極度“厭女”?
原型故事可能提供一種思路。
艾德·蓋恩並非沒有父親,但父親是個酒鬼,對兩個孩子從未有過合格的家庭教育。
母親奧古絲塔,則是個虔誠而狂熱的天主教徒,在以生育為目的的性生活之外,她一生憎惡並抗拒性。

她接受了男權社會的一整套PUA理論:性是邪惡的,性歡愉對女人來說是罪惡,所有追求歡愉的女人都是惡魔的工具。
然後又原封不動用同一套理論PUA自己的兒子。
為了“保護”兒子,她拒絕兒子有任何異性接觸,在艾德8歲時,就舉家搬到平原鎮農場,與世隔絕,讓艾德錯過了社會化的過程。

艾德戀母,又憎惡母親。
母親厭女,又豔羨其他女人。
母子關係在整個畸形糾纏的過程中,走到母親去世,艾德發病。
覆盤幕後故事,即使艾德並沒有皮臉那冷酷的電鋸作武器。
但男權社會PUA女性—母親製造惡魔—殺人狂獵殺女性的惡性迴圈,顯然更讓人直冒冷汗。
可惜,[德電]繼續了殺戮剝削和女性剝削之路。

繼續在血漿上飆量,在感官上加碼。
可今天是2022年了,砍殺片過時40年了。
什麼極端場面還沒見過的當下,又還有多少人會從虐殺(主要是女性)與血漿中找樂子呢?

▼
▼
【推薦閱讀】
從[寄生蟲]看韓國半地下文化|東亞國「私生飯」往事|“婚姻是什麼?長期賣春合約。”|那一晚,人質和劫匪幹了個爽|男女通吃的人,都長什麼樣?|中國人“不能公開談性”簡史|生而為女球迷,我很抱歉|男人看女人幹架時,卻在幻想寬衣解帶|女人們能穿上褲裝,用了幾百年時間|論臺灣髒話裡的“幹你孃”|我懷念,曾經有個坦蕩的色情片盛世|出軌這種事,當然要組團才划算|歡迎來到,偉大的攝像頭時代|噫,韓國男人“好羞恥”|易烊千璽怎麼了|《少年的你》裡的性隱喻,看懂了嗎?|銀幕上的臉,是一個人的終極裸體|我喜歡,80年代這個肌肉裸男|去他*的世界,做新一代“垮掉”|這是我戒掉雙十一的第三個年頭|《小丑》與鏡子的曖昧關係|日本人“斷袖分桃”往事|兩個男的搞在一起都能幹嘛|昆汀「抄」了,昆汀又「抄」了|愛是永恆的,但相愛不是|島國電影怪奇片名大賞|西方「亂倫畸戀」源流考|不是“媽蟲”,是驕傲的全職媽媽|只有獨立的女人,才配得上這條裙|「伍迪·艾倫式」話癆片簡考|霓虹燈與髒亂的暴力美學恰天生一對|那些跟明星上床的女孩,後來怎樣了|星戰是一齣外太空的家庭倫理肥皂劇|朱亞文這身衣裳,怎麼像太監?|自有性幻想以來就有觸手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