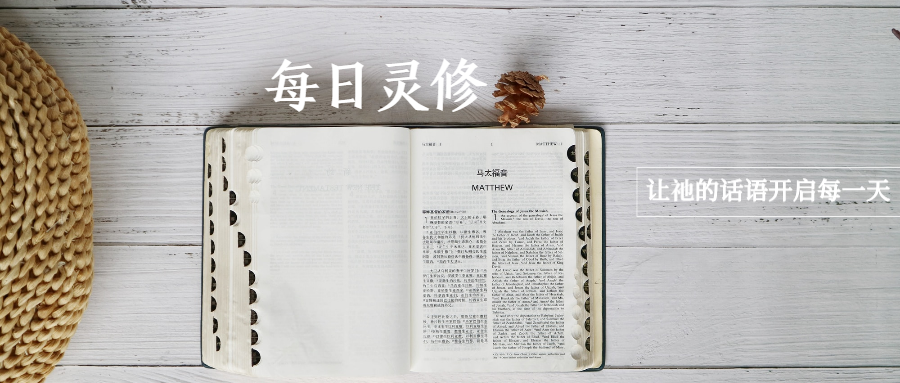作者:芒格書院
來源:芒格書院(ID:mungeracademia)
北京時間2月22日21點,伯克希爾哈撒韋官網公佈了2024年年度報告,以及沃倫·巴菲特最新的致股東信。
在最新的股東信中,巴菲特提到:“60年前,現任管理層接管了伯克希爾。這一舉動是一個錯誤——我的錯誤——並且困擾了我們二十年。我應該強調,查理立即發現了我這個明顯的錯誤:儘管我為伯克希爾支付的價格看起來很便宜,但其業務——一家大型北方紡織企業——正走向沒落。”
60年之後,“這家公司——仍然以伯克希爾·哈撒韋的名義運營——支付的所得稅遠遠超過美國政府從任何公司收到的金額——即使是市值達數萬億美元的美國科技巨頭。”
巴菲特如何將伯克希爾從經營不善的紡織公司,發展為全球矚目的商業帝國?2月27日晚,價值投資徵文一等獎獲得者崔士懿與芒格書院志願者廖斌將和大家一起回顧了伯克希爾不可複製的60年。
以下是此次直播精彩內容的實錄回顧,共計約9300字,預計閱讀時間30分鐘。
01
一如既往的股東信
廖斌:崔老師看完今年的股東信之後有什麼感受?有沒有超預期的地方?
崔士懿:實際上我們已經盼這封股東信很長一段時間了,都很期待。
這封股東信我認為還是一如既往的,很穩定。如果我們現在翻看他在1965年的股東信,甚至說1957年的第一封致合夥人信,內容都是一如既往的穩定。包括他的一些風格就是一直很保守、很真誠、很幽默。
2019年剛釋出完股東信的時候,巴菲特接受CNBC的採訪,他就說:“我每次寫股東信的時候,就在想,我是在給我的姐姐Doris,給我的妹妹Bertie寫信。”他每次寫信的時候就會把他姐姐跟妹妹放在這個開頭,然後寫完之後再把它換成“致伯克希爾·哈撒韋”。他是以給自己的家人寫一封家書的態度。像是跟家人一塊合夥做了一個生意,然後過年了,我要給我的家人寫一封報告,說這個經營的怎麼樣。他就是用非常保守、非常真誠的口氣來說的。而我們知道絕大多數公司他們的股東信或者是年報是給機構看的,或者是給一些大的投資者看的,而他是給一些親人看的,給自己的合夥人看的。
廖斌:把股東當作合夥人。
崔士懿:要追根溯源的話,是因為伯克希爾這個公司是從巴菲特的合夥企業BPL進化出來的。他在19年股東信裡就說他跟芒格在經營兩個合夥企業的時候,裡邊全是他的朋友或者是朋友的朋友,沒有一家機構。用他的原話來講,“都是在我還穿球鞋的時候就在幫我的人”。所以他的風格就是一如既往,很淳樸、很幽默,讀起來特別的順口,很溫馨,像一封家書,很親切。就是這封信是不是他寫的,一看就能感覺出來。
廖斌:是的,比如今年股東信一開頭就是說“錯誤”。那為什麼說他保守呢?
崔士懿:你看他在今年的股東信,如果我們說他的開篇是打個招呼 “To the shareholders of Berkshire Hathaway”。如果這個不算的話,今年的股東會一共是八個章節,它的第一個章節就是錯誤Mistake,很保守、很謙虛的口吻。一個最好的投資人,會先說我們犯的錯誤。
廖斌:對,他不是說我給你們賺了多少錢。
崔士懿:他從來不說這種話。實際上今年的業績是非常超預期的。他在一開始說,“在19-23年這這幾年裡,我一共在股東信裡提到過16次的mistake 或者error。”就是說這個人非常的謙虛。
02
巴菲特投資思想的轉變
廖斌:因為今年是伯克希爾的60週年,2015年的時候是50週年,當時巴菲特除了股東信,還單獨寫了一份《伯克希爾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當時的查理·芒格也寫了一封。1975年十週年的時候其實他也有一個簡短的一個回顧。那60週年這個關鍵的年份裡,股東信有沒有什麼不同的地方?他投資思想有沒有一些重大的轉變。
崔士懿:就是這封信的一些核心思想,過去60年以來的歷封股東信都有提到。很多話,也可以在過去60年以來的股東信裡找出原話來。就是第一買好生意,第二找好經理人。第三就是用合適的價格。當然前提是看懂生意。
廖斌:我們主流的解讀是,他以前更偏向於,特別是在合夥企業時期,可能會買一些菸蒂股,然後到伯克希爾之後,尤其是從這個喜事糖果之後,他買的企業質量就越來越高。另外一個就是說它的價格,他一開始不是說便宜的價格嗎?到後面就更會強調合理的價格,你覺得這個變化明顯嗎?
崔士懿:這個還是非常明顯的。我剛才想說他在做配置的時候有兩類錯誤。第一類就是他誤判了某些生意的長期經濟屬性啊。這個一個典型的就是這個德克斯特鞋業。德克斯特損失非常大。然後因為換股的交易讓他的錯誤又雪上加霜。第二類錯誤就是他選錯了經理人,或者就是說在用人的時候不果斷,該換的時候不換,造成了一些損失。
實際上還有第三點,他沒有在這封信裡說。他是在別的地方,或者他的歷年的信裡提出來的,就是剛才你提到的價格的問題。我們舉個例子,他在從12、13年開始買那個亨氏。後來又透過亨氏反向併購了卡夫。他們收購亨氏的時候是一個合理的價格,但是他在反向收購卡夫的時候,溢價非常高。
又過了兩年,到了15、16年,他開始併購PCC,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公司,做精密鑄件的。這公司今年收入大概是100億美元,淨利潤大概能賺到15億美元左右,15% 的淨利率,很不錯了。但是他們為這個公司付出的價格過高了,又加上這些公司前兩年因為那個波音737,它很多的履約也出現了問題。他也在2019年股東信裡說一次性地減值了110億美元。
他後來就說,再好的生意如果你付出的價格過高的話,它也是一筆非常糟糕的投資。再差的生意只要你的價格足夠合適,它還可能是一筆好投資。所以說好生意跟這個投資它還不是一回事。
廖斌:這個我有點理解不了。過去我們說巴菲特買公司都是很保守的,但是他買PCC這個價格太高了。
崔士懿:他過去一般都是光找便宜貨買。他自己後來在股東信裡反思說他犯了兩個錯誤,第一個就是說他錯估了這個生意未來的盈利能力,所以為這個盈利能力付出了過高的價格,這是他自己公開承認的錯誤,是在2020年股東信的開篇。但是有一點,就這個公司本身有形淨資產的回報率是非常高的,就是50億的淨資產它每年能夠產生15億以上的利潤,ROE大概是30%。當然有波動,但是穩定來看的話也是很高的。但是他為這個質量付出了過高的溢價,後來他也減持掉了。
也跟這個行業環境有關,因為他買的時候是在15、16年,那個時候美聯儲的利率處於一個量化寬鬆的環境之下。那個時候,利率很低,極低的利率就推高了資產價格。他當時也是連著幾年沒有大大的收購了。所以那筆收購目前看來的話,公司是個好資產,經理人也很好,但這筆生意的問題的話還是他“為了好資產付出了過高的價格”,但在今年股東新的開篇沒有提。
廖斌:是不是說有一些好的資產不是隨時都有機會給你併購的,整體收購的機遇是可遇不可求的?
崔士懿:對,因為伯克希爾的問題就在於他太大了。2023年的時候,它實際上已經成為全美淨資產最高的公司,就超過6000億美元了。
為什麼它現在很難增長了呢?你想一下它現在淨資產6000億美元,即便是保守地講,就以這個標普500的年化10%來衡量的話,對於它來講,淨資本漲10%,就要增長600億美元。另外它有一個原則,如果在買股票的時候它儘量,除非發生特殊情況,它一般不會買超過10%。如果超過10%的話,根據美國證監會的要求,你就要定期頻繁地披露相關的資料,就很麻煩。
所以說他買蘋果、買可口可樂、買美國銀行這些公司,包括買一些公司,它基本都是保持在百分之十以下,包括這一次買日本的五大商社也是10%以下,這是他的一個原則。他要買公司,買10%,他又要保證每年漲600億美元。
所以說即便是他只是拿出一筆600億來,在短時間內翻一番,那這樣的話他也要買入那種市值在6000億以上的公司(因為不能超過10%)。全世界來看的話,能夠進入這個投資門檻的公司可能就幾十家,這裡邊大部分是科技公司,他也看得很少。所以說,他再實現大規模增長的難度是越來越大了。
廖斌:所以它跑贏指數這個難度是越來越大,可能最後它就會變成一個指數的替代品。
崔士懿:從1984年開始,那個時候伯克希爾的規模已經很大了,很難跟過去一樣年化20%以上的增長,他就一直不停的給他的股東們說要降低預期。
03
伯克希爾成功最重要的原因
廖斌:你覺得伯克希爾成功最重要的原因是什麼?有沒有人可能複製它的成功呢。
崔士懿:幾乎是不可能。巴菲特在股東會上的回覆是說,如果讓他再來一遍,他也來不了。這裡邊有很多運氣,甚至背後有美國的國運,美國的資產。因為美國的底層資產是非常好的。如果說巴菲特出生在阿富汗,出生在古巴,不可能成為現在的巴菲特。
廖斌:卵巢彩票。
崔士懿:它有兩個東西是不可複製的,包括說它最核心的保險生意,就是說以保險浮存金來做投資。有很多人甚至可以說全世界的保險公司都想打造成伯克希爾,但是沒有一個人能夠做到,連線近都做不到。
廖斌:這個保險浮存金很好用,又有承保收益,又有投資收益,為什麼別人做不了?
崔士懿:這個就是問題所在了,如果這個事情看起來這麼好的話,肯定就會帶來競爭,一競爭的話肯定會造成保費的價格不夠。保費不足的話不足以覆蓋它的成本的話,短期還可以。如果考慮到投資收益,長期來看的話,這個事情是不可持續的。他之所以能做到,是因為他在這個進化過程中遇到了很多偶然的機會。比如,伯克希爾的保險從67年到85、86年一直就是在跌跌撞撞中往前走,很難做,中間吃過大虧,還被人騙過保,曾經還一度出現了危機。
印度的知名投資人帕伯萊,他曾經在97年向巴菲特問過一個問題,他就是問可不可以拿一部分資金來做像那個KPCB,像紅杉之類的這種風投。後來這個帕寶萊真的就是完全模仿伯克希爾,以保險浮存金為模式來打造一家公司,結果沒做下去。這個保險生意是一個同質化的生意,門檻不高,沒有太高的壁壘。巴菲特從67年到85年這接近20年的時間裡,他也沒有做出來,沒有特別好,還沒有那麼大的優勢。
82年之後他把這個保險生意的管理交給了那個戈特伯格,之後戈特伯格重組了一些人力,包括招來了阿吉特等人,慢慢摸索出來那個巨災險。從80年的後期,透過巨災險的特殊的賠率,類似的這種業務,因為那是一種非標業務,而非標業務在當時的環境之下是有很多業務視窗的,他可以拿到鉅額的保費。
透過一些偶然的機會,阿吉特86年進入伯克希爾,一直到89年他第一次出現在伯克希爾的股東信裡。然後巴菲特從那開始,每一年的股東信裡,都單獨讚揚阿吉特,一直到今年的股東信。
伯克希爾它有全世界最大的淨資產,另外它有與保險無關的,每年接近400億的現金流。這個業務結構很難複製,還有他公司的文化,公司的信用等。
他在股東信裡實際上說得非常清楚,包括他怎麼巧妙地安排一些現金流。比如鐵路是一個現金流非常穩定的生意,它很難有大的爆發式增長。當時收購BNSF的時候,巴菲特沒有用伯克希爾去收購,他用那個國民賠償保險公司去收購。因為保險公司,尤其是這個巨災險業務,將來肯定有一年會出現大的虧損。有可能連著10年都在賺錢,因為沒有巨災發生,你收了保費。但是這個災難只要一來你鐵定是鉅虧的。
巴菲特為了對沖掉這種波動,把鐵路公司安排在保險公司下邊,構造了一個非常穩健的結構。伯克希爾內部類似的這種結構安排非常豐富,包括他的能源公司。伯克希爾在美國西部有很多的發電廠,風電、光伏,在東部和中部也有,佔據了全美國這個天然氣的15%。美國大概8%的風電、光伏也是它的。這是它的一些對沖性的安排。如果發生了經濟危機,對保險的需求不會減退,對能源、對運輸也是。而且越是到這個有風險的時候,保險往往是最好佈局的時候。所以說它有很多保守的、反脆弱性的一些安排,然後使得這個結構更加的穩健。因此現在除了那種極端的恐怖主義、核攻擊、生化武器攻擊之類的,就是常規的經濟因素的話,我們應該是想象不到什麼東西能夠給它帶來巨大的衝擊,應該是沒有。
廖斌:這個結構安排,原來有這些考量,這個我倒是學到了。我以為他買BNSF,是為了純粹的投資收益。當時主流的解讀就是說是因為伯克希爾太大了,很多特別好的生意,他也買不了多少,所以他只能退而求其次。但是從你這個角度來說,倒是更能理解了,它其實是對沖這個巨災保險的,或者說做一個安全墊。
崔士懿:當然,這是一個加分項吧。前提一定是這個生意本身有吸引力,還有價格。但是他透過把它們加入到伯克希爾的這個資產池裡邊,能夠對原本一個波動很大的保險生意有一個更好的平衡。
04
蓋可車險今年的表現突出
崔士懿:今年這個生意層面,我認為最大的一個驚喜就是蓋可車險的一個大爆發。有一位紐約的股東,他是伯克希爾超過30年的股東,然後他連著三年都把一個非常尖銳的問題拋給了巴菲特他們。就說伯克希爾的幾個支柱生意裡邊,一個就是蓋可車險,一個就是BNSF這個鐵路公司。蓋可車險,已經被它的主要競爭對手前進保險連續3年打得抬不起頭來。然後阿吉特就給他解釋說。“我們在做,我們在做。”
從那個他的那個經理人Tony Nicely2018年退休之後,19年到23年,這個生意遇到了大問題。尤其是2023年竟然鉅虧接近20億美元。這是10年之前能夠穩定地給伯克希爾每年貢獻大概10億美元淨利潤,貢獻250 億到300億的浮存金的這麼一個生意,到了前年2023 年,竟然能夠虧損了20億美元。
後來在19年底,就是在疫情之前,他安排那個託德卡姆斯專門去負責這個事。19年底去了,然後用了好多年的時間開始理順了。它實際上是,有一個詞叫Telematics,我們可以把它理解為是一種高科技的那種電子化的資料畫像,之前蓋可對這種科技的投入確實是忽略了。
去年我們確實看到了它的一個經營成果,今年這個蓋可車險的淨利潤大概在七八十億美元,這是一個非常恐怖的資料了。
我看了今年的所有的生意,看了一遍股東信,它的這個能源,它的鐵路都沒有質的變化。包括它的製造業、服務業、銷售,整體上都是大差不差的。今年的最大的變化就在於保險承保業務的大變化,這個蓋可車險功不可沒,應該說是最大的意外驚喜吧。
05
伯克希爾的保險浮存金是不是負債
觀眾提問:伯克希爾為什麼不做壽險?
崔士懿:他也做。他在那個通用再保險下邊有一個小板塊,但是規模很小,不超15%,基本就在 10% 左右的。透過這些佈局你就能夠看出來伯克希爾是多麼保守,他為什麼這麼做呢?因為保險的浮存金它是一項負債。
這個錢,是我們持有但並不擁有,“we hold, but not own”。浮存金是我們持有但並不擁有的一個資產,這個錢一定要是屬於別人的。他為什麼沒有那麼多壽險業務?因為壽險有一個天然的屬性,就是壽險可贖回,包括銀行可能被擠兌,這種情況很少見、很罕見,但一定會發生。
像08年金融危機的時候,很多保險公司就會被擠兌,因為伯克希爾一方面它承擔很多保單的義務,還有很多股東的義務。所以他要讓自己在任何情況之下,哪怕是發生了經濟危機,哪怕發生了戰爭,哪怕紐交所被關閉半年,哪怕是最意外想不到的情況發生了,他也要能夠及時兌付。所以說他就刻意地減少了在壽險方面的開拓,包括他在17年股東信裡說,為什麼我們的保險業務比銀行還要好呢?因為銀行你也可以拿存款,我也可以投資存款,但是這個存款,這個負債在極端情況的之下是有可能被擠兌的。
廖斌:這是生死風險。
崔士懿:這是真實存在的,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但它一定會到來。我們不知道哪一天發生戰爭類似的意外,但它有可能會到來。巴菲特就是說,他不會讓伯克希爾,置於這種風險之下。
因為這個財險是先收保費,它不存在對手的履約風險,包括伯克希爾從2002-2014年參與了大量的衍生品交易,包括高等級的債券擔保,為國債擔保,當然最多的就是賣出4個指數的看跌期權。他有一個特點,任何情況之下他都是先收錢的。這就是一個浮存金的思路,我先收錢,然後我再為你遠期的風險去兌現。當然他評估過機率。
所以說為什麼他的重心放在這種財產險,放在意外險上?就是他是把那種擠兌,把這種資金贖回的可能性降到零。就是說任何情況之下,伯克希爾都不會面臨那種大量的現金需求,這個局面任何時候都不會。哪怕美國的道瓊斯、納斯達克、紐交所都關了,甚至說永久性地關了,就沒有股票了,我光透過我的生意我也可以兌付掉,所以它這個優勢別人是不具備的。
廖斌:就像巴菲特經常用的那個比喻——俄羅斯輪盤賭。這個機率即使非常低,一旦你中了,就如果這一發是有子彈的,那可能就是沒了。即使你贏了,其實你不需要這麼多錢。
崔士懿:我們還是透過巴菲特的履歷梳理這個原因。因為伯克希爾是從他和親戚朋友一起組建的BPL裡邊誕生出來的。他在七八十年代的時候,他能夠認出伯克希爾90%的股東,就是說他的股東大部分都是他認識的人。
廖斌:而且他們的身家都是給了他的。
崔士懿:對,所以說他不想讓自己有那種意外,連可能性都沒有,就是不會讓那種事發生。所以說,他為什麼選擇這個保險而不是銀行,而不是壽險,而是那種財產險和意外險作為現金流,作為這個浮存金。
實際上浮存金這個概念是巴菲特在1986年的股東信裡第一次提到,後來他一直在每年的股東信裡重複的說,重複到現在 40 年了。
順便說一句,除了他之外,其他的保險公司很少有這麼看的,就是他對這個事的理解很透徹。
比方講浮存金,在伯克希爾的資產負債表裡,浮存金在他的右上角是一個負債,目前大概在1700億。這個地方我們要澄清一個情況,這個事不說清楚的話,你永遠不可能理解伯克希爾。
就這個浮存金這個事看起來很簡單,但是如果對於一般的公司的話,一個負債,比如說短期貸款,比如說是應付賬款,它就是負債,你要付的。但是伯克希爾的浮存金透過它的結構安排,它實際上是一個叫週轉金,它永遠不會付。我們可以把這句話說得稍微絕對一點,就是伯克希爾這個浮存金他永遠不會付出去,因為他有很多結構的安排。就是說它在極端情況之下,比方說今年我一筆業務也不做了,它最高的下限是能夠下降3%。
在1996年股東會上就有人問他,你為什麼認為伯克希爾的浮存金跟別的公司不一樣呢?他是這麼說的,因為96年的時候他剛合併了那個蓋可車險,是帶著小 30 億的浮存金來的。他自己透過1967到1996這30年一共積攢了小30億的浮存金,加上蓋可車險的30億, 就是60億。別的負債你要付息你要還賬,但是第一我的保險業務是增長的,在我保守的評估之下,我預期,但我不保證,它會逐步增長嗯。而且整體看來長期看來是賺錢的。
所以,96年的60億浮存金負債以及今天的1700億的浮存金負債,在資產負債表看來,按照會計準則看來是負債需要扣除的。但是在30年前96年的股東會上,他就說在我看來這個東西比伯克希爾淨資產還要好。換句話講,你當時你借他60億的現金,他是不換的。事實也證明了,他從30年前的60億增長到今天的1700億。而且他這個浮存金不但沒有減少,而是以一個非常穩健,但是並不快的增長。他今年股東現在梳理一個數字,就是透過20年的經營,這20年的保險業務一共帶來了320億稅後利潤。
相當於我拿著1700億然後投資,那就保守算按賺10%。保守說,就按之前1000 億。這1000億,10%我每年淨賺100億,同時我還能20年賺320億,就每年15億。這個邏輯實際上很簡單,但其他公司沒有一個能做得到的。伯克希爾是有自己的結構設計的。
廖斌:雖然它是負債,但實際上它不要還。反而可以拿來賺錢。
崔士懿:如果我們對一個公司來估值的話,不考慮別的因素的話,我就是要把淨負債扣掉。這是一個很基本的常識。伯克希爾這個負債,它確實叫負債,但是你如果理解它的商業模式的話,理解伯克希爾這個一路走來的這個商業邏輯的話,它實際上是一個比淨資產還要好的東西,這是他在 96 年股東會上一個非常經典的一個表達。
這事他可能說錯了,你也可能不信,但是就這麼走出來了,這個負債真實地給公司帶來的價值,它比淨資產還要值錢。因為淨資產它本身是不能增值的。就是說如果按教科書來理解的話,這是錯的,負債是我要未來要承擔的一個義務,但是伯克希爾給我們帶來了很多的這個新的啟發。
巴菲特在86年就開始說浮存金這個事,到現在也恐怕也不是每一個人都能理解。
廖斌:是的,你這麼一說感覺就清晰很多。
崔士懿:比如我們在給伯克希爾估值的時候,這1700億到底你剔除不剔除?這就能檢驗你有沒有看過伯克希爾股東信。
廖斌:伯克希爾 60 週年了,現在這個結構以這個財險浮存金為基礎的,這個結構是不是一開始就是設計的,還是偶然的?
崔士懿:這個也是偶然,按照他在23年股東信上的說法是,他最初的設想是想透過銀行。他是1967年買了保險,69年買了銀行。因為在1970年左右的話,它透過銀行投入的錢是更多的,是多於保險的。
只是這個69年出臺了一個商業銀行控股法案。巴菲特說當時美國的監管層可能是為了防止金融業的交叉感染。於是就要求分業經營,這個銀行控股公司不能經營別的。所以那個方案出來之後,巴菲特就被迫將伊利諾伊國民銀行(INB)剝離掉了。他後來在23年下半年的股東信裡提到過這個事,他說如果不是有那個法案的話,可能我們伯克希爾就是一堆銀行,而不是一堆保險了。
當時,他們確實是在到處買銀行,他們在到處看銀行,他們保險看得很少。所以有很多東西它也不是設計出來的,它雖然有意往那慢慢走,但是環境變了,然後它根據環境又進化了幾個東西,就是說這裡邊有很多意外。
後來,巴菲特很幽默地說,“重點不在於我們擁有什麼,而在於你怎麼充分運用你已有的東西。”
06
伯克希爾的估值
廖斌:聽你介紹完之後,保險可能清楚一點了,那麼整個伯克希爾是怎麼來估值呢?
崔士懿:我們也不用自己發揮,我們就按巴菲特自己說的話。
首先伯克希爾現在資產最大的就是它一堆控股生意,我們今年看到它這對控股生意的這個淨利潤已經來到了470億了。怎麼給它估值?就按巴菲特買生意的一個標準就給他 15 倍,當然是很主觀的哈。每個人都不同的標準,就是巴菲特跟芒格他們對伯克希爾的估值也不一樣,所以我們更沒法給他一個準確的估值了,準確的估值也不存在,所以只是一個思路,就15倍。控股生意這一塊470億,給15倍估值的話大概7000億,這是第一塊。
第二塊就是股票,他們目前的股票減了蘋果之後還有2700億,這是市值。我們就籠統的說這裡邊的成本大概1000億,但是他要交稅的這2700億的市值減去1000億的這個成本,資本收益就是1700億的利潤。
順便說一下,伯克希爾不是一個好的投資架構,為什麼呢?因為它是一個公司,你以公司的平臺去投資股票的話,得繳公司所得稅。巴菲特也承認以伯克希爾來做投資,買股票不是好的一個方式。
但是我們就是退而求其次,把這中間的這個資本損益、資本收益1700億,然後乘以20%的稅扣掉之後,我們就保守算扣掉三四百億,這就是2400億或者2500億,因為它還在成長。在這一塊的話大概就接近1萬億了,就9500億吧。
廖斌:差不多是它現在的市值了。
崔士懿:就這兩塊,光股票跟生意,拆開了賣掉,現在也是這個錢。還有3500億的現金,按照目前的利率的話,一年就120億美元以上的淨利息收益,所以說的話加上這塊現金就是目前賣掉值12000億了已經。
還有另外一塊,就是如果他有一些按照權益法核算的資產,比方說西方石油,卡夫亨氏、伯克迪爾,就這幾個公司,它的持股超過20%,按照會計法出來的核算,它就說不能列入股票了,按照權益法來算。他目前這些公司,今年是賺了15億。就再按15倍估值吧,225億。
所有這幾塊加在一起,能夠板上釘釘的,就是他們的這些資產已經1.2萬億,這1.2萬億還要交給這個這麼一個好的結構,交給這麼一個人(巴菲特)來為我們管理,這管理費大概得值多少錢呢?
就巴菲特從95年一直到15年,一直在說一個事兒如何給估值,有三點,一個是投資,一個是經營,還有另外一點。這前兩點都是定量的,我們可以算出來的,你可以保守,你可以激進,你可以客觀,你可以主觀,但是這都是數字,你可以量化。
但第三點是你沒法量化的,就是運用效率。同樣是60年前,同樣是兩個紡織廠,一個給巴菲特,一個給別人,結果是不一樣的,所以說這就它的資本的運用效率。
所以說我認為伯克希爾在1.2萬億的話,就是說你可以無腦買入的一個價格。更重要的是主要是伯克希爾的這個經理人,他特別代表股東利益,只要價格夠低他就回購股票。
這就是我給伯克希爾的估值。
版權宣告:部分文章推送時未能與原作者取得聯絡。若涉及版權問題,敬請原作者聯絡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