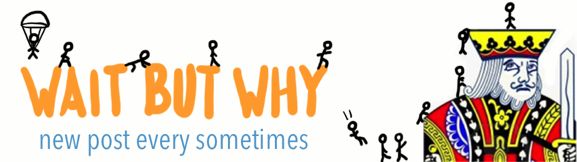一
死是日常的問題、也是哲學的問題,更是很難解的神經科學問題。
莎士比亞讓王子感嘆要不要死(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雖然也是神經生物學問題(Hamlet的大腦要根據當時的資訊決定是否結束承載大腦的個體)、是大腦對自身決策的神經生物學問題,但非本文討論的問題。
本文主題是,如何確定一個人“死”了。
內容非哲學、亦非技術,而是介紹一個巧妙的實驗設計:選擇重要的問題,用二十多年的舊技術,透過巧妙的實驗設計,解決問題。
何為“死”?
有些貌似簡單的現象實際很難定義,而確定生死還是“人命關天”的大事。
確定人死的方法,從前可能是看還會不會動;後來檢測是否有心跳、呼吸;再加上有點科學的檢測是瞳孔對光反射,扒開眼瞼,給光後觀察瞳孔是否縮小。這些方法,分別只說明個體的部分功能缺失,並不說明人完全死了。在任何外界刺激下全身都不動,可能是死了、也可能僅僅運動系統有問題不能表達,而感覺、認知、思維並無問題;心跳、呼吸可以是外周心臟和肺的問題,也可以是腦的低階部分所含的心血管中樞和呼吸中樞的問題,但腦的高階區域還活著;瞳孔對光反射也是針對腦中參與對光反射的區域,並非大腦皮層…
平常對死亡的粗略定義,一般過得去,例如在醫院以外常將無呼吸、心跳作為判斷死亡的標準。但是,在現代醫院只依據呼吸、心跳判斷死亡就不合適。這一問題,不僅與個體有關,與家庭成員如何決定是否撤銷維持呼吸心跳的機器有關,也為人類普遍關心的死有關。
神經生物學結合現代成像技術,可以化解貌似哲學問題的人類實際問題、找到物理學答案。
腦的功能分割槽
要理解後面的解決辦法,需要知道腦的功能分割槽。
1796年,德國醫生Franz Joseph Gall(1758-1828)提出腦不同區域可以透過腦的外殼(顱骨)為外界所觀察。這一假設的第一部分(不同腦區可能有不同功能)是正確的,而第二部分(顱骨反應腦功能)是錯誤的,因為顱骨容易觀察,一般人都能看“顱相”,所以謬誤部分被廣為傳播,發展出所謂“顱相學”(phrenology)的偽科學。
人腦功能分割槽早期的範例為 法國醫生Paul Broca(1824-1880)所發現。1861年4月12日,51歲的 Leborgne成為Broca的病人。患者青年時代起發作癲癇,31歲後基本不能自主說話,在誘導下偶爾可以罵人,還有右側癱瘓、無感覺等症狀。4月18日患者去世,病理解剖顯示左側腦區區域性損傷(Broca,1861)。同年Broca收治患者Lelong,也有語言障礙。至1863年,共8位語言障礙患者,皆有左腦損傷(Broca,1865;Finger,2004)。左腦損傷部位後來稱為Broca語言區,其後很多工作證明Broca區對語言的重要性。

圖1 Broca語言區
患者Leborgne腦左側(自Dronkers等,2007)
解剖和生理學家繼續進行靈長類和人腦的分割槽,如十九世紀德國的Gustav Theodor Fritsch(1838-1927) 和Julius Eduard Hitzig (1838-1907)、英國的David Ferrier (1843-1924),二十世紀初英國的Charles Scott Sherrington(1852-1952)和Harvey W. Cushing (1869-1939),德國的Korbinian Brodmann(1868-1918)和Fedor Krause (1857-1937)等。
美國科學家Wilder Penfield(1891-1976)在洛克菲勒基金會支援下,在加拿大蒙特利爾神經內科研究所(Montreal Neurological Institute)治療癲癇病人時,徵得患者同意,用電極刺激大腦,確定了人運動皮層和感覺皮層的代表區(Jasper and Penfield,1951)(圖2),找到全身體軀的每一部分對應的腦區。

圖2 大腦體區感覺與運動代表區
左為人體不同部位在大腦初級感覺皮層的代表區,右為初級運動皮層代表區(自Penfieldand Tasmussen,1950)
初級感覺皮層位於中央溝後,初級運動皮層位於中央溝前。
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的Roger Sperry自1940年代末起研究動物兩半球分開的後果。大腦兩半球由神經纖維組成的胼胝體所連線,Sperry切除動物的胼胝體可以看到兩半球分開後資訊不能交流,但無甚特別發現。研究生Michael Gazzaniga加入Sperry實驗室後,決定檢測人腦兩半球分開的影響。當時治療癲癇的一種辦法是切開胼胝體。Gazzaniga等設計實驗發現人腦兩半球的功能有所分工,包括語言主要是左腦(Gazzaniga et al., 1962, 1963, 1965; Gazzaniga andSperry,1967)。當然大腦分工並非很絕對,而是相對的優勢,所以稱語言的左腦優勢。
人腦功能分割槽並不意味著功能區域是固定的。事實上,部分割槽域損毀後,其他區域可以逐漸代償,有時相當大的區域損毀後都獲得很強的代償。
腦:物理學的用武之地
神經科學的研究,從來有很強的物理(和化學)交叉。
義大利醫生兼物理學家Luigi Aloisio Galvani(1737-1798)發現電刺激蛙腿導致肌肉收縮,為電生理的開端(因為物理學家Alessandro Volta(1745-1827)對蛙腿收縮實驗的改進和不同理解,開創了電化學和現代人造能源,這是另一光輝歷史)。
檢測神經系統電流、電位的方法,檢測腦活動的方法,都為神經基礎研究和臨床應用不斷需求。從二十世紀初的腦電圖(EEG)到八十年代的正電子掃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PET)、九十年代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imaging,fMRI),都推動了腦機理的研究、改善了腦疾病的診斷。
目前,PET和fMRI主要(但不僅僅)用於檢測區域性腦血流。fMRI作為檢測BOLD(blood oxygen level dependent)訊號的方法,為日裔科學家小川誠二(Seiji Ogawa,1934-)在美國Bell實驗室工作期間發明(Ogawa et al., 1990)。因為脫氧的血紅蛋白(dHb)與氧化的血紅蛋白(Hb)磁性不同,能夠被fMRI所檢測。神經細胞活動增加時,腦的區域性血流增加,帶來更多Hb、改變dHb和Hb的比例,fMRI可以檢測到BOLD訊號,間接反映區域性腦區神經細胞的活躍程度。
用fMRI(和PET)可以對活人大腦在無創性條件下進行觀察,是神經科學的重要突破,並帶來很多有趣的發現,如:可以檢測一般人與專家在聽音樂或下棋時腦區的差別,可以檢測特定經濟決策時腦區的活動,等等。
自然,現在無需Penfield年代由專家開啟病人腦殼將電極插入人的大腦皮層,一般醫生就可以用fMRI觀察正常人大腦的區域活動程度。
目前fMRI的空間解析度在毫米,時間解析度在秒。相對於一個神經細胞只有微米、神經電訊號傳遞在毫秒,腦成像的空間和時間解析度都有待提高。是由fMRI本身的改善可以提高時空解析度,還是出現其他新技術,需要物理學家回答。生物、醫學研究者只能以現有技術進行研究,但選擇問題和設計實驗還是有思考和創作的可能性。
與植物人對話
現代醫學在可以維持人的呼吸心跳的同時,給醫學、倫理出了難題。目前有些國家由社會或家庭經濟狀況影響是否維持植物人的呼吸和心跳,有些國家則完全由家庭成員決定,這並未解決根本的問題,而僅為程式和規則。
如何確定植物人有無意識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英國劍橋大學的Adrian Owen等於2006年在《科學》雜誌發表一篇短文,用fMRI探尋植物人的意識是否存在(Owen et al., 2006)。他們檢測的患者23歲時於2005年7月因為車禍導致腦損傷,雖然有睡眠覺醒的週期,但無臨床醫生可以檢測到的反應,完全滿足植物狀態的診斷。Owen等先在對她說話的時候檢測fMRI,發現好像影像上有反應,但不能確定是有意義的反應。Owen等設計實驗,請正常人設想自己打網球,發現可以用fMRI觀察到腦的特定區域(SMA,輔助運動區)有BOLD訊號,而正常人設想在家裡走動幾個房間時在另外腦區有BOLD訊號。Owen再用語言請患者設想打網球、或在家裡走動,結果發現與正常人一樣的腦區域有BOLD訊號,從而認為該植物人實際有意識。

圖3想象打網球或室內走動時大腦皮層的BOLD訊號
上排兩個為植物人的大腦皮層fMRI成像,下排為正常人的成像;
左為研究者要求被試想象打網球時的訊號,右為被試想象在室內走動的訊號(示意圖,原圖見Owen et al.,2006)
此後,Owen指導的課題組對英國54位診斷為植物狀態的人進行fMRI檢測,5位可以檢測到fMRI的反應,其中一位更神奇:在外界問話時,可以在fMRI訊號上顯示yes 或no(Monti et al., 2010)。
在fMRI的腦成像上,並無直接表示yes或no的區域。Owen等請被試者在回答yes時想象自己打網球,而如果回答no時想像在家裡走動,這樣在正常人可以觀察到打網球的特定BOLD訊號表達yes、在家走動的特定BOLD訊號表示no。在檢測的54位患者中,一位可以正確地回答yes和no。比如問他父親的名字:Alexander是你父親嗎?Daniel是你父親嗎?每次問題後請他用打網球或在家走動代表yes或no,結果他只在被問他父親真名時出現打網球的訊號,其他都顯示在家走動的訊號,說明他能夠學會臨時制定的規則並給予正確的答案。
這位年輕男子的反應說明他肯定有意識,對於他的家人有很大意義:不僅他活著,而且可以與他交流。目前不能檢測到反應的其他患者,並不能斷定缺乏意識,還待新的實驗設計和檢測方法。
fMRI所需要的機器價格昂貴(數百萬美元),不適合一般家庭使用,也不是所有醫院的常規裝置。因此,Owen等開始試用EEG,發現也可以觀察到訊號(Cruse et al., 2011)。
神經生物學研究,對人類思考生死的問題提供了科學基礎。
非常清楚的是:交叉學科大有作為。
進一步閱讀
Broca P (1861) Remarques sur le siège de la faculté du langage articulé;suivies d’uneobservation d’aphémie (perte de la parole). Bulletinsde la Société Anatomique (Paris) 6:330–357, 398–407.
Broca P (1865) Sur le siège de la faculté du langage articulé. Bulletins de la Société d’Anthropologie 6:337–393.
Cruse D, ChennuS, Chatelle C, Bekinschtein TA, Fernández-Espejo D, Pickard JD, Laureys S, OwenAM (2011) Bedside detection of awareness in the vegetative state: a cohortstudy. Lancet 378:2088-2094.
Dronkers NF,Plaisant O, Iba-Zizen MT, Cabanis EA (2007) Paul Broca’s historic cases: highresolution MR imaging of the brains of Leborgne and Lelong. Brain130:1432–1441.
Finger S (2004).Paul Broca (1824-1880). Journal of Neurology 251: 769–70.
Gazzaniga, M.S., Bogen, J. E. and Sperry, R. W. (1962) Some functional effects of sectioningthe cerebral commissures in man. Proceedings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USA 48:1765-1769.
Gazzaniga MS,Bogen 3E and Sperry RW (1963) Laterality effects in somesthesis following cerebral commissurotomyin man. Neuropsychologia 1:209-215.
Gazzaniga MS,Bogen 3E and Sperry RW (1965) Observations on visual perceptionafter disconnection of the cerebral hemispheres in man. Brain 88:221-236.
Gazzaniga MS andSperry RW (1967) Language after section of the cerebral commissures. Brain 90:131-148.
Ogawa S, Lee TM,Nayak AS and Glynn P (1990) Oxygenation-sensitive contrast in magneticresonance image of rodent brain at high magnetic fields. Magnetic Resonance in Medicine 14:68–78.
Owen AM, ColemanMR, Boly M, Davis MH, Laureys S, Pickard JD (2006). Detecting awareness in thevegetative state. Science 313:1402.
Jasper H andPenfield W (1951). Epilepsy and the Functional Anatomy of the Human Brain,2nd edition, Little and Brown.
Monti MM, VanhaudenhuyseA, Coleman MR, BolyM, Pickard JD, Tshibanda L, Owen AM, Laureys S (2010)Willful modulation of brain activity in disorders. New England Journal ofMedicine 362:579-589.
以上首發《饒議科學》作者饒毅
二
The Mother Who Never Stopped Believing Her Son Was Still There
幾十年來,伊芙·貝爾始終堅信,在嚴重腦損傷後失去反應的兒子仍保有意識。科學最終證明她是對的。
本文即將刊登於《大西洋月刊》2025年6月,印刷版標題為“Is Ian Still In There?” 。作者簡介:薩拉·張是《大西洋》雜誌的專職撰稿人。本公眾號轉載自《邸報》。
攝影:薩拉·布萊森納

2025年2月,伊恩·伯格與母親伊芙·貝爾
那年五月的清晨,豐田皮卡撞向大樹的衝擊力如此劇烈,39年後樹幹上仍留著一道清晰的裂痕。車內,三名十幾歲男孩的身體向前猛衝,速度驚人。
一名男孩當場死亡;第二名被發現時在車外尚有氣息;第三名男孩伊恩·伯格則被卡在駕駛座上,前額右側腫起一塊淤青。他的頭部受創極重——遠比淤青表面看起來嚴重得多——這導致他柔軟的腦組織猛地撞擊堅硬的頭骨內壁。在腦組織與骨骼碰撞處,神經纖維拉伸、扭曲、撕裂、迸裂。
當破拆工具將他從殘骸中救出時,伊恩還有呼吸,但已失去意識。“求你別死。求你別死。求你別死。”母親伊芙·貝爾在醫院裡俯身哀求著他。她想象著用一根金色套索纏住他的腳,不讓他飄向遠方。
伊恩活了下來。昏迷17天后,他終於睜開眼睛,但眼球在房間裡瘋狂轉動,無法聚焦或追蹤物體。他無法說話,無法控制四肢。醫生說,嚴重的腦損傷使他陷入植物人狀態。他雖活著,卻被認為已失去認知——沒有思想、感覺和意識。
伊芙厭惡“植物人”這個詞,她認為這是“非人類的分類”。如果在1986年問她,她會說相信17歲的兒子會完全康復。伊恩曾是個英俊、受歡迎的男孩,正與新女友熱戀——彷彿是被命運眷顧的黃金男孩。在學校,他以擁抱問候每個人(包括老師)而聞名。他和車內的兩個朋友屬於一個關係緊密的高年級小團體。但那年六月本該是他畢業的日子,伊恩卻仍躺在醫院病床上,最大的“成就”是終於能自主排便了。
“這算什麼生活?”伊恩的哥哥傑夫記得自己當時這樣想。他第一次到醫院時,曾環顧房間尋找拔除生命維持裝置的插頭。兄弟倆此前曾聊過類似場景,傑夫告訴我:“如果我出了什麼事,連自己擦屁股都做不到,一定要殺了我。”因母親堅持讓弟弟活著而憤怒的傑夫選擇逃離,一度搬到聖托馬斯居住。
事故三個月後,當醫院的醫生對伊恩已無能為力時,伊芙將他帶回家。她堅決主張讓兒子與家人同住,而非在冷漠的療養院接受護理。幸運的是,她有足夠空間安置伊恩和他的所有專業裝置。事故發生前幾周,伊芙的丈夫馬歇爾在紐約伍德斯托克附近偶然發現一座名為“彩虹小屋”的舊旅館正在出售,這裡曾是獵人和漁民的住所。他喜歡為他們的大家庭(包括他的兩個成年子女、侄女侄子,以及伊芙的四個孩子,伊恩是最小的)打造一個家族聚居地的想法。交易在伊恩住院期間完成。
在小屋裡,伊芙和輪流更替的護理人員維持著伊恩的生命:為他洗澡,將家常菜攪成泥透過餵食管餵食,更換導尿管的集尿袋。她還制定了密集的治療計劃,核心是每天長達六小時的“心理運動模式訓練”——她在書中讀到的一種鍛鍊方案,由一組志願者活動伊恩的四肢,模擬嬰兒學爬的動作模式。朋友和熟人前來幫忙進行模式訓練,有些人甚至住進小屋的客房,一待就是數月甚至數年。他們形成了一個以伊恩為中心的非傳統大家庭。每個週日,伊芙都會為眾人烹製豐盛的晚餐。

薩拉·布萊森納為《大西洋月刊》拍攝
1986年伊恩駕駛皮卡撞上的那棵樹,至今仍留有事故的疤痕。
這種缺乏科學依據的模式訓練最終並未真正幫助伊恩,但母親不願糾結於此。她定期致電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詢問最新的腦損傷研究進展。當主流醫學無能為力時,這位在60年代以“準波西米亞/垮掉派”身份搬到伍德斯托克的女性,熱情地轉向替代療法。伊恩接受過靈性導師拉姆·達斯、用擺錘治病的“神奇男子”、顱骶療法師、佛教僧侶、菲律賓“心靈外科醫生”,以及印度昌迪加爾一位治療師的治療。伊芙和馬歇爾曾親自推著租來的摺疊輪椅,帶他完成7000英里的印度之旅。在經歷這一切後,伊恩的狀況仍未改善,伊芙感到憤怒——這是她罕見地允許失望刺破自己不懈樂觀的時刻之一。
儘管如此,如同許多植物人患者的家屬一樣,她堅守著一位母親的信念:伊恩能理解周圍的一切。為他剃鬚時,她特意留下他一直試圖蓄起的稀疏鬍鬚;當他的高中朋友去看“感恩而死”樂隊演出時,她會為他穿上扎染襯衫,用輪椅推著他同去。她的堅持既是為了伊恩,也是為了自己:如果兒子有意識,就意味著她表達愛的舉動不會被忽視,說出的話語不會被置若罔聞。
科學用了數十年才追上伊芙的認知,但她在一個關鍵方面是正確的:伊恩仍有意識。如今醫生們一致認為,他能看、能聽,至少在某種程度上能理解周圍的人。
過去20年間,隨著研究人員利用新工具窺探曾被認為缺乏認知功能者的大腦,意識科學經歷了一場反思。伊恩是去年發表在《新英格蘭醫學雜誌》上一項里程碑式研究的參與者之一。該研究發現,25%的無反應腦損傷患者基於腦活動顯示出意識跡象。這一發現表明,美國可能有數萬人像伊恩一樣——許多人住在療養院,護理人員可能完全不知道他們的病人正默默理解、思考和感受。這些患者生活在極度孤立中,有意識的心智被困在無反應的身體裡。醫生們才剛剛開始探索如何幫助他們。



薩拉·布萊森納為《大西洋月刊》拍攝;貝爾家族供圖
伊恩出院後,伊芙和輪流更替的護理人員、替代療法治療師試圖幫助他康復。自始至終,伊芙都堅信兒子能理解周圍的一切。
對伊恩來說,即便不是在最初,至少在早期就已有跡象顯現。事故三年後,他開始發笑。
伊芙和他在廚房,漫不經心地用滑稽的假聲唱著《危險邊緣》主題曲時,聽到了那聲“哈!”。是笑聲?是笑聲!“除了咳嗽,這是三年來我從他口中聽到的第一個聲音。”她告訴我。漸漸地,伊恩開始對其他事物發笑:伊芙編造的關於一個叫鮑里斯的脾氣暴躁的俄羅斯人的故事,“碎片”這個詞,鍋碗瓢盆的碰撞聲,鑰匙的叮噹聲。關於放屁和大便的笑話一直是他的最愛——他的大腦似乎保留著17歲少年的幽默感。親朋好友認為這意味著他們熟悉的伊恩仍在某處。他還可能在想什麼呢?
當時,伊恩並未定期看神經科醫生。但即便看了,80年代的大多數神經科醫生也不知如何解釋他的笑聲——這與傳統觀念相悖。
醫生們於1972年首次定義了持續性植物人狀態,距伊恩的事故發生不到15年。弗雷德·普拉姆和布萊恩·珍妮特創造了這個術語,用於描述一類令人困惑的新患者——由於醫療進步,他們在過去致命的腦損傷中倖存下來,卻被困在意識邊緣。這種狀態不同於昏迷(一種眼睛閉合的暫時狀態)。植物人患者是清醒的,眼睛睜開,可能並非沉默或靜止。他們會呻吟、活動四肢,只是沒有目的或控制。儘管身體仍在呼吸、睡眠、甦醒和消化,卻似乎與外界毫無關聯。如今,專家有時將植物人狀態稱為“無反應覺醒綜合徵”。
當時,兩位醫生還將其與閉鎖綜合徵區分開來(普拉姆幾年前幫助命名了後者)。閉鎖綜合徵患者意識完全清醒,但除了眼睛通常無法移動(讓-多米尼克·鮑比在1997年出版的關於閉鎖綜合徵的著名回憶錄《潛水鐘與蝴蝶》中,就是透過一次眨一隻眼寫出全書的)。相比之下,普拉姆和珍妮特認為植物人狀態是“無意識的”,沒有完整的認知功能。
那麼,笑聲意味著什麼?到90年代,一些最著名的意識研究專家(包括普拉姆和珍妮特本人)開始意識到,他們或許過於絕對或草率地否定了被診斷為植物人的患者。研究人員記錄到,一些所謂的植物人患者出現了潛在意識的閃現:他們偶爾能說出單詞,偶爾能抓取物體,或似乎能用手勢回答奇怪的問題——這表明他們至少有時能感知周圍環境。他們似乎既非植物人,也非完全清醒,而是在一個連續體上波動。
這種中間狀態在2002年被正式認定為“微意識狀態”,由專門研究腦損傷後康復的神經心理學家約瑟夫·賈奇諾牽頭(昏迷、植物人狀態和微意識狀態有時統稱為“意識障礙”)。

薩拉·布萊森納為《大西洋月刊》拍攝
2007年春天的一天,伊恩的繼父馬歇爾在一塊長滿青苔的石頭上滑倒,髖骨骨折。當他和伊芙等待救護車時,電話響了。賈奇諾聽說了伊芙向國立衛生研究院的諮詢,對見見伊恩很感興趣——他想知道微意識診斷是否適用於伊恩。如果適用,伊恩可能有資格參加一項新的實驗性試驗。
賈奇諾並未作出任何承諾。但伊芙告訴我,經過這麼多年,“他是我聽到的第一個帶來積極可能性的聲音”。因此,即便馬歇爾躺在身邊髖骨骨折,兩人都不敢結束通話電話。
大約在同一時期,2006年,劍橋大學認知神經科學家阿德里安·歐文領導的研究人員發表了一份驚人的病例報告,表明即使是植物人患者也可能保留某種意識。歐文發現一名23歲女性在車禍後數月的行為檢查中仍無反應,但在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中,她的大腦活動驚人:當被要求想象打網球時,血液流向大腦的輔助運動區(幫助協調運動的區域);當被要求想象在家中房間走動時,血液流向大腦的不同區域,包括對空間導航至關重要的海馬旁回;當被告知休息時,這些腦活動模式停止。至少從fMRI掃描的有限視窗來看,她似乎能理解所有指令。
“令人不安和困擾。”一位神經科醫生如此描述該研究的意義。同時,這也頗具爭議。另一位醫生回憶起此後不久的一次科學會議,會上發言者對是否接受研究結果各持己見。fMRI的發現是否只是偶然?歐文未將發現告知該女性的家人,因為研究的倫理協議未明確他能透露多少資訊。他希望自己能告知。該女性於2011年去世,家人從未得知她可能有意識。
隨著時間推移,歐文和他的團隊發現了更多他們所稱的“隱性意識”患者。有些被診斷為植物人,有些則被認為處於微意識狀態(基於眼球追蹤和服從指令等行為)。研究人員發現,外在反應與內在意識並不總是相關:身體反應最明顯的患者,在被要求想象任務時,腦活動跡象未必最清晰。因此,隱性意識只能透過fMRI等窺探大腦內部活動的工具檢測。
2010年,歐文的合作者、比利時神經科醫生史蒂文·洛雷斯在fMRI中向一名22歲的微意識狀態男性患者提出五個是非問題,涉及他父親的名字和摩托車事故前的最後一次假期等。回答“是”時,患者需想象打網球30秒;回答“否”時,想象在家中走動。研究人員僅提問一次,但他全部答對,每次相應的大腦區域都會啟用。
很難說大腦掃描上的彩色畫素究竟描繪了怎樣的人類意識體驗。要故意回答問題,患者必須理解語言,還需將問題儲存在工作記憶中,並從長期記憶中檢索答案。在與神經科醫生的交談中,他們反覆提到這項研究,認為這是隱性意識最有說服力的證據。
幾年後,歐文用同樣的是非問題法發現,一名植物人患者似乎知道自己腦損傷後出生的侄女。對歐文來說,這表明該男子仍在形成新記憶,生活並未從他身邊完全溜走。在另一案例中,歐文不僅用fMRI向一名38歲植物人男子提問,還詢問他腦損傷12年後的生活質量:他現在痛苦嗎?不。他是否仍像從前一樣喜歡看電視上的曲棍球比賽?是的。
我採訪的大多數研究人員都不願推測這些腦損傷患者的內心生活,因為答案超出已知科學範疇。洛雷斯告訴我,微意識患者的大腦確實會對疼痛或音樂產生反應,但他們對疼痛或音樂的體驗可能與你我不同。他們的意識狀態可能類似於半夢半醒的朦朧地帶,且幾乎肯定因人而異。歐文認為,他的一些植物人患者可能實際上“完全清醒”,類似於閉鎖綜合徵患者(完全有意識,但連眼睛都無法移動)。在被證明相反之前,他認為沒有理由不姑且相信他們有意識。
接到賈奇諾辦公室的電話幾個月後,伊恩的家人前往新澤西會見這位研究人員。在檢查室裡,賈奇諾對伊恩進行了一系列高強度測試。他發現伊恩能偶爾按指令伸手夠紅球。他會對鑰匙叮噹等巨響發笑,賈奇諾說這可能只是對聲音的簡單反應。但伊恩也會對笑話(尤其是青少年式的笑話)恰當地發笑,彷彿能理解幽默和意圖。這些行為足以讓伊恩在事故20年後獲得一個全新診斷:非植物人狀態,而是微意識狀態。
賈奇諾的合作者急於讓伊恩進入fMRI機器,觀察他大腦內部的活動。在另一次前往紐約市fMRI設施的行程中,家人見到了威爾康奈爾醫學院的神經科醫生、弗雷德·普拉姆的弟子尼古拉斯·希夫。希夫也對伊恩的笑聲及他可能“心有靈犀”的可能性感興趣。希夫的團隊向伊恩展示圖片、播放聲音(以觀察他的大腦能否處理面孔和語音),並要求他想象在屋內走動等任務。
伊恩的哥哥傑夫也在掃描現場,此時他已回到紐約。擠在fMRI控制室裡,看著科學家們盯著弟弟的大腦,他記得自己對他們要求伊恩想象的事情充滿懷疑。“你們真覺得他能理解你們?”他問。


薩拉·布萊森納為《大西洋月刊》拍攝
左:威爾康奈爾醫學院神經科醫生尼古拉斯·希夫懷疑伊恩“心有靈犀”。右:伊恩的腦部掃描圖。
科學家們確信如此。他們相信伊恩仍保留某種意識,也認為若運氣好且工具得當,有可能解鎖更多意識。這曾在其他患者身上發生過。在一些特殊案例中,清醒與無意識之間的界限比想象中更易突破。
2003年,阿肯色州的特里·沃利斯在療養院作為植物人躺了19年後,突然喊出“媽媽!”,接著說“百事”——他最愛的汽水。此後,母親將他帶回家。沃利斯頸部以下無法活動,記憶和衝動控制存在障礙,但開始用短句說話、認出家人,並繼續索要百事可樂。回想起來,他最初的19年可能根本不是植物人狀態,而是微意識狀態。他的母親看到了療養院其他人未注意的跡象:沃利斯偶爾用眼睛追蹤物體,目睹患有痴呆的室友死亡後會變得煩躁。
隨著時間推移,沃利斯的大腦逐漸恢復至能重新說話的程度。希夫及其同事後來對他進行掃描時,發現了神經元連線在損傷數十年後仍在形成和修剪的跡象。“特里改變了我們對可能性的認知。”希夫告訴伊恩的家人。
還有南非的路易斯·維爾容,1999年因服用唑吡坦(更廣為人知的商品名是安必恩,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是一種本應讓他入睡的鎮靜劑)而開始說話。他在被卡車撞擊後也被宣佈為植物人,一位醫生稱他為“捲心菜”。母親回憶,他在服用唑吡坦25分鐘內開始發出第一個聲音,當她說話時,他回應:“你好,媽媽。”隨後藥物效果如來得一樣迅速消退。
維爾容每天繼續服用唑吡坦,最終恢復到即使不服藥也能保持清醒的程度,但每日一劑能讓他更有活力。“九分鐘後,蒼白消失,面色紅潤。他開始微笑大笑。十分鐘後,開始提問。”2006年一位見過他的記者寫道。包括金剛烷胺和阿撲嗎啡在內的其他幾種藥物也有類似的喚醒效果,儘管僅對極少數患者有效。在某些人身上,出於未知原因,這些藥物可能足以啟用受損大腦,“如同乘上波浪”,研究過安必恩治療患者的希夫告訴我。
研究人員稱,最重要的結論很簡單:隱性意識患者存在,且並非極為罕見。
新澤西的格雷格·皮爾遜於2005年作為希夫和賈奇諾研究的一部分,在丘腦植入電極。丘腦是大腦中核桃大小的區域,位於顱底開口上方(脊髓與大腦連線處),這一位置使其在腦損傷時尤其脆弱:當瘀傷的大腦腫脹時,無處可去只能向下,對丘腦造成巨大壓力。由於丘腦通常負責調節覺醒(希夫將其比作大腦的起搏器),該區域損傷可引發意識障礙。希夫想知道刺激丘腦能否恢復其部分功能。事實上,手術中開啟電極時,皮爾遜喊出了多年來的第一個詞:“Yup.” 他最終能背誦《效忠誓言》的前16個詞,並對母親說“我愛你”。
受損的大腦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更像一盞線路故障、忽明忽暗的燈,而非線路被徹底拆除的燈。若是如此,這些神經迴路便可被操控。神經外科醫生懷爾德·彭菲爾德數十年前便意識到這一點,當時他發現輕輕按壓大腦某一區域可使清醒患者失去意識。
若考慮每天發生的事,意識其實是動態的、可調節的,這並不奇怪:我們夜晚入睡時失去意識,次日清晨重新清醒。當大腦受損嚴重、無法自行恢復時,能否透過人工手段“重新喚醒”意識?
2007年皮爾遜的研究發表後,希夫辦公室的電話應接不暇。他和同事開始尋找更多患者,包括最初反應比皮爾遜更微弱的人——他們的狀況將考驗電極深部腦刺激的極限。
鑑於伊恩雖反應有限但仍可辨識,他似乎是完美人選。研究人員謹慎地不做保證,但伊芙懷揣著伊恩有朝一日能對她說“我愛你”的希望,家人同意加入試驗。
長話短說:伊恩的深部腦刺激並未奏效。在植入電極的手術中,他說出了1986年以來唯一清晰的詞——“下”,回應“什麼是上的反義詞”的提問,隨後再次陷入沉默。在接下來的數月裡,治療師花數小時要求伊恩移動手臂或回答問題,均無結果。
當時從事影片製作的傑夫用鏡頭記錄了整個過程。他本打算製作一部紀錄片,記錄他期待中的弟弟康復。除了拍攝試驗中的伊恩,他還錄製了家人的採訪,詢問聽到伊恩再次說話對他們意味著什麼。
他從未完成這部紀錄片。他覺得,沒有奇蹟般的康復,這個故事太過悲傷。去年冬天,傑夫翻出舊錄影帶,我們在客廳電視上一起觀看。他自近20年前拍攝後便再未看過。“不忍直視。”他多次說道。

薩拉·布萊森納為《大西洋月刊》拍攝
事故發生時,伊恩(高中班級影片中的畫面)距畢業僅剩一個月。
伊恩回家後,彩虹小屋的生活基本恢復原樣,但有一件事確實改變了——尤其是對傑夫而言。得知科學家如今認為伊恩保留某種意識後,他對弟弟的態度徹底轉變。他開始花更多時間陪伴伊恩,兄弟倆重新建立起親密關係。“伊恩,你是有意識還是棵植物?”我探訪時傑夫調侃道,“我覺得你是植物,長得像金橘。”
傑夫最終承擔了越來越多的護理工作,如今透過醫療補助成為兼職護理員,協助86歲的伊芙。每天晚上都是傑夫哄伊恩入睡,仔細鋪平床單確保他不會整夜壓在褶皺上。他在伊恩左側墊上額外枕頭,因為他的頭總愛往那邊歪。
對伊芙而言,照顧孩子是天性。她告訴我,她一生的志向就是成為母親。她18歲結婚,很快接連生下三個孩子。當婚姻出現裂痕,她和第一任丈夫決定嘗試開放式關係。1964年,伊芙在伍德斯托克一家咖啡館當服務員,店主讓一個叫鮑勃·迪倫的歌手住在樓上。她和男人們調情,和迪倫調情——後者帶她去打檯球,給她看正在創作的《塔蘭圖拉》書稿(“鮑勃比蒂莫西·柴勒梅德可愛多了,”談及近期迪倫傳記片的主演時她說)。最終她離婚,第二任丈夫是伊恩的父親,第三任丈夫馬歇爾是紐約市一位事業有成的藝術家。伊芙和馬歇爾原本計劃等伊恩畢業後多在紐約生活,車禍徹底打亂了一切。
此後,伊芙重新全身心投入母親的角色(馬歇爾在2011年去世前一直協助照顧伊恩)。即便如今有傑夫和每週五天在崗的兩名護士,伊芙仍堅持親自完成某些任務:修剪伊恩的指甲和頭髮(頭頂頭髮漸稀,露出深部腦刺激手術的淡淡疤痕)、為他剃鬚。和兒子說話時,她會俯身靠近,兩人相似的鷹鉤鼻幾乎相觸。這時,伊恩會發出“啊啊啊”的聲音,彷彿試圖和母親交談。

薩拉·布萊森納為《大西洋》拍攝;貝爾家族供圖
伊恩的繼父馬歇爾與伊芙共同照顧他直至2011年去世。
“我覺得伊恩為媽媽而活。”傑夫某次回憶起醫院場景時告訴我,當時伊芙在兒子昏迷的身體旁哀求,用想象中的金色套索將他拴住。她當時向伊恩承諾,只要他活著,她願意為他做任何事——因此有了各種治療師、研究試驗,以及39年來不離不棄的照料。
伊恩在深部腦刺激手術康復期間,伊芙讀到E.E.卡明斯的一首詩,深受觸動,從此每天早晨都大聲讀給他聽。詩的第二節寫道:
(我曾死去,今日重獲新生,
這是太陽的生日;這是生命、
愛與翅膀的生日:是歡樂的
無限大地的盛事)
希夫繼續探索嚴重腦損傷患者意識的極限。去年,他與歐文、洛雷斯及該領域其他研究人員發表了迄今為止規模最大、最全面的隱性意識研究,即包含伊恩的《新英格蘭醫學雜誌》研究,發現四分之一的植物人或微意識腦損傷患者存在隱性意識(希夫更傾向於“認知運動分離”這一術語,以強調患者心理與身體能力的脫節)。“我們的感受是‘哇,找到這些人並不難’。”希夫告訴我。
研究人員並不認為所有意識障礙患者都保留認知功能——根據這項研究,大多數可能沒有。但最重要的結論很簡單:隱性意識患者存在,且並非極為罕見。
這些發現引發了關於我們對嚴重腦損傷患者倫理責任的深刻問題。康奈爾大學醫學倫理學家約瑟夫·芬斯(常與希夫合作)在2015年出版的《權利降臨心智》一書中指出,此類患者不應被“冷漠的醫療體系拋棄”,或淪為僅需餵食和清潔的軀體。“長久以來,我被剝奪了一切身份,”腦損傷患者朱莉婭·塔瓦拉羅在回憶錄《抬頭說‘是’》中寫道,“我開始認為自己連動物都不如。”她能寫出這本書,得益於一名特別細心的語言治療師在她受傷六年後,終於注意到她能用眼睛交流。但芬斯告訴我,患者常被送進無法提供足夠關注和康復治療的長期護理機構,而這些治療本可發現意識的微妙跡象。
這些患者也尤其易受虐待。2019年,鳳凰城某機構一名據稱為植物人(可能為微意識)的患者意外分娩,工作人員驚慌報警。她在該機構住了多年,直到護士看到嬰兒頭部才知道她懷孕——她被一名男護士強姦了。
在某些案例中,隱性意識患者可能根本無法進入長期護理——他們在醫院撤去生命支援後直接死亡。“回溯15、20年前,醫生中瀰漫著大量虛無主義。”耶魯大學神經科醫生凱文·謝思說。儘管醫學對腦損傷的態度已不再那麼悲觀,醫院仍很少用fMRI檢測隱性意識:重症監護患者可能過於脆弱,無法移動到fMRI機器處,而該技術過於笨重昂貴,無法引入重症監護室。
北卡羅來納大學神經重症專家瓦里納·布林溫克爾認為,該技術應常規用於腦損傷患者。她告訴我2021年在之前工作單位治療的一名6歲車禍男孩的故事。她最初認為他無法存活,第一次fMRI掃描顯示無意識跡象。布林溫克爾開始懷疑醫生是否在延長他的痛苦,但團隊在第10天、計劃與男孩父母討論撤去治療前再次檢測。令她震驚的是,男孩的大腦現已活躍:當被要求在fMRI中執行特定心理任務時,他能做出反應。
腦植入物已在幫助某些癱瘓患者用思維控制游標或透過電腦合成語音說話。
起初,布林溫克爾不知如何向男孩家人解釋fMRI結果:儘管暗示他仍有認知功能,但無法保證他能恢復到做出身體或語言反應。她告訴我,同事見過家庭因照顧嚴重腦損傷兒童而掙扎,所有人都警惕提供虛假希望。
醫生最終告知男孩父母發現,母親稱fMRI給了他們同意另一場手術的信心。手術成功了。四年後,男孩重返校園,用眼球追蹤裝置交流,坐著輪椅四處活動,讀寫和數學能力與同齡人相當。
科學家如今在尋找更簡單的隱性意識檢測工具。似乎早期顯示意識跡象的患者預後更好。現於西安大略大學的歐文最近發表了一項使用功能性近紅外光譜(透過頭骨照射光線)的研究。哥倫比亞大學簡·克拉森團隊正試驗置於頭部的腦電圖電極。
但即便經過20年研究,對於受傷多年後被發現有隱性意識的患者,醫生能做的仍幾乎為零——多數情況下仍束手無策。希夫辦公室牆上貼著五名患者的腦掃描圖,提醒自己工作的人性意義。他如今在探索腦植入物,這類技術已在幫助某些癱瘓患者用思維控制游標或透過電腦合成語音說話。未來幾年可能至關重要,多家資金充裕的公司正測試與大腦互動的新方式:埃隆·馬斯克的Neuralink(或許最著名)使用類似縫紉機的機器人植入細絲;Precision Neuroscience的薄膜漂浮在皮層上方;Synchron的植入物透過頸靜脈向上穿入大腦。
讓任何此類植入物在伊恩這樣的嚴重損傷患者身上奏效都將極具挑戰。伊恩的年齡和已植入大腦的電極也使他不太可能成為早期候選人。這項技術(若終將適用於他這樣的人)可能對伊恩來說為時已晚。
即便在1972年普拉姆和珍妮特首次描述植物人狀態時,兩人已預見將面臨“人道主義和社會經濟影響的難題”。他們描述的植物人患者如今可無限期存活——但應該嗎?代價為何?誰來決定?很快,普拉姆本人便被要求對一名21歲女性的生命發表意見。
1975年,普拉姆成為凱倫·安·昆蘭案的首席證人。昆蘭因服用摻酒的安定後昏迷,陷入植物人狀態。父母希望撤去她的呼吸機,醫生拒絕。在隨後的法律糾紛中,昆蘭的家人和朋友作證稱,她曾在談論癌症患者時表示不想“靠機器維持生命”,但無從知曉她對當前狀況的意願。普拉姆斷言她“不再有任何認知功能”,另一名醫生在法庭證詞中將她比作“無腦怪物”。
最終,法庭批准父母撤去昆蘭呼吸機的請求。圍繞她案件的爭議激發了對當時尚屬新穎的預立醫療指示的關注,這類檔案允許人們闡明未來失能時是否及何時願意死亡。法庭承認生命並非永遠值得延續,這一裁決也催生了美國初興的“死亡權利”運動。
到2000年代初佛羅里達州的特麗·夏沃案引發全國關注、重提許多相同法律倫理問題時,科學已變得更為複雜。夏沃因心臟驟停昏迷後也被診斷為植物人,八年後狀況未改善,丈夫尋求撤去餵食管,父母激烈反對。儘管多數專家認為她是植物人,支援父母的人卻抓住新定義的微意識狀態,辯稱夏沃仍有意識。家人公佈影片片段,稱顯示她對母親聲音有反應或用眼睛追蹤米老鼠氣球。他們認為,若她仍有意識,就不應被“判處死刑”。
夏沃成為宗教右翼的旗幟性人物,輿論兩極分化。一方視為父母尊重女兒生命,另一方視為執迷虛幻希望。賈奇諾告訴我,由於在定義微意識狀態中的關鍵角色,佛羅里達州長傑布·布什辦公室曾請他檢查夏沃。他計劃進行的行為檢查本可幫助判斷夏沃的反應是真實還是隨機,但他最終未去佛羅里達,因為法庭程式使再次檢查失去意義。
夏沃在2005年撤去餵食管後死亡。如今普遍認為她很可能是植物人(屍檢發現她的大腦已萎縮至正常大小的一半),但賈奇諾仍疑惑這與她的意識水平有何關聯。由於從未親自檢查過她,他個人保留判斷。
若夏沃(或假設如她一樣被診斷為植物人的患者)事實上處於微意識或隱性意識狀態,這是否會改變“是否讓她活著”的權衡?如何改變?一方面,扼殺人類意識是可怕的;另一方面,有人可能認為,被困在完全無法選擇、毫無自由的身體裡,比死亡更糟糕。在回憶錄和採訪中,重獲交流能力的腦損傷患者(包括塔瓦拉羅)談及絕望、虐待和無盡的厭倦:他們甚至無法轉頭凝視另一塊牆漆。一名年輕男子描述了被粗心地安置在輪椅上、被迫壓著睪丸坐數小時的特殊痛苦。有些人曾試圖憋氣自殺,卻發現身體無法做到。傳統觀念中完全無意識的植物人狀態至少提供了微薄安慰:無意識的人不會經歷痛苦或折磨。
根據比利時神經科醫生洛雷斯對65名閉鎖綜合徵患者的調查,三分之一僅能用眼睛交流的患者曾經常或偶爾想過自殺,但多數從未有過。他們稱自己快樂,且閉鎖時間更長的患者報告更快樂,這與其他研究顯示殘障人士長期適應能力很強的結論一致。當然,回應調查者並不完全代表所有腦損傷患者——畢竟他們至少仍能交流,儘管困難。
那些完全失去交流能力的隱性意識患者呢?他們為活著感到快樂嗎?據我所知,僅有一人曾有機會回答這個問題。在2010年的研究中,22歲男子連續正確回答五個是非問題後,洛雷斯決定提出最後一個他尚不知答案的問題:你想死亡嗎?
該男子此前反應明確,這次卻模糊不清。掃描顯示他既未想象網球也未想象房子,似乎既非想“是”也非“否”,而是更復雜的想法——具體是什麼,我們永遠無從知曉。
我向畢生致力於理解意識障礙的研究人員提出類似問題:你會選擇活著嗎?“如果無人施救,援助無期,我不想處於任何一種狀態。”希夫說,他對未來可能幫助這些患者的腦植入物研究持務實態度。
歐文更具哲學性。他告訴我,人們得知他的研究後,許多人說寧死也不願如此,連他妻子也這麼說。但他更不確定。他沒有預立醫療指示。或許唯一比“想死卻被迫活著”更糟糕的,是看著所有人在“關鍵時刻”決定你死亡,而你卻在那一刻意識到自己其實想活。
去年冬天我某次探訪彩虹小屋時,傑夫除錯了伊恩的腳部開關——家人嘗試過的無數輔助裝置之一——為我播放預錄語音。“嘿,薩拉,謝謝你來!”傑夫用抑揚頓挫的聲音說道,“很高興見到你。”家人曾一度希望伊恩會動的左腳(不像固定的右腳)能成為交流方式,但他從未能可靠地按指令踩下開關。不過偶爾,他會用力按下綠色大按鈕,觸發語音。

薩拉·布萊森納為《大西洋月刊》拍攝
儘管起初質疑母親讓伊恩活著的決定,哥哥傑夫如今成為他的護理者之一。
我無法知道這動作在多大程度上是自願的,但伊恩的腳確實在某些時候更活躍。某天我們在廚房餐桌旁吃午餐聊天時,它“啪嗒、啪嗒”作響。“嘿,薩拉,謝謝你來!”他是想加入對話嗎?“嘿,薩拉,謝謝你來!”如果是,他想說什麼?
還有一次我見過他的腳如此頻繁移動——在前一次探訪、我們首次詳細談論伊恩車禍時。車禍發生在清晨,男孩們徹夜相聚後,伊恩駕車。當伊芙被要求辨認死亡男孩山姆的遺體時,她認出了伊恩最近從佛羅里達旅行帶回送給他的白色貝殼項鍊。第三名倖存男孩最終不再與高中朋友聯絡,大家認為是倖存者內疚所致。
我想知道我們的談話是否讓伊恩痛苦,是否該在他面前重提這些往事。在我看來,他的臉似乎格外緊繃,腳“啪嗒、啪嗒、啪嗒”動著。還是說,我只是在對無法回應的人投射自己的想法?“伊恩知道他害死了最好的朋友,”那晚傑夫說,“意外的。”
第二天,伊恩在咬牙。伊芙告訴我,這有時會發生,可能是哪裡疼、腸胃不適,或睫毛進了眼睛。他們試圖逐一排除原因,但始終是猜測。我想起前一晚的談話,是否陌生人追問他生命中的創傷事件可能讓他煩躁。
伊恩無法從不想參與的對話中抽身,也無法糾正我們的錯誤。如果他的記憶和認知基本完好,那麼他有太多時間活在自己的思緒裡。他是否對朋友之死有了自己的感悟?是否感到倖存者內疚?是否曾希望自己遭遇的是車內朋友的命運,而非現實?或許無法產生這些想法本身就是一種慈悲。
某次,傑夫決定重新程式設計伊恩的腳部開關,部分是為了逗莫莉·霍爾姆開心——她自2008年起成為伊恩的護士,因在冰上滑倒撞傷肋骨。莫莉高中時就認識伊恩,他是她哥哥的朋友。事故後她開始來彩虹小屋參加模式訓練,站在伊恩右手邊,後來成為護士。她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腦創傷中心,照顧像伊恩一樣的年輕男子。在一些植物人患者身上,她會看到看似意識的閃現,但作為毫無經驗的護士,她哪敢質疑醫生的診斷?莫莉說,該機構的一些男子很少有訪客,他們的孤獨與伊恩家中的溫暖截然不同。
這正是多年前吸引極度不快樂的14歲少女莫莉來到彩虹小屋的原因(好吧,她承認,車禍前曾瘋狂暗戀伊恩)。這也吸引了其他人,包括模式訓練時期暫住小屋客房的人:伊恩的女友瓦萊麗·卡申、傑夫21歲懷孕且剛與男友分手的朋友凱倫·麥肯納,以及最出人意料的——車禍中死亡男孩的母親蕾妮·蒙大拿。
伊芙在醫院裡聽到蕾妮悲痛欲絕的哭聲,後來兩人見面時,這兩位母親並未因各自的悲劇隔閡,反而感到彼此相連。

瓦萊麗、凱倫和蕾妮都因各自生活的困境來到彩虹小屋。兩位年輕女性住了一兩年,成為摯友。凱倫在伊恩受傷前根本不認識他,最初作為家庭朋友到醫院探望,因無所事事主動提出幫伊芙看護伊恩。她住在小屋時生下孩子,伊芙擔任拉瑪澤呼吸法教練陪在她身邊。照顧伊恩的經歷促使凱倫報考護理學校,最終成為她首次見到伊恩的那家重症監護室的護士。
蕾妮住了幾年。她不責怪伊恩導致山姆死亡,儘管她知道別人會。當我問她是否想過如果命運互換會怎樣,她立刻回答:“我可憐的孩子會被送進收容機構。”
她沒有能力在家照顧他,也沒有彩虹小屋這樣的地方。作為單親媽媽,她和男友的關係瀕臨破裂。伊芙和馬歇爾接納她進入社群,讓她免於漂泊。“他們救了我的命。”她說。她的人生也在此發生意外轉折:蕾妮與伊芙的弟弟短暫相戀後,於1988年生下女兒莫爾加妮。
在這些混亂的境遇中,伊芙和蕾妮的友情昇華為親情。伊芙也陪伴了這個新生命的誕生,親手剪斷莫爾加妮的臍帶。回到小屋後,她們把女嬰放在伊恩腿上,讓他抱著這個因他人生軌跡改變而誕生的新生命。如今37歲的莫爾加妮告訴我,她最早的記憶就是蜷在伊恩腳邊看電視。
回顧伊恩車禍後的生活,伊芙更願意談論收穫而非失去:一個新侄女、一生摯友、整個彩虹小屋社群。她早已決定,要用自己頑強的樂觀支撐他人——尤其是伊恩。在我們長談的數小時裡,我從未聽她沉溺於消極情緒。
在這一點上,傑夫不像母親。“傑夫更會說‘我懂你的痛苦,兄弟’。”莫莉告訴我。她補充說,兩人有著不同的紐帶,“因為傑夫承認,有時候,這一切真的很糟。”
“是啊,確實很糟,對吧?”傑夫說,“無法交流太糟了。”
傑夫的應對機制是幽默,有時帶點黑色,有時很孩子氣。好在伊恩最可靠的反應是笑。當他真的笑起來,輕笑會變成整個胸腔的震動。傑夫仍夢想著能幫助弟弟交流的技術,目前,他們還有腳部開關。
莫莉受傷後,傑夫錄製的語音是為了逗她和所有人開心:他模擬放屁聲,製造物品散落的聲音,大喊“天啊!怎麼回事?”然後把開關放在伊恩左腳下方。

薩拉·布萊森納為《大西洋月刊》拍攝
莫莉和傑夫共同照顧伊恩,並將在伊芙去世後繼續承擔這份責任。
傑夫如此渴望讓莫莉振作,還因為他們是情侶,從2000年相戀至今。在這段關係中,傑夫與莫莉護理的另一位患者——一個活潑的男孩——結下深厚情誼,男孩最終在20多歲時死於大皰性表皮鬆解症(又稱“蝴蝶皮膚綜合徵”)。他們沒有親生子女,卻成為一個護理單元,對男孩共同的愛讓感情更深。如今他們共同照顧伊恩,並將在伊芙離去後繼續承擔這份責任。
我最後一次離開彩虹小屋時,伊芙讓我明白她希望人們從伊恩的人生中感受到什麼:“這不是個悲傷的故事。”莫莉對此表示認同。沒錯,有時很糟,但伊恩始終被愛他的人環繞,這些人將愛轉化為實實在在的陪伴。
彷彿是為了呼應,伊恩的腳部開關突然啟動:放屁聲、物品散落聲、“天啊!怎麼回事?”也許這只是他腳部的隨機動作,也許他想反駁母親的評價,也許他同意自己的故事並不悲傷。要是他能親自告訴我們該多好。
說明:本號刊發來自各方的文章,是為了獲得更全面的資訊,不代表本號支援文章中的觀點。由於微信公眾號每天只能推送一次,無法即時更新,因此,本站目前在騰訊新聞釋出最新的文章,每天24小時不間斷隨時更新,請收藏以下地址(請完整複製),隨時重新整理:
https://news.qq.com/omn/author/8QIf3nxc64AYuDfe4wc%3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