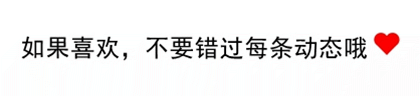贏在閒暇時
原創|孫貴頌
胡適先生說過:“凡一個人用他的閒暇來做的事業,都是他的業餘活動。往往他的業餘活動比他的職業還更重要,因為一個人的前程往往全靠他怎樣用他的閒暇時間。他用他的閒暇來打麻將,他就成個賭徒;你用你的閒暇來做社會服務,你也許成個社會改革者;或者你用你的閒暇去研究歷史,你也許成個史學家。你的閒暇往往定你的終身。”

八小時之外,一個人要忙的事情有很多:有些是屬於非幹不可的,如做飯,如購物,如家務;有些屬於可幹可不幹的,如聊天、喝酒、看電視;有些屬於喜歡乾的,如讀書、寫作、打麻將。
而最終成就最大的,或許就是最喜歡乾的某些事甚至是某件事。
世界著名發明家愛迪生一生中經常是一邊工作,一邊利用業餘時間搞實驗,有時一天只睡4個小時。
他有句名言:“天才就是百分之一的靈感和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如果沒有那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天才也就歸於零。
愛迪生的妻子擔心他經常通宵達旦地工作,累垮身體,勸他找個地方休養休養。“上哪休養呢?”“你自己找個地方吧!”“我自己喜歡的地方?”愛迪生拍拍腦袋,說:“好的,我找到一個我喜歡的地方了。”於是說好,次日動身。
然而,當妻子準備好了行裝,卻找不到愛迪生了。最後發現,他原來就在實驗室裡。愛迪生對妻子說:“這就是我喜歡的休息勝地啊!”

曾與一位在博物館工作的朋友聊天,他告訴我:“許多人都以為我這個工作很枯燥,沒意思,佩服我耐得住寂寞。其實他們不知道,我這一輩子最為慶幸的,是學了一個考古專業,幹了這樣一個對口的職業,真是如魚得水。”
這位朋友,閒暇時間,幾乎都用於鑽研考古業務。就連春節放假期間也喜歡到辦公室坐一坐,看看書,摸摸文物,因為太有感情了。也正因為如此,他成了著名的考古學家。
作家無一例外,最初都是業餘作者。因為喜歡,乃至熱愛。因為熱愛,所以勤奮。沒有一個人是自己不愛學習、被外力逼迫寫作而成為作家的。因為在他們看來,正如雜文作家阮直所說:“讀書是讀一顆高拔靈魂的思考,讀一個偉大生命的舞蹈。而寫作則是精神貴族最奢華、最極致的享受。”
曾有朋友與我探討寫作問題。我問他,你一年寫幾篇文章?回答說:“七八篇。”我笑了。這樣的人,哪怕有非凡的才能,也成不了一個作家。因為他的業餘時間肯定沒有花在讀書與寫作上。雖說稿酬有限,寫作是個出力卻不一定能討利的事情,但卻是真正的文學愛好者最熱愛、最喜歡的事情。
如果,八小時之內是決定現在,那麼八小時之外的閒暇時光則決定了未來的成敗。
來源|前線理論圈、守望新教育。
給教育一些“閒暇”
原創|李希貴
我知道這是一個過於理想化的命題。
但我也知道,這應該成為我們孜孜以求的教育理想。給教育一些“閒暇”,給孩子們一些“閒暇”,也給我們的教師一些“閒暇”。只有如此,我們的教育才能真正走出浮躁,走出急功近利。

紐約大學教授尼爾·波茲曼經過認真考證後發現,“學校”這個概念是希臘人發明的,在希臘文中,“學校”一詞的意思就是“閒暇”。在他們看來,只有在閒暇的時候,一個文明人才會花時間去思考和學習。
原來如此!
我的一位朋友曾經在她經營的一所民辦學校裡,給老師和學生創造了一些聊天的機會,讓大家在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的談話中收穫成熟。在她看來,聊天可以聊出智慧,聊天可以聊出靈感,聊天甚至可以聊出神奇。
考察英國的伊頓公學時,發現它同樣有一個讓師生聊天的時間。每逢週末,每位老師都要帶十位學生回到自己的家裡,與他們一起做飯,一起遊戲,在輕鬆自如中互相敞開心扉。事實上,在聊天中,真才能駐足,情才能瀰漫,教育也才能真正奏效。有人曾經對伊頓公學的畢業生做過一次調查,發現在母校的所有活動中,他們認為最應該保留的專案竟然是週末的聊天。
想一想羅素的成長經歷吧。他之所以能夠成為偉大的哲學家、數學家、邏輯學家和社會思想家,並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並不是由於學校的系統訓練,恰恰相反,用他自己的話說,正是由於16歲前他始終沒進學校,而是一直在家裡與祖母閒聊。甚至後來進入劍橋大學之後,對他影響最大的也並不是正規的學校教育,而是同著名學者懷特海等人的聊天。
這的確有點兒讓我們這些從事學校教育的人難堪,也的確耐人尋味。
莎士比亞曾經在《亨利六世》中篇第四幕中,借劇中人之口,怒斥學校教育之弊端:“你存心不良,設立什麼文法學校來腐蝕國內的青年……我要徑直向你指出,你任用了許多人,讓他們大談什麼名詞呀,什麼動詞呀,以及這一類的可惡的字眼兒,這都是任何基督徒的耳朵所不能忍受的。”

當然,對創辦學校而腐蝕了王國青年的說法,我們並不敢苟同,但是我們從中可以發現,那些用瑣屑和無聊充斥學校生活、擠佔孩子們閒暇時間的做法,終究是不受他們歡迎的。
很喜歡蘇霍姆林斯基的那個帕夫雷什中學,在他的筆下,我們看到,孩子們在草場上嬉戲,在曠野上露宿,在野外燒火做飯,在自己組織的夏令營裡生活,在自己栽種的葡萄樹下采摘果實,在涼亭裡做家庭作業,在野外清新的空氣中看書討論:學校已經真正成為孩子們嚮往的地方。
很嚮往《論語》裡描繪的那個境界,孔子與弟子們“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看上去頗有點兒優哉遊哉的閒情逸致,其實這才是誕生孔門七十二賢的土壤和空氣。
我們現在已經很難感受到這樣悠閒恬靜的學習氛圍了,我甚至有點兒懷念自己的小學生活。記得有一年冬天,我們的班主任老師不時地被勒令到中心學校去接受批鬥。每當這個時候,沒有了老師的我們便圍在火爐旁進行一個燒石灰的實驗。我們把校園裡用來蓋新房子的石頭敲打成碎塊,檢驗可能燒成石灰的石頭品種……“閒暇”裡發生的故事,卻成為小學裡的美好時光!
當然,給教育一些“閒暇”,單純靠校長的能力是沒有辦法做到的,需要我們教育部門乃至全社會的共同努力:我們的考試製度需要變革,我們的課程方案需要完善,我們的用人觀念需要改變。等到有一天,我們的學校真的讓學生、讓教師有了更多“閒暇”了,我們才可以說,我們的教育已經開始走向常態、走向成熟了。
文章來源:源創圖書、守望新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