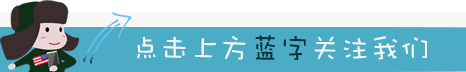稽核釋出 | 三聯.CREATIVE

3年前的春天,仇晴的女兒一歲半,工作和母職之間的矛盾越來越膠著,她自然而然地想到自己的母親。一通電話打過去,母職來電轉接。
母親湯曉紅的拒絕乾脆利落:“我不能幫你帶孩子,我有我想做的事情。”彼時,湯曉紅50歲,從未想過幫女兒帶孩子,而是卯著勁發展蘇扇文化。在一個退無可退的年紀,她守著底線不動搖。“我這個年紀,一旦迴歸家庭,就很難再出來了。”
對仇晴來說,這是一個意料之中的答案,這就是她的母親。
兩個女人似乎坐在了蹺蹺板的兩端,一頭要往高處走,另一頭就不得不落下去。在女性命運的窄處,答案似乎指向綁架與犧牲,但在這對母女身上,產生了另一種可能性。

“我能做自己喜歡的事,不容易”

“人家粉絲好奇提問,你為什麼要板起臉來懟人家?!”
“我不是懟,我們這代人就是這樣講話的!”
“新品扇子的扇頭圓的好看!”
“我覺得還是方的好看!”
……
自從3年前湯曉紅和仇晴開始一起在抖音上直播賣蘇扇,母女倆吵過的架比前30年加起來還要多。儘管彼此心中都繃著一根職場的弦,但創業夥伴之間的爭執還是難免變成母女間的倒苦水。

作為合夥人的母女二人難免爭吵
仇晴的眼淚總是先掉下來:“我今天這麼辛苦,還不是因為你想搞蘇扇!”
湯曉紅一口軟糯的蘇州口音,每個字又像是拍在桌面上的:“你媽媽的性格你知道,我不搞蘇扇會死不瞑目,哪怕眾叛親離我也要做!”
距離那天的直播開始還有半小時,湯曉紅努力繃著眼淚,她是直播間的出鏡人,要顧忌儀容。仇晴是助播,她撂狠話不播了,湯曉紅瞪圓了眼睛問:“你確定嗎?!”仇晴不說話,過了一會兒,她抹掉眼淚,除錯直播裝置,開播後把鼻音重解釋成感冒,這一篇就算翻過去了。
下一次,她們還是會爭吵,還是會翻篇,還是會跟這把扇子緊緊纏繞。
她們直播間裡的扇子,是起源於蘇州的摺扇,2006年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自宋代起就是文人雅士的“懷袖雅物”。

刺繡扇
拿起一把蘇扇,湯曉紅最先想到的往往不是姑蘇風雅,而是人。做框的人、雕花的人、竹刻的人、畫扇面的人……湯曉紅的丈夫是開料的人,也就是用機器把木料劈成扇骨的雛形,和其他工序上的師傅一樣,十七八歲進廠,心思全在手藝上。
但在這樣的家庭背景下,小時候的仇晴對蘇扇的印象卻很稀薄。她對老扇廠的記憶停留在1998年,那年她5歲,跟著大人去辦爸爸的下崗手續。懵懂的她並不清楚眼前的一切意味著什麼,直到很多年後,一位與父親差不多時間下崗的師傅同她講起當時的窘境:三十啷噹歲,看著手裡的一沓錢,不知道以後的路在哪裡。

父親和年幼的仇晴
那之後,家庭的擔子落在湯曉紅的肩膀上。丈夫雖然在機械模具廠找到了新工作,但又受了工傷,需要手術。家庭開支驟然吃緊,女兒的補課費也沉甸甸地壓了下來。
那時的她只比現在的仇晴大幾歲。提起仇晴的三十幾歲,湯曉紅是羨慕的,“她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
年輕時,湯曉紅被分配到絲綢廠工作。她曾想去新落成的蘇州工業園區闖一闖,但被她的父親極力反對。再後來,身為“妻子”和“母親”的責任,完全蓋過了她自身的需求和自由。
“我媽媽是很堅強的人,我從來沒有聽她抱怨過一句話。”取而代之的是對仇晴的全力託舉。“讀好書才有出路”幾乎是那一代蘇扇家庭的共識,他們不允許下一代繼承手藝,迫切需要一種確定性。
仇晴從小擅長寫作。讀高中時,相關專業的老師看過她寫的小說認為很有天分,可以發展。湯曉紅託人打聽,得知女兒或許可以參加藝考,考中戲的戲劇文學專業。
但對一個本就咬緊牙關生活的家庭來說,藝考意味著什麼?
“藝考班一節課的費用等於我父母大半個月的工資。就算能考上,未來的不確定性也太強了,我們沒有試錯的成本。”仇晴親眼目睹過那種失去工作之後的人生失序。於是,按部就班地高考,從西班牙語系畢業,成為一名翻譯,是她握緊命運的方式。

翻譯工作中的仇晴(左)
直到現在,這份慣性讓仇晴在購物時仍傾向於選便宜的。而每到此時,湯曉紅便會說,你就選你喜歡的。仇晴就像湯曉紅的鏡子,照見心底的缺口。
湯曉紅真正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行事時,已經45歲了。
2017年,走上管理層的她被丈夫當年所在的扇廠聘為負責人,一度擔任蘇州工藝美術行業協會副會長。命運讓這個家庭和蘇扇再次相逢,湯曉紅被激發出一種使命感:“仇晴爸爸當年沒活幹,在這裡下崗,我去一定要把它做得蒸蒸日上。就這種想法。”行業的蕭條依然在持續,且直觀體現在工人的收入上。大多數扇廠工人的月薪只有1700塊。微薄的工資撐不起因常年工作佝僂的背,越來越多工人像仇晴父親一樣選擇轉行。
自立門戶的個體師傅也難逃行業衰敗的陰影。曾經有一回,客人定製的扇子需要一種特殊工藝,湯曉紅尋遍師傅後在一間保安室找到了會這門手藝的人。對他來說,當保安意味著每月2000元的收入,而做扇子可能幾個月都沒有訂單。
若非迫於生計,手藝人鮮少會主動放下自己從少年時就拿起的刻刀,就像仇晴的父親。在仇晴工作後不久,他便又回到了扇廠。“當時他工作的機械模具廠即將上市,經濟前景很好,但他就是要回去做扇子。”

女扇
制扇師傅們的離去和歸來讓她備受觸動。制扇是苦活,有的師傅因為嚴重的頸椎病,睡覺時要把頭垂在床沿,幾乎垂到地上。“如果不把扇子宣傳出去,我就不配坐在這個位置。”
她一直是個要強的人,年輕時在絲綢廠上班,總是車間裡的第一名。她對“做事”的渴望一直都在,這一次,她絕不含糊,年齡、母職、金錢,都不能再阻礙她——從那以後,她帶著扇子和師傅跑遍全國各地的展銷會,希望找到一條與外界連線的路。
“扇子賣不出去,不是工人的錯,是經營者的錯,我不是想要偉大,我只是不想在蘇扇的史書上,手藝斷在了湯曉紅的手裡。”湯曉紅說。
她身高只有一米五出頭,紮在展銷會的人堆裡,踮起腳尖、抻著胳膊,遠遠望過去,只能看到一把扇子被舉在半空中,搖搖晃晃。

湯曉紅(右二)在展銷會上介紹蘇扇
作為女性,湯曉紅身上有傳統的烙印。她曾經擱置自我價值,直到女兒長大成人,才重啟自己的事業。她身上又有現代女性的一面,在即將退休的年紀成為扇廠的管理者,彷彿沒有一般人在這個年紀對“躺平”的渴望。傳統和現代的雙重標準是她那一代女性普遍面臨的困境,也是蘇扇的困境。
離開扇廠後,湯曉紅曾與一位電商老闆合作,對方提議在抖音直播推廣蘇扇。但很快,雙方因價格策略的分歧而分道揚鑣。
比如拿貨價1000元的扇子,對方定2000元,但湯曉紅對此不認同。“我認為1300元比較合適,價格太高,會把很多人拒之門外。”她語氣堅決,“作為蘇州人,我希望讓更多人瞭解蘇扇,而不是用高價嚇退他們。”
兩人不歡而散,但湯曉紅有了意外收穫——她終於找到了那條讓蘇扇走出去的路。“求來的訂單很難把手藝傳下去,蘇扇需要的不是被扶持,而是被看見。”
當湯曉紅提出要自己做抖音時,做扇子的丈夫卻頭一個反對,擔心她做不好會丟了面子。這一次,湯曉紅決定一意孤行,但對智慧手機一竅不通的她很快陷入新的迷茫。3年前的這個時候,她總是喋喋不休地說著自己的苦惱和設想,說著說著眼圈就紅了。她被卡住了。
仇晴看著母親這副模樣,於心不忍。她至今記得,當她決定陪湯曉紅從頭開始學做抖音時,湯曉紅的眼睛就像是被什麼點亮了。兩代女性在此匯流,傳統與現代的碰撞在她們的手中悄然展開。

“我們像戰友,能把後背交給彼此”

當一個50歲的女性和29歲的女兒決定一起創業,付出和取捨都是彼此無法迴避的隱痛。

仇晴一家
仇晴的父親本就不支援湯曉紅創業,現下更是反對女兒的加入:“你讓仇晴幫你,就是害了她。”
仇晴結婚後與丈夫生活在成都,回到蘇州不僅意味著夫妻異地、骨肉分離,還要離開穩定且收入優渥的翻譯崗位。
“我不知道這把扇子到底能走多遠,我不想耽誤仇晴。”湯曉紅和仇晴訂立了“半年之約”:用半年時間摸索賬號運營、培養員工。半年後,仇晴還是要回到既定軌道當中去。可半年又半年,母女倆一直在往前走,誰也沒有回過頭。

湯曉紅(左)和仇晴在準備直播
期間也有大學同學問及仇晴的工作,仇晴回覆在做扇子,對方打出一個問號。這是一個格格不入的回答,圈子裡的人都在做外貿或是翻譯,社交平臺上盡是大家在各國旅居的照片。每當刷到那些照片,仇晴腦袋裡會有一秒鐘的空白,“不是失落,也不是羨慕,有點複雜” 。
“到現在我都在想,如果仇晴不跟我做扇子,會不會有更好的發展。”這個念頭一直橫在湯曉紅腦海中,但她不敢動搖仇晴,“沒有仇晴,我就沒有左右手了。”她只能在自我拉扯中,把事情做下去。
最初,由於經費緊張,她們沒有租專門的工作室,第一個直播場地是仇晴的臥室。仇晴的床被拆了,只能打地鋪,孩子跟著湯曉紅夫妻睡在唯一的床上。

第一個直播場地,是仇晴的臥室
每天早上8點,仇晴把女兒送到幼兒園,回來後準備11點半的早班直播,下午2點下播後開始發貨,直到晚上6點,期間要去幼兒園把孩子接回來。晚上8點晚班直播前,仇晴的父親必須把孩子帶出去,10點直播結束後才可以回家,不然孩子找媽媽的哭鬧聲會傳到直播間裡。
她們的第一場直播在2022年6月17日。蘇州的夏天籠罩在悶熱的暑氣裡,仇晴的父親帶著孩子躲進地鐵,小小身影在大大的車廂裡跑了整個夏天,直播間終於稍有起色。
“蘇扇市場很難一下子火起來。”究其原因,價格和文化形成的門檻反倒是次要的,一些商家用機制冒充手工、單純追求利潤所造成的市場亂象,要靠日復一日的正向宣導去修復。“這件事沒有技巧。”湯曉紅說。
@扇扇來遲 剛開播時,也曾被老玩家當作是黑心商家。
當時有人在彈幕問:“身份是多少?”
仇晴不解:“我講扇子,為什麼要問我身份證號?”
彼時,她剛剛涉足蘇扇行業,還不知道這個專業術語指的是摺扇平放時,小骨和大骨加起來的厚度。
“騙子!”一個刺眼的詞出現在螢幕上。仇晴不得不嚥下滿腹委屈:“當時的我確實不夠專業。”
後來,她坦承自己有所欠缺,也在直播間及時彙報自己的學習成果。術語不認識,木料不會看,自己查,找老師傅挨個問。不久行話溜了,後來也會看扇子了,能分辨出材質與工藝,也能自如應對行家們的提問。
半年前,仇晴從忙碌中抽身,跟隨蘇扇名家徐家東學習扇面灑金工藝。“我想要體會手藝人的感受。”握過制扇工具的手,再拿起直播間的扇子,她心裡踏實了許多。質疑依然存在,但她已經變得從容。
灑金工藝的門檻相對低,學習一陣子後,仇晴的作品已經能夠上架銷售。每次發貨前,她至少要檢查三遍,稍有瑕疵便毫不猶豫地重做。客戶訂10張,她要準備15張,從中挑出最好的交付。“我更理解師傅們的心情了,他們肯定也為了一把扇子焦慮了千千萬萬遍。”

仇晴(前)跟隨蘇扇名家徐家東學習扇面灑金
當初的粉絲倒也沒有就此離開,而是留下默默觀望。很久之後,他留言說:“當時我以為又來了一個騙人的商家,沒想到你們一步步越做越好。”她感受到一種善意,粉絲們不會因為她的笨拙而認定她不夠優秀。
這也是她樂於在鏡頭外當助播的原因,摒除了外型、家世等等外在因素,純粹地去談蘇扇本身。創業之初,仇晴怕媽媽接受不了差評,不太情願湯曉紅出鏡。湯曉紅卻始終堅定地坐在主播位上,“我就坐在鏡頭裡,我不會跑,請大家放心。”用個人信譽為每一把扇子背書,是屬於老一輩人樸素的信念。
兩人一內一外坐在直播間裡,不苟言笑的湯曉紅被粉絲稱作“湯寶”,取“家有一老如有一寶”的意思,而一旁娓娓道來的仇晴則被喊為“哈哈”。“我們倆的風格確實不同,我比較嚴肅,仇晴比較活潑。有人覺得我講話衝,她會緩和一下。”湯曉紅說,“她老說我‘懟人’,我說我沒有啊。”
慢慢地,她們彼此間的稱呼也不一樣了,無論是工作還是生活,仇晴越來越少喊湯曉紅“媽媽”,更多是喊“湯老師”,而湯曉紅也自然地介紹仇晴是“我的搭檔”。血緣與理想共生,親情與使命交織,在母女關係之外,她們之間有了新的聯結。
“我們像戰友,能把後背交給彼此。”仇晴說。
在仇晴看來,她們還是會爭吵,但都是方法之爭,底線都是想讓扇子活下去。
年輕玩家的湧入或許是一個“活下去”的標誌。她們堅持直播一年後,不再只有老玩家用專業術語試探直播間的深淺,入門級的問題冒了出來,還有粉絲專門前來根據漢服款式定製蘇扇。有位年輕粉絲說,自己原本對蘇扇毫無興趣,無意間刷到,觀望許久,買下了他的第一把摺扇。“年輕人代表未來。”湯曉紅說。每一把扇子都是一座橋,一端連著活下來的歷史,另一端,正通向尚未命名的未來。

鏡頭下的湯曉紅(中)

“有沒有50塊的手工扇?”

價低利薄,所以在入行之初,母女倆就做好了面對困難的準備。“我們商量好了,我們倆每人每月能賺3000塊就足夠。”
即便如此,動輒成百上千元的蘇扇仍然屬於貴价產品,直播間裡仍不時有初來乍到的粉絲質疑價格過高。有人問:“有沒有50塊的手工扇?”
仇晴算了一筆賬:如果算1位師傅1天做1把扇子,一把扇子50塊,也就是一天的收入。1個月不休息也只能賣1500元。還要扣除材料、運輸等成本,到手可能只剩不足千元。“那為什麼不去當保安?”她反問道。

做摺扇的材料之一,雲妃竹扇骨
湯曉紅曾經跟仇晴講起,一些老師傅的家裡層層疊疊地堆著邊角料,當寶貝一樣收著。她也從老師傅手裡接過那些用布帛裹著遞來的摺扇。因為愛惜,所以堅持。“如果老師傅們的工價守不住,年輕的師傅看不到未來就轉行了。”
湯曉紅介紹,現今蘇扇師傅的年齡結構呈倒金字塔,大部分在50歲以上——也就是仇晴父親那一輩,年輕人很少。
為了留住年輕師傅,湯曉紅和仇晴不計成本,不問結果。年輕師傅普遍只做過成本偏低的竹製摺扇,很少有機會操刀木製摺扇。即使是沒有經驗的師傅,她們也會提供小葉紫檀、老山檀香等名貴料子,鼓勵他們練習:“做壞了不要緊,不用賠錢,工價照付,你就練。”
這種信任,讓年輕師傅有了更多底氣去探索和精進。

“95後”師傅陳剛正在檢視木料
@扇扇來遲 的粉絲中,90後、00後的年輕玩家不在少數。年輕人的需求常新,老師傅招架不住聞所未聞的潮流元素,反倒是年輕師傅挑起了大梁。
“一些年輕師傅的職業軌跡是跟@扇扇來遲 重合的。2022年入行,到2025年時,他們的作品已經越來越成熟。”仇晴說,“如果沒有直播間帶來的關注和機會,很多人可能根本不會踏入這一行。”
新鮮血液的湧入正順應了湯曉紅的主張。在她看來,蘇扇行業應該形成“價格層次有序、從業者代際銜接”的良性結構。“高價產品穩步升級,中低價位持續補位,避免市場斷層。比如500元的漲到600元,原有價位仍有新人接續,300元產品也保持供應。”
在年輕一代裡,38歲的張欣威是蘇派竹刻的傳承人,和仇晴算是同輩人。一次,他被仇晴硬拉來直播間做嘉賓。仇晴的本意是請他講解“竹刻”技藝,但張欣威的分享遠遠超出了她的預期。他從作品中的設計元素講起,細緻到某位書法家的字跡、某段歷史的淵源,將竹刻背後的文化脈絡娓娓道來。

制扇師傅張欣威在進行竹刻
那天,直播間的氣氛異常熱烈。粉絲們紛紛留言:“能給我上一把嗎?”“搶一把!”銷售資料飆升,直播間的人數不僅多了,停留時間也顯著延長。人們不再只是匆匆劃過,而是停下來傾聽、提問,與張欣威展開對話。
事後,仇晴和母親覆盤這次直播:“原來不是大家不愛蘇扇,是我們沒把門道講透。”
為了請動更多師傅,仇晴有笨辦法:“軟磨硬泡,一次不行就兩次,兩次不行就三次,看誰先不好意思。”
她也理解師傅們的顧慮。“如果是虛頭巴腦的直播間,他們肯定不願意去,他們在觀察我們是不是真的在認真做事。而我們請他們,也不是為了賣多少扇子,還是為了介紹蘇扇。”
仇晴從不把臺前的壓力轉嫁給師傅。每次合作,她都“報喜不報憂”。前不久,幾個師傅做客直播間,眼尖地發現自己的扇子還沒賣完。“不是說都賣完了嗎?”
“馬上就賣了。”仇晴連忙找補。

湯曉紅(左)和制扇師傅楊惠義
師傅們對直播間的關注,遠比仇晴想象的要細緻。一個多月前,她去村裡拜訪師傅們,正說著話,看到幾位素未謀面的師傅在門外張望。被發現後,他們笑著解釋:“我們就是想聽聽客人們怎麼說。”
曾經有一位客人收到扇子後密密麻麻寫了11條調整意見,仇晴把扇子連同那張意見紙寄給了師傅。師傅很快回復:“建議很好,我改。”合作的師傅們大多都是如此,“他們很珍惜現在能被大家看到的機會”。
他們低頭打磨的是現在,而未來已經在抬眼望見的地方。隨著直播間需求擴大,湯曉紅和仇晴正加緊尋找新師傅。“我們已經建聯的師傅有100多位,長期合作的有30多位。”仇晴說。像是自動勾連的宇宙,將散落的蘇扇匠人凝聚成星群。當引力場形成,傳統手藝人也會在數字星河中重煥光芒。

湯曉紅(左)到制扇師傅家中拜訪

“接力棒已經擺在我的面前”

“要說這三年純粹是為了我媽的堅持、我爸的情懷嗎?也不盡然。”仇晴頓了頓,“在和師傅們打交道,和扇子打交道的過程中,我也確實被這門手藝吸引了。”她的語氣裡帶著一種意外的篤定。
在眾多蘇扇形制中,仇晴獨愛無肩直方形制的摺扇。它的扇骨修長,線條筆直,稜角分明,開合利落,劃拉一聲開啟,像是闖入一個嶄新世界。
“接力棒已經在我面前了,就看我的手要不要去握。”這是此刻仇晴能清晰感受到的。
她進入這一行時,其實不確定自己能不能混出個名堂。但如今的她已不再為此焦慮。“人生就像寫小說,你永遠不知道最好的作品會在什麼時候出現。張愛玲說,出名要趁早。但也有人一生都沒能做出自己滿意的作品。”她的語氣平靜。“但是我站在這裡,就會有年輕人看到,‘她很年輕,她和我們一樣,她選擇了這個行業。我是不是也可以?’”
讀書時,父母並不希望她進入蘇扇行業,現在她覺得自己的女兒或許可以。“最難的階段,媽媽已經帶我跨過來了。”她說。

湯曉紅(左)母女三代人
這些年,母女倆沒少為這把扇子鬧彆扭,可手底下的活越磨越細,心裡的結反倒越拆越松。在剛剛過去的婦女節,抖音電商“尋找同行者”把鏡頭對準了這對母女“合夥人”,記錄下了她們的故事:
湯曉紅曾對她說:“如果我可以給你更好的資源和背景,你肯定會做得更好。”仇晴的回答是:“我有你這樣的媽媽,我很自豪。”
此刻,她們的生活被直播間一分為二,母女倆在中午和晚上兩個班次的直播中輪轉。一個人直播時,另一個人就打包發貨,或者和家人一起帶孩子。母職和事業的座標系正在被重構。她們跳出了固有的期待,她們雖然磕磕絆絆,但走了很遠。
而那個下定決心的身影,可以是29歲,也可以是50歲。就像@扇扇來遲 的名字:雖然有點遲,但一切剛剛好。

湯曉紅(左)與仇晴
設計排版丨趙姝萌
圖片來源丨抖音 受訪者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