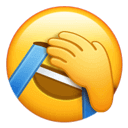雷蒙德·卡佛(1938~1988),美國當代著名短篇小說家、詩人。被稱為“美國二十世紀下半葉最重要的小說家”和小說界“簡約主義”的大師,是“繼海明威之後美國最具影響力的短篇小說作家”。極其精簡的故事,在乏味的生活中找到驚人的新意;冷調的筆法,潛伏著隨時可能爆發的張力,《倫敦時報》在他去世後稱他為“美國的契訶夫”。
我的朋友梅爾·麥克吉尼斯在不停地說著。梅爾·麥克吉尼斯是個心臟病醫生,有時候,這種身份給了他這樣說話的權力。
我們四人圍坐在梅爾家的餐桌旁喝杜松子酒。從水池後面大窗戶照進來的陽光充滿了廚房。四人裡有我、梅爾、梅爾的第二任妻子特芮薩(我們叫她特芮)和我的妻子勞拉。那時我們住在阿爾伯克基。但我們都是從外地來的。
餐桌上放著冰桶。杜松子酒和奎寧水被不停地傳來傳去,不知怎麼的,我們就談到愛情這個話題上來了。梅爾認為真正的愛情決不次於精神上的愛。他說他離開去上醫學院時,已在神學院裡呆了五年,他說回顧在神學院的那些日子,仍然覺得那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時光。
特芮說在梅爾之前和她住在一起的那個男人非常愛她,愛到想殺死她。特芮說:“有一天晚上他揍我,拽著我的腳踝在臥室裡拖來拖去,嘴裡不停地說,‘我愛你,我愛你,你這個婊子。’他不停地把我在臥室裡拖來拖去,我的頭不斷磕著東西。”特芮看了看大家,“碰到這樣的愛情你們怎麼辦?”
她瘦得皮包骨,有一張漂亮的面孔,深黑色的眼睛,棕色的頭髮一直拖到背上。她喜歡綠寶石做的項鍊和長長下垂的耳環。
“我的天哪,別犯傻了。那不是愛,你知道這個。”梅爾說,“我不知道你該叫它什麼,但你絕對不能把它叫做愛情。”
“你愛怎麼說怎麼說,我認為那就是愛情。”特芮說,“也許對你來說這很瘋狂,但它同樣是真實的。人和人不一樣,梅爾。不錯,有時他是有些瘋狂的舉動,我承認。不過他愛我,或許在用他自己的方式,他的確愛我,那裡面有愛情,梅爾,別說沒有。”
梅爾噓了口氣,端起酒杯轉向我和勞拉。“那個人威脅要殺死我。”梅爾說。他喝乾杯中的酒,伸手去拿酒瓶。
“特芮很浪漫,特芮是那種踢—我—我—才—知—道—你—愛—我型別的人。特芮,親愛的,別那樣。”梅爾把手伸到桌子對面,用手指摸了摸特芮的臉頰。他衝她咧嘴笑了笑。
“和什麼解?”梅爾說,“有什麼好和解的?我清楚我知道什麼,就這些。”
“我們怎麼就說到這個話題上來的呢?”特芮說,她端起酒杯喝了一口。“梅爾滿腦子都是愛情。”她說,“是吧?親愛的。”她笑了笑。我想這個話題應該結束了。
“我只是不想把艾德的所作所為叫做愛情。我沒別的意思,親愛的。”梅爾說,“你們怎麼看?”梅爾轉向我和勞拉,“你們覺得那是愛情嗎?”
“你問錯人了。”我說,“我連那個人都不認識,只是聽人提起過這個名字。我怎麼會知道。你得知道具體的情況。但我想你的意思是說愛情是一種絕對。”
梅爾說:“我說的這種愛情是指,我說的這種愛情是,你不會想著去殺人。”
勞拉說:“我對艾德一無所知,也不瞭解當時的情況,不過誰又能夠評判他人呢?”
我碰了碰勞拉的手背,她衝我快速地笑了笑。我抓起她的手,它很溫暖,指甲光潔,修剪得十分整齊。我用手指攥住她的手腕,把她摟到懷裡。
“我離開他時,他喝了老鼠藥。”特芮說,她雙手緊抱雙臂,“他們把他送到聖達菲的醫院。那時我們住在那裡,大約有十里遠。他們救了他的命。但他的牙齦因此變了形。我是說它們從牙齒上脫開了,牙齒像狗牙一樣立著。我的天哪。”特芮說。她沉默了一會兒,鬆開兩臂,端起酒杯。
梅爾把一小碟酸橙遞給我,我拿了一塊,把汁擠進酒裡,用手指攪了攪冰塊。
“後來更糟了。”特芮說,“他朝自己嘴裡開了一槍,就連這件事也給搞砸了。可憐的艾德。”特芮搖了搖頭。
梅爾四十五歲,身材瘦長,滿頭鬆軟的捲髮,臉和胳膊都因打網球曬成了棕黑色。沒喝醉的時候,他的每個動作和手勢都很精確,非常的謹慎。
“可他確實是愛我的,梅爾,你得同意這個。”特芮說,“這是我對你的惟一請求。他愛我的方式和你的不一樣。這不是我要說的。但他愛我,你能同意這一點,是吧?”
勞拉端著杯子身子往前傾,她把雙肘擱在桌上,兩手握住酒杯。她瞟了眼梅爾,又瞟了眼特芮,單純的臉上帶著迷惑的神情等著答案,好像很奇怪這樣的事情怎麼會發生在你朋友身上呢。
“我來告訴你們是怎麼回事。”梅爾說。“他用他買的點二二手槍威脅我和特芮。噢,我不是開玩笑。這傢伙老是威脅我們。真該讓你們看看那些日子我們是怎麼過的,像逃犯一樣。我自己甚至買了一支槍。你能相信嗎,像我這樣的人?但我真的買了,用來自衛,就放在車子儀表板旁的匣子裡。有時我必須在半夜離開公寓去醫院,知道嗎?我和特芮那時還沒結婚。房子、孩子、狗和所有的一切都歸了我前妻,我和特芮住在現在這所公寓裡。有時,像我說的那樣,我會在半夜接到出診電話,必須在凌晨兩、三點鐘趕到醫院。停車場裡一片漆黑,我還沒走近車子就嚇出一身冷汗來。不知什麼時候他就會從灌木叢裡竄出來或是從汽車後面給我一槍。我是說,這個人瘋了,他完全有能力安裝一個炸彈之類的東西。他沒日沒夜地打我的服務專線,說要和醫生談談,我一回電話他就說,‘你這個婊子養的,你沒幾天活頭了。’諸如此類的事情。我對你們講,真是太恐怖了。”
“聽起來像是一場噩夢。”勞拉說,“可是他開槍自殺後到底怎樣了?”
勞拉是個法律秘書。我們是因為工作關係認識的。不知不覺中我們就好上了。她今年三十五歲,比我小三歲。除了彼此相愛外,我們相互欣賞並願意在一起待著。她是個容易相處的人。
梅爾說,“他在屋裡朝自己的嘴裡開了一槍,有人聽到槍響,報告給經理。他們用總鑰匙開啟房門,看到發生的事情,叫了救護車。他被送來的時候我恰好在醫院裡。他還活著,但已經不可救藥了。他活了三天,頭腫得比正常人的頭大了一倍。我以前從沒見過這種情形,我希望這輩子再也不要見到了。特芮知道後想去陪他。我們為這事大吵了一場。我認為她不該看到他那副樣子。我認為她根本就不該去見他,我現在還這麼認為。”
“他死時我在他的房間裡陪著他,”特芮說,“他再也沒能醒過來,但我一直陪著他。他沒有別的親人了。”
“他非常危險。”梅爾說,“如果你把那叫做愛情。那就請便吧。”
“那是愛情,”特芮說,“當然,在大多數人眼裡那可能不太正常。可是他願意為它而死,他確實為它死了。”
“我他媽說什麼也不會稱它為愛情。”梅爾說,“我是說,沒有人明白自己為何而死。我見過許多人自殺,我可以說沒有一個人知道自己到底為什麼而死。”
梅爾把手放在脖子後面,椅背向後傾斜著。“我對那種愛不感興趣。”他說,“如果那也是愛情的話,它就歸你了。”
特芮說:“我們那時很害怕。梅爾甚至立了一份遺囑,並寫信給他在加州做過特種兵的弟弟,告訴他一旦發生不測好去找誰。”
特芮喝著杯子裡的酒。“梅爾是對的——我們過得像逃犯一樣,整天提心吊膽的。特別是梅爾,是不是呀,親愛的?我甚至報過警,但警察也無能為力。他們說必須等艾德真的幹了什麼才能採取行動。那不是笑話嗎?”特芮說。
她把最後一滴酒倒進杯裡,晃了晃瓶子。梅爾起身到櫥櫃旁,從裡面又拿出一瓶來。
“嗯,尼克和我知道什麼是愛情。”勞拉說,“我是說,對我倆而言。”她用膝蓋碰了碰我的膝蓋。“你該說點什麼了。”勞拉說,把笑臉轉向我。
作為回答,我拿起勞拉的手舉到嘴邊,很誇張地吻了一下。大家都被逗笑了。
“你們兩個傢伙,”特芮說,“快別那樣,真讓我噁心。你們還在蜜月期,看在老天的份上。你們還狂熱著呢,真是的。等著瞧吧。你倆在一起多久了?有多久了?一年?一年多?”
“嘿,夥計們,”他說。“咱們乾一杯。我建議大家乾一杯。為愛情乾杯。”梅爾說。
後院裡,一隻狗叫了起來。窗前那棵白楊樹的葉子輕聲拍打著窗玻璃。下午的太陽好像進到屋裡來了,光線充沛舒適。我們有了如臨仙境的感覺。我們再次舉起酒杯,衝著彼此咧嘴笑著,像是一群商量好要去幹一件不讓乾的事情的孩子。
“我是說,我會給你們舉一個很好的例子。然後你們可以自己作結論。”他又往杯子裡倒了些杜松子酒,加了塊冰和一片酸橙。我們一邊呷著酒,一邊等著他。勞拉和我又碰了碰膝蓋,我把一隻手放在她溫暖的大腿上,再也沒挪開。
“我們當中有誰真正懂得愛情嗎?”梅爾說,“在我看來,我們只不過是些愛情的新手。我們說我們彼此相愛,這沒錯,我不懷疑這點。我愛特芮,特芮愛我,你們倆也彼此相愛。你們知道我現在所說的這種愛是什麼。肉體上的愛,那種把你驅向某個特別的人的衝動,還有對另一個人的本質的愛,愛他或她精神上的東西。肉慾之愛和……好吧,就叫它情感之愛吧,就是每天都關心著另外那個人。但有的時候,我很難接受我愛過我第一任妻子這個事實,但我愛過。我知道我愛過。所以我想就這點而論,我很像特芮。像特芮和艾德。”
他想了一會兒接著說道,“曾經有一段時間我覺得我愛我前妻勝過愛我的生命。但現在我從心裡恨透了她。我真的是這樣。你們對此作何解釋呢?那個愛情怎麼了?它到底出了什麼毛病,這是我想知道的。我希望有人能告訴我。再有就是艾德。好吧,我們又說起艾德了。他那麼愛特芮,以致於想殺死她,最後他把自己給殺死了。”梅爾止住話頭,吞了一大口酒。“你們倆在一起呆了十八個月,你們彼此相愛。從你們的一舉一動裡看得出來。你們因愛而發光。但是,你們在相遇之前也曾愛過別人。你們也都曾結過婚,像我們一樣。甚至在這之前,你們可能還愛過其他的人。特芮和我在一塊兒五年了,結婚也四年了。可怕的事情,可怕的事情是,不過也是件好事,不幸中的萬幸吧,你可以這樣說,就是如果我們中誰出了什麼事——請原諒我這麼說——但假如明天我們倆有誰出了事,我想另一個,另一個人會傷心一會兒,你們知道,但很快,活著的一方就會跑出去,再次戀愛,用不了多久就會另有新歡。所有這些,所有這些我們談論的愛情,只不過是一種記憶罷了。甚至可能連記憶都不是。我錯了嗎?我說得太離譜了嗎?如果你們認為我錯了,我希望你們立刻給我指出來。我想知道。我的意思是,我什麼也不清楚,我率先承認這一點。”
“梅爾,看在老天的份上。”特芮說。她伸出手握住他的手腕。“你快醉了吧?親愛的?你已經醉了?”
“親愛的,我只是說說話而已。”梅爾說。“行了吧?我不必非得喝醉了才能說出我的想法。我是說,我們大家只是隨便聊聊,對不對?”梅爾說。他把眼光定在她身上。
“寶貝兒,我不是在批評你。”特芮說。她端起她的杯子。
“我今天不值班,”梅爾說。“讓我提醒你一下,我不值班。”他說。
梅爾看著勞拉,像是認不出她來了似的,像是她不是從前的她了。
“也愛你,勞拉。”梅爾說。“還有你,尼克,也愛你。你們知道嗎?”梅爾說。“你們倆是我們的好朋友。”梅爾說。
梅爾說,“我本來要告訴你們一件事,我是說,我想證明一點。注意了,這件事發生在幾個月前,現在還沒結束,它會讓我們感到羞愧,我們在談論愛情時,說起來就像知道自己在說什麼一樣。”
“閉上你的嘴,哪怕就這一次。”梅爾安靜地說道,“你能不能行行好把嘴閉上一分鐘?我要說的故事是,有對老夫婦在高速公路上遭了車禍。一個年輕人撞了他們,他們給撞得稀爛,沒人覺得他們能挺過來。”
特芮看了看我們,又回頭看著梅爾。她看上去有點擔憂,也許用這個詞來形容太重了一點。梅爾把酒瓶沿桌子傳了一圈。
“那天晚上正趕上我值班,”梅爾說,“那是五月或六月的一天。我和特芮剛坐下準備吃晚飯,醫院來了電話,高速公路上發生了這起車禍。喝醉了酒的孩子,十幾歲的小年輕,開著他爸爸的小貨車一頭扎進了這老兩口開的野營車上。這對夫婦七十來歲。這孩子(大約十八、九歲)沒到醫院就死了,方向盤穿透了他的胸骨。這對老夫婦還活著,你們知道,我是說,也就剩一口氣了。他們遍體鱗傷,多處骨折,內傷,大出血,挫傷,撕裂傷,全了,而且,他們每人都得了腦震盪。他們的狀況很糟糕,相信我說的。當然,他倆的年齡對他們來說更是雙重的打擊。要說那女的比那男的還要糟,除了以上說的外,她脾臟也破碎了,雙膝的膝蓋骨骨折。好在他們繫了安全帶,天曉得,這才暫時保住了他們的命。”
“夥計們,這是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廣告,”特芮說。“這是發言人梅爾文·麥克吉尼斯博士在發言。”特芮大笑。“梅爾,”她說,“有時你真是太那個了,但我愛你,寶貝。”她說。
“特芮是對的。”梅爾坐下後說,“繫上安全帶。言歸正傳,他們還算有點人形,這倆老的。我趕到時,那個孩子已經死了,像我說的。他就在牆角的一張擔架上躺著。我看了一眼那對老夫婦,告訴急救室的護士馬上給我找一位神經科專家、一位整形外科醫生和兩個外科醫生來。”
他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我會盡量長話短說。”他說,“我們把這兩個人抬進了手術室,沒命地幹了幾乎一整夜。這倆人,他們的生命力簡直不可思議。你偶爾會碰上這樣的人。我們盡了一切努力,天快亮時,我們給了他們百分之五十的機會,給她的機會也許還少一點。就這樣,他們第二天早上還活著。於是,我們把他們轉到特護病房。呆在那裡的兩個星期裡,他們一直頑強地支撐著,各方面都越變越好。我們就把他們轉回到他們自己的病房。”
梅爾停了下來。“現在,”他說,“咱們幹掉這瓶廉價的杜松子酒,然後去吃飯,好不好?我和特芮知道一個新去處,我們就去那兒,到那個新地方去。不過得先把這瓶廉價的爛酒喝完再說。”
特芮說:“實際上我們還沒在那兒吃過飯。不過它看起來還不錯,從外面看。”
“我喜歡食物。”梅爾說,“你們知道嗎?如果我這輩子可以重來的話,我想當一名廚師,知道嗎?是吧,特芮?”
“特芮知道,”他說,“她可以告訴你們,不過讓我對你們說這個。如果我可以轉世投胎到一個不同的年代,你們知道嗎?我想投胎成一名騎士。因為穿著那身盔甲你會感到很安全。在槍和火藥發明之前,做一名騎士是很不錯的。”
特芮說:“假如你轉世成一個農奴。那年頭農奴的日子可不好過。”
“農奴的日子從來就沒好過過,”梅爾說。“但我猜就連騎士也是別人的撲人。難道不是這樣?另一方面講每個人都是別人的撲人。不是那樣嗎,特芮?我喜歡武士,除了女士外,還因為那一身盔甲,要知道,他們不會輕易受到傷害。那會兒沒有汽車,知道吧?不會有喝醉的年青人來撞你的屁股。”
“僕人,撲人。”梅爾說,“有他媽的什麼差別?你反正知道我的意思。行了吧。”梅爾說。“我沒文化,我知道我的那點玩意兒。我是心臟外科醫生,沒錯,但我只是個修理工。我在裡面亂整一氣,把東西鼓搗好。他媽的。”梅爾說。
“他只不過是個謙虛的江湖郎中。”我說。“不過梅爾,他們有時會悶死在盔甲裡。如果裡面太熱而他們又累又乏的話,他們甚至要得心臟病。我讀到過他們有時會從馬背上掉下來,爬不起來了,因為那副盔甲使得他們累得站都站不起來。他們有時被自己的馬踩在腳下。”
“那太可怕了。”梅爾說。“那是件很恐怖的事情。尼基。我猜他們只好躺在那兒等著,直到有人過來把他們做成羊肉串。”
“正是。”梅爾說。“一些僕人會過來把這個狗雜種刺死,以愛的名義,或他媽的那些他們在那時為之而戰的東西。”
勞拉的臉色還是紅紅的。她的眼睛發亮。她把杯子送到嘴邊。梅爾又給自己倒了杯酒。他仔細地看著標籤,像是在琢磨一長串數字。他然後慢慢地把酒瓶放在桌上,又慢慢地去拿奎寧水。
“那對老夫婦怎樣了?”勞拉說。“你的故事還沒講完。”
屋內的光線和剛才不一樣了,變得越來越暗淡了。但窗外的樹葉子還在閃閃發亮。我凝視著它們在窗子玻璃和貼著佛米卡貼面的臺子上留下的圖案。當然,它們和先前留下的不一樣了。
特芮說:“繼續你的故事,寶貝,我只是開個玩笑。後來怎樣了?”
“梅爾,別這樣,”特芮說。“別總這麼嚴肅,甜心。連個笑話都受不了?”
梅爾把目光定在勞拉身上。他說:“勞拉,假如我沒有特芮,假如我不是這麼愛她,假如尼克不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會愛上你的。我會把你掠走,親愛的。”他說。
“講你的故事,”特芮說,“然後我們就去那個新地方,可以嗎?”
“可以,”梅爾說。“我說到哪兒了?”他說。他盯著桌子看了會兒,又開始了。
“我每天都順便過去看看他倆,有時一天兩次,如果恰好我在那兒有別的事情。石膏和繃帶,從頭到腳,兩個都這樣。你們知道,就像在電影裡看到的那樣。他們就是那副樣子,跟電影裡的一模一樣。只在眼睛、鼻子、嘴那兒留了幾個小洞。她還必須把兩條腿吊起來。她丈夫抑鬱了好一陣子。即使在得知他妻子會活下來後,他的情緒仍舊很低落。但不是因為這場事故,我是說,事故只是一方面,但不是所有的。我貼近他嘴那兒的小洞,他說不,不是這場事故讓他傷心,而是因為他從眼洞裡看不到她,他說那才是他悲傷的原因。你們能想象得到嗎?我告訴你們,這個男人的心碎了,因為他不能轉動他那該死的頭來看他那該死的老婆。”
“我是說,看不見那個狗日的女人,這簡直要了那個老狗屁的命。”
也許這時候我們都有點醉了。我很難把注意力集中起來。陽光從房間裡消退,從它進來的那個窗子退了出去。儘管這樣,仍沒有人站起身來,去開啟頭頂的燈。
“聽著,”梅爾說。“我們喝完這狗日的杜松子酒。剩下的剛夠每人一杯。然後我們去吃飯。我們去那個新地方。”
“他有點沮喪,”特芮說。“梅爾,你為什麼不吃片藥?”梅爾搖了搖頭。“我什麼都吃過了。”
她在用她的手指來刮桌子上的東西,稍後,她停了下來。
“我覺得我想給我的孩子打個電話。”梅爾說。“你們都不介意吧?我去給我的孩子打電話。”他說。特芮說,“要是瑪喬裡接電話怎麼辦?你倆聽我們說過瑪喬裡的事吧?親愛的,你知道你不願意跟瑪喬裡說話,那隻會使你更加難受。”
“我不想和瑪喬裡說話,”梅爾說,“但我想和我的孩子說話。”
“梅爾沒有一天不嘮叨這件事,他希望她再嫁人,要不就死掉。”特芮說,“不說別的,”她說,“她在讓我們破產。梅爾說她不結婚是為了故意刁難他。她有個男朋友跟她和孩子們住在一起。所以,梅爾也在養著她的男朋友。”
“她對蜜蜂過敏,”梅爾說。“如果我不祈禱她再婚,就祈禱她被一群狗日的蜜蜂扎死。”
“呲呲呲呲呲呲呲——”梅爾用手指作蜜蜂狀在特芮的喉嚨上比劃著。然後雙手垂下來,一直垂到身子兩旁。
“她很邪惡。”梅爾說。“有時我真想裝扮成一個養蜂人去找她。你知道嗎?戴著那種像頭盔一樣的帽子,有可以放下來遮住臉的擋板,大手套和防護服。我去敲門,把一窩蜜蜂都放到她屋子裡去。當然,我得首先確保孩子們都不在家。”
他把一條腿蹺到另一條腿上,看上去他費了很大的勁。然後,他把兩隻腳都放在地板上,身體前傾手肘支在桌子上,用雙手托住下巴。
“要不我還是不給孩子們打電話了,這恐怕不是個什麼好主意。也許咱們直接去吃飯,怎麼樣?”
“聽起來不錯。”我說,“吃或者不吃,或者接著喝。我可以現在就出去,向落日走去。”
“就是我說的意思,”我說,“就是說我可以這樣繼續下去,就是這麼個意思。”
“我可要吃點東西。”勞拉說,“我想我這輩子從來沒這麼餓過。有什麼可以墊墊的?”
我能聽見我的心跳。我能聽見所有人的心跳。我能聽見我們坐在那兒發出的噪音,直到房間全都黑下來了,也沒有人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