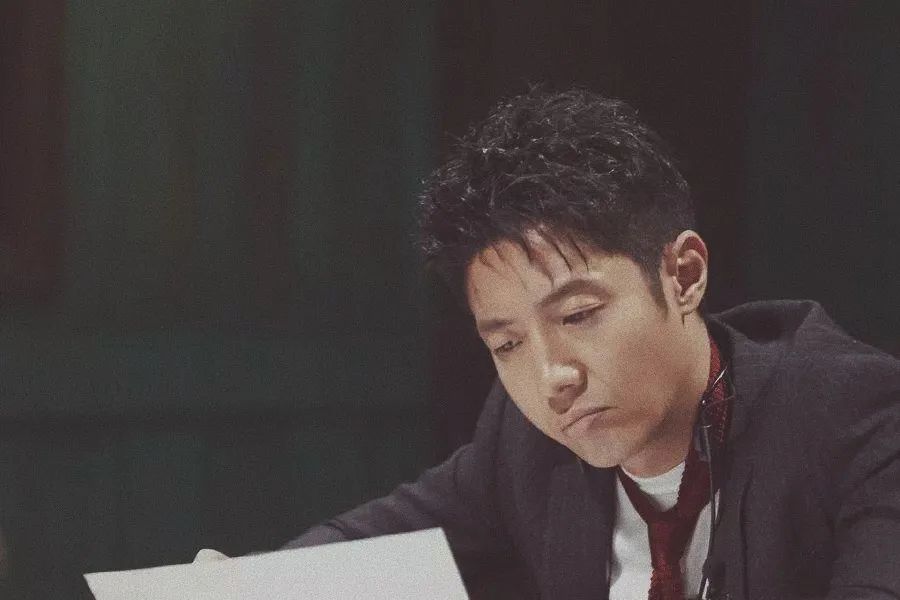一本書,總會有一本書的命運。英國丹寧法官名著——《法律的正當程式》,正好驗證了這句名言。

丹寧法官,何許人也?1923年,寒門之子丹寧,不懈打拼,擔任出庭律師。出道二十年後,成功轉型為法官。83歲高齡,卸下廿載英國民事上訴法院院長一職。
投身法律職業一甲子,法官生涯四十年,獲贈國內外數十所大學榮譽博士學位的丹寧,創下普通法國度史無前例的紀錄。尤其讓人稱道的是,丹寧法官不畏流言,大膽挑戰“判例主義”,積極參與各種法律變革,貢獻良多。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最偉大的司法改革家”,《泰晤士報》讚譽:“丹寧勳爵給人的印象常常是大氣磅礴,無所畏懼。英國法律又一次贏得了長治久安的格局,他的事業載入了史冊。”名滿天下,當之無愧。
丹寧感慨:“今天的權力結構與十九世紀的權力結構大不相同了。在本世紀,政府關注生活的各個方面,我們有‘福利國家’之稱。政府各部門在很多方面有廣泛的權力,行使不受制約的自由裁量權。然而,無論在什麼樣的信條佔統治地位的情況下,對普通人來說總有危險存在,原因在於這樣一個事實,即所有的權力都是可以被濫用或誤用的。二十世紀的法院面臨的重大問題一直是:在權力日益增長的年代,法律如何對付濫用或誤用權力的局面。”
丹寧提醒世人:“我們保護個人自由的程式是有效的,但防止濫用權力的程式卻不那麼有效。正如鏟和鍬不再適合挖煤一樣,釋出訓令、調卷令和案件的起訴程式也不再適合於新時代的要求了……在當代,我們不得不應付各種變化,這些變化和三百年前發生的事情具有相似的憲法性意義。讓我們來證明我們是能夠應付這種挑戰的吧!”

司法工作之外,著書立說是丹寧的最愛。1949年推出處女作《法律下的自由》,大獲好評。此後《變化中的法律》《通向公正之路》《法律的訓誡》《法律的未來》《最後的篇章》與《法律的界碑》逐一問世,外界讚賞有加。1981年,大西洋兩岸的法學家、法官與律師濟濟一堂,專門討論丹寧的司法哲學及法律著作。“在普通法國家,不讀丹寧的書,就無法從事司法工作!”
1980年出版的《法律的正當程式》,處處展現獨特的丹寧風格。他從親身經歷的案件中,夫子自道,一一盤點憲法、民法、衡平法、家庭法與國際法難題,帶領讀者共同踏上探尋法治奧義的旅程。
他以案說法,娓娓道來,穿插恰到好處的文學典故,讀來讓人春風撲面,眼前一亮。
開門見山,丹寧破題立論。正當程式指的不是枯燥的訴訟條例,而是出現在1354年愛德華三世的法令中:未經法律的正當程式進行答辯,對任何財產和身份的擁有者一律不得剝奪其土地或住所,不得逮捕或監禁,不得剝奪繼承權或生命。“我所說的正當程式與麥迪遜提出的美國憲法修正案非常相似,它已被1791年第五修正案所確認,即未經正當的法律程式,不得剝奪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財產。”直指問題核心,令人耳目一新。
1963年,丹寧受首相麥克米倫委託,擔任官方調查員,對轟動一時的“普羅富莫大臣蘇聯間諜案”展開獨立調查。“在人心浮動、眾怨迭生時,只有一種人能秉公行事得到大眾的信任,這就是法官。法官獨立於行政機構之外,因此,法官就可以暢所欲言。”
“雖然公眾利益要求儘可能完全查明事實,但是還有更重要的公眾利益要予以考慮。即對每個人都公正執法,這一公眾利益是超越其他一切利益之上的。無論如何,作為法官講話,我把公正執法放在首位。”丹寧調查報告出爐,強調政治家失職,導致謠言四起。不旋踵,首相麥克米倫辭職,議會發言時,他不忘致謝:“為丹寧勳爵完成了這件我請求他完成的複雜而困難的任務,我願意當眾表示我的謝意,我相信下院和全國也同樣懷有這種感激之情。”

《每日電訊報》以號外刊登丹寧報告全文,人們排長隊爭相購閱。戴維斯女士激動地告訴記者:“他是我所見到的最好法官!”獨立電視臺播放丹寧紀錄片主題曲《前進,基督戰士》,丹寧從此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
《法律的正當程式》此書出版不久,正值北大教授龔祥瑞出訪英國。看到書店中熱銷的《法律的正當程式》與《法律的訓誡》,龔先生買下兩本佳作。回國後,老先生組織三四名學生,精心指導他們翻譯出版這兩本書。
1985年,《法律的正當程式》出版,二十餘年暢銷不衰。龔祥瑞教授最後一次訪問英國,應巴特沃思出版社邀請,與丹寧法官相見。丹寧夫婦特意從家鄉乘計程車來到倫敦,下車時,馬路上的行人立即把他認出來,丹寧聳聳肩:“不奇怪,因為自己常在BBC電視臺回答法律問題,所以人們都認識自己。”
初次見面,兩人一見如故。聽到《法律的正當程式》中文譯本出版,丹寧極感興趣。龔教授告知中國有幾十萬讀者愛讀他的書時,老人眼裡充滿了淚光。
當下中國,法律的正當程式曙光乍現,大幕已緩緩拉起,靜待主角出場亮相。
回首來時路,法治薪火相傳,永不止息,讓我們向燃燈者致敬!
譯者李克強
老同學眼中的李克強
李克強是從安徽考上來的,與我同年。比我高半個頭,一米七六的樣子,身材非常勻稱,膚色較黑,濃眉大眼,鼻直口寬,頭髮有點卷,耳朵也很有福相,給人感覺是英氣逼人。話不多,但講起來很有分析力,非常精闢。
克強當時分在一組,和王志勇、王建平、叢培國等在一起。因此,我們之間平時接觸不是很多,說話也不是很多。他給我最深的印象就是學習異常用功。沒有課的時候,一早就離開宿舍,吃好早飯就去圖書館,除了出來吃中午飯和晚飯之外,一直要待到晚上閉館才離開。

李克強所在的宿舍
由於我們這一代人的小學、中學都在“文化大革命”中度過的,沒有外語的基礎,所以克強入學時的英語也不好,但他非常勤奮,自己製作一個小本本,正面是一個英語單詞,反面是中文解釋,苦記硬背,看到英語單詞認識了,理解了,就翻過去;不認識或者還不太記得住,就看反面的中文解釋(《南方週末》去年發表的關於北大法律系77級的那篇文章,記者將這一點搞錯了,寫成:“正面是英語,反面也是英語”,這樣,就無法讓讀者理解當時我們背外語的方法和過程)。
克強學英語的刻苦勤奮,現在的年輕人是無法想象的,他走在路上也在背,上食堂吃飯排隊時也在背,外出坐公共汽車等車時也在背。正是由於他抓住了生活中點點滴滴的時間,拼命苦讀英語,因此,沒過多久,克強的英語水平就上去了,大三以後就開始翻譯英文原版的法律文獻了。1980年5月17日,我的日記是這麼寫的:“克強同學真不簡單,他翻譯的《英國憲法資料》已被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錄用,共一萬多字。他另外翻譯的兩篇文章,也初步為我係雜誌《國外法學》看中。他寫的《資訊控制與法學》的論文,已由系裡列印,送交《法學研究》。他與周振想同學合寫的報道《法律系學生五四科學討論會》也將被《光明日報》錄用”(當然,這些內容有的也是從其他同學那裡聽來的,沒有核實過)。克強後來還和其他同學一起合作翻譯了幾部西方著名法學家的名著(如英國丹寧勳爵的《法律的正當程式》一書,就是由克強等三名同學翻譯的,該書於1999年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李克強(右二)與同學留影
在我與克強同學的交往中,有兩件事印象比較深刻,至今依然非常清晰。一件是我們兩人認識的過程。那是入學之後的事,在一次全班大會上,聽取系裡領導的講話。我一邊聽,一邊翻看手裡的同學花名冊。我當時的學號是36號,跟在我後面的37號同學叫李克強。在這次大會之前我已經知道了他是從安徽考上來的,1955年出生,去農村插隊落戶,是個知識青年,入學之前是大隊黨支部書記,還獲得了全省學習《毛選》的先進個人的稱號。我想這個同學的經歷與我非常相似,我應該認識他,交流交流。此時,我看到坐在身邊的一位同學也在翻看同學名冊,於是,我就問他:你是哪個小組?他說是一組的。我又問他:哪個是李克強?他說我就是。同時,他馬上反問:你是何勤華吧?我說是啊(大概是我們的學號連在一起,故他對我也比較注意)。就這樣,我們認識了。之後,有過幾次我們坐在一起聽學術報告的經歷。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們聽一個外國專家的講座,專家講到一個名詞:canon law,講座中多次出現。我沒有聽出來,就問克強:什麼是canon law?他就告訴我:canon law就是教會法呀,我才反應過來。同時也對他的專業外語水平感到欽佩。
還有一件印象比較深的事情,是在1979年我們讀大二的時候。有一個晚上,我們看了香港電影《至愛親朋》,它描寫的是資本家之間為了獲取最大經濟利益而彼此競爭,乃至完全喪失了朋友、親戚、父女、夫妻感情的故事,雖然許多地方模仿了巴爾扎克小說中的情節和手法,有些誇張和搞笑,但看過以後,給人的印象還是很深的,而且人也很興奮。趁著一股熱情,我就將看後的一些想法,結合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闡述的關於資本在遇到剩餘價值時就變得活躍起來,以及資本主義為了利潤將人世間溫情脈脈的面紗完全揭開的原理,花了兩個晚上一氣呵成寫了一篇兩萬多字的文章。寫好後給我們宿舍的幾位同學看後,大家都沒有提出什麼意見,但都建議我將文章給克強看看,說他看了許多西方經濟學的書,對經濟理論比較有研究。於是,我就將文章給了克強。三天以後,他將文章還給了我,我就請他幫我提提意見。他說,我們同學之間就不講客氣話了。你這篇文章,雖然下了點功夫,而且也看得出,你對馬克思的《資本論》也非常熟悉,作為習作是沒有問題的,但如果要投出去發表,則還有兩個問題必須解決:第一,你文字太囉嗦,至少可以刪掉三分之二;第二,你必須補充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西方資本運作的新情況以及經濟學理論的新成果。
可以想象,克強的這個意見,如果是換作另一個同學聽了,可能會深受打擊,非常沮喪,因為他的意見實際上就是把文章給否定了。但我聽了以後,感覺到他講得還是有道理的:一則我當時寫東西確實很囉嗦冗長,這一點李志敏老師已經批評過我好多次了。二則我對西方資本的情況以及西方經濟學理論成果並不瞭解,甚至可以說是一片空白。這樣,我最後聽從他的意見,將此文作為習作,既不修改(按照我當時的水平和能力也沒有辦法修改),也不投出去,就一直放在了抽屜裡。大學畢業整理行李時,我還看到過這篇文章,之後因為不斷搬家,資料丟失了許多,這篇文章,也不知道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丟掉了。

李克強與夫人程虹
回憶上述小事,並將其寫出來,主要目的是要說明,一個人的成長並不是很容易的。就拿寫東西而言,我雖然也寫了並且公開發表了不少論著,但開始時完成的成果,許多都是很幼稚、很粗糙、很膚淺的,後來之所以一點點有進步,主要是因為自己比較執著,從不放棄,不斷琢磨,並且得到了像李志敏、由嶸、徐軼民、陳鵬生、餘先予等老師以及武樹臣、李克強、陳興良等同學的指點、幫助乃至批評。因此,任何人都不必埋怨自己的處境,只要你能夠多聽他人的意見,善於吸取身邊每一個人的長處,來彌補和充實自己,就一定可以有所進步,慢慢前進。
關鍵詞
教授
同學
法官
理論
李克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