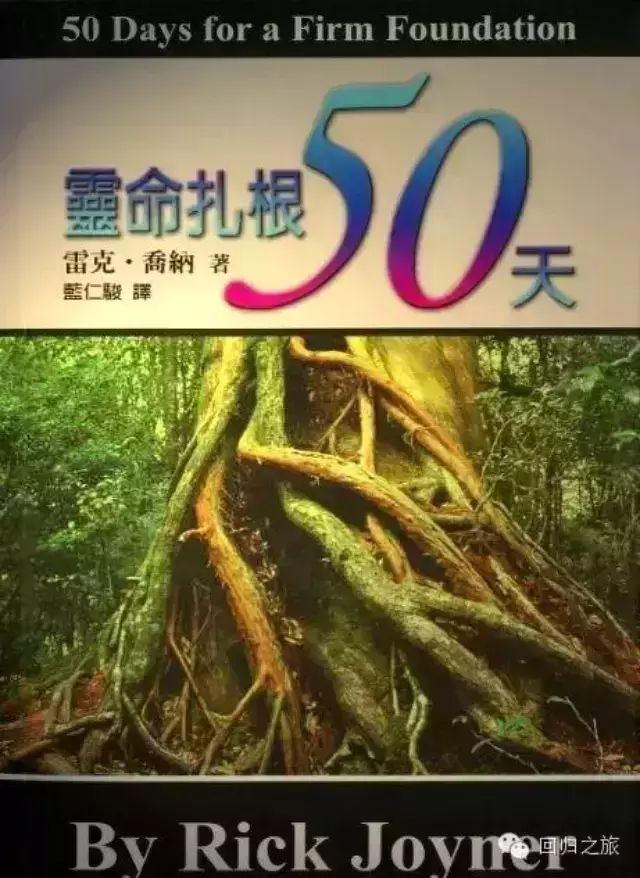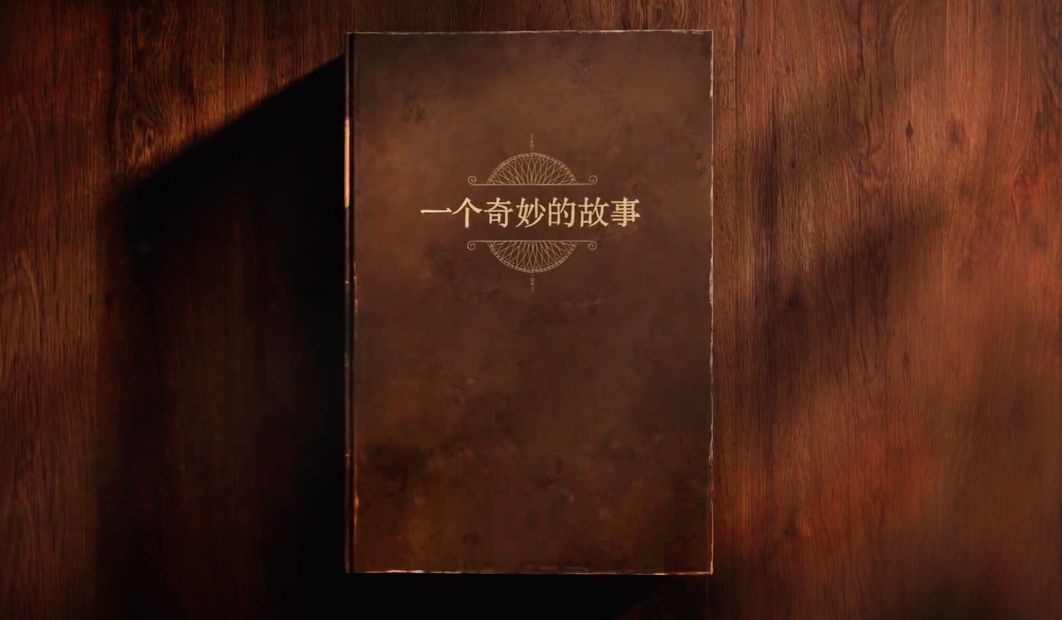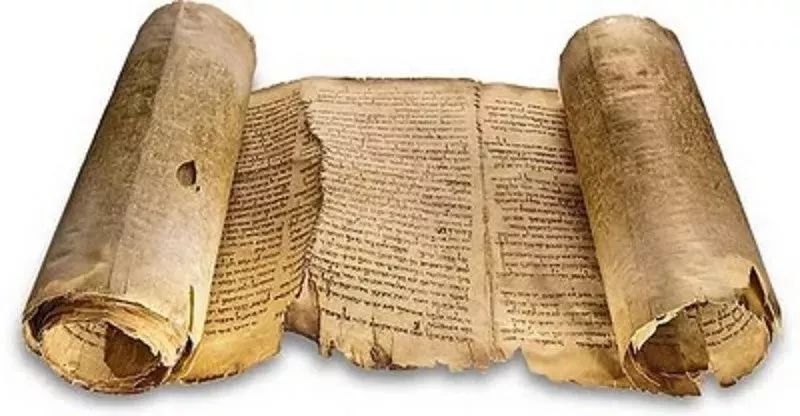耶穌的一生遵循一個從降卑到升高的一般模式,然而這一升移並不是完全直線型的,而是伴隨著一些對比情節。降生敘事既包含恥辱又包含威嚴,祂的公開侍奉引來讚美和嘲諷、歡迎與拒絕,既有“和散那”的呼聲,又有“釘祂十字架”的呼喊。臨近死亡陰影時,祂彰顯了登山變像的半遮掩轉折。
從十字架的悲慟到復活的壯麗,這一過渡並不突然。從裹屍布到墳墓的石頭,敘事越發增強地往轉折點推進。升高始於下十字架,人們常常會想到古典基督教雕像“哀悼基督”。在耶穌屍體的處置上,規則被打破。在正常司法處境下,被釘十字架的罪犯屍體要被政府拋棄,沒有埋葬儀式就扔到“欣嫩子谷”——耶路撒冷城外的垃圾站。在那裡屍體被焚燒,以外邦方式火化,失去傳統猶太葬禮的尊嚴。作為一種維持公共衛生的方式,欣嫩子谷的火不停地焚燒,以便使城市的垃圾得以清除。對於耶穌來說,欣嫩子谷是地獄的一個恰當比喻,一個火永遠不滅、蟲子永遠不死的地方。
彼拉多在耶穌的事上作了例外,也許他飽受良心煎熬,因著同情同意了埋葬耶穌的請求。也許他是被神至高的護理推動,確保先知以賽亞有關耶穌與財主同葬、神不會讓祂的聖者見朽壞的預言得以實現。基督的屍體被香料膏抹,用細麻布裹起來,放在一個屬於貴族亞利馬太的約瑟的墳墓裡。
三日之久世界陷入黑暗,跟隨耶穌的婦女們悲慟哀哭,僅有一點安慰就是被允許執行一個溫柔之舉——膏抹耶穌的屍體。門徒們已經逃竄,抱團躲藏起來,他們的夢想被一句呼喊終結了:“成了。”
三日之久神在沉默,然後祂發出可畏的響聲。神以大能滾開墳墓前的石頭,發出生命的創造之能,將之充滿基督靜止的身體。耶穌的心臟開始跳動,在榮耀的動脈裡輸送著榮耀的鮮血,將榮耀的能力輸送到死亡所萎縮的肌肉中。裹屍布不再束縛祂,祂站起身離開墓穴。在一瞬間,已死的變為不朽,死亡被勝利吞沒。在歷史中的這一刻,約伯的問題一次為所有人作答:“人死了,還能再活嗎?”這是人類歷史的分水嶺,在這裡,人類的愁苦化為輝煌。在這裡,初代教會傳講的福音訊息隨著一聲呼喊誕生:“祂復活了。”
我們可以將這一事件視為一個象徵,一個可愛的關於希望的故事。我們可以將之降低為一種道德主義,作出一個講道人如此總結的宣稱:“復活的意義在於我們可以用辯證的勇氣面對每一天的黎明。”辯證的勇氣是現代虛無主義鼻祖尼采發明的把戲,辯證的勇氣是處於張力中的勇氣,這張力就是:人生沒有意義,死亡即根本。我們必須鼓舞起來,即使我們的勇氣毫無意義。這種對復活的否定滲透著刪節版存在主義盼望的絕望。
然而,新約宣告的復活是一個清醒的歷史事實。早期基督徒對辯證符號沒什麼興趣,只對斬釘截鐵的事實有興趣。真正的基督教與時空中的耶穌復活共存亡。基督徒這個稱號飽受苦難,從成千種考驗的重擔到無數種不同定義。一本詞典將基督徒定義為一個文明人,一個人可以不相信復活就做個文明人,但按照聖經這個人絕對做不了一名基督徒。宣稱自己是基督徒卻否認復活的人是拿虛謊的舌頭說話,我們應當躲避這樣的人。
復活敘事幹犯了大衛•休謨的機率測試,被布林特曼歸為不能作為聖經核心真理的神話。對於保羅凡布倫,那個上帝之死神學家來說,復活甚至不是聖經教導的一個真實歷史事件。他將之降解為一個“洞察力處境”,門徒在其中突然“領會了”耶穌,在新光照下“看見了”祂。凡布倫的理論違背了清晰聖經文學解經的每一項原則,新約作者旨在宣告死人復活,這一點不存在於任何嚴謹的文字爭議中。一個人可以否認這一思想,但不能否定說這個思想未被宣明。
即使是布林特曼也向早期教會“復活節信仰”的歷史事實讓步,然而他顛倒了聖經中的次序,爭辯說是復活節信仰導致了復活的傳講。聖經指明是復活導致了復活節信仰,因果關係的微妙差別是信心與背教的差別。聖經作者宣佈他們是復活基督的目擊證人,以他們的生命見證信心的誠實無偽。早期教會願意為信仰而死,現代教會卻作出讓步,一個證據就是一個主要宗派因著復活產生教會分裂而不願意重新確立身體復活這一教義。對基督復活的信心確實是分裂性的,它將基督徒與格鬥者分別開來,激起滿懷敵意的尼祿用活人火炬給他的花園照明。
耶穌的復活其原初意義是顛覆性的,它涉及基督徒信仰的根本。沒有了它,基督教不過是另一個以人類智慧的陳腔濫調給我們的道德感撓癢癢的人造宗教。
使徒保羅言明瞭一個“沒有復活”的基督教有什麼清楚、無可辯駁的後果。他推理說,如果基督沒有復活,我們就必須得出以下結論(林前15:14-19):
我們所傳的是枉然。我們的信心也是枉然。我們是為神妄作見證的。我們仍在罪中。我們所愛的那些死去的人已經滅亡了。我們是眾人中最可憐的。
這六個後果尖銳地揭示了復活與基督教本質間的內在關聯,耶穌的復活是基督信仰的必要條件,拿走了復活你就拆毀了基督教。
然而,聖經作者並不是將他們對復活的宣講建立在它與整個信仰的內在一致上,它並非僅僅是從其他教義得出的一個邏輯推論,我們必須肯定復活,不是因為它的反面是殘酷的,我們肯定復活,不是因為沒有它人生就是無望而不可忍受的。我們的宣信不是建立在猜測上,而是建立在經驗性資料上。他們看見了復活的基督,他們與祂交談,與祂一同吃飯。不論是祂的死還是祂的復活,都不是發生在一個角落裡,就像約瑟•史密斯宣稱領受了特殊啟示那樣。耶穌的死是一個公共奇觀,是一個有公共記錄的事件,復活的基督一次被五百人看見。聖經在這件事上呈現的是歷史。
對於聖經關於耶穌復活記載的最強烈抗議,跟對聖經其他神蹟的最強烈抗議一樣,就是說這些事是不可能的。諷刺的是新約對於耶穌的復活採用了截然相反的方向,彼得在五旬節的講道中宣告說:“神卻將死的痛苦解釋了,叫他復活,因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
為了宣告這裡宣佈的原則,我必須允許自己使用一次雙重否定。基督不復活是不可能的,因為要死亡拘禁基督,必須對死亡定律做出極限、不可想象的違背。現代人將“死去的就一直死亡”視為不可改變的定律,然而,這是一條墮落自然界的定律。在猶太教的自然觀念中,死亡是作為對罪的審判進入世界,創造主命定了罪的工價是死刑:“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這是原初的警告。神在人犯罪之後對人類生命予以延緩,但不是無期限的。原初的刑罰並未完全撤除,大自然母親變為最主要的死刑執行者。亞當被造時,既有“死亡的可能性”,也有“避免死亡的可能性”;藉著他的犯罪,他“避免死亡的可能性”被沒收,並且作為審判,他獲得了“不死亡的不可能性” 。
耶穌不是亞當,祂是第二個亞當;祂沒有罪,不論是原罪還是本罪。死亡對祂不具有合法的佔有權,祂是因著被歸算給祂的罪受刑,然而一旦贖價付清,歸算就從祂身上移除,死亡在祂身上就失去能力。藉著死,祂付上了贖價;在復活中,耶穌被證明清白、完全無罪。正如聖經所宣稱,祂是為了我們的稱義復活,也是為了祂自己的清白復活。
休謨的機率論因著復活是一個獨特事件而將之拋棄,他在一種演算法上是對的,復活的確是個獨特事件。儘管聖經也記載了其他復活事件,例如拉撒路的復活,但它們全都歸屬一個截然不同的類別,拉撒路後來又死了。耶穌復活的特殊性與祂獨特性的另一個方面緊密相連,就是祂的無罪;如果獨特性也能有程度之別,那麼無罪就是耶穌位格中更加獨特的一維。
要神允許耶穌永遠被死亡拘禁,等於是要神違背祂自己義的性情;那就變成了一件不義之舉,一件神絕對不可能犯下的舉動。真正的震驚之處不是耶穌復活了,而是祂在墳墓裡待了三天之久。也許這是神屈就人類不信的軟弱,因此允許基督暫時被拘,以便耶穌的確死了以及復活的事實不會被質疑,被人錯誤地當成昏厥後的復甦。
復活將耶穌與世上任何主要宗教區別開來。布哈達死了,默罕默德死了,孔夫子也死了;這些人中沒有一個是無罪的,沒有一個提供代贖,沒有一個以復活被證明清正。
如果我們在復活事實前在不信中蹣跚搖擺,我們若是能思想一下那個週末往以馬忤斯路上走的兩個人的遭遇就好了。路加為我們記載了這一事件,那兩個人正在離開耶路撒冷的路上,耶穌匿名與他們同行。他們努力向耶穌講解十字架事件,對耶穌明顯的茫然無知感到明顯的不耐煩。當他們講到婦女們說耶穌復活時,耶穌責備他們:“‘無知的人哪,先知所說的一切話,你們的心信得太遲鈍了。基督這樣受害,又進入他的榮耀,豈不是應當的嗎?’於是從摩西和眾先知起,凡經上所指著自己的話,都給他們講解明白了。”當兩個人的眼睛開了以後,他們當晚認出了耶穌,彼此說:“在路上,他和我們說話,給我們講解聖經的時候,我們的心豈不是火熱的嗎?”
基督徒絕不是懷疑論者,基督徒是一個帶著一顆燃燒之心的人,一顆被複活實際點燃的心。
節選自作者著《耶穌是誰》第四章,喬蘭山以妲譯,改革宗翻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