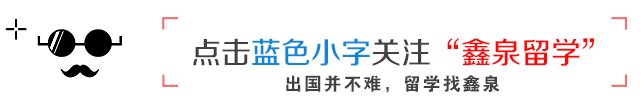我從小就特別喜歡讀古書,一開始是讀白話文翻譯,慢慢過渡到文白對照,中學以後就經常閱讀原文了。記得我最早愛讀的是《莊子》,因為裡面有很多故事;後來愛讀《左傳》《史記》,因為裡面有更多、更成系統的故事。隨著年歲漸長,我逐漸開始關注那些故事之外的東西,例如“為人處世的道理”,乃至“治國平天下的道理”——當時還不知道,這些道理有一個總稱,叫做意識形態。
人不中二枉少年,高中和大學時代的我是相當中二的,周圍也團結了一群中二的朋友。所謂中二,主要表現有兩個:第一是覺得自己能得到最轟轟烈烈的愛情,第二是覺得自己能夠為天下大事找到解決方案。今天咱們先不說第一條,只說第二條;怎麼解決呢?無非是依靠實踐和讀書。作為學生,不可能有太多真正的實踐機會,主要還是靠讀書。我選了很多人文社科方面的課,還去圖書館借了很多書,其中既有中國書,也有外國書。不過我內心深處,最愛讀、最寄予厚望的,還是中國書尤其是中國古書。為什麼呢?
第一,中國古書是我們的祖先寫的,契合了我年輕時的樸素愛國主義情緒,感覺自己與當年的作者血脈相連。第二,中國古書更貼近中國傳統文化,理解起來更容易一點,不像外國書還要先理解許多文化背景。第三,“博覽古書、神交古人”是一件很酷的事情,譬如讀《論語》可以神交孔子,讀《傳習錄》可以神交王陽明;相比之下,神交柏拉圖、奧古斯丁、孟德斯鳩,好像就沒那麼酷了。說一千道一萬,我是中國人,我愛自己的祖國、母語和文化傳承。如果能從我們的傳統文化當中發掘出閃光的東西,我絕對是不會去求助洋人的。
我中二病最嚴重的那陣子,跟社團的師妹們去唱K,手裡都拿著《尚書正義》和《四書集註》。其實不僅是為了抓緊時間讀書,更是為了向師妹們顯示自己很酷(可惜她們大多不吃這一套)。記得某年夏天,我在學校南門外的餐館裡,熬了一個通宵讀完黑格爾的《歷史哲學》,其中對中國“歷史停滯、缺乏創造力”的評價令我頗為惱火,還寫了一篇文章指責他對中國的理解太膚淺。我還把自己的文章拿給哲學系的師姐看,對方含蓄地指出,“你作為一個業餘愛好者是合格的”,但這樣的文章寫不寫都是一回事。
有些人工作之後就變得很現實,不再想宏大敘事了;但我不一樣,工作的前幾年還是很愛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尤其是讀了康有為的《孔子改制考》以及梁啟超的《清代學術概論》之後,我發現了今文經學這個“瑰寶”,相見恨晚,感覺對傳統文化的理解更深刻了!所謂今文經學,是誕生於西漢前期、帶有強烈社會改革色彩的儒家思想。與後世流行的古文經學(漢學)和宋明理學(宋學)相比,它有幾個鮮明的特徵:
-
今文經學認為孔子是一個改革家,儒家是一個改革學派,《春秋》就是為後世立法。誰要是說孔子守舊、述而不作,今文經學家會第一個不同意。 -
今文經學非常關注制度的“頂層設計”,例如一個國家到底該怎麼組織?天子、諸侯、士大夫和老百姓分別應該履行什麼職責?如何使得社會各階層上下融洽、各得其所?反而是對道德哲學沒那麼重視。 -
今文經學很有理想主義情操,對於什麼是“正義”、什麼是“天下大同”,有完整的理論和實踐框架。當然,各家學派的框架往往各不相同乃至彼此牴觸,但骨子裡仍是理想主義的。
第一次讀到《孔子改制考》,我拍案叫絕:誰說中國人只會因循守舊,誰說儒家只會翻故紙堆!孔子一介書生,手無寸鐵,卻透過改寫六經、建立學派的方式,設計了幾百年後的社會制度,堪稱公元前五世紀的大改革家。後來又讀皮錫瑞的《經學歷史》,更是感嘆於先秦儒家竟然如此有先見之明,銳意進取、不畏強暴(尤其是後來一統天下的暴秦),創造了偉大的制度和文化。梁啟超總結認為,中國近代的落後不是傳統文化的問題,而是程朱理學、陸王心學大行其道,越來越重視修身養性而不是解決社會實際需求,這才導致了西方後來居上。我非常贊成,恨不得穿越回去跟康梁二位先生交朋友,感覺自己經脈中的中國血更加鮮紅、更有生氣了。
當然我是不會滿足的,又繼續去讀更多的古書,包括今文經學家最推崇的《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二者我都很喜歡,前者恢弘,後者謹慎。小小的一部《春秋經》,竟然能夠講出這麼多的“大義”,實在令人歎服中國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民國時期的楊樹達寫了一本《春秋大義述》,指出法國輸掉二戰是不遵循春秋大義的結果,我們中國必將贏得抗戰則是春秋大義的功勞。這本書寫得很有煽動性,我出差坐高鐵的時候都帶著,有時候不禁讀得熱淚盈眶!
然而,讀著讀著,或許因為讀得實在太多了,又或許因為年紀變大了,我產生了越來越多的懷疑情緒。首先,《公羊傳》《穀梁傳》裡面那些大而化之的道理,似乎缺乏可執行性。例如我最喜歡《穀梁傳》的正義論,什麼是“正”、什麼是“不正”,說得清清楚楚;但要如何維護正義呢?還有晚清今文經學家提出的意識形態,絕大部分亦是高高在上,不能直接拿來富國強兵,甚至難以作為制度設計的藍本。就連康有為自己主導的戊戌變法,也只是拿《公羊傳》做了個幌子,具體措施一半是抄的西歐、一半是抄的日本。至於說依靠“春秋大義”打贏抗戰,仔細一想更是荒誕不經:要怎麼贏呢?開啟《春秋》,誦讀聖人的微言大義,日本鬼子就會痛哭著放下武器投降嗎?
其次,今文經學設計的制度,歷朝歷代有誰實踐了?準確的說,有一個朝代,那就是王莽的新朝——其結果如何大家看得很清楚。晚清今文經學家的文化影響力不可謂不大,但無論民國還是當代的制度,好像都不是來自他們。我們甚至可以進一步說,自從孔子誕生,兩千五百年來,中國沒有任何朝代的制度,是完全依託儒家文化或任何一種傳統文化而建設的(新莽是唯一例外)。這是因為傳統文化不夠合理嗎?還是因為現實太複雜,只能見招拆招?不管是哪種原因,我們好像都不應該沉浸在故紙堆中,指望幾千年或幾百年前的古人,能為我們提供什麼解決現實問題的靈丹妙藥。
如果今文經學不行,那麼其他儒家學派就更不行了。王陽明很受現代人推崇,其實主要講的還是道德哲學,教大家怎麼修身養性;朱熹更是如此,而且思想更加僵化,沒有提供社會改革的任何理論基礎。再往前則是從鄭玄到孔穎達一脈相承的古文經學,其核心思想是尋章摘句的訓詁學、考據學,教我們如何理解古代聖賢君子每一句話的具體含義。我相信,對於養成高雅的生活情趣,這些知識應該相當有用;可是高雅的生活情趣能拿來富國強兵嗎?能解決任何實際問題嗎?明朝的遺民譏諷士大夫“平時袖手談心性,臨難一死報君王”,我們再怎麼精讀傳統文化,還能讀的比明朝士大夫更深嗎?

上述疑惑,一旦產生就無法遏制,愈演愈烈。於是,從二十六七歲時開始,我讀的中國古書漸漸少了,反而增添了許多外國書,例如十八世紀以來英美及歐洲大陸思想家、哲學家和法學家的書。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和孟德斯鳩的《波斯人信札》,讓我十分敬佩,其中有許多中國古人從未提出的觀點;丹寧勳爵關於普通法的一系列著作,尤其是《法律的正當程式》,也大幅開闊了我的眼界。我必須承認一件事情:如果沒有西方文化的傳播,單純依靠中國傳統文化,要產生那些現代性的思想乃至發生啟蒙運動、工業革命,簡直是不可能的事情!晚清的今文經學家們,以及民國的章太炎、錢穆、楊樹達等大師,花了一輩子時間論證“中國傳統文化應有盡有、萬事俱備、不用依靠外來思想”——可是隻要讀的書足夠多了就能意識到,那是何等荒謬的論點啊!
我算是體會到了晚清中國知識分子的矛盾與不甘心:主權在民、人人平等、法治、福利國家,這些現代性的社會思想,為何沒有誕生於中國?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法學,這些現代社會科學為何也全部發源於西方?而且,我們的先輩不是沒有想過略過這些思想、只學習自然科學和工程學方面的東西——不止一個晚清官員嚴肅指出,洋人只是“船堅炮利”,我們要“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學習洋人的理工科就行了,別的東西還是中國傳統文化好。自從甲午戰爭、庚子國難,上面這套理論迎來了總破產,不想學也得學了。
為了解開“中國傳統文化為什麼沒有誕生現代性”這個謎題,我找了很多當代歷史學家的書。他們提出了很多解釋,有些很有道理,但總覺得不夠直接。於是我又去讀《春秋穀梁傳》,這本書的文字很優美,拿來當散文讀也是很好的。晉朝人範寧給這本書做注,寫的序言裡面,有這樣一句話,曾經多次從我眼皮底下溜過去,這次卻引發了我的格外注意:“天垂象,見吉凶;聖作訓,紀成敗。欲人君戒慎厥行,增脩德政。蓋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履霜堅冰,所由者漸。。”
翻譯成白話文就是:“上天降下了天象,聖人寫下了訓示,都是希望教導君主,讓他們謹慎行事、修煉品德。可惜我們苦口婆心地勸導你,你卻自高自大地不肯聽,積重難返,最終釀成了災難!”
我第一次看到這句話的時候,心想:“昏君真不是東西啊!要是換了賢明的君主就好了。”後來又看到這句話,心想:“為什麼歷史上總是昏君多、賢君少?是先天教育不足還是後天墮落了?”再後來更成熟一點了,再看到這句話,心想:“能不能想個辦法約束君主,讓他們必須聽聖人的話?”其實,古代的知識分子比我想的更多,做的也更多,可是無一例外失敗了。早在一千八百年前,諸葛亮在《出師表》中就對後主提到,“親賢臣、遠小人”是國家興旺的必要條件;可是在他死後,後主仍然走上了“親小人、遠賢臣”的道路。連諸葛亮都教不好自己的君主,後人還能做得更好嗎?
所以,在讀過盧梭、孟德斯鳩和丹寧勳爵的書之後,我再次看到《春秋穀梁傳序》中的那句話,想到的卻是:“為什麼要有君主?既然君主是釀成災難的根源,不應該把這個根源取消掉嗎?”退一萬步講,就算取消不掉,也應該用制度去限制他,讓他在合理的範圍內活動,而不是依靠幾個“聖人”孜孜不倦地去教導,因為事實一再證明他是不會聽的!
公允地說,中國傳統文化不是沒有思考過這個問題。公元前四世紀的孟子就提出過“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十七世紀的黃宗羲寫了《原君》,指出“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天下最大的禍害就是君主)!很可惜,形勢比人強,知識分子的一支筆肯定抗不過君主的刀劍。朱元璋讀了《孟子》之後,就很想把這個已經死了一千多年的老頭子抓起來;黃宗羲的思想,在“避席畏聞文字獄”的清朝前期,更不可能流傳開來。如果沒有受到君主的暴力威脅,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能不能產生堪與啟蒙運動相提並論的思想成果?歷史不容假設,但問題究竟出在哪裡,已經昭然若揭。
在其他社會科學乃至自然科學問題上,何嘗不是如此?唐宋以前,社會風氣還是比較寬鬆的,容得下知識分子乃至普通百姓做各種各樣的嘗試,所以中國還沒有落後;明清以後,隨著君主專制的不斷加強,以及自上而下的科舉考試對知識分子的毒害日益加深,大家“胡思亂想”的空間和慾望就都越來越小了——沒有“胡思亂想”,就不會產生像樣的新思想。所謂聖人君子,連“誨爾諄諄”的機會都喪失了,只得眼睜睜地看著君主“聽我藐藐”。在這樣的環境裡,中國能誕生什麼現代經濟學、社會學、法學呢?更談何文藝復興、地理大發現、工業革命?
這還不算完,因為大家都目睹了君主的富貴尊榮,所以都想在自己的地盤上當君主:父親希望兒子(以及老婆)把自己當做皇帝崇拜,官員希望下屬(以及子民)把自己當做皇帝服從,就連老師也希望學生(乃至學生家長)把自己當做永遠不會犯錯誤的皇帝。看起來天下只有一個皇帝,其實到處充斥著小皇帝、土皇帝。如果這種事情發生在兩千年前,倒是可以用“歷史侷限性”去解釋;可是這種事情發生在歐洲人已經發動了一場又一場資產階級革命、砍掉了一個又一個國王的人頭的情況下啊!等到他們殺過來了,中國官員還在嘮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不知道他們腦海中的“中學”究竟比“西學”先進在哪裡?是下跪磕頭的姿勢更流暢,還是老子打兒子、教師打學生的動作更純熟?
魯迅先生曾說:“中國書雖有勸人入世的話,也多是殭屍的樂觀;外國書即使是頹唐和厭世的,但卻是活人的頹唐和厭世。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對於這句話,歷來爭議不小,所以我們的課本也並不收入。二十年前的我,大概會覺得魯迅偏激了;現在則完全贊成他。被兩千多年曆史的君主專制(現在時髦的說法叫“秦制”)束縛、形成森嚴的上下尊卑觀念、人們無不被困在一畝三分地裡、既沒有行動自由也沒有思想自由的文化,不是“殭屍”又是什麼呢?活人未必一切都好,但是最差的活人也比殭屍更強。很慚愧,魯迅先生早在九十多年前就參透了的真理,我卻非要自己再證實一遍,相當於“重複發明輪子”。
人類各自有各自的祖國,熱愛自己的祖國是天經地義的,就像熱愛自己的父母一樣。但是人類的精神文明沒有國界線,自然科學成果如此,人文及社會科學成果也如此。少讀中國書(尤其是少讀“傳統文化”)、多讀外國書,絲毫無損於中華民族的偉大,也不改變中華文明是人類歷史上最光輝燦爛的文明之一的事實。在此我還是想援引我十分喜愛的《春秋穀梁傳註疏》的結尾部分,體現我此時此刻的心情:
“中國者,蓋禮義之鄉,聖賢之宅。軌儀表於遐荒,道風扇於不朽。麒麟步郊,不為暫有。鸞鳳棲林,非為權來。雖時道喪,猶若不喪。雖麟一降,猶若其常。”
(所謂中國,就是禮義之鄉、聖賢之宅。法律制度能夠傳播到荒僻之地,道德情操能夠激勵到千秋萬代。麒麟在郊外出現,不是暫時現象;鸞鳳在林子裡棲息,也不是偶爾出現。雖然現在中國之道已經淪喪了,但我們心中還是覺得彷彿沒有淪喪。雖然麒麟只是偶爾降臨中國,但我們還是覺得它好像經常來一樣。)
“此所以所貴於中國,《春秋》之意義也。”
(《春秋》就是這樣讚美中國的。這就是《春秋》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