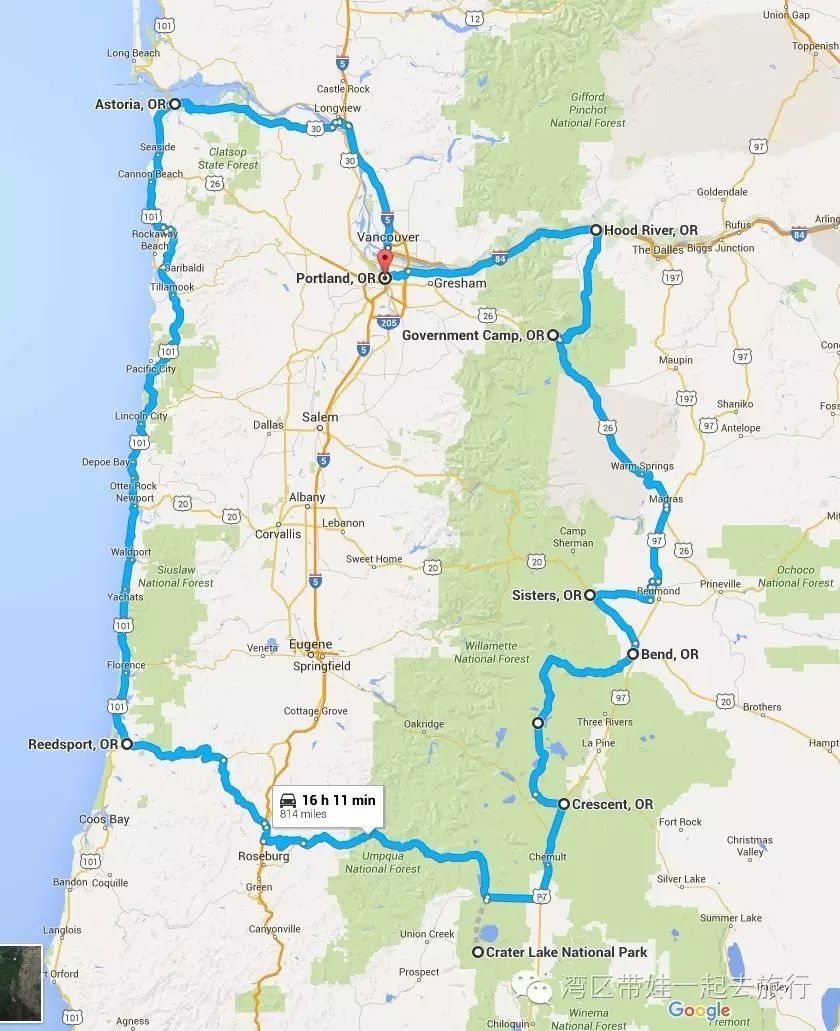“今天過得怎麼樣?讓我抱抱你,辛苦了。”在安靜的環境下,伴隨溫柔低語,裹著柔軟的毛毯,戴上熱敷眼罩,緊繃的神經終於鬆弛下來。
只不過,這種情緒上的安撫,要靠“凝聽”和觀看來完成。
除了繾綣耳語,耳機裡傳來撫摸毛毯的摩挲聲、輕捏凝膠熱敷袋和按壓熱毛巾的聲音,畫面則以觀眾為第一視角,模擬深夜歸家後被人照顧的過程。
這是MTkoala在B站最受歡迎的ASMR助眠影片之一,播放量高達138萬。
“這個人在幹嘛?”有的人無意中點進影片,看見MT或對著雙頭麥克風低吟,或雙手抓撓某物,覺得不明所以,甚至留下諸如“發神經”的惡評。
在MT看來,人的感覺無法相通。ASMR的有趣之處就在於,它是一種非常私人化的體驗。觀看者被喚起什麼,取決於需要什麼。
有的人可能覺得ASMR很無聊,也可能會覺得與性有關。但對很多人而言,他們是想找回被呵護和撫慰的感覺。
“好舒服啊”“心靜下來了身體也困了”“真的感受到了熱敷凝膠熱敷袋的溫暖”等評論在MT的影片中不斷刷屏。

MT撫摩毛毯
在大眾語境下,ASMR仍是一個名字繞口又難記的古怪圈子。
很長一段時間,它有一個頗為曖昧的中文譯名“顱內高潮”,再加上涉及睡覺這個私密性很強的領域,很多人望文生義地將其與“性”“慾望”聯想在一起:
ASMR和性高潮有什麼相似之處嗎?這是一種“性癖”嗎?
後來,ASMR正式更名為“自發性知覺經絡反應”,但仍未糾正大眾對它的錯誤觀感,還是有很多人不解:ASMR到底是什麼?就是哄人睡覺嗎?
實際上,ASMR的本意從來與性無關,也永遠不會有關。
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ASMR是在重現噪音。很多研究指出,能觸發ASMR的聲音,恰恰是日常中那些被忽視的細節,比如塗抹手霜、水倒進玻璃杯、翻動紙張等。
但不同於單純的自然音效或白噪音,ASMR更關注特定的情境,比如掏耳朵,撫摸頭髮和眉毛,理髮師輕輕按摩頭皮,花灑噴出溫度和水壓都剛剛好的水霧到後脖頸。
正是這些生活中不經意間由聲音、視覺、觸感、氣味構建的場景,成為了ASMR最核心的觸發點。
這些特定的場景會讓人產生一種奇異的舒適感,就像觸電了一樣,頭皮發麻,但又感覺很放鬆,有一種被撫慰的溫暖感。
MT稱:“有的人可能永遠都對ASMR沒有感覺,但有這種感受的人,其實在知道這個概念前,就體驗過了。”
她也發現,這些場景存在一個共性:讓人感受到被照顧、被關注、被愛。

對很多人而言,MT有一種渾然天成的沉靜、溫柔與堅定,能喚醒童年時期被母愛呵護和照顧的感覺。
所以,不同於其他大多數ASMR博主被粉絲稱為“女友”,MT的粉絲們更喜歡稱她為“媽媽”。
去年,MT就真的就當起粉絲們的媽媽,製作了照顧寶寶的ASMR影片。
“寶貝,我們該喝奶粉啦,剛好溫溫熱。”點開影片,觀眾以躺在嬰兒床裡的視角,享受被MT像媽媽一樣照顧:餵奶、撫摸臉頰、擦拭身體,耳畔則是她的輕聲絮語。
幾乎所有人都存在一個共通之處:嬰兒時期被母親抱在懷裡、撫觸、有節奏地搖晃、輕拍。長大後,雖然不再有過這樣的體驗,但這份被好好照顧的記憶始終埋藏在腦海中。
聲音的記憶,總是格外獨特。某個突如其來的瞬間,一些空氣中細微的震顫,就能讓腦海中搖搖欲墜的記憶復甦。
就像這條ASMR影片,哪怕只是奶粉搖晃碰撞杯壁的聲音,也能讓人恍惚間嗅到奶水的香甜氣息,甚至是感受到溫熱,回想起一些長大後再也沒有過的感覺:
“小時候媽媽帶我去朋友家,我在我媽懷裡睡著了,她抱著我和朋友繼續聊天,我耳朵貼著她的胳膊感受她的聲音透過她的胸腔和骨骼悶悶地傳遞過來。”

MT為寶寶擦寶寶霜
還有一位新手媽媽看完MT照顧寶寶的影片後,留言道:“剛哄完崽崽睡覺的新手媽媽終於可以享受一次被哄睡了,好幸福!!!”
不只是所謂的哄睡或催眠,MT更想做的,是將成長路徑中那些溫暖的回憶,復刻在成年人身上,用聲音照顧那些疲憊、忙碌、孤獨的大人。

很難用一個詞準確形容MT的聲音是什麼樣的。
“我的聲音還蠻普通的,說不上有多出彩,也說不上難聽。”即使從降噪世界中的耳語落地到現實世界,MT的聲音也不帶任何強烈的情緒表達,有一種天然的溫柔。
就像學生時代以來的暱稱“考拉”,MT從小喜歡抱抱,自帶一種讓人安心的氣質,哪怕隔著螢幕,也彷彿能撫平對方的焦慮。
她至今都難以忘記,初中後座女同學為自己剪髮尾分叉時的奇異感覺。
對方的指尖輕撫過髮間,腦袋裡像突然閃過銀光,一陣陣酥麻感從頭皮延伸至耳朵,形成一股蔓延全身的暖流,這讓她暗暗驚歎“哇好舒服哦”。
MT後來才瞭解到,觸發這種奇特生理現象的瞬間就是ASMR。從那時起,她就一直很想念這些細節。

童年時期的MT
直到2013年,她睡眠有點不太好,在影片網站無意中發掘到一些梳頭、低語的、引導冥想的影片,才找到了久違的共鳴,“感覺很舒服,整個人變得鬆弛,就產生了睏意。”
也是在那個時期,這些讓她安然入睡的影片開始打上ASMR的標籤,在外網火了起來,但在國內影片網站,相關內容還是一片空白。
於是,MT向自己一生摯愛的ASMR博主Maria學習,買了一支可以錄製立體音的錄音筆,嘗試錄了一條助眠影片投稿到B站。
她彷彿是在講述睡前故事那樣,一邊輕輕翻動書頁,一邊輕聲細語地介紹英文原版立體書《彼得·潘》的內容。
和現在動輒各種分鏡頭、摳綠幕做場景的成熟影片相比,MT早期的ASMR影片更像是“習作”,沒有華麗佈景,也沒有過多剪輯,只有低語輕聲、指尖與空氣之間細碎的碰撞。
那時,由於不被理解,MT只能躲著父母,拍攝和製作影片。

隨著對這個圈子的深入接觸,MT發現創作ASMR影片非常講究技術。
2015年,錄了幾期影片後,她升級裝備,購置了一個模擬耳朵雙聲道麥克風,開始錄製真正意義上的ASMR影片。
步入這個降噪世界後,她不斷放飛自己的想象力,用小刷子模擬採耳的聲音、用毛絨耳罩模擬下雷雨聲和海浪聲、轉動雨棍模擬溪流聲、用小棍碾磨鹽粒發出踏過雪地的聲音……
這些讓人身臨其境的聲音,讓擬聲詞顯得格外笨拙。

MT用刷子模擬採耳聲
經過幾期影片的嘗試,她也慢慢摸索出屬於自己的敘事化風格,開始鑽研各種劇情類影片,扮演不同的角色。
但無論扮演誰,觀眾都不會在MT的影片中,看見暴露的低胸裝或者黑色絲襪,聽見具有挑逗意味的話語。
有時,她是閨蜜或姐姐,有時是牙醫、化妝師或水療師,有時甚至還是文物修復師和魔法世界的女巫……讓觀眾代入不同的敘事場景中,享受被不同人照顧的感覺。
最早圈粉的一期影片,就是2016年《姐妹的照顧》。通過後期剪輯,她一人分飾一對性格迥異的雙胞胎,照顧螢幕前的觀眾。
當時她只有幾千粉絲,這期影片播放量卻突破了60萬。從此,關注MT的粉絲數開始呈指數級增長。不過一年時間,關注她的粉絲就達到了10萬。

MT扮演一對雙胞胎

幾乎是一夜之間,ASMR從爆款,淪為禁詞。
2017年,直播行業興起。在流量的裹挾下,不少人藉助ASMR做擦邊直播,讓這個原本純粹的圈子蒙上陰影。
雖然ASMR的本意與性無關,但很長一段時間,它和軟色情被劃上等號。這也讓很多認真創作的ASMR創作者遭受了意想不到的重創,MT也不例外。
那一年,除了做影片,MT也開始做直播。由於節目節奏舒緩,她常常從晚上九點開始直播,連續播四個小時,下播時已是深夜一兩點。
作為哄人入睡的人,MT卻因此常常失眠。
“上班的同時,還要直播,超級累。”MT稱。直播4個小時,她始終是緊繃的狀態,不能隨心所欲說話,還要時刻注意身邊的一切音量。
這種緊繃感導致她有時勉強睡著後,夢裡居然還在直播。有時閉眼沒多久就天亮了,要準備去上班。

直播間的MT
強撐半年後,MT實在吃不消,她不顧父母反對,辭去石油行業一家國企的文職工作,成為全職ASMR主播。
對她來說,下定決心脫離既定軌道,並不算難。“我物慾不算強,比起這種朝九晚五的穩定,我更喜歡自由地做喜歡的事。”
她熱愛ASMR行業,但並不擅長直播。
性格內斂的她,早期拍攝露臉的影片時,不太敢直視鏡頭,眼神飄忽不定。為了克服鏡頭恐懼,她會把攝像頭想象成自己的閨蜜,“時間久了,那種尷尬的感覺也就麻木掉了。”MT稱。
但是,當題材偏向“男性向”時,比如服務男明星、為男顧客剃鬚,她還是會很不自在,所以她的影片題材多為“女性向”。
這樣的MT成了ASMR直播間裡少見的清流。
畢竟在許多平臺,ASMR的感官刺激迅速滑向“嬌喘聲”“吮吸聲”“舔耳聲”等內容,主播的鏡頭從臉部逐漸滑向胸部,衣服布料也越來越少。
一時之間,ASMR從一種聲音表達的藝術手法,變成一種牟取暴利的手段。
儘管聲音與色情的邊界變得模糊,但MT依然對ASMR保持敬畏之心,在直播間用聲音照顧孤獨的人,最高峰時有50萬人同時線上圍觀。
而MT的收入,則穩定在每月八千至一萬元之間。雖然不高,卻已遠超她在國企的兩千元工資,更重要的是,她終於自由地做著自己喜歡的事。
MT的直播生涯只維持了一年時間。
那段時間,一些影片網站的ASMR直播不允許露出麥克風,也不讓博主小聲說話,甚至搜ASMR標籤,只能搜出一片空白。
MT這樣正常的直播間也被平臺“一刀切”,賬號和作品被限流,沒有播放量。
創作環境驟變,很多ASMR博主黯然離場。有人感慨地表示:“ASMR在中國淪為了浮躁人心的廉價產物”。
但MT沒有離開。她放棄直播,繼續專心做影片。無法使用“ASMR”這個關鍵詞,她就改成“助眠”“解壓”。儘管流量退潮,收益驟降,她依然堅定地紮根在這個圈子的核心。

談起當年的艱難處境,MT早已釋然。
她語氣平靜地說道:“要說多氣憤,也沒有。大家只是走的路不同。跳舞也可以擦邊,唱歌也可以擦邊,ASMR只是其中一種方式。”
她說得輕描淡寫,那些早已轉向其他賽道的人已無影無蹤,只有她還在,低聲細語地陪伴一個個失眠的夜晚。
MT的堅持,後來也逐漸被父母所理解。她不必再躲著錄製影片,有了一間7平米的小工作室,專門用於打造一片脫離現實的ASMR世界。
為了構建這個複雜的世界,她傾盡積蓄購置道具和裝置,有時要花好幾月時間,才能買到她需要的東西。
為了推敲臺本的一句臺詞,她會不計成本地大量閱讀與調研。為了找到最適合的發音節奏,會反覆試音。有時因為沒有靈感,甚至還會失眠,生物鐘完全錯亂。
在一期扮演牙醫的ASMR影片中,她為了讓聽眾更有沉浸感,花了一個月時間蒐集醫療道具,甚至去請教當牙醫的粉絲,學習專業知識。
每一聲器械的碰撞、每一句問診的語氣,都被她小心翼翼地打磨。
在這個聲音越來越嘈雜的時代,總有人願意陪伴那些被忽視的孤獨。她聲音很輕、很小,但她的堅持,比誰都清晰。

拍攝故事向視頻MT要準備大量工具

十年過去,中國已經有5億人睡不著。
據中國睡眠研究會發布的《2025年中國睡眠健康調查報告》統計,一半以上“00後”和將近一半“90後”熬夜至零點以後。此外,睡前經常使用電子產品的人,睡眠困擾率高達51.5%。
助眠需求的激增,也催生了睡眠經濟,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哄睡師”,盲盒級50元/小時,花魁級包月28888元。
在這股熱潮下,ASMR重拾清白。
MT的B站粉絲數穩步增長至57.2萬。在這3650個深夜,她的影片和音訊滾動播千萬次,陪伴數百萬人從學生時代到步入職場,從“睡不著”到“我又來看MT媽媽了”。
但MT發現,很多粉絲從大學步入職場之後黏性就變低了。“可能因為他們工作忙,累得倒頭就睡,不再需要聽ASMR了。”她感慨道。
在鏡頭前撫慰入睡焦慮的MT,也有自己的焦慮。

不同於其他助眠服務的火熱,ASMR是一個稍顯鬆散的圈子,商業化程度不高,也難以變現。
另一方面,隨著短影片和直播業務的崛起,以中長影片為主的ASMR內容,能分到的蛋糕越來越小。
即便如此,MT也不願打破自己原則和底線,去直播,去帶貨。她依舊保持初心,深耕於播放時長超20分鐘、剪輯繁複、回報越來越低的ASMR中長影片。
收益直線下滑,創作卻愈發燒錢。近兩年為了維持內容質量,她把這些年的存款幾乎掏空,裝置、道具、場景一個都不省。

MT工作室的工具
雪上加霜的是,MT的愛人此前從事建築土木行業,由於近兩年行業變動,如今也待業在家。
資金最緊張的時候,向來報喜不報憂的MT,迫於無奈向父母借錢交了今年的醫保。
面對現實壓力,MT開始嘗試變通。她在B站開通包月充電專屬影片,粉絲可以透過內容付費這種實際的方式,表達對她的支援。但依舊杯水車薪。
如今34歲的MT開始覺得迷茫,“如果做不了ASMR,或者沒辦法繼續做這個了,之後我該怎麼辦?”平臺政策在變,受眾群體有限,自己也會老。
MT認識的一些同行也存在相同的煩惱,有的人迫於家庭壓力考公上岸,“他一下從家族地位最低的人,變成了地位最高的人。”她調侃道。
不過,MT還沒想好自己以後要做什麼,畢竟從24歲錄下第一條影片開始,她所有的時間、精力、熱情與技能,都被投注在這件事上。
“會有點迷茫。”MT低聲說。但她不會回頭看,不為過去的選擇後悔,隨即又篤定地說道,“當下最重要的事,還是把影片做好。”

比起生存焦慮,創作瓶頸才是真正讓MT頭疼的事情。
這十年,MT已經在B站投稿417個影片,幾乎每個影片的題材都不重樣,影片製作也越來越精良,最近的幾期影片甚至堪比一部部微電影。
但相比國外電影工業水準的ASMR團隊,人力和資金的不足限制了MT的創作高度。“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鋪一個綠幕,像他們那種能夠實景搭出來的場景,那是真的是做不到。”
除了愛人偶爾幫忙打打下手,比如搬運笨重的裝置和道具、充當模特,從撰寫臺本,準備服化道,到搭設場景,都是MT一個人操持,“我養不起團隊,這確實是沒辦法。”
儘管如此,她依然每天寫臺本、試音、搭景,哪怕熬夜到凌晨兩三點,她也窩在那間七平米的工作室裡,一遍遍聆聽耳麥中的回放,力求讓聽眾在耳語中沉入夢境。
與此同時,隨著各種影片大模型釋出,從切萬物演變為吃萬物,各種違背常理的獵奇向AI ASMR正佔據短影片平臺,大肆收割流量。
對於AI技術的強勢入場,MT一如既往得很樂觀。
她認為ASMR博主不會被AI ASMR替代。無論技術如何發展,“人的在場”始終是ASMR影片難以割捨的部分,那些人類共通的感受和經歷是AI無法復刻的。
在她看來,未來AI技術更為成熟時,哪怕沒有充足的人力和過硬的技術,她一個人或許也可以製作出電影工業級水準的影片。
或許,再過三十年,MT依舊在用聲音照顧我們。只不過,那時她已經不是“MT媽媽”,而是“MT奶奶”。
部分參考資料:
1、文藝研究|降噪世界中的耳語:ASMR亞文化與大眾文化中的聲音轉向
2、澎湃新聞|ASMR哄睡師,從愛好者到百萬粉絲博主
3、嗶哩嗶哩|在7平米小屋,她連續10年哄網友入睡
圖片來源:受訪者授權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