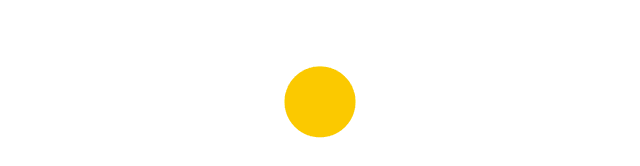從浙大,到美國,往香港,再歸重慶,
齊帆在近十年間,體驗了不同的角色。
他強調,建築人不能囿於自己的小圈子,
而是要跟上時代的脈搏,
用架構的理念來督促自己為城市的發展出一份力。
採訪人 | 李
編輯 |李, 藝夢
本期人物
Qi Fan |齊帆
幾里設計合夥人/設計總監

浙江大學 建築學學士
賓夕法尼亞大學 碩士
曾任職於美國SWA Group和香港大學建築學院學科導師,現為專注城市尺度綜合設計的獨立事務所JILI DESIGN幾里設計創始合夥人。
以下為正文
A=ArchiDogs
Fan=齊帆
A:你一直走著一條令人豔羨的人生之路,那浙大和賓大有著怎樣不同的求學體驗呢?在港大的教學體驗又帶來怎樣的收穫?
Fan:浙大教學體系是國內學派,在日常訓練裡,把各種尺度到型別都走一遍,浙大的建築學特色不在於學術深度有多深,而在於它像杭州這座城市一樣很開放,學習期間有機會參與到很多不同的專業裡,並認識不同系別的人,圈層的約束很小。
但它和美國的教育體系差異則非常大,本科期間習慣於一個學期做幾個studio,國外則是一個學期做一個專案,在不同區域挖掘不同深度。國外學習強度要大得多,讀研期間會越來越清晰地認識到自己的未來,該在什麼領域做什麼事,所以壓力會很大。但自己對專業抱有很大的興趣,研究生階段學習非常投入,也是對學科體系和價值觀理解最深刻的時候。
我在港大做教職期間,主要負責基礎教育工作,以及和內地大陸高校的連結。大一時是通識性教育,港大的公共基礎課程,主要涉及對城市、環境、人文的理解。而大三、大四的教育跟國內不太一樣,國內是拿著教材告訴你,城市劃分含哪些概念、考點是哪些;港大則更重視教育的互動,很有意思,理解城市的方法像研究生時代的方法,把城市剖析成交通、垃圾回收處理等不同方向,即細分到城市幾個大的不同的點。
一年級學生組隊會參與到不同課題裡,比如說你選的課題是城市垃圾回收,那就去研究城市有幾個垃圾回收點,這麼大個城市,垃圾是怎麼運作的,前半學期體驗城市,後半學期組隊後製定研究方法自己去調研。
A:也就是說實踐性更強,那港大建築學方面的教育又有怎樣的特色呢?
Fan:學科內的通識教育要細分一點,建築學院內部的通識教育就是研究城市空間、形態及結構。全校的通識教育,則是關注什麼是香港這個城市,從交通層面、水的層面、垃圾的層面去全面解構城市,怎樣去理解你所研究的這個方面,比如步行體系,郊野公園體系。研究生課程,更多的是組織studio課程,典型西方式的教育。香港更偏向於西方的教育體系,鼓勵學生去做presentation,不停去自我研究、挑戰和表達。對我而言啟發更大的是,香港不同層面的基礎性學科教育,以前只能管中窺豹,現在的兩年時間可以全職參與到裡面去,收穫挺大的。
A:畢業時應該面臨很多選擇吧,為什麼會獨獨挑選港大教職這份工作呢?
Fan:其實是對學術比較感興趣,想趁自己年輕的時候,去嘗試不同的職業。國外讀書、國外設計、國內設計院,不同城市生活的狀態是怎麼樣的,這些都是三十歲之前可以極致去體驗的。一開始對學術這個體系很感興趣,但不知道自己適不適合,想著國內讀博士,進高校,開自己的工作室這很安逸,這輩子就這麼定下來了,於是想去了解這個體系,同時也想去體驗香港的生活,接觸到獨特的教育體系。
A:的確是很棒的體驗,之後選擇回到家鄉重慶工作是出於什麼原因呢?
Fan:雖然我對教職工作很感興趣,但學校這個平臺成長很緩慢。作為一個有充分自我認知的年輕人,像建築這種實踐派學科,覺得自己沒必要全職在學校,更大的價值在於實踐和對社會做貢獻。學校像個象牙塔把自己保護得很好,每天相對比較形而上,而我的心很大,想在我想改變的地方,留下自己的印記。



魔幻而立體的城市
離開重慶十多年,之前對重慶的認知比較簡單,但作為重慶人,對重慶是有很強的情感的,跟重大、川美做學術交流時,察覺到這座城市在發生某種變化。我希望能為這座城市做某種貢獻,而不是簡單地說我想造三座房子出來,我希望帶來更多的資源,去影響它的進步,這會讓我更有價值。
而深圳、上海這些城市不需要我,那裡有大量的精英海歸,是頂級設計師的樂園。我從這些城市是去汲取它們的營養,而在重慶,我們是輸出,希望帶給重慶一些東西。回來時自己想為這座城市多做些事情,我們有很好的學術資源,構思著把學術作為一種價值帶入這種城市,所以就成立了幾里工作室。
A:學術方向和實踐方向都是致力於舊城更新中的各個尺度研究與實踐,那幾裡工作室也是專注於“城市更新”嗎?
Fan:一開始想做城市更新的,像成都是把重心更多地放在新區開發這一塊。但渝中半島,沒土地能做新區開發,只能做舊城更新,生活方式的更新,比如成都的太古里,是成為更有趣的業態而不是傳統的新區,高大上的尺度建築背後,對老城裡充滿了想象。
A:所以從太古里的業態中你獲得了怎樣的靈感呢?在專案整合和跨界思考後,又如何在實踐中嘗試自下而上的更新方式?
Fan:太古里更多是簡單的自上而下的業態,由非常有情懷和能力的地產商,買來做開放式街區。渝中區地很難拆,老城遷改成本很大,民間門面也極具商業價值,高度混合的建築群,不能說拆了做個低密度街區。所以借鑑自下而上的方式,社會的效率會更大,透過輕投入的景觀基礎設施、交通基礎設施,介入一些新元素的刺激來帶動整個區塊的成長,區域具備更大的商業價值和旅遊價值後,一定會有民間的資本和智慧介入。

遠洋太古里全景
比如太古里周圍,年輕人一看,有大量的旅遊經濟價值,那我也想來開個花店,洋氣的青年民宿,外區的更新便自然地自下而上。渝中區不見得有這樣的機會,介入一個太古里來帶動,但可以透過一些有意思的東西,來帶入城市的更新。相信只要這個地方匯入了很多人流和商業流,民間的資本一定會蜂擁而至。
如果本地居民租金提升,年輕人能開店,那便從城市的良性迴圈裡獲益了。現在要考慮的是,未來的更新怎麼讓大家都參與進來,政府投更少的錢,並且最大化刺激整個城市智慧的資本。
A:改造過程中,要找到異化、有歷史價值的東西,而不是簡單的仿古、做仿古建築街,城市需要獨特的印記和價值,這點如何做到?
Fan:重慶一定要用當代的思維去看城市,活在當下,這個時代對好的東西的追求,對美的追求,對好的空間和商業業態的追求,是我們要去滿足他們的。

錦裡街道

洪崖洞夜景
做錦裡的時候,是對城市文化一種很前衛的追求方式,仿古就是我們的方式。但現在我們的訴求,城市的眼界、格局、修養更進步了,這個年代不需要仿古了,錦裡、洪崖洞都是二十年前的東西了,那是上個年代城市主流人群的傾向,而現在我們看,90後的意識已經走到前面了,沒有舊的東西就展望未來,有舊的東西,就好好保護它。看70、80年代的老廠房覺得感動,那個年代的美學是這樣,存在就是合理的。
但今天再去修一個何必呢,2017年大家喜歡太古里,又何必再去造一個錦裡呢?比如今後大家又喜歡科技感,幻想未來,太古里同樣也就成了歷史建築。
A:哈佛GSD把重慶作為一個城市實驗室,你認為是什麼吸引他們來到這座充滿張力的城市,因為立體、魔幻嗎?
Fan:重慶是個多中心的城市,沒有絕對中心,而是透過橋樑隧道把各個區連在一起,每個商圈不會跨圈消費,每個區都有自己的shopping mall。而幾里的合夥人中有哈佛的博士,便考慮哈佛大學有沒有可能來重慶做個選題,做個studio,他們就很感興趣。



哈佛大學的同學們正在整理自己的成果
重慶作為建築學的範本城市,很有價值,很有意思,城市的地域具有多樣性,我們也希望透過引進學術資源,從而能開啟城市的維度。這座城市很立體、很獨特,城市老東西、新東西對比,地形跟城市建設的矛盾,交通的層次,這些點作為建築學研究的方向很有意思。
A: 透過學術課題的研究,對鵝嶺片區有怎樣的認識和改造呢?
Fan:鵝嶺山上有個老廠房,它的投資人和我們一起來做了活動,很有情懷的藝術商人。鵝嶺二廠我們區域性參與,但對整片山體和老舊居民區的未來也有個認識,透過哈佛的學術研究,找到有意思的點,更新出來是會很有國際維度和獨特性的,不是老舊的弄堂和衚衕,不是簡單的立面粉刷,而是透過獨特的點刺激城市的更新,形成重慶版山地居民的大片區。鵝嶺是渝中區最陡的地方,很有城市研究樣板的價值,希望用以點帶面,向外延展的方式來改變這個城區。


渝中半島

哈佛的同學做的分析維度的綜合模型

最魅力的地方:小區域中不同尺度的建築
更新過程中也遇到了很多問題,如投資強度、老建築的結構、周邊社群的居民關係,市政配套的不完善,處理地形地貌的難度,這都需要花精力去研究和應對,但從中也學到許多。
A:這次研究取得了怎樣的學術成果呢?而且你們有個更獨特的創舉,就是把學術活動開放給市民,從中有別樣的收穫嗎?
Fan: 學術效果很好,出書策展,對重慶而言,對學界、市民而言算一個思維維度的開啟,深圳有雙年展、本地活躍的學術圈層,重慶也需要提升自己的眼界、格局,學習怎麼跟世界對話,同時也讓世界認識我們。
至於開放給市民是覺得,學校對學校,城市建築學的教育模式有點封閉了。只是建築師之間對話,建築師和地產商對話,市民會不瞭解這個專業。建築學從沒想過去做國民美學教育,去引導市民,可他們未來也許會影響你的決策,希望城市小而美的,都是來自於市民組成的個體,但他們對專業的認知有多少呢。市民或許接受仿古,但沒接受到當代最先鋒的思想潮,只有當代的東西才能讓我們的商業和城市空間持久生存下去,我們需要傳達這種觀念和審美理念。
A:幾里工作室最近有一個比較有意思的專案“混沌星球”,可以簡要介紹一下嗎?
Fan:是老工廠加一個混凝土的入口的建築,混沌目前為現在國內最大的網際網路知識分享社群,線上線下社群,裡面是學術的分享空間,偏科技和創業類的。


混沌星球1687實景照片
我們希望把它建造得有儀式感和精神感,像教堂般,象徵重慶新時代的知識堡壘。


知識分享空間
A:作為建築師,你喜歡徒步旅行,這樣的過程會給建築設計帶來靈感和啟發嗎?
Fan:對一個城市旅行,要徒步,才會有完整的感知。拿著地圖走,可以丈量出城市的尺度,曼谷半小時只能走一點,而在吉隆坡半小時卻走了很遠,東京核心區從東到西走一遍,腦子裡很熟悉這座城市怎麼樣,坐地鐵不會有這樣的感覺。而且我對城市比較敏感,不經意會看到很多小東西,很有趣的空間、咖啡店、畫廊。又比如重慶,a、b兩點之間會有十幾種不同的路徑,徒步可以感受不同的空間城市。
A:幾里設計今後的發展規劃是什麼呢?
Fan: 創業要懂10個緯度的事,而不是一個緯度的。當老闆和打工是不同的,你要多方考慮,如刺激員工積極性,收款,稅務,人際關係的處理等等。
未來想走得更有意思,去擁抱一些新的業態。建築師要跨界,建築師在網際網路,IT界也有architect這個詞,是構架師的意思,現如今走到現在小眾的衚衕裡,建築有些孤芳自賞,我們很美,但不能參與到社會更深層次的分工。未來我們需要把自己定義成一個構架師,去整合城市產業裡的構架,既能做設計,也能構架未來的城市更新需要的功能空間,而不只是做美的設計,希望能連結到學術的思考。
A:最後,對於現在年輕的建築師,包括在學校的學生,可以給一些具體的建議麼?
Fan:建築師不能封閉自己,認為你的職業發展途徑就那幾種,地產公司、事務所、設計院等。未來社會是在顛覆性的進步,建築師如果不主動地走出去,只是個設計師,這很被動。在學校裡,不要只跟建築師玩,玩一些很形而上的東西,要學會多跟網際網路、藝術、工程、經濟的同學溝通,很多行業是很開放的。
經濟學很開放,建築學很封閉,儘量多連結,因為我們是建構師,需要了解每個行業的發展,建築走在前面去整合別人的行業資源,最後形成新的可能性。談逼格的建築理論,只會玩形而上的雙年展,只跟建築圈層對話,這樣略顯狹隘,未來是建築和科技跨界的趨勢,所以我們要有更開放的心態。
採訪人 | 李
編輯 | 李, 藝夢
版權宣告
版權歸作者所有,如需轉載請聯絡ArchiDogs或作者獲得授權
THE END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