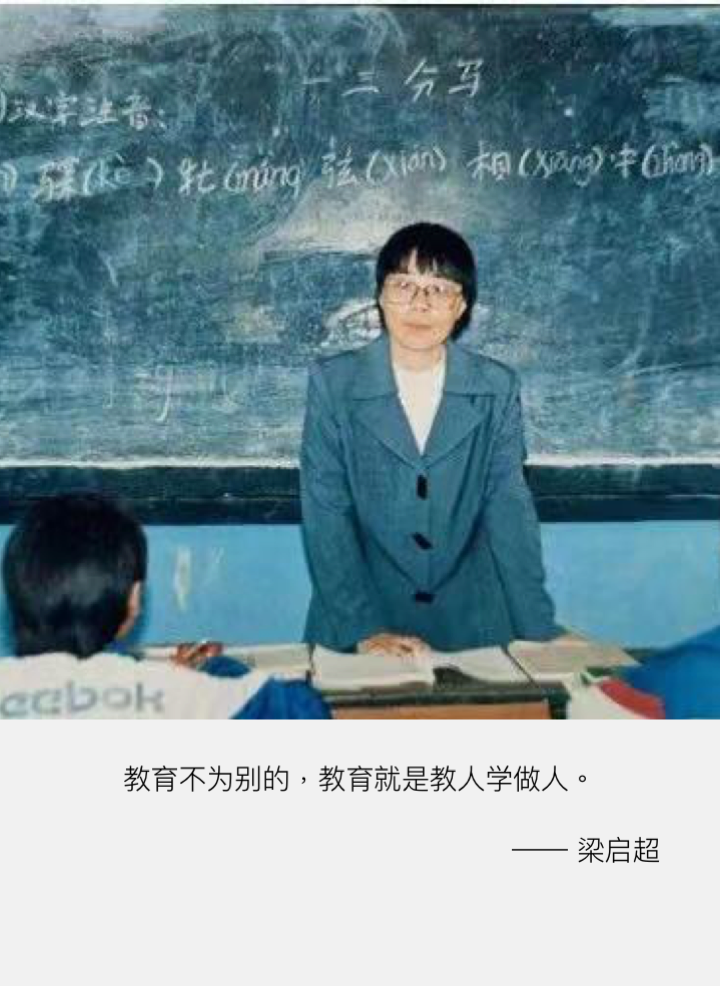【導讀】近日,上海電視節白玉蘭獎頒獎典禮上,電視劇《山花爛漫時》獲得最佳女主角和最佳導演兩項大獎,再度引起關注。在“主旋律”劇作屢陷刻板與沉重窠臼的當下,《山花爛漫時》以一種意想不到的方式照進現實:它不歌頌苦難,而以喜劇筆觸寫就信仰;它不神化典型人物,而是讓“七一勳章”獲得者張桂梅成為一個有淚有笑、既聰慧又狡黠的真實女性。本文是編劇袁子彈的創作談,從人物立意、劇情鋪陳到價值追求,層層解析這部電視劇為何能在人們早已熟悉的故事中,再次擊中情感的共鳴點。
這不是一個關於犧牲的敘述,而是一個關於“高階快樂”的構建:她不是苦情女主,而是“麻辣教師”;不是悲情英模,而是一個在荒山野嶺中,仍能帶閨蜜家訪、講粗口、為一頓肉笑出聲的生活家。編劇以“人活在環境與關係中”的視角,細緻鋪陳張老師身邊的生態與人物群像,從閨蜜、教師到政府官員,從“穀雨”們的成長曲線到“鐵三角”政治生態,用煙火氣勾連出理想主義紮實的根基。
創作談中最打動人的,並非張老師的“偉岸”,而是她與眾人一同“在路上”的姿態。在這裡,95%的平庸與5%的閃光被公允書寫,每一個小人物的努力,構築起女校得以成立的真正脈絡。《山花爛漫時》不是對個人的頂禮膜拜,而是對一種共同價值的回應與禮讚。
這是一部不偷懶的作品,也是一份在創作中不斷追問“真實是何”的手記。如作者所言:“了不起的從來不是苦難本身,而是苦難中的拼搏與堅守。”在這個意義上,《山花爛漫時》的真正主角,正是那一朵朵在貧瘠之地倔強綻放的山花。她們不求奪目,但願爛漫。
電視劇《山花爛漫時》得到觀眾喜愛,也得到一些研究者肯定。作為編劇,我很高興,也有些感慨,就想借這個機會說說心裡話。
▍主旨的建立:高階快樂,而非苦中作樂
《山花爛漫時》是“命題作文”,而且可以稱得上“命題作文”中最“死亡”的那種,原型影響力極大,地位非常高,而且在電視劇創作之前,已經被各種媒體報道過,大家心目中都有一個既定的張桂梅老師形象,這意味著想要打動觀眾,需要的情感閾值更高了。
所以製片人李行找到我,說想做電視劇的時候,雖然我本能地感興趣,且對張桂梅老師充滿好感,但我第一時間想的是怎麼推掉這個活,因為普通觀眾已經對張老師有了固定認知,各種優秀的新聞團隊都在跟拍和採訪張老師,很多人認為有新聞和紀錄片就夠了,還有必要寫電視劇嗎?但李行再三跟我說,張老師沒有你想的那麼可怕,那麼板正,是個很有趣的人。她講到張老師去家訪的故事,當時很多學生住在山上,路還沒修好。張老師去家訪時經常帶著她的閨蜜,僱一輛摩托車載著她上山。因為雲南的山區大多是九轉十八彎,看著房子在那裡,開著開著房子就不見了,來一陣雲或霧,路就沒了,她們就無奈地停下來聊天,聊完準備走人了,雲霧散了,天又開了,房子又出現了,就又騎著摩托一路前去。這個形象一下子就打動了我,因為特別鮮活。我在媒體給到我的,一個充滿犧牲精神的、艱苦的張老師之外,看到了她的笑聲、她的閨蜜,看到了她家訪路上真實遇到的事,以及她是如何解決的,這些一瞬間就擊中了我。
我跟李行說,聽起來張老師並不是一個艱苦的形象,而是一個快樂的形象,是一個真正投身自己熱愛的事業的人應有的狀態,我說,咱們為什麼不能把她寫成“麻辣教師”呢?國外有那麼多非常熱烈非常燃的青春作品,為什麼我們一寫到這類題材,一寫到老師,就是“蠟炬成灰淚始幹”?咱能不能寫點愉快的、勵志的,把青春該有的“燃”給帶出來?我相信好的老師心裡面是有一把火的。而且我看了很多張老師的報道,比起敘述張老師有多少種病,她多麼艱苦,我更關心她要做成這件事該有多難。一所學校平地而起,還是免費的,我忍不住問自己,地從哪來?錢從哪來?怎麼招的人?誰批的編制?為什麼可以招生?為什麼每個年級只招100個學生,而不是300個?我管一個孩子都那麼難,這個人卻帶大了成百上千個孩子,把她們都送進了大學。從這些困擾我的問題裡,我意識到這不是一個光靠犧牲就能成就的人,相反,這應該是一個非常強大的人。
寫張老師離不開一個難字,這個難我們迴避不了,這是這個人物、這個故事自帶的。但我特別希望她是強大的、有趣的,而不是被動承受的。犧牲不是她最偉大的價值,人到了無可奈何時都可以犧牲,但靠著犧牲和承受就可以成為張老師這樣的人嗎?不可能!犧牲背後肯定有跟別人不一樣的東西,正是這個東西促使我想要完成這個創作。

2024 年底,《山花爛漫時》播出後,袁子彈到雲南麗江華坪女子高階中學參加思政大講堂的電視劇專場“微光的力量”,與張桂梅老師合影
帶著這些問題,我很快去了華坪。大家聽到麗江華坪可能會跟我一樣,誤以為它離麗江很近,其實它跟哪裡都不近。我早上六點多從北京出發,飛到昆明,又坐了六個多小時的車,將近晚上十點才到華坪。為了讓我保持狀態,片方很貼心地租了一輛非常好的車,有一個星空頂,非常漂亮,但六個小時下來,星空頂都快給我看吐了。也正是這個經歷,讓我第一次對張老師肅然起敬,因為那時張老師已經全國聞名,是最有資格走出那個地方的人,但她依然選擇留在華坪。我想象她無數次前往麗江、昆明,為了幾塊錢去募捐,去找各種部門,前前後後努力了七八年,我想,這得是多麼強大而堅韌的人?得是什麼樣的理想主義者?我相信她一定沒有坐我這麼好的車,她是靠什麼堅持下來的?我的這次創作,其實是一個慢慢走進她、相信她,再到真正理解她的過程,因為剛去的時候,很多事我不懂,也不理解,我不知道支撐她的是什麼,但在創作的過程中,我慢慢摸到了屬於張老師的那個核。
我是第二天見到的張老師,張老師對採訪者有很多要求,比如不能奇裝異服、不能戴首飾、不能化妝等,因為她不希望我們的到來影響學生們的學習。因為張老師的堅持,我沒有采訪任何一個在校學生,這也讓我意識到她是真正關心學生、能從學生立場出發的老師,我對她的印象更好了。見她之前我很忑忑,因為我已經對她有了很多腦補,有了創作思路。很多時候新聞對於原型人物是賦魅的,見到原型之後,有可能大失所望,也有可能你對原型的理解跟本人大相徑庭,這些都會嚴重動搖創作者的信念。結果見到張老師讓我非常開心,因為她恰好就是我想象的樣子,非常聰明、有趣,狡黠又質樸。狡黠是指她充分知道她面對的是誰,她有溝通的智慧和解決問題的技巧,質樸是指她本質是真誠的。在整個採訪過程中,儘管病痛纏身,但張老師幾乎沒有停下來的時候。她時不時拿起喇叭吼兩句,多次停下來處理學校的問題,也會聊起她年輕時如何時髦、漂亮。我一下子就覺得屬於創作者的構想與眼前這個人合上了。同時她又賦予了這個人物更多喜劇色彩。她善談、幽默,說話帶著很多粗口,完全不是我們刻板印象裡的“主旋律”英模的樣子。她不沉重,甚至還有點搞笑,有點沒規沒矩,她跟學生邊界感非常弱,可以像朋友一樣聊天,和學生家長不那麼熟,也可以自然而然地嘮起嗑來。
也是從那一刻起,我確定我要寫一個喜劇,不僅因為我看到的張老師是這樣的,也是因為我的創作理念:張老師不是因為吃了最多苦而被表彰的,而是因為在苦難中表現得最強才被表彰的。所以我要透過苦寫她的強,沒有苦難,張老師所做的一切就顯露不出應有的價值,但我關注的不是苦難本身,而是苦難里長出的希望和勇氣,長出的那些頑強而堅韌的花。我們的劇名叫《山花爛漫時》,這個意向與創作思路是高度貼合的。山裡的小野花,不見得是最美麗的,不見得是最能佔據這個舞臺中心的,但它一定是生命力最頑強的。這種強首先表現在永遠有行動,永遠有方法。大家如果注意的話,就會發現劇中的張老師幾乎沒有停下過,她很少坐著討論一件事情,而是吃著飯、幹著活就把問題給解決了。我始終讓她處於一種不穩定和不停頓的狀態。這不光體現在演員的表演細節裡,也體現在劇情設計上,你會發現我從來沒有試圖給張老師蓋棺定論,沒有試圖給她和女校畫上一個句號。我們的戲完結在張老師拎著大喇叭訓斥學生浪費的場景上,這是一個完全生活化的場景,我們沒有試圖讓她停下來,讓她作為一個英雄被表彰,這是劇本立意上我覺得做得很好的地方,甚至是最好的地方。
除了永遠有行動、永遠有方法,我也極力去展現張老師樂觀積極的態度。我們希望讓大家覺得,當你為自己喜愛的事業奮鬥時,你不是吃苦,不是承受,不是犧牲,而是熱愛。發自內心的熱愛讓這件事情像遊戲一樣有趣,張老師為了自己鍾愛的事業不斷升級打怪並獲得成就感,這是一般人很難碰觸到的高階快樂。我們常常說現代人喜歡躺平,可張老師讓我久違地看到了,一個人為了自己的理想而奮鬥是一件多麼閃耀、快樂的事。張老師苦嗎?論生活條件肯定是苦的。但她是在吃苦嗎?我不認為。我覺得她是在享受。學生當然離不開她,但張老師更離不開學生們。她從學生這裡得到了一個理想主義者所能擁有的最高快樂,這也是我創作時極力想要傳遞的:能對抗疲憊、對抗人生瑣碎、對抗“躺平”心態的從來都不是名和利,而是找到你內心真正熱愛的東西。
唯樂觀與熱愛能成就偉業。在創作中,我一直刻意避免把張老師當成犧牲者,避免渲染苦難,而是極力去寫她的樂在其中,寫她的革命樂觀主義和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我希望把張老師那種豐沛的情感、昂揚的鬥志充分地傳遞給大家,讓一切艱難與困苦成為張老師偉大事業的磨刀石,讓苦難背後的人性成為整個敘事的主角。
▍人物的開掘:立體維度和英雄人物的A/B面
在核心人物的開掘上,為了打破書寫英模人物的慣性思維,我努力發掘人物的立體維度。談到張老師,大部分人的第一印象是英模、老師、“七一勳章獲得者”,那麼除了這些,還有沒有其他維度,是真實存在但人們還不瞭解、不熟悉的?比如作為母親的張老師。很多人不知道,張老師是當地兒童之家的院長,她給上百個孩子當了十幾年“張媽媽”。網上有人攻擊張老師,說她沒有母性,是因為自己沒有孩子,才鼓勵女孩子們專心讀書走出大山,這是完全不瞭解張老師才會說的話。比如張老師與她的閨蜜如何交往?一個英模,也需要有閨蜜在旁邊時不時嘮嗑、說話、吐槽嗎?比如張老師如何與當地官員打交道?在職場這個維度上,張老師怎麼搞定領導、團結同事,有哪些職場技巧?他們的關係有哪些變化?圍繞著這些,我設計了很多煙火味十足的日常,比如兒童之家每年過年的包餃子吃硬幣,比如張老師拿到置裝費,給孩子們買了一頓大肉,給人吃進醫院去了;比如她跟閨蜜方瓊剪頭髮、買衣服,一起看大象,教她怎麼打點領導、怎麼處理人情世故……
劇中張老師跟教育局長周善群、副縣長馬永強鐵三角的戲我非常喜歡。我經常把鐵三角的戲放在吃吃喝喝的場合,用食物拉近與觀眾的關係,而不是板著臉談事情、講道理。劇中有張老師送禮的情節,送禮送什麼、怎麼送,也都精心設計。張老師跑到縣政府大院去送禮,這個地點的選擇可以看出她並不擅長送禮,而甘蔗作為禮物更是既輕又真,非常符合張老師一貫的風格。包括鐵三角的最後一場戲,周善群要退休了,來找張老師聊天,清高文人的姿態完全放下來了,兩人從職場上下級蛻變為朋友關係,周善群最開始否定張桂梅,後來被她打動、說服,到這個時候真正成為朋友,因為他們是真正為同一個理想奮鬥的夥伴。
透過這些立體維度,我們發掘出了在所謂常規“英模張桂梅”這個主身份底下別的身份、別的屬性,而對這一部分張桂梅的描寫,讓我們得以夯實“主旋律”創作所要呈現的那個主身份,甚至為其提供理由和情感動因,讓劇中的張老師得以真正落地。可以說,這些平時不被注意的維度,恰恰是她英模這個主維度得以成立的原因。
常規英模劇的另一個問題,是習慣從已完成的角度去描繪人物,在英模的高度和既成事實面前,人物遭遇的困難變得不值一提,他的最終通關也變得毫無懸念。英模劇最常見的橋段是一群人圍著這件事發表各種議論,觀點有對有錯,然後核心人物出場,發表一通演說後,大家就被他折服了,就定下來執行了。但在創作過程中,我反覆問自己,這符合事實嗎?不符合。張老師提出要辦女校時,我採訪的幾乎所有物件都對我說,當時覺得她絕對搞不成,可以說,在張老師遇到的所有困難裡,最大的困難就是被懷疑,因為辦女校這件事,無論從哪個階段來看,都有成千上萬個辦不成的理由。可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張老師依然去做了,而且堅持不已,終於讓不可能的事變成了可能。
所以對我而言,比起大眾熟知的已辦學成功、榮譽加身的張老師,我要抓住的是那個最初的張老師,那個不被信任、不被認可、被各種質疑的張老師。女校不是天然就該成功的,女校的成功是張老師及身邊所有人竭盡全力的結果,缺少任何一環,事情都可能有著截然不同的結果。如果說英模敘事也有AB面,張老師的A面就是大家熟悉的:她是“七一勳章”獲得者,既有犧牲的豪情,又有作為教師的崇高責任感;她信仰強大,託舉起了許多女性走出大山的夢想……這是我們“主旋律”創作的應有之義,也是必須表達的。那麼這些重要嗎?重要,但遠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那些不被看見、不被熟知的英模的B面。哪些事情曾經讓英模跌進溝裡,差點成不了英模?哪些突發情況讓英模陷入絕境,差點半途而廢?我要尋找的是這些東西,因為面對困難的態度才是英模和普通人真正的分野:那些讓她猶豫、動搖、痛苦、彷徨的,才是最重要的部分,也是讓故事充滿懸念、讓大家感興趣、讓大家覺得英模不愧是英模的根源所在。
除了人物定位,現實題材電視劇裡怎麼處理主人公跟其他人的關係,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它的真實性和想要傳遞的核心價值。在張老師與其他人的相處上,我儘量採取平視視角,消解她的權威性,和她身份帶來的天然正確和威嚴感。在劇中,張老師無論跟學生也好、上司也好,都不卑不亢。她沒有等級性的觀念,眼中只有她要辦成的事和必須克服的困難;她不諂媚,也不爹味,從不高高在上地進行說教,同時又是團結的冠軍:她讓所有人為了同一個目標奔赴,證明了人是可以同頻共振,可以真正互相感染的。而所有這些,都最大程度地把張老師從“神”拉到人的範疇,讓她變得更可親近、更真實可信。
▍生態的營造:人是活在環境與關係裡的
在確定了張老師的人物基調之後,接下來要解決的,是如何營造她周邊的生態,這個生態,既指張老師所處的社會環境:貧困山區,路途遙遠,多民族混居,重男輕女,整體教育水平低;更指張老師所處的社會關係生態:她身邊有些什麼人,生活在怎樣的關係裡。圍繞這個思路,我把要設計的角色分成了幾大類:第一類是學校類的,有老師,有學生。老師們都是為什麼來到學校,又各自面臨什麼問題?學生寫幾代,都有怎麼樣的個性與困境?第二類是政府類的。張老師要建校,要批地,要搞編制,需要面對哪些部門?這些領導上到什麼層級?下到什麼層級?她的直屬領導是誰,分別與她是什麼關係?第三類是社會類的。張老師錢不夠要募捐,可能遇到誰?企業家,還有無數的普通人,怎麼去寫這個龐大的群體?還有學生家長們。他們從事什麼職業?當地有沒有扶貧脫貧建設?他們參與了什麼事情?在構建這個生態的過程中,我不光鎖定了我要寫的人物,也找到了整個劇本的敘事重心:我要寫的不是張老師從小到大的日常,而是她如何竭盡所能完成一個在外人看來不可能的任務。所以我從一開始就放棄了過多描寫她的丈夫,這不是我的重點。我選擇從建校寫起,讓周圍的生態能最大程度與張老師同頻共振;而結束的點則落在了張老師看大象遷徙這麼一件小事上。因為大象是母性氏族,象群有頭象,帶著小象,我覺得特別符合張老師當下的狀況:你不知道她走向何方,但是她始終在走向更好的地方,我想傳遞出充滿希望的在路上的概念。
關於寫不寫第二代學生,我和導演一度有過激烈的討論,因為第一代的戲已經寫到極致了,留給第二代的空間不多,導演擔心第二代很難超過第一代。但從社會生態的角度看,我覺得應該寫,因為張老師面臨的生態是不斷變化的,只有讓大家看到穀雨等人的迴歸,看到教育是可以反哺當地的,才能展現整個社會形態、意識和觀念的變化,從而讓故事形成邏輯上的閉環。教育絕非一載之功,張老師也不斷遇到新的問題,在辦學這件事上她並未獲得完全的成功,而是依然在路上。這個連貫性既是社會生態本身的連貫性,也是人物核心的連貫性。
我想以劇本第一集為例,說明為什麼生態的營造對於人物塑造至關重要。全劇開篇是方瓊拉肚子,張老師騎著摩托車離開。摩托車的選擇和旱廁的出現,非常符合南方山區的特色,快速交代了張老師所處的地理環境;然後是她的閨蜜拉肚子,人物關係出場。她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她會和閨蜜一起去家訪,這是一個非常親切的形象。她的閨蜜因為鬧肚子在旱廁裡出不來,這種情況下正常人會選擇等,她不是,她明明不擅長騎摩托車,卻騎上摩托車走了。這說明了什麼?說明張老師是個風風火火的人,她非常關心學生,她一刻也等不了,她要去救她。進村後張老師看到了自己曾經的學生,為了“追”兒子已經懷了四胎,能直觀看到當地重男輕女的程度,這也是穀雨的第一個參照系,讓觀眾看到,如果張老師沒有救她,她的人生可能會是什麼樣子。然後是穀雨為了三萬塊錢要把自己給賣了。這是張老師面臨的直接困境。在張老師與迎親隊伍對峙的同時,我設計了女瘋子的出場,她是農村裡隨處可見的被侮辱、被遺忘的女性代表,她只有一句臺詞:“不是我剋死的。”但透過這句臺詞,你不光能想象她的故事,更能看到在當地像這樣早嫁的、受困於婚姻的女性是非常普遍的,這是穀雨的另一個參照系。到這裡,我還擔心呈現得不夠,又設計了張老師的兩個本子,一本記錄著她手裡所有輟學的學生姓名與輟學理由,另一本是募捐的本子,記錄著何年何月誰捐了多少錢。這些對周邊生態的營造,不光讓觀眾看到了張老師面臨的問題是什麼,她面對的是什麼層級的困難,也看到了她的解決方案:她想辦一所免費的女子高中,且已經不是頭一次這麼想、這麼做了。有了這些鋪墊,張老師才能在半夜敲開教育局長周善群的大門,才能在黨代會上說出我有一個夢想那一番話。

2021—2022 年採風時,主創團隊在張桂梅老師一直擔任院長媽媽的兒童之家與她合影。參與者有製片方歆光影業集團總裁康捷(左一),以及製片人李行(左五)等
人不是孤立存在的,他必然活在某種環境與關係裡,他的行為與所處的生態息息相關。我們花大工夫去營造張老師周邊的生態,不光是因為這種生態是張老師成為張老師的原因,更是因為人物的互文為她之後的一切選擇、行動提供了理由和外部支撐。也只有充分呈現張老師所處的生態,觀眾才能對女校的難和張老師的強真正感同身受,才能理解建校的急迫性和必然性,真正沉浸到劇情裡去。
▍配角的打造:95%的平庸和5%的閃光
《山花爛漫時》是一個大女主戲,也是一個群像戲。因為張老師已經足夠高尚,已經承擔了太多理想主義的光芒,所以在其他人物的塑造上,我堅持找到屬於普通人的視角,而不是把他們寫成跟張老師一樣的理想主義者,或者天然的追隨者。我寫這部劇有一個最大的感受,對於普通人來說,通常95%的人生都是暗淡無光的,有著最普通的人性和最平庸的煩惱,只有5%是稱得上高光的瞬間。所以在除張老師以外的人物上,我極力尋找這種普通的人性和平庸的煩惱。比如基層幹部的代表馬永強和周善群。馬永強是一個有進取心的官員,我抓到他的第一句話是“副的,副的”,這是一個典型的公務對話,很能展示他的得意和油滑;而周善群清高,我抓到他的第一個點是茶杯,跟他這個人一樣,走到哪兒都端著,所以張老師薅走他,首先是薅走他的茶杯,這些細節是非常普通但又能讓人物充分成立的。馬永強前期一直都是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張老師想要說服他全力以赴建女校卻沒成功,最後給他薅到滑肉館。我設計了一個店主家的小姑娘,在他們說話的過程中,這個小姑娘始終進進出出,被她爸爸指揮著端酒端肉、加水添飯,她甚至沒有跟馬永強產生任何交流,馬永強卻突然答應了張桂梅的請求。為什麼?因為他看到了真實的困境。當這個問題沒有呈現在面前時,你可以計算得失,但這個瞬間就是那不普通的5%,是馬永強的人性閃光。同樣的,當開學遭遇暴雨,學生們無法趕來上課時,周善群也放下了他的清高和上下級規矩那一套,堅決站在了女校這一邊,讓馬永強不要再打官腔,不管想什麼辦法,都得把孩子們接出來。這場戲是他的人生高光,但除此之外,他也怕事,也想躲。我決不迴避這種躲。因為這才是普通人該有的想法和人性。
我們劇中有四個主要老師,我要做的,是從非常私人的角度,找到他們各自來女校的理由和人生閃光點。其中丁笑笑脫胎於我採風中採到的一句話,當時女校初創,剛來的老師們發現得睡在一個沒封頂的水泥筒子裡,去招一些還不存在的學生,大家都崩潰了。有個老師說:“天啊,張老師你這個學校不垮沒有道理。”張老師認為完蛋了,她肯定要走了,結果她又說:“反正你也幹不了多久,你幹多久,我就陪你多久吧。”這非常灑脫、達觀,我們抓住了這個點,設計了丁笑笑。她的困境不在於普通生活的困境,而是被認可、尋找自己道路的困境,所以什麼事她都覺得很開心,很酷,是真正為了快樂做這個事的。魏庭雲是典型的繼承了中國君子之風、有著職業榮譽感的女性,秋瑾、呂碧城興辦女學,是這樣的人物在感召著她,你可以看到她在故事裡面任勞任怨,甚至是自我激發的,不但自我激發,還激發愛慕者一起努力。戀愛腦姚小山,我給他設計了大量喜劇情節,我們讓他一時戀愛腦上頭就來了,後來得不到回應差點就走了,他和張老師互動,有那種喝醉了吐槽上司之後覺得丟人、不好意思見面的點,特別日常也特別有趣。還有少數民族贅婿陳四海,我給他找了兩個點:一是他是官迷,人家覺得累、嫌麻煩的工作,他歡歡喜喜就來了,因為是個正經主任;二是少數民族這個點,不光顯示了雲南是中國少數民族最多的省份,做了一定文化宣傳,讓大家進一步感覺到了當地的生態,也跟常見的重男輕女形成對比。你認為正確的事情,在另一個社會制度下就是不正確的,女性不是天然就該承擔勞役的。到底應該選擇事業還是家庭?我很開心能在一個男性身上討論這個經典話題。
包括離開的老師蔡虹,我們沒有對她做任何批判,而是真實地呈現了她,甚至讓她質問了張桂梅,讓張老師無話可說。為什麼這麼設計?因為我真的很想說,做不到像張老師那麼高尚很羞恥嗎?不羞恥,這就是普通人的想法,她說得沒錯呀,我們努力學習不是為了搞一份錢多事少的工作嗎?英雄固然偉大,當普通人錯了嗎?沒錯,普通人才是大多數,也正因為如此,才襯托出英模的偉大。我就是希望讓大家看到,生活可以有不同的樣子,大部分人選擇了普通的、平庸的生活,選擇了錢多事少,少部分人燃燒了自己,走向了更光輝、更英雄、更了不起的道路,這就是生活的真實。
包括“四朵金花”,她們對應著不同的問題:穀雨敏感,高度自尊,她的困境是完全被物化、忽視,被家庭拿來換錢;蔡桂芝遭遇家庭暴力,她需要挺身而出保護母親,同時面對著因病返貧的窘境;寧華則是被當作男孩養大,缺失了對社會性別身份的認同;柳細鶯甚至把苦難看作理所當然,看不到生活的其他可能……對這些人物現實困境的展示,不僅讓這些女孩顯得鮮活動人,也展露了張老師性格的不同側面,讓人意識到,女校的成功絕非張老師的孤身奔赴,而是人與人之間互相感染、共振的結果。回過頭去看女校這件事,我一直覺得很神奇,因為這是每一個人帶著各自的目的、在裡面發揮了應有作用的結果。中間但凡有一個人沒有這樣做,比如說老師再走兩個,學校就辦不下去了;學生不自強,第一屆學生沒考上,後面撥款就沒了,生源也沒了,這完全可能。正因為無數普通人在其中發出了自己那5%的微光,女校這件事才得以成立,而不是張老師像太陽一樣,一個人孤懸在上。我要寫的不是太陽的誕生,而是一個星系。我們當然有著太陽這樣能量巨大的星星,但旁邊的星星也一樣重要、一樣璀璨。
▍不偷懶的創作:守正與出奇並不矛盾
透過這次創作,我還有一個重要體會,那就是守正和出奇並不矛盾。很多時候我們出於內心的傲慢,覺得這是重大題材,要傳遞的價值觀太多了,受的侷限太多了,就放鬆了自己在藝術上的要求,好像它天然獲得了一種豁免權,不好看是正常的。可事實呢?事實上這就是一種純粹的偷懶。比如說,認為“主旋律”題材就應該板著臉講故事,認為張老師這樣的人物就應該是嚴肅的、沉重的,這都是藝術的偷懶。
我舉一個例子。高考那場戲對全劇至關重要,在高考前,我們需要一場戲把情緒壓到極致,也需要給到孩子們一個釋放的空間。在創作時,我想她們能幹什麼?幾乎沒有經過任何思考,我腦海裡就出來了爬山、看日出、吶喊,好像當然就應該如此;第二個備選方案則是在操場裡跑圈,這已經成為一種思維定勢。可我反過來問自己,這群女孩子剛從山裡出來,是沒見過山呢,還是沒見過太陽?好不容易進到城裡讀書,在高考前最關鍵的時候花半天時間呼哧呼哧爬山,就為了看日出吶喊,這合理嗎?不合理。但很多戲就這樣拍了,甚至演員也不會覺得有問題,就這樣演了,因為站在都市人的視角,這確實能起到療愈心靈的效果,但放在這群學生上,這就是純純的偷懶。包括前面說的陳四海面臨的選擇,按慣性思路,他絕對應該選擇留下,因為辦學校是多麼偉大的事,按照我們的主流敘事,這樣的事是永遠排在小家前面的。但我讓他扛完女校最難的那一段就回去了,因為作為家庭的一員,他憑什麼不承擔家庭責任?小家不重要嗎?走婚制度和少數民族的文化是擺設嗎?高尚一時也是高尚,能堅持到現在已經很了不起了。我的戲永遠應該跟著人物走,而不是進入主流創作的套路里。
長期創作的人很難擺脫套路,但至少在這個劇上,我不想偷懶,因為像張老師這樣了不起的人物,值得我們更認真地表達,不應該隨便把這個題材消耗掉。比如在張老師的建校動機上,我們能按西方的那套人物結構去解構我們這片土地上成長的人物嗎?不能,因為我們這片土地上就不成長西方式的英雄,中國的英模解決的從來都不只是個人問題,中國最小的社會單位是家,再往上是族,族上面是國,中國人一直是在這樣的體系裡面實現自我完成的。只從個人的角度出發,你是無法理解張老師的。所以要寫好張老師,你得打破內心的傲慢,得真正進入張老師,進入那些女孩子們,問問她們會不會去山上面吶喊,對於讀書這件事,她們是什麼感受。我採訪過一些已經畢業的學生,她們說我們就是苦學苦讀,我們心裡面比任何人都清楚這就是唯一的機會,不成就是死,就是回去嫁人,出去打工,就是這樣的命運。所以我後來想到了解壓大會,讓張老師帶著學生們自己罵自己,我甚至控制了時間,就一堂課的時間,因為孩子們宣洩完還得繼續苦學苦讀,這才是她們的生活真實,是她們的人物邏輯裡應該長出的東西。
對於我來說,這次創作與其說是想要出奇,不如說是在追求真實的過程中,我看到了事情跟我想象的有很大差別。我所認為的感動、我所認為的燃點,包括我所認為的痛苦,這並不是人物真實的感受和痛苦。所以我要做的,是捨棄傲慢,放棄那些並不真實的套路,比如常規的大女主很少歌頌愛情,但我沒有讓張老師鄙視她的愛情,不是斷情絕愛才能成為大女主。張老師回憶起她的亡夫,充滿了美好,她描述得非常坦然、幸福,為什麼要去迴避這一面?這一面會讓她的偉大打折扣嗎?不會。包括魏庭雲和姚小山的愛情,我沒讓它建立在曖昧、親親抱抱的小情小愛上,相反,我完全將它建立在了理想和信仰上,也許很難,但我們做到了,我們用最小的戲達成了最大的效果。

2025年1月在澳門,金鵝獎結束後,騰訊給《山花爛漫時》舉辦慶功宴,大家一起回顧創作歷程,既感慨萬千,又覺得很有意義
所以只要不偷懶,守正和出奇是可以同時達成的。守住價值觀,守住你應該表達的內容,這是“主旋律”創作的應有之義;而出奇,這個奇是戲劇的奇,更是生活的奇,人物真實的奇,是你要找到真正符合生活邏輯性,符合生活真實的那些細節來支撐你的人物,來讓她展現出跟別的英模人物不一樣的特點。我看英模劇最大的痛苦是他們全長一樣,人物調性全都一樣,既沉重,又正確、乏味。事實上,他們能做成這麼大的事業,多少證明他們是個性非常激烈和明確的人。一個個性模糊,沒有自我堅持、自我信念的人是不可能完成偉業的。那為什麼我們創作出來的英模人物會如此千篇一律?是我們的人物不夠牛嗎?不是的,這是創作要反思的問題,而不是人物要反思的問題。是我們在創作中偷了懶,浪費了真實土壤裡孕育出來的有力量的人物。
▍沒有反派,只有信仰的旗幟高揚
創作之初,我給劇本創作定下了幾個目標:一是絕對的真實性,二是充足的戲劇性,三是一定的社會性。寫張老師,不能只停留在故事的層面,它一定會涉及幾個繞不開的話題,一是貧窮,二是性別不平等,三是她的信仰和紅色教育。寫貧窮,我不光寫貧窮的成因,寫落後觀念對貧困地區的影響,也寫在政策和教育的扶持下,貧窮是如何一點點被改變的,所以在劇中可以看到路修通了,可以看到新建起的芒果園,可以看到穀雨們的迴歸,透過這些,你可以看到教育是如何改變當地的貧窮和愚昧。寫性別不平等,我不去強調兩性對立,而是努力表達了在生活中看到、感受到的種種女性困境,包括月經羞恥、酒桌文化、職場歧視、性騷擾等,展現了不同情境下的女性互助。我不希望立一個壞的男性角色作為靶子,把他打倒,女性就天然正確了,強大了,我要展現的是真正的女性困境,這種困境有時候甚至是在善意下達成的。比如公安局那場戲,非常有代表性,警察聽到穀雨在洗腳城上班,即使確認她是被性騷擾了,還是會說“小姑娘以後別去那種地方瞎攪和了”,這不是善意嗎?但背後深層的邏輯是什麼?是覺得她去了那種地方才會遭遇這些,這就是結構性的歧視。包括大家對女校的評判,怎麼現在還有專收女生的學校,這些真實的困境才是最需要被關注的。
我們的反派從來不是某個個體的人,而是千百年來根深蒂固的愚昧、貧窮和落後的宗法觀念。比起某些極端情況導致的特例,我希望更全面地展現出縣城乃至山區的整個生態:比起沒能力和無機會,更可怕的是對自身境況的不自知,以及對未來缺乏信念和希望,這就是張桂梅老師常常提到的“窮根”。這種精神上的貧窮遠比物質上的貧窮更頑固、更可怕。所以我塑造了農村隨處可見而又總是被忽視的“女瘋子”,小小年紀就為了拼男孩懷四胎的女學生,不堪家暴奮起反抗的辛欣媽媽,愛女兒卻把一切生活苦難遷怒於妻子的蔡桂芝爸爸,沒有惡意卻總是議論著寧華的爺爺奶奶們,以及下意識指責穀雨的派出所警察們……我希望透過這些觸角一樣的人物,將張老師畢生與之對抗的貧窮和落後觀念具象化地呈現在觀眾面前,也將教育是如何改變她們命運的過程如實地展現在觀眾面前,讓大家在關注這些的同時,也更理解張老師和女校在當下的社會意義:了不起的從來不是苦難本身,而是苦難中的拼搏與堅守,是打破桎梏、突圍而出的決心和勇氣。
此外,我選擇在劇中直面張老師的信仰,詳細解析她信仰的由來。梳理完張老師的前史,我們會發現這信仰不是無根之木、無源之水。在張老師人生的低谷期,是組織拉了她一把,是華坪質樸的山區女性讓她看到了人生的意義和責任。她要回報華坪。這也是我為什麼要保留阿麗這個人物的原因。同時,這種信仰又是接地氣的。女校經濟困難時,幫助她的是黨的幹部;條件艱苦,老師出走,留下來的基本都是黨員——張老師的個人經歷驅動她靠近信仰,信仰又反過來支撐、反哺,為她提供力量。在劇中,我寫了張老師在差點被奪走校長職務時在樓頂唱《紅梅贊》的情節。那是一個純粹的革命樂觀主義者才會有的行為。她想要改變山區女孩們命運的出發點非常純粹,因此,她能從信仰中汲取力量。她的生活和信仰不可分割。我也特別喜歡女校最艱難時刻,張老師生病,周善群接她回來那段戲。學生們在黑暗中點著蠟燭念《沁園春·長沙》,那是真正的青春飛揚,那是真正的信仰,那個信仰的流淌是充分自然的,念著念著一瞬間,燈突然亮起來,這時候,人物的信仰是從她生活裡結結實實長出來的,所以一點也不尷尬,相反,它是充分可信、動人的。
寫張老師這個戲,給我更大的觸動是,我以前一直以為改變世界是一個宏大命題,只有擁有很高社會地位和很大社會能量的人,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世界。我以前創作寫不到位,我會對自己說,不能怪我,因為它太難了,遇上不合理的事,不敢挺身而出時,我也總是對自己說,沒辦法,世界太大了,而我太渺小了。但張老師讓我看到,普通人能以什麼樣的方式去改善我們所在的世界。比起高高在上的同情和審判,我更希望《山花爛漫時》喚起的是對那些還在泥濘中掙扎的人的深深理解,是不卑不亢的關心和動容,是張老師“踹醒一個是一個”的、從微末做起的點滴努力。我希望透過這個劇的創作,以張老師和女校教師、學生們的精氣神去感染、影響當代的青年,讓觀眾感受到那種昂然勃發的生命力,讓他們意識到,理想依舊值得追逐——有善念、有善行、能堅持,我們每個人都能讓世界發生一點好的轉變。
編輯/魯方裕
本文原載《文藝理論與批評》2025年第3期。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絡版權方。

訂閱服務熱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