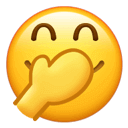2024年的雙十一,據國家郵政局網站和國家郵政局監測資料統計,全國郵政快遞企業共處理快遞包裹7.01億件。快遞已然成為我們每一個人日常生活裡不可或缺的存在,但似乎我們都不曾深入地瞭解在快遞領域的那些工作人員的工作日常。

2020年,22歲的牛童考取了攝影專業的碩士研究生,他45歲的母親,被工廠裁員,重新應聘成為一家快遞公司的分揀員。牛童開始拍攝母親身邊的快遞員的生活。
如今牛童已研究生畢業,成為一名老師。他翻出從2020年底到2023年初拍的這組照片,和編輯分享了他看到、拍到、體驗到的一種快遞員的人生。他至今都沒有覺得這個專案結束了。

媽媽有個城市夢
我的媽媽來自安徽宿州,她很早就離開家去南京打工。她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在工廠裡從事體力勞動。2020年時她被工廠裁員,於是去了快遞公司工作。
她的崗位是分揀,負責在城市的大型快遞集中中心,把每件快遞分揀對應的區和街道。媽媽工作特別認真,能找出很多錯件。老闆覺得她做得不錯,提拔她做了領班。

快遞員的流動性很強,很多時候大家並不在意社保和醫保的問題。媽媽主動提出需要繳納保險,公司給她交了社保。2022年,媽媽患了癌症,於是她辭了職開始治病。

和很多人一樣,媽媽選擇從安徽農村來到大城市,一是為了能有更高的收入,二是抱著有可能留在城市的夢想,即使是靠著辛苦的體力勞動。就這樣,媽媽在南京一做就是十幾二十年。
快遞員的孩子們
我主要拍攝的是江蘇、安徽地區的快遞行業,這裡面的快遞員大多來自於蘇北、皖北和西北地區,他們織起了一片同鄉網路。
我跟拍的快遞員們有著相似的畫像:他/她們的年齡在40至60歲之間,從老家來到城市之後,輾轉於不同的工作崗位上,但一直伴隨不變的是經濟和心理的雙重壓力。
這兩種壓力是捆綁存在的,快遞員的社會認同感不高,他們渴望窺見外界的精彩,在時間流逝下老去,也將這種夢想寄託於後輩身上。
他們努力掙錢,期望能給孩子更好的生活,讓孩子能擁有更好的教育環境,但這些孩子會因自己的家庭出身而產生巨大的心理落差,尤其是當他們成績很好時。這樣的落差,也會傳遞到父母身上。
我成長在南京,媽媽說:“我是獨自在出租屋裡看著天花板長大的。”
下面這張照片是一對母子,孩子的父母也是從事快遞行業。照片裡的背景是一家人在學校旁邊租的出租屋,這是個20平米的地下室,有一張床和衛生間。我的母親瞭解他家的情況,於是想讓我和這個處在青春期的男孩聊聊。

我在這個男孩身上看到了超乎同齡人的成熟,明明是個初中生的他有著成年人的身影。他喜歡瞭解政治,並且很清晰地規劃了自己未來想學的專業,他還想去當兵。他的學習成績很好,班主任說他未來肯定能考上211之類的學校。
在閒聊時,我們從歷史聊到了遊戲,從遊戲聊到了懵懂的青春。我能感受到他所承擔的家庭期望。在高強度的學習下,他把自己的需求壓抑的很低,把家裡以及學校的壓力都歸在了自己身上。男孩父親跑貨車運輸,時常在外。在和他父親的交談中我能感受到他對孩子的自豪。他父親曾對我說,希望孩子不要有壓力。但對於早熟的孩子和疲憊奔波的父母,他們都不知道該如何處理自己的情感和焦慮,他們對彼此的關心是錯位的。
很多現實,對於大人來說是一根刺,對於孩子可能就是一根棒子。

上面圖中的阿姨我很早就認識了,最開始她還在送外賣,獨自撫養著即將升學的孩子。她一般是晚上做夜單,中午和下午的時間給孩子做飯,她的孩子學習成績很好。
一年冬天的夜晚,下著雪,她送單到一個老小區,那裡不讓電瓶車進入,於是她拿著所有的單子一路小跑,不小心掉到了景觀池裡,她身上穿的棉襖都溼了。那天晚上她害怕訂單超時,忍著疼痛把單子都送完,回家後她哭得很難過,她的身體開始不太能受風。
後來她經朋友介紹,進入一家快遞公司做了快遞分揀員,她每天的工作雖然時間久但輕鬆一些,分揀時將快遞按區號分配好,再掃描入庫。新的工作不必讓她經歷風吹日曬,而且還能交社保。

我意識到,快遞業也為許多人提供了一種庇護。
比如快遞行業裡有個工作叫「劃大筆」,負責把分揀錯誤的單子分配到正確的地方。這樣的工作比送外賣要輕鬆。如果遇到品行良好的快遞站點承包商,每個月也可以有5000左右的收入。
如果說外賣員被關注和討論是因為被看見,快遞員更像是隱藏在演算法後面的人。

許多快遞站點是由個人承包的,也常發生承包商對待快遞員不公平的情況,這讓很多人就會選擇跳槽去別的快遞公司。當發生了意外情況造成站點缺少人員時,那個片區的快遞就會堆積,每件堆積的快遞都會按天罰錢,罰款額度累計到一定大時,承包商就有可能“爆雷”,還留在驛站的快遞員自然也拿不到該有的工資。
罰款機制也是快遞業繞不過的話題,而且罰款額度很高,特別是接到投訴時,要罰的金額相當於當天的工資。

“你從哪裡來?
要到哪裡去?”
媽媽做完癌症治療的手術之後和我說,想回鄉下靜養。我一開始不理解她為什麼要回去,家裡的生活水平、醫療甚至人際圈和城市有著很大差別。在和這些快遞員更多地相處之後,我覺得他們和媽媽都有一種鄉愁:他們懷念已經流逝的童年。
我覺得他們始終處於“中間的位置”:非城市,非農村。他們遊離於農村與城市,本地與外地,農民與工人之間。或許以一種返回的方式,他們能重新尋找自己的身份與情感的落點。於是我決定和這些快遞員一起回了他們在農村的老家。
下面這張照片裡是一對父女,爸爸在城裡做快遞配送員。他從十幾歲起就在城裡做油漆工,後來結識了一幫江湖朋友,這些讓他在城市裡獲得過“短暫的認同”,但這些關係曾經將他帶上迷途。

和他更多的交流後,我感受到他更想要身份的認同,於是返回了家鄉。
下圖這對60多歲的老夫妻,他們的兒子結婚時買了房,但後來因為各種原因而丟了工作。老兩口為了幫兒子,跟著老鄉從農村出來到城裡做快遞。在交流中,我能感覺到伯伯的淳樸和侷促,也能感受到他的焦慮,他面部和手部的抽搐不斷地透露出他的緊張。在工廠裡,老兩口默默地工作也很少和人交流。

後來我跟著伯伯回了老家,看到了他在田間熟練地打化肥的樣子,才明白這才是本屬於他的生活,去城市裡做快遞只不過是被現實推到那裡罷了。他們的兒子後來找到了工作,老兩口回到了縣城開始幫忙給兒子帶孩子。
下面這張照片中的爸爸在城裡做快遞員,他這次回家是為了給女兒辦入學手續。他請了一天假,過兩天就要趕回去。看到這位爸爸,我想到了我父母年輕時養育我的生活狀態,我也終於理解了媽媽為什麼想要回家。原來,感情都是滯後的。

“家鄉和城市之間,
好像永遠有一層霧隔著”
我在完成拍攝的過程中,也去做了分揀員。當時一個下午的時間,我掃描了1200多個件。

我給快遞員們拍照時都是用膠片相機拍攝的。
如果用數碼相機,快遞中心的人會擔心我把這些素材發到網上炒熱度。另一方面,大家會對鏡頭有恐懼感,但當我用大畫幅相機去拍的時候,大家反而覺得這是一種娛樂和休息。很多人小時候在照相館見過這種相機,但從來沒有真正地接觸過。
我總共拍了四五百張大畫幅照片。在開始這個專案時,我也處於壓力比較大的人生階段,攝影成為了我當時的情緒出口。我已經記不清一共拍了多少位快遞員,膠片拍攝不可控性很強,有些照片即使拍了但最後也無法成片,但我覺得這也是一種“緣分”。

快遞員在轉運中心的工作時間是輪班倒,有凌晨班,也有白天班。許多快遞員會在輪班間隙就近休息。

在不上班的時間裡,大部分快遞員會在宿舍躺著刷短影片,或者幾個人約著出門去踏青,幾乎不會有額外的消費。反而回到老家後,他們可以和同鄉約著打牌,聊城裡的見聞。

我也遇見過一位快遞員阿姨,她喜歡看書。還有一個叔叔說話也很有詩意,他問我在哪上學,我說在西安,他接下來說的一句話我至今還記得:“雖然我沒有去過西安,但用我的手,摸過了上海、北京、西安的快遞,這些指紋代替我去了中國的很多地方。”

我和另一個快遞員回老家時,他特意帶上了快遞員的制服。制服好像一個標籤,穿上它,他就是一個在城市裡工作的快遞員。
他帶我去了他小時候經常去玩的地方,這是附近村落裡的唯一一個山坡,他很懷念這樣的地方。那天霧濛濛的,在山坡上放眼望去可以看到許多人家的祖地。他無法前進,也無法後退回農村。不久之後,他就要回到有霧霾的城市上班。

在家鄉和城市之間,好像永遠都有一層霧隔著,他也不知道自己屬於哪裡。
就像他不知該如何面對迷茫和重複的恐懼,我也無法找到我的座標,感覺自己像是一個孤島。
但我在和快遞員們的接觸中確認了一點:我來自這裡,來自這樣的家庭,我不應該去迴避。

圖片/口述:牛童 編輯:yidan
運營:小石 監製:Alga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