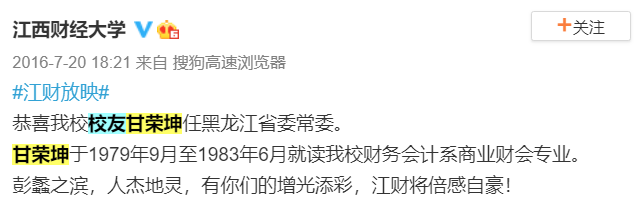100 年前,他們以為我們現在每天只要工作 3 小時。
文丨曾夢龍
編輯丨黃俊杰
“一個偉大社會必要的組成部分包括限制工作時間、提供收入保障。”
“一個人每天只需要工作 3-4 小時。”
“人應該隨自己的興趣今天干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從事畜牧,晚飯後從事批判。”
這些願望不來自社交網路,而是 100 多年前,分別源自哈耶克、凱恩斯、馬克思。他們基本不認同對方的主張,但都相信隨著生產力提升,社會將縮短工時、保障收入、增加閒暇,讓每個人都有機會發展自己所長,成為健全公民。
100 年後的今天,生產力達到並超越了他們的美好願望。每個製衣工一年能做的襯衣多了不止 20 倍、每個海員完成的貨運量提升 50 倍以上,平均每個發達國家農民的勞作已經可以餵飽 150 人。資訊科技的進步更是超出當年最狂野的想象——Apple Watch 裡的晶片可以在 10 秒內完成阿波羅計劃和曼哈頓工程裡所有人、所有計算機的全部計算。
生產力提升幾十倍沒有把人們的工作時間壓縮到每天 3 小時。科技與勤勞組合成了一些現代性 “奇蹟”:本週六,在很多城市名義最高氣溫 39 度的情況下,幾個外賣平臺動員數百萬勞動力,一天完成了至少 1.8 億個訂單;義烏商家現在只要花 1.1 元就能讓一件貨被人上門拿走,裝上大貨車開上一兩千公里,最後送到顧客手上。
按照官方數字,中國人平均每週工作 49 小時。在特定的行業,比如《晚點 LatePost》更關注的科技和網際網路領域,每月工作超過 240 小時是一些公司不成文的要求。
精神和身體壓力與勤勞相伴而至:免疫力下降讓許多人患上帶狀皰疹;甲狀腺結節、高血壓等疾病日漸高發和年輕化;猝死不再罕見,有父母看了新聞後,給在網際網路公司上班的孩子送了一臺應對心梗的 AED,並囑咐他要 “放在工位,這樣不但自己能用,同事也能用。” 令人發笑的自救辦法也因此誕生:淘寶上出現一種新的 USB 配件,插在電腦上就會模擬滑鼠和鍵盤操作——因為有公司監控員工每天的打字時長。
工作為什麼是這樣?工作可以是什麼樣?
2018 年夏天,王行坤(現任天津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去深圳三和人才市場調研。他發現在成為 “大神” 之前,這些南下打工的人進過不少廠,但是工作又累又枯燥,能不能拿到工資都是未知數。被中介欺騙或者社會毒打後,倦怠令他們放棄幻想,選擇日結工作,幹一天休息三天。
後來幾年,反思高度競爭和超長工作文化的實踐在中國社會出現,有了 “00 後整頓職場”, “996.ICU”,“數字遊民”,攜程三天辦公室兩天遠端的混合辦公方式,給員工漲薪水減工時的 “胖東來模式”。處在不同階段的美國也一樣,星巴克的員工排除層層阻力成立了工會,曾經是服務業模範僱主的舒爾茨被迫坐在國會聽證席上接受議員拷問。
以工作為中心、工作殖民生活的狀態是現代社會的產物,現在不斷遭遇挑戰。
2021 年,我們在轉折時點做過多個學者訪談,討論個體與公司、企業與環境的衝突。四年之後,問題的各方各面都變得更極致。工作是個中性的詞,有人真心享受自己的工作,但懷疑工作意義的人顯而易見大幅增長。我們可以給殘酷的競爭環境找到合理性,也相信長期來看,市場會回到某種平衡,但問題持續夠久就會產生不可逆轉的創傷,就像凱恩斯說的,“長期來看,我們都死了……只會在風暴中說等風暴過去,大海會再次平靜是沒有意義的。“
這幾年,中國、美國和歐盟這三大經濟體各自以不同方式響應反內卷、減少貧富不均的呼聲。反思為效率犧牲一切成了全球趨勢。本次我們對談的王行坤以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理解工作問題,完全站在個體福祉的立場。最近他在音訊平臺 “看理想” 更新完課程《反思現代工作:打工人如何尋獲自由》。

《“後工作” 理論》是王行坤主編的圖書,收錄了羅素、波蘭尼、薩林斯、弗洛姆等西方學者對當前工作制度的批判與反思。《對工作說不》是王行坤給《晚點 LatePost》讀者推薦進一步理解工作問題的新書。他說,這本書不僅有理論探討,還做了很多訪談,展示那些主動減少工作時間和主動退出工作的人的想法。
有學者認為,被工作所困是 “資本主義的本質”:讓人不斷產生慾望與需求,然後讓人透過消費滿足。這種經濟理性容不下既不生產,也不消費的閒暇。
王行坤覺得,這只是表面原因,根源是個人與企業的力量對比。因為從歷史看,“勞動時間是一個可變數”,8 小時工作制就是抗爭凝結出來的成果。作為一個左派學者,王行坤相信普通人的力量。他認為已經有了變化的訊號:全社會已經或多或少地意識到,工作世界處於巨大的危機之中。未來可以走向一個不以工作為中心的社會。
今年 5 月,《晚點 LatePost》與王行坤影片對談 3 個小時。有這麼一段令人印象深刻。他說,他認同羅素 1932 年在《閒散頌》寫的:“現代的生產方法為所有人提供鬆弛感和安全感的可能;但我們卻選擇了一些人工作過度、另一些人忍飢挨餓的命運。至今為止,我們仍然像在沒有機器的時候那樣忙忙碌碌;這無疑是愚蠢的,但我們沒有理由永遠愚蠢下去。”
以下是《晚點 LatePost》和王行坤的訪談節錄。
勤勞工作如何成為美德,懶惰又是不是一種權利?
晚點:你曾說,“現代社會是一個工作社會”。以工作為中心的現代社會是如何建構起來的?
王行坤:源於 “僱傭關係” 的出現。以前大部分人是農奴或者小農,要麼依附領主、提供勞役服務,要麼自己耕種,收穫產品,不存在僱傭關係,也不能隨處流動,不能隨意出賣自己的勞動力。
進入工業資本主義,現代人擁有了出賣自己勞動力的自由,在這個前提下,有了僱傭關係,就有了現代意義上的 “工作”。
晚點:出賣勞動力的 “自由”,是不是正如馬克思所說,“自由得一無所有”?
王行坤:是的,而且獲得這種 “自由” 的代價很大。對勞動力的改造是一個漫長而野蠻的過程。農民本來世代以來都在公共用地上放牧,15 世紀 “圈地運動” 出現後,新興資本家趕走農民,將公地變成養羊的牧場。被趕走的失地農民只能進入城市。進城之後,也不能當流浪漢,因為有各種法律懲罰流浪者,包括鞭刑、烙印、監禁,相當於逼農民進廠。
晚點:農民被逼進廠之後,要適應資本主義的時間觀念。“勤勞” 作為一種 “美德”,就被工廠制度發明出來了。你怎麼看待 “勤勞”?
王行坤:“勤勞” 本是一種工作倫理:努力工作,沒日沒夜地工作。它想達到的目的是,原本只需工作 8 小時,但資本家想讓工人工作 12 個小時,但只付 8 小時工錢。所以,在我看來,“勤勞” 是一種意識形態,是對過度勞動的合理化,目的就是讓打工人心甘情願地為老闆賣命。
晚點: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就寫過《懶惰權》,反思 “勤勞” 以工人階級美德的姿態出現。
王行坤:《懶惰權》寫於 1880 年。當時,歐洲工業革命已經完成,工人階級已經接受 “勤勞” 的觀念,拉法格把它稱為 “對勞動的狂熱”。拉法格警醒工人,不能中了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毒,要認識到勤勞的危害。
他覺得,勤勞會讓人的身體和智力退化。比如 1840 年,很多英國工人因為過勞,不到 40 歲就死掉了。又由於工作過於簡單,腦力得不到發展。他呼籲,工人階級應該懶惰下來。懶惰不是什麼都不幹,而是工時縮短、工資增加,拿到的錢要夠生活。多出來的時間也不是完全享樂,而是有意識地發展智力、能力。
有個點很有意思,拉法格說,有些民族是勤勞代表,其中就有中國人。當時很多中國人在歐洲是貧苦勞工,比較聽話、順從,沒有反抗意識,只想賺錢。
晚點:所以,1880 年勤勞就成中國人的標籤。
王行坤:但這個標籤也在變化。比如改革開放初期,城裡的下崗工人和剛進城的農民工進入港資、臺資和外資廠工作。不習慣資本主義勞動紀律和節奏,工廠主也曾抱怨中國人懶、不勤勞,沒有時間觀念。隨著他們逐漸適應,“勤勞” 的標籤又貼回來了。
所以 “勤勞” 是在一定製度下被塑造的。就像現在有中國人覺得非洲人懶,那是因為非洲人還沒被工廠完全規訓和改造。

王行坤在節目中提到,寫《過勞時代》的日本學者森岡孝二因為嚴重過勞,心臟病發作離世,令人唏噓。《職場媽媽生存報告》比較了瑞典、民主德國、聯邦德國、義大利、美國職場媽媽的工作和家庭平衡狀況,發現瑞典最好、美國最差。
晚點:你引用過兩個資料,放在一起看很好玩。一個來自國家統計局,2023 年全國企業就業人員每週工作 49 小時,說明中國人的確勤勞;一個是諮詢公司蓋洛普的調查,也是 2023 年,中國員工的敬業度(指打工人在工作時的歸屬感和熱情)只有 19%,而全球平均是 23%、美國是 33%。怎麼理解這兩組資料同時存在?
王行坤:說明很多企業都在使用疲勞戰術。人長時間過度工作,不可能還有歸屬感和熱情。減少工時,反而能調動打工人的積極性。比如一天工作 6 小時,人更能集中注意力,勞動生產率更高,也更喜歡這份工作。
上班人需要的自由,不僅僅是 8 小時工作制
晚點:100 年前,凱恩斯和羅素都曾提出,隨著生產力發展,人們會有更多閒暇,每天只需工作 3 小時或者 4 小時。在你的論述中,你說,“科技越來越進步,但人們卻越來越忙碌”。為什麼他們的預言沒有實現?
王行坤:比較複雜。有一派觀點認為,消費作為生產力紅利,替代了閒暇。因為人總有消費慾望,且永遠不能滿足。有人說它是廣告帶來的,也有人說它源自人的攀比心。消費慾望使人願意長時間工作。
但我覺得不是根本。因為勞動時間是一個可變數。取決於打工人和資本家的力量對比。當打工人組織化力量強大時,可以要求更少工時或者更高工資。在工業革命時期的英國,工人一週工作 6 天、每天 15 小時。經過不斷的集體抗爭,到 20 世紀初,實現一週 5 天、每天 8 小時工作制。1970 年代,新自由主義興起後,工人討價還價的力量變弱,待遇下降,工時不減反增。
在我看來,消費主義看起來是打工人的主動選擇,其實是被動選擇。因為他們沒有辦法降低工時,只能接受加班,然後透過消費給自己提供安慰。
晚點:最近這些年,由於貧富差距拉得過大,西方上班人的力量也有變強跡象,德國、法國等都在嘗試縮短工時。
王行坤:法國有些企業採用一週 35 小時工作制,德國工會呼籲一週工作 28 小時。雖然它們沒有大規模實現,但在嘗試縮減工時。每次媒體報道國外一週 4 天工作制等新聞時,國內都有很多評論,類似一週 4 天不敢想,能落實 5 天 8 小時就不錯了。
晚點:但減少加班能解決問題麼?
王行坤:工時只是一方面,像很多打工人是靠加班才能賺到足夠的錢活下去。所以減工時的同時要漲工資才行。現在很多工作不穩定、工作待遇和保障很差,政府應該提供更多福利托底,比如更普惠的醫療、教育、住房。雖然西方福利國家在解體,但相比之下,國民能被託底的待遇仍然比中國好很多。
晚點:這幾年有關 “工作” 問題的事件、現象和討論很多,你覺得大眾關心或擔憂之中,問題的關鍵是什麼?
王行坤:問題關鍵是,未來能不能回到過去那個充分就業的時代? 我覺得中西方都回不到以前了。現在的失業是結構性問題,很多人找不到工作不是沒有能力或者不想找。而是即使找到了,工作也不穩定或者待遇差。所以大家擔心和抱怨都變得很多。
晚點:失業率更高了是現實。企業也不可能無限增加工作機會。這種情況下,還有什麼破局辦法?
王行坤:我認為應該有一種新的分配製度,讓人不一定透過工作獲得收入,比如全民基本收入,每位合法公民都能按月領取一份錢。有了這份託底收入,人的生活態度會更積極,自信面對未來,更會願意工作。
晚點:可以想像,有人會反駁說,中國是發展中國家,要解決醫療、教育、住房、醫保、社保、農村養老金等福利問題,離全民基本收入還比較遠。
王行坤:我覺得不衝突,都可以有。
過去政府是投資基建,現在應該投資人。這也是政府的新說法。(注:2025 年《政府工作報告》稱,推動更多資金資源 “投資於人”、服務於民生。)投資於人其實就是投資與人相關的醫療、教育和養老等等,讓人們生活得到更全面的福利保障。這也能帶動生產率提高、產業升級,讓人敢去消費,可以提振內需、拉動經濟迴圈。人變好了,社會沒有道理變得不好。
晚點:你提到不穩定工作是現在的一個趨勢,而且低失業率是個假象,很多國家的就業都是不穩定工作。該如何理解這種狀況?
王行坤:一是在科技發展過程中,很多人被淘汰掉了。二是全世界都生產過剩,只能發展第三產業。但第三產業的高精尖工作很少,大部分工作都是低端服務業,待遇差、不穩定。
這是一個兩極化的普遍趨勢。一邊是大資本家、高階白領,一邊是底層的 “窮忙族”,中間階層越來越少。因為以前大部分中間階層是工人階級或者普通白領,但現在兩者都在被漸漸取代,導致大部分人都處在相對底層。
我覺得這是技術和生產關係共同造就的結果。因為技術發展可以讓人有更穩定的工作,也可以讓人有更不穩定的工作。這是一種制度設計。企業追求更多利潤,想降本增效,自然會減少員工數量,壓低員工工資,讓很多人處於不穩定狀態。
有工作不等於有發展空間,上班正在 “去技能化”
晚點:社會學家佈雷弗曼(Harry Braverman)在《勞動與壟斷資本》中提出 “去技能化” 理論。他認為,勞動過程出現 “管理者負責構想,勞動者只需執行” 的特徵,導致打工人技能水平退步。AI 出現後,很多人為此焦慮,感覺技能都沉澱給 AI 了,自己更沒什麼價值。你也表達過 “去技能化” 是個工作趨勢,那在當下的科技環境裡,有辦法對抗嗎?
王行坤:“去技能化” 最早討論是針對流水線上的藍領工人,現在人們發現,白領也一樣。網上流行一句話:“現在在格子間哼哧哼哧做 PPT 的人,和當年踩著縫紉機的女工們,其實沒有本質區別。”
“去技能化” 是資本主義追求利潤的必然結果。打工人的可替代性增強,人力成本就便宜了,管控難度也降低了。
如果要應對,個人層面只能努力多學點技能,但大部分人很難有精力做到。所以更重要的是改造生產關係,讓 “以利潤為本” 稍微偏向 “以人為本”。比如老闆適當注重人的技能發展,在生產過程中,讓勞動者能稍微參與思考和決策,和管理者相對更平等些。這是一種民主化的改造方式。
但是現在社會的工作裡,不平等越來越嚴重。有學者說掌握資料、演算法或者 AI 的人是 “雲封建領主”,普通人則是 “雲農奴”。“雲農奴” 在平臺上免費勞動,貢獻資料和生成內容;“雲領主” 抽取 “雲租金”;入駐平臺的商家則是 “雲佃農”,要給 “雲領主” 分成。最後整個社會如果變成極端不平等,肯定是有問題的。馬克思當年就預見到了人被機器(今天是 AI)取代的趨勢,但他的解法是公有制。改良的話,就是比爾·蓋茨等人提出的對機器人徵稅。

探討白領 “去技能化” 的著作《白領》和批判 “雲領主” 的作品《技術封建主義》。迪朗之外,希臘原財政部長瓦魯法基斯也寫過 “技術封建主義” 為主題的書 Technofeudalism: What Killed Capitalism 。
晚點:在現代社會,很多人會說自己是 “牛馬”,類似的,美國人會說 “薪奴”(Wage Slave),背後也是 “專制主義” 邏輯。對此,你怎麼看?
王行坤:這是一種帶有反抗意識的反諷。馬克思也使用過類似 “牛馬” 的詞語,叫 “役畜”(拉車的牛、馬、驢等)。他說,如果工人階級不知道反抗,只知道埋頭工作,那麼就會像役畜一樣。他想喚醒工人階級,讓他們敢於爭取和改變自己的地位。
類似的,1922 年,毛澤東、劉少奇在組織安源路礦工人罷工時,打出的口號就是 “從前是牛馬,現在要做人”。所以,認識到自己的 “牛馬” 地位有一定進步意義,關鍵是,認識之後,怎麼真正 “做人” 是個問題。
晚點:也有些人覺得,自己和老闆是契約關係或者交換關係,雙方本應平等。但你提到伊麗莎白·安德森的著作《私人政府:老闆如何主宰我們的生活(以及為什麼我們一言不發)》[Private Government:How Employers Rule Our Lives (and Why We Don't Talk about It)],說這種平等是虛妄。為什麼?
王行坤:對,安德森想揭示,老闆與員工看似是平等的契約關係,背後實際存在深刻的權力宰制。她將企業看作私人政府,老闆是獨裁者,可以在很多方面干涉員工。包括工作場所內,也包括工作場所外,比如社交媒體、回家之後。
所以這不是真正的平等。但平等並非不能爭取。雖然公司是老闆創立的,但員工創造了很多利益。在政府裡,公民有參政、議政的權利。類似的,在私人政府,也就是企業,員工也應該有說話的權利,可以追求工作場所的民主化。

哲學家安德森揭示員工和老闆權力關係的作品《私人政府》;普利策獎得主特克爾關於工作感受的口述史著作,裡面提到很多美國人都將工作看作一種對身體和精神的雙重暴力。
異化,無意義和找回積極自由
晚點:一些人會說自己被工作 “異化” 了。“異化” 這個概念來自馬克思,但現在用得比較泛,能不能正本清源講下?比如他在《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裡有段話挺精彩:“勞動為富人生產了奇蹟般的東西,但是為工人生產了赤貧。勞動生產了宮殿,但是給工人生產了棚舍。勞動生產了美,但是使工人變成畸形。勞動用機器代替了手工勞動,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蠻的勞動,並使另一部分工人變成機器。勞動生產了智慧,但是給工人生產了愚鈍和痴呆。”
王行坤:馬克思談 “異化” 主要分為 4 個層面:
第一,員工和自己生產的產品沒有關係,對它沒有任何話語權,只能從老闆那裡獲得一點報酬。這和以前的工匠不一樣。工匠可以選擇生產或者不生產某種產品。產品出售之後,利潤都歸工匠所有。
第二,老闆規定了勞動過程,員工沒有說 “不” 權利。很多人的異化感都來自於此:這個活我本來不想幹,或者對我沒有任何意義、沒有個人成就感,但我不得不幹。
這帶來了第三層異化。老闆和員工處於疏離或對抗關係;二是社會上人和人關係的異化。因為勞動者都要找工作,互相競爭,這樣就被割裂了,沒法團結起來。
最後一層是人和自己的異化。我想成為什麼和我實際的身份是分裂的。我對現在做的事情不滿意,對現在的自己不滿意,沒有辦法成為自己想成為的人。
晚點:現代工作給人帶來的倦怠或者無意義感挺普遍的。你覺得人們應該努力從工作中找意義,還是不應該對工作奢求太多,把意義放在生活裡?
王行坤:這是個見仁見智的問題。有的人覺得自己和工作是一種工具化關係:我付出勞動,賺到錢就可以了。但有些人無法承受工作的無意義,會感到精神痛苦。
很多人的身體和心理問題,其實都和工作相關,比如人在職場裡覺得壓抑、憋屈,或者被領導 PUA(精神控制)。這些影響都是實實在在的。
晚點:諮詢公司任仕達(Randstad)每年會發布《工作趨勢報告》。在 2025 年的報告中,“工作和生活平衡” 22 年來首次超越 “薪酬”,成為員工更重視的因素。近半數的人會因 “有毒” 工作環境而辭職,較去年上升 11%。48% 的人會拒絕與自己價值觀不符的工作,29% 的人曾因與領導觀點不合離職。中西方年輕人都有著更看重工作和生活平衡、職場環境和文化、工作意義的趨勢,和上一代人明顯不同。你怎麼理解這個全球趨勢的出現?
王行坤:環球同此涼熱,很多國家年輕人的工作比父母輩要差,工作變得不穩定,看不到希望,引發對工作的反思。以前在西方是為新教倫理努力工作,中國是勞動光榮、努力拼搏,但現在共同的趨勢是躺平。
中國網上有句流行語,“人生是曠野,不是軌道”。美國 2022 年也有個年度熱門詞彙,叫 “quiet quitting”,意思是 “在職躺平” 或者 “精神離職”。只幹份內的活,拒絕加班,放棄上進。最近 TikTok 上流行 “soft life”,類似中文的 “慢生活”,拒絕忙碌,發展興趣,愜意生活。
因為現實看不到希望,努力好像也沒啥用處,工作又太累了。不如索性停下來,關注自己。
晚點:那麼在這種 “工作危機” 下,你看到哪些解決可能?有看到實際案例麼?
王行坤:工作現狀有很多問題,需要解決。解決方案有兩種,一種是創造更多就業,讓所有人都有工作可做。但這種思路我覺得不可能實現,這是烏托邦。主要原因前面我們分析過了,可以補充的是,並非所有就業都是好的。有些工作沒必要存在,也對社會沒有好處,比如廣告、公關、服務有錢人的奢侈浪費或者 “打手” 需求。但那些真正造福社會的工作,比如環衛工,受到的尊重和待遇遠遠不夠。
第二種是改變分配製度。因為工作不多,就讓想工作的人去工作。沒有工作的人由於有全民基本收入,可以探索自己的興趣,做對社會有益的事情,比如藝術創作、問題鑽研。這比充分就業可能更現實。
晚點:也許有人認為你的想法太烏托邦了,不可行。
王行坤:可以給你舉個例子。舊金山一群環衛工透過搞合作社,改變了自己的工作。環衛工作自尊感比較低,社會也看不見他們。但由於合作入夥的方式,他們可以安排自己的工作,能做多樣化的業務,包括戶外清理、修理機器、參與合作社管理,上班時間也減少了。這些變化讓他們工作時更加自主,也提高了自尊感和工作滿意度。
這個例子對改造家政工也有啟發。現在很多家政工都是去別人家裡,但如果改造成公共服務,比如公共的託兒所、養老院、食堂,他們的成就感可能會提高,類似社工。
晚點:你的音訊課程的副標題是 “打工人如何尋獲自由”。怎麼尋獲?
王行坤:當時起標題的時候,編輯想的是 “打工人如何找回自由”。我說,打工人從來就沒自由過,怎麼 “找回” 呢?在馬克思看來,打工人是 “自由得一無所有”,處在一種相對奴隸的地位。所以最後副標題改成了 “尋獲” 自由。
以賽亞·伯林區分過 “消極自由” 和 “積極自由”。消極自由是不被幹涉的自由,積極自由是想做什麼的自由。積極自由在現代社會更稀缺,比如我是個窮人,沒錢唸書,想成為科學家,可能性很低。剛才我們討論了安德森,她倡導的也是積極自由。在企業裡,打工人要有話語權,要參與到企業決策裡,什麼事老闆和員工商量著來。
當然,打工人也需要消極自由。例如,下班之後,老闆最好別找員工。歐洲對此還有立法,叫 “斷網權”;老闆和員工要有邊界感,不能言語騷擾、性騷擾。但真正要尋獲自由,打工人得有一定力量保障之下。沒有力量,只能是一種虛假的自由。
晚點:在有保障之前,個人能做些什麼?
王行坤:個人也很重要。前段時間我有個師妹吐槽:她懷孕了,老闆問她,你怎麼偷偷摸摸懷孕,才上幾天班,來這生孩子啦,第三個了嗎?實際上是她第一次懷孕。她當時回懟道,咋啦,你不鼓勵生育啊?她說當時她氣得發汗,後來反思,覺得懟得不夠徹底。
所以很多時候,員工要有意識回懟老闆的不當言論,讓他們知道不能隨便說話,不能在言語或者行為上隨意侵犯。
題圖來源:Fight Club, 1999
– FIN –

《晚點 LatePost》推出週末版,希望把視線擴充套件到各種各樣的創造者。簡單來說,我們想知道誰在創造,並以之影響周邊;我們既注視當下,也回顧過去,尋找形塑今日世界的源頭;我們關注技術、商業,也關注歷史、人文,打量這些領域的交匯處的湧現。
讓我們關注的可能是一款產品、一家店鋪、一種包裝的設計思路,也可能是某種工作哲學、產品理念、管理方法,可能是一種有趣新穎的生活方式,甚至是在今天仍然煥發光彩的古老思想。
“已經創造出來的東西相比有待創造出來的東西,是微不足道的。” 這是維克多·雨果的話——我們希望《晚點》週末印證這句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