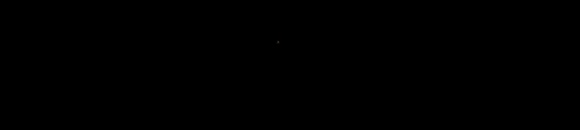華爾街,在這個以「美國金融中心」聞名於世的地方,向來是白人精英男性的競技場。
沒人料到,一位年輕華裔女生的創業事蹟,會成為一段傳奇,引來《華爾街日報》等多家知名報刊的報道:
20歲,頭也不回地從哈佛大學輟學;
22歲,登上《福布斯》「30位30歲以下人物」榜單;
28歲,已然成為管理著10億美金資產的公司領導人。
華裔女孩Eva shang的成功,沒有複製大眾印象中「借用移民實現精英教育,從而完成到精英階層改變」的路徑;
反而以「輟學」姿態狠狠打臉了這其中備受追捧的教育方式。
或許,教育的真正目的,從來就是幫持著一顆樹苗按照自己的軌跡長大,而非強行將它限制在一個世俗標準的模板裡。

Eva三歲時就跟隨著家人,背井離鄉遠赴美國。
父親早逝,妹妹患有肌肉萎縮,一家人的花銷都揹負在媽媽的身上,彼時媽媽只是靠一份精算師的工作賺取生活所需。

為了能減輕媽媽身上的負擔,Eva自小就幫著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務,照顧身體不便妹妹的責任也主動包攬下來。
好在Eva讀書上有天賦,高中就考進位於賓夕法尼亞州排名第二的公立高中。
大學更是進入哈佛大學,主修經濟學專業。
雖然此時她仍需要透過學生貸款來讀書,生活也並沒有因為考上名校而立馬迎來好轉。

對於大多數人來說,考進哈佛都意味著某種意義上的「成功人生入場券」,似乎自此便有了世俗認可,只待畢業便能走向另一種人生。
尤其是對於信奉精英教育的家長們來說,沒有比頂級名校哈佛更能驗證「教育成功」的地方。
但Eva卻並不這樣想。
她在剛入學時,也曾積極參加實習,暑假實習在華盛頓的一家辯護律師辦公室度過,夢想過畢業成為一名民權律師;
也嘗試過別的職業,還面試了哈佛為校友提供職業服務的諮詢公司。
然而實習期間的感受並不美好,現實給予的參考經驗也很殘酷。


當Eva在考慮未來道路時,發現自己可以選擇的那家民權律師事務所的薪資,甚至「不足以償還我的學生貸款」。
她意識到自己「不想成為精英階層的僕人」。
更重要的是,即使在學校裡,她也並不能夠適應「哈佛那種排外的社交俱樂部文化」。
如果要她強行擠進以西方文化認同為主流的社交圈,無疑是種痛苦。
精英聚集的名校標籤並不能為她帶來認同感,反而讓她覺得割裂:
周圍的環境在不斷地提醒我,我已經不再是年輕人,我需要在成年人的車道上競爭。
周圍的環境在不斷地提醒我,我已經不再是年輕人,我需要在成年人的車道上競爭。
讀完短短幾個學期後,Eva果斷選擇輟學。
儘管彼時她已經獲得了哈佛公共服務校長獎學金,儘管嚴格說來,她還是個高中學歷;
媽媽更是不贊同,堅持認為她工作兩年後就會重新回到哈佛。

然而Eva頭也不回地決定走自己的路,不去管別人的聲音。
和志同道合的同學Christian Haigh(也是輟學生)共同商議後,兩人一起在舊金山建立了公司Legalist。

公司創業的理念來自於Eva曾在律所實習時的感受:
司法系統對那些沒有錢請律師的人不利,強大的對手會用透過提議和證據,來折磨一家小公司。
這絕不是一個革命性的見解,但它讓我想做點什麼,訴訟金融是一個自然的延伸。
司法系統對那些沒有錢請律師的人不利,強大的對手會用透過提議和證據,來折磨一家小公司。
這絕不是一個革命性的見解,但它讓我想做點什麼,訴訟金融是一個自然的延伸。
她察覺到,雖然在官司中,勝訴可以拿到很可觀的賠款,但請律師打官司是需要一大筆支出的,很多處於相對弱勢的一方沒有經濟實力來承擔。
而Eva建立的這家公司,正是為了這些相對弱勢的群體。

事實上,這項創業無論從哪方面講都不容易。
2016年,雖然在Eva看來「訴訟融資市場會達到可觀的30億美元」,更廣闊的市場正在前方等著他們。
但當時的現實情況是,兩個輟學的學生,都沒有過任何創業經歷。
雖然因為這項大膽舉動,兩人成為哈佛的校園明星;
但在投資人眼裡,這份勇氣或者說衝動也不能作為加分項存在,就連Eva自己也清楚:
如果我是一個投資人,我也不會認真對待一個拿著電腦的20歲輟學生。
如果我是一個投資人,我也不會認真對待一個拿著電腦的20歲輟學生。

起初這種模式並不被人看好,Eva四處奔走拉投資,吃了許多閉門羹,但她從來沒有放棄。
好在,市場證明了Eva選擇賽道的眼光足夠前瞻。
Legalist獲得收益的思路很明確,向那些有極大勝訴可能的官司原告支援訴訟費用貸款,一旦贏得官司,Legalist將獲得25%-30%的利潤分成。
而如何判斷勝訴可能,則是藉助AI演算法。
熬過最初幾年後,Eva這種另闢蹊徑的AI資料分析方式,逐漸展現出明顯成效。

後來幾年裡,Legalist所幫助過的原告,涵蓋各大食品加工商、小型玩具企業等,所對抗的被告中甚至有美國政府,但案件80%都以勝訴告終。
2022年下半年,Eva已經籌集了超4億美元的資金,公司管理資產也足有6.65億美元。

©Legalist官網
在白人精英男性聚集的華爾街,這個華裔女生的名字已然成為傳奇,也勾起無數人的好奇:
一個輟學生,沒有接受過完整的本科教育,怎麼能在一眾精英中突出重圍?
或許答案就在她之前的經歷中。
中學時期,因為亞裔身份,Eva的學校生活充斥著歧視和排斥。
面對這種情況,Eva最先想到的是要和同樣遭遇這類狀況的人聯合起來,一起打破歧視。
於是她成為民權活動的領導者,勇敢為處於弱勢群體中的人發聲。
這些弱勢群體,也包括妹妹所處的殘障人士群體。
因為妹妹「為什麼玩具裡沒有代表殘疾兒童的娃娃」的疑問,Eva向玩具製造商請願,希望他們能夠製作一個專屬殘疾兒童的玩具娃娃。
這項網路請願活動最終獲得了超過14萬個支援簽名,也為Eva換來登上TED發聲的機會。

17歲的Eva選擇帶著妹妹一起登上TED,發表了《為什麼殘疾女孩很重要》的演講,呼籲大家能夠以同等目光對待殘障人士群體:
殘疾孩子可以改變世界,就像其他人一樣。
殘疾孩子可以改變世界,就像其他人一樣。
光是演講還不足夠,她還同妹妹一起出版了一本小說,名叫《Mia Lee is Wheeling Through Middle School》,在亞馬遜評分極高。

到這時候,已經有許多人注意到Eva所做的事。
《赫芬頓郵報》邀請她成為供稿作家,聯合國基金會「女孩向上運動」也讓她來擔當青少年顧問。
小小年紀就已經積極投身社會活動,在任何處境中敢於嘗試和破局,這些經歷才真正為她的未來開拓了無限的可能。

「哈佛輟學生」逆天改命的創業故事,我們不是第一次見到了。
不論是因為意識到計算機商業前景,選擇從哈佛輟學的微軟創始人比爾·蓋茨;
還是為了想專心研發Facebook,走上同一條道路的馬克·扎克伯格。

越來越多的例子,似乎在為精英教育和「學歷崇拜」去魅。
Eva並不是那種只是悶頭學習、視成績為一切的「乖小孩」,比起已經擁有什麼,她更在乎還能做到什麼?
忙於功課,也不忘在閒暇時間撰寫科幻小說;面臨不公,就勇敢站出來為所有相似遭遇的人發聲。
即便考上精英夢校,但只要想清楚也能果斷輟學;創業艱辛,仍不減少自己做志願者的機會。
想做什麼就勇敢去做,即使不被支援、一時看不到結果,也不會放棄,這樣的精神遠比代表成績的數字更珍貴。

對於Eva來說,從哈佛畢業是一條最常規、最不需要冒險的路,但卻不是她最想走的路;
只有一次的人生,她選擇跟隨自己的內心。
Eva的行動也改變了媽媽的想法:
我看到法律資料的潛力,它可以改變很多事情,也可以幫助很多打不起官司的人。
我看到法律資料的潛力,它可以改變很多事情,也可以幫助很多打不起官司的人。
這樣的精神同樣影響了坐在輪椅上長大的妹妹,如今也考入哈佛大學,活躍於各大公益活動,為殘疾人士勇敢發聲。

©《哈佛校報》
當然,Eva從輟學到創業成功只是個例,並非說只有透過這種方式才能成功。
而是或許有時候,主流所奉行的教育理念並非適合所有人,當確定已經找到更合適自己的道路,離經叛道的勇氣也應允許存在。
畢竟,「因材施教」才是教育的終極道路。
比起代表成績的數字,名牌大學的畢業證書,敢於設想、勇於實踐的行動力才是最珍貴、最難培養出來的特質吧。
▫
本文圖片來源網路
撰文丨姜姜
編輯丨qko
主編丨眠去
出品丨麥子熟了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