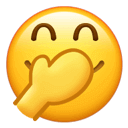最近,「精神內耗」這個詞彙頻繁出現在我們的視野中。
你是否也曾有過這樣的感受?在工作、學習或生活中,常常陷入自我否定的情緒,過於嚴格地要求自己,逐漸走入「糾結、較勁、反覆思考」的迴圈之中。人們在努力自我控制的過程中,往往需要消耗大量的心理資源,而當這些資源不足時,就會出現「內耗」的狀態。
偶爾經歷這種情況並不需要過於擔心,但如果這種狀態持續時間較長,就需要引起注意,因為它可能導致焦慮、抑鬱等負面情緒的產生。

因此,識別這些情緒,並做好心理調適,對於消除心中的「陰霾」、維持良好的心態至關重要。
10月10日是世界精神衛生日,這一節日旨在提高公眾對精神疾病的認識,分享科學有效的防治知識,消除公眾對精神疾病的偏見。

正值世界精神衛生日
故事FM與日慈公益基金會聯合釋出特別節目
邀請「心靈魔法學院」專案老師周婷
來講述心理學對她的滋養



在留守兒童的眼中,我看到了無盡的憂鬱


有的種子是會在很早的時候就種下的。我在縣幼兒園的時候,有一天,有一個孩子在數學課上做題做錯了——所謂的數學課是以玩耍的形式進行的。但那個孩子的反應,我可能這輩子都忘不了。我們發現他做錯了的時候,那個孩子馬上哇哇大哭,給了自己三個耳光。
我被嚇到了,我站在那裡不敢動。我當時心裡想:他們家的養育發生了什麼?——這個畫面至今都刻在我心裡。
那段時期同時發生了很多事情。因為要拆掉青少年活動中心,我就去了教管站(負責全縣基礎教育的部門)。去那之後一年的時間,我出現了很多次的內心對話:我喜歡什麼?我真的要在這個地方一直幹下去嗎?
那是 2018 年,與此同時我的婚姻也出現問題了。因為這些原因,我也才會去思考我要什麼樣的生活。2017 年的大年初七,我去了北京。那是我開始學習正面管教(一種家庭教育課程)的開始,從那時起接觸心理學。
後來我去局長辦公室,說我很想去學校上課。2018 年,我就去了現在這所江東小學。
這個學校在城郊。這些年整個教育系統都在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但這所學校因為城不城鄉不鄉,一直沒有得到太多關注,師資和資金投入都會被忽略。建校至今沒有舉行過一次運動會, 400 米的跑道都沒有。
雖然學校在城郊,但城裡的孩子肯定不願意去,家長在城裡務工的那些農民家的孩子,沒有辦法進到城裡的學校,就只能取其次來我們這兒。到目前為止,全校的學生當中只有一個是父母有正式工作單位的學生,就是我們副校長的孩子。其他的全部都來自務農的家庭。留守兒童佔到了 40 %到 50 %。
我來到這裡最初是上語文課,當語文老師的過程中,又學了非暴力溝通、積極心理學。我發現,我們這個學校如果這樣發展下去,絕對是一種惡性迴圈。

周婷學習非暴力溝通課程


試著牽著他們的手,走進他們的家庭


周婷決定開心理課的那一年是2021年。自那以後,她運用這些年所學的心理學知識為孩子們設計課程。然而,更為重要的是,她多次走下講臺,走進孩子們的生活,傾聽他們的心聲,以及那些塑造他們生命底色的農村家庭故事。
在這樣的留守學校,我覺得最普遍的一種現象就是缺愛,因為家長的關注不夠。
其中有一個孩子,長得挺帥的,我們稱它為「小易」。第一次接觸到他,是有一次,他的班主任哭得稀里嘩啦,到行政樓來說,剛才她被嚇死了,她班上有一個孩子差點跳樓了。
我就很好奇,為什麼會跳樓。她說,那個孩子犯錯了,她就批評了他,那個孩子就拼命地跑,她在後面追。孩子為了擺脫班主任的追趕,他就直接要往窗戶外面躍下去。老師一把就抓住他了,沒抓住的話,他就跳下去了,但他不是為了自殺,他是怕老師罵。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這個孩子的名字。
第二次接觸到他,是那個老師來告訴我這個孩子失蹤了,在學校找了很久都沒找到。我就開始在學校裡面找人,那天我正好穿了一雙高跟鞋,我腳很疼。找了兩圈也沒找到,我就打著赤腳,拎著鞋子,使勁喊他。
因為第一次接觸中,我沒有罵他,跟他聊了很久,他就跟我成了朋友。但我們也只接觸了一次,聯結不是那麼深,所以我喊他,他都沒有答應我。直到我的腳打出血泡來了,我就喊著說,「小易,週週老師的腳穿了雙高跟鞋,已經出血了。我很擔心你,要是你聽到的話,你出來好不好?我們聊一下,沒有問題的,我會保護你。」後來這個孩子從男廁所的最裡面出來了,就那個地方我沒去。

課間周婷與孩子們搞怪自拍
後來我就持續關注他,開始瞭解他的家庭。小易媽媽也是在他很小很小的時候就跑了,孩子從那一刻開始,就變得特別敏感。我又聽說他爸爸做生意,各種不順利,也就頹廢了,在家不幹活,就靠奶奶和爺爺務農養活著。
第三次是放假回來以後,我發現小易額頭上有一道疤,很長,大概三四釐米,我就跟他聊。因為從那以後我就經常會去看他,或者平時看到他,我都會叫他,會給他擁抱,告訴他我很喜歡他,遇到困難可以隨時來找我。
當新學期看到他額頭上的那道疤的時候,我就問他。他告訴我說,和爸爸發生衝突了,因為玩手機,情緒爆裂了以後,他就自己直接把頭往玻璃上撞,劃了一道口子。其實這樣的孩子被教導的都是用暴力去解決問題,情緒是很不穩定的,因為爸爸也是情緒來了就打他,沒有情緒的時候就溺愛。
這個孩子更讓我擔心的是,他經常被老師停課,停到教室外面。他也特別愛搗蛋嘛,所以老師也很煩躁。他每一次犯錯的時候,都會深深地埋著頭,像一個罪人一樣。因為從小老師就說他是個壞孩子,家長也說他是個壞孩子,這樣的一個「壞」字,每天不斷地在說他的時候,就像一把枷鎖,壓彎了孩子的腰。
我很心痛的是,我們沒有辦法改變家庭,也沒有辦法改變教育,我就總在想,學校的課程可以給孩子們帶來一些東西。
那個時候沒有教材,我自己在網上找一些素材給孩子們上課。但真的很苦惱,因為我是非科班出身,學的內容也是以家庭教育為主,對於孩子們的課程的系統性就不夠強。買來的教材呢,理論的東西比較多,孩子們喜歡的形式的東西比較少。但我還是覺得,上了總比不上好。

孩子們展示心理課成果


與日慈結緣


給孩子們上了一年用自己收集的素材串起來的心理課之後,突然有一天,我學積極心理學時臨時加的一位朋友發了條朋友圈,那條資訊是,有一個專注做青少年兒童心理健康的組織,他們的心智素養課是免費領取的。我其實真的以為這是不可能的事情,只是因為當時沒有資源嘛,就想著試一下。結果一試,發來的東西太讓我驚喜了!
最初,日慈的課程還不像現在是分成一到六年級,當時還是一些「心智素養包」,比如「樂學包」、「小目標主題包」。我給孩子們申請的是一個「情緒包」,孩子們用做手工的方式,做了一個情緒火山。
那個課堂真是讓我永生難忘。學習材料呈現的方式是孩子喜歡的手工課,孩子們每人都有一本書、一份資料紙,大家都可以動起手來。有一個像火山的小土包那樣很形象的圖畫紙,旁邊有很多條細條,就讓他們塗上顏色:你的情緒是什麼顏色的。塗上顏色以後,用剪刀刮一下,它就會像火苗一樣的了。孩子們就覺得很神奇。讓他們探索自己的情緒,寫上解決問題的辦法,他們真的很願意參與。
更巧妙的是,除了手工,還有孩子們喜歡的動畫片。農村很多的孩子都沒有進過電影院。能夠看到那麼多好玩有趣的動畫片,他們開始認識情緒了,他們開始真的知道,原來我的身體裡面住著那麼多的小夥伴。通常大人們會說,「你哭什麼哭!男孩子不可以哭!」現在江東小學的孩子只要上過心理課,就會說,「情緒沒有好壞,情緒是我們的朋友。」

孩子們根據材料瞭解心理知識


嘗試自我關懷


除了任教心理課,周婷也在嘗試透過其他方式影響孩子身邊的更多的人。她曾經自己錄製心理科普短影片發給家長,為全校老師舉辦心理讀書會,或在每週一的例會上分享簡短的心理知識,比如非暴力溝通的方法。
然而周婷的每一次嘗試都很少有人願意關注,很快都以夭折告終,這讓周婷產生了不小的挫敗感。她也由此看到,當下青少年心理問題資料飆升的背後,在我們的教育和養育觀念中存在的深層根源。

孩子們在心理課上玩遊戲
我在這個學校,到今年九月就是七年了。看著這些孩子從最初來的時候,幼兒園或一年級,到現在要畢業,跟隨我那麼多年。我就在想:上的每一節課,有一個點能夠成為他們的支援,我覺得就很好。哪怕有一瞬間,ta 會想起我說的一句話,我們看的一段影片,做的一個手工,或者是我們塗鴉的時候,看到的自己的那一份情緒,這些都叫自我關懷吧。當我們沒有辦法去要求家長、社會、沒有學過心理學的老師去改變,起碼我們可以自我關懷,從這裡開始。


不斷充實自己


上課之餘,周婷也會報名參加日慈基金會每年舉辦的線下的教師成長課程。在北京、在上海、在大理,她結識了來自全國各地的心理老師,對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的總體圖景有了更宏觀的理解。

周婷在不斷的學習心理知識
參與了舞動療愈、教練技術、自我關懷這些服務於教師成長的課程,周婷感到教學內容也融入了自己的生活,滋養了自己的生命。這樣,也就更有餘光去照亮其他人的生命。

周婷給家長上心理課
在日慈的線上線下教師培訓中,周老師一直堅持學習,不斷充實自己:「希望能跟隨日慈成長,給自己賦能,再賦能孩子,把所學內化並應用到我的工作和生活當中,對自己今後要堅持做的事情,內心也更加篤定。」

兒童青少年階段是人格塑造的關鍵時期,日慈公益基金會致力於為鄉村兒童青少年提供心理健康教育,填補鄉村心育的空白,培養學生自我認知、情緒管理和人際交往等技能,以提升其社會情感能力,降低心理問題的發生率。
兒童青少年心理困擾日益嚴峻,還有許多鄉村鄉鎮地區的孩子,需要得到愛和支援!
您是否願意和我們一起幫助更多這樣的孩子呢?
加入月捐計劃,成為持續照亮孩子心靈世界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