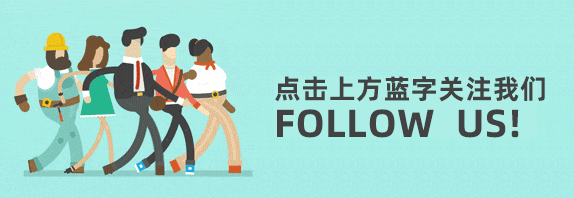作者:Simson Garfinkel
編輯:吳海波


無論你身在何處,MIT 永遠是那個點燃你求知慾、激發你夢想的地方。但你是否知道,在她百年輝煌之前,也曾面臨辦學困境與嚴峻挑戰?正是無數校友不離不棄、力挽狂瀾,讓 MIT 挺過風雨,走向世界。從一場小型聚會開始,MIT 校友協會已走過 150 年,串聯起全球校友的智慧、情感與信念。這段歷程,既是 MIT 的傳奇,也是屬於你我的光榮。

1915年,MIT技術俱樂部成員參訪亨氏公司總部|圖片來源:MIT博物館

1874年1月,寒風中的波士頓帕克豪斯飯店(Parker House)迎來了一群意氣風發的青年——MIT第六屆畢業生、1873級校友。這是MIT歷史上第一次班級年會,參與者雖不多,卻意義非凡:這群剛走出校園的理工男孩,正試圖塑造他們和母校之間新的紐帶。
那一年,MIT剛走過第十個年頭,總校友人數才110人,但土木工程畢業生喬治·W·布勞杰特(George W. Blodgett)敏銳地意識到:這個數字,將迅速擴大。於是,他當場提出一個大膽的建議——建立一個屬於全體MIT人的校友總會。
V
或許是在熱騰騰的帕克豪斯小麵包陪伴下,提議迅速獲得透過。與會者隨即選出喬治·W·布勞杰特(George W. Blodgett)、威廉·A·金博爾(William A. Kimball)和韋伯斯特·威爾斯(Webster Wells)三人,組成籌備委員會。
幾個月後,金博爾展開了實際行動。他給所有有地址可查的畢業生寄出一封問卷式信函,真誠地詢問:“是否覺得有必要成立一個校友協會?”結果超出預期,大家紛紛回信支援。
終於,1875年1月29日下午,在MIT的羅傑斯大樓裡,27位校友親自到場,見證了MIT校友協會的誕生。那一刻,MIT不僅是一個校園,而是一種精神的延續;一種超越時間與空間的聯絡,就此建立。

喬治·W·布勞杰特(George W. Blodgett)
MIT 第六屆畢業生,土木工程專業出身。他是首位提出“建立全體校友組織”的倡議人。在 1874 年的聚會上,他提出創辦校友協會的建議,並主動投身組織工作,成為MIT校友社群的早期架構者之一。
威廉·A·金博爾(William A. Kimball)
MIT 早期畢業生,後成為首任校友協會秘書。他不僅是協會組織的實際推動者,還在1874年寄出調查信,廣泛徵詢校友意見,並在首屆大會上明確提出“幫助畢業生就業”作為協會的首要使命。他的組織能力和遠見為協會早期發展奠定基礎。
韋伯斯特·威爾斯(Webster Wells)
MIT 數學教授,畢業後留校任教,長期致力於教學改革。他是MIT早期教師中最活躍的校友組織者之一,同時也以撰寫數學教科書著稱,對後期 MIT 的數學課程體系建設產生深遠影響。

在創會大會上,威廉·A·金博爾(William A. Kimball) 明確指出,MIT 與傳統文理學院的教育路徑截然不同。哈佛、耶魯的畢業生或許還會繼續攻讀法律或醫學,而 MIT 的年輕人——他們一畢業,就要踏上工程師的職業道路。
正因如此,MIT 校友協會成立的第一使命,便是幫助這些新鮮出爐的工程師們找到第一份工作。這不僅是對校友的扶持,也是對 MIT 的正向反饋,更是對當時正在崛起的現代工程行業的一種有力支援。
作為協會首任秘書,金博爾提出了具體而務實的機制:
這一使命,成為 MIT 校友文化中最早也最核心的傳統之一:你走出校門,但不會走出MIT的網路。

1875年,MIT校友協會正式成立,首任會長由1868級畢業生、礦業工程教授羅伯特·H·理查茲(Robert H. Richards) 擔任。他不僅是MIT最早的14位畢業生之一,也是深受學生敬仰的導師。不久後,他迎娶了 埃倫·斯沃洛·理查茲(Ellen Swallow Richards)——MIT歷史上第一位女性畢業生與第一位女性教師,兩人共同書寫了MIT早期的學術與性別平等傳奇。
協會的組織章程則由理查茲、前述的金博爾(William A. Kimball),以及 查爾斯·R·克羅斯(Charles R. Cross)——1870級校友、當時的物理助理教授——共同起草。整整257個字,開宗明義:“本協會旨在透過增強會員對學校和彼此的興趣,促進學院與畢業生的共同福祉。”年費定為1美元。

羅伯特·H·理查茲(Robert H. Richards)
MIT 1868 級,首任校友協會會長。MIT首屆畢業生之一,礦業工程教授。不僅是校友組織的奠基人,也是推動MIT實踐教育的先行者。他娶了MIT第一位女畢業生埃倫·斯沃洛,兩人堪稱MIT的“理工伉儷”。
埃倫·斯沃洛·理查茲(Ellen Swallow Richards)
MIT 1873 級,首位女畢業生、首位女教師。MIT歷史上第一位女性畢業生,也是第一位女性教師。她是環境科學和家政學的奠基者,用一生實踐“知識服務社會”的MIT精神。
查爾斯·R·克羅斯(Charles R. Cross)
MIT 1870 級,物理助教,章程起草人之一。MIT早期物理教育的關鍵人物,協助撰寫校友協會憲章。他既是學者也是組織者,為MIT早期制度建設立下基礎。
然而,更令人動容的是發起者的身份:他們並非“畢業即遠行”的普通校友,而是一批將MIT當作終身事業的“Lifers”——既是校友,也是教職工,更是學校最忠誠的佈道者。
正如MIT歷史學家菲利普·N·亞歷山大(Philip N. Alexander) 在其著作《A Widening Sphere》中所說:

1877年,MIT校友協會設立了一個全新機構——“學校委員會”,旨在密切關注課程設定、管理方式和辦學方針。那年6月,在年會上,1869級校友、未來波士頓地鐵系統設計者霍華德·A·卡森(Howard A. Carson)提交了一份報告。他高度評價了MIT在工程教學方面的前瞻性,同時直言不諱地指出:化學教學依舊停留在“讀書聽講”的舊模式,缺乏實驗操作,這是一個嚴重的弊病。
然而,真正的危機遠不止於教學方法。實驗教學裝置昂貴、空間受限,而學生繳納的學費根本不足以支撐開銷。MIT 的財政狀況急轉直下:
-
1876屆畢業生還有43人
-
1877年驟降至32人
-
到1878年,只剩下19名學生完成學業
這場辦學危機使得學校不得不裁撤三位正教授,全體教師被迫減薪,甚至高層一度認真討論是否要“關閉學校”。
當時的第二任校長約翰·丹尼爾·隆克爾(John Daniel Runkle)面對困局束手無策,最終黯然辭職。關鍵時刻,創校元老、首任校長威廉·巴頓·羅傑斯(William Barton Rogers)“火線迴歸”。
但問題仍在:MIT全體畢業生僅有233人,許多人尚未立足社會,無力金援母校。面對幾乎無解的困境,羅傑斯沒有放棄。他動用了自己在政商學界積累多年的人脈資源,四處奔走,最終籌集到一筆“可觀的捐贈基金”,為MIT續上一口生機之氣。
到了1881年,羅傑斯邀請著名經濟學家、教育家弗朗西斯·阿馬薩·沃克(Francis Amasa Walker)出任第三任校長。這位“職業改革者”將MIT帶出了陰霾——教學體系煥然一新,招生人數穩步回升,到1888年,畢業生回升至77人,MIT的校友總數也增加到了579名。

隨著校友們在各自行業站穩腳跟,MIT 校友協會不僅資助設立了“羅傑斯獎學金”,也將年會搬進了波士頓最奢華的楊氏飯店(Young’s Hotel)。1894年,《波士頓環球報》報道該年會迎來了8位女性校友,其中包括1894級的瑪麗安·L·馬霍尼(Marion L. Mahoney),她也是世界上第一位註冊女建築師之一。
而真正讓校友活動煥發文化生命力的,是一種叫做“煙談會(Smoke Talks)”的獨特形式——集社交、思想、科技於一體的小型沙龍。
-
1894年11月,在MIT建築樓的客廳裡,校長沃克講述美國關稅制度的變遷,大家邊聽講邊參觀機械實驗室,談笑風生。
-
1895年的煙談會以“航空”為主題,1870級校友薩繆爾·卡伯特(Samuel Cabot)預言飛行器將徹底改變城市格局。與會的哈佛天文學教授、1879級校友W.H.皮克林也信心滿滿地預測:“實用飛行器,近在眼前。”僅八年後,萊特兄弟實現了人類首次飛行。
-
1896年4月,1893級的查爾斯·L·諾頓展示MIT研製的X光管為校長沃克拍攝的手部照片,意外發現其骨中殘留一枚南北戰爭時期的金屬碎片,全場譁然。

1896年一次校友協會的“煙談會”上,1893級校友查爾斯·L·諾頓展示了一張校長沃克手部的X光片,意外發現其中嵌有一塊金屬殘片——那是南北戰爭時期炮彈襲擊留下的傷痕|圖片來源:MIT博物館
這些煙談會,不只是學術講座,更像是一場場 MIT 式的“科技家宴”——既充滿好奇心,也飽含人情味。

煙談會的熱度催生了一個更持久的空間——MIT技術俱樂部(Technology Club)於1896年成立,並租下紐伯裡街71號四層樓,作為校友會所。這棟建築可謂功能齊全:
-
地下室設有洗衣房
-
一樓為廚房與餐廳
-
二樓為客廳與吸菸室
-
頂樓則設有圖書室、檯球室和宿舍
開業時會員已達300人,兩年後激增至581名常駐成員,年費12美元(外地和在校生只需6美元)。1896年12月,《波士頓晚報》稱其“正迅速成為MIT社交生活的中心”。

1916年,紐約技術俱樂部成員參加MIT校友日遊行|圖片來源:MIT博物館

進入20世紀,MIT 校友社群不再侷限於波士頓。1899年1月,《Technology Review》創刊,開始記錄全國各地校友會的動態。
同年2月3日,西北校友會在芝加哥舉行年會,透過電話線路即時連線密爾沃基、紐約、費城、華盛頓、匹茲堡、聖路易斯以及波士頓技術俱樂部——當時這在技術上堪稱突破性創舉。
芝加哥會場的130位校友人手一部聽筒,遠在新澤西的托馬斯·愛迪生透過電話致辭:
雖然波士頓當晚受暴風雪影響,訊號不穩,150位校友聽得不甚清楚,但他們三次高呼校呼——“MIT, rah, rah, rah! Technology!” 終於引來芝加哥校友的會心回應。

20世紀初,MIT再度陷入財政困境。一時間,關於與哈佛合併的訊息甚囂塵上。時任校長亨利·S·普里切特(Henry S. Pritchett)被曝正就合併事宜進行磋商。這一訊息迅速點燃了校友群體的警覺與行動力——班級秘書火速發起“反合併請願”,校友協會同步展開民意調查,結果一致反對。
校友們深知:MIT不是哈佛的“技術分校”,它代表的是另一種教育理念——以科學、工程和應用為核心,以實踐和創造為根本。這份獨立性,不容妥協。
最終,在各方努力下,馬薩諸塞州最高法院駁回了MIT土地出售案,合併計劃正式終止。那一刻,MIT不僅保住了校園,更守住了靈魂。


1904 年,MIT 的班級秘書們發起了一項反對與哈佛合併的請願行動,校友協會也隨即對是否合併進行了全體校友投票|圖片來源:MIT博物館
危機過後,MIT迎來轉折。1909年起,學校開始籌劃整體搬遷至劍橋。新校長理查德·麥克勞林(Richard Maclaurin)成功籌措建設資金,翻開發展新篇。1916年6月14日,MIT在波士頓交響樂大廳舉行喬遷慶典,1,500名校友親臨現場,並透過電話連線同步連線全美34座城市的校友分會。
本次遠端慶典由1895級校友、AT&T“長線”網路負責人阿爾伯特·W·德雷克全程技術保障,執行順暢無誤。活動當晚共籌得超過300萬美元善款,為MIT新校園的騰飛奠定堅實基礎。
從拒絕合併,到集體遷校,校友們用實際行動捍衛了MIT的獨立精神,也親手推動了她邁向世界一流科技殿堂的關鍵一步。
此後,校友協會和班級秘書持續維護 MIT 大家庭的聯絡網路;校友亦成為學校發展的堅強後盾。如今,全球 200 餘個校友分會將 MIT 人凝聚在一起,每年數千名校友回到校園,與老友重聚,共同慶祝他們身為 MIT 社群一員的獨特榮光。

150年來,MIT校友不僅沒有遠離母校,反而用技術、資金和信念一次次為MIT續航。他們的故事,是科技與情感的交響曲,是一所大學與全球校友的雙向奔赴。無論你是校友、在讀學生,還是科技愛好者,MIT校友協會的歷史都值得我們細細品讀——它教會我們:真正的教育,不止於畢業。
參考資料: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2025/04/22/1114502/m-i-t-rah-rah-rah-techn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