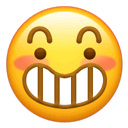馬平,植物科學畫家。
我爸爸認為他肩負著責任和使命,要奉獻自己,對內蒙古自治區的植物自然資源做一個總結。但我對此沒有那麼重的責任,我只能對我的父親負責。我決定留下來,是犧牲我自己,成全我父親的事業,對我來說這是一件很難的事情。
自然灰
2024.12.21 廣州
大家好,我是馬平,我的職業是植物科學畫畫師。
這是我畫的植物生態畫,一個是湖南的柳杉林,一個是蘆葦。

下面左邊這幅圖畫的是蒿屬,蒿屬很龐大,包括很多種植物,比如製作青蒿素的青蒿。這張圖是標準的植物科學畫,畫了它詳細的解剖結構,有花、花外面的總苞片,花的雌花和兩性花,還有雄蕊、花托、花柱的柱頭、種子。

右邊的是蛇菇,是香港的胡秀英博士發表的新種。我在給它畫了植物科學畫之後,看到它的生境感覺非常奇妙,不足10公分的長度卻看起來這麼高大,而且它生長的環境這麼美,所以後來我就又畫了一個小的生境圖。
走上植物科學畫之路
引領我走上植物科學畫道路的,是我的父親馬毓泉教授。我的父親是江蘇蘇州人,出生於1916年,1935年高中畢業於蘇州中學,之後就到北京大學讀書,學習生物學。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北京大學南遷到了長沙,和清華、南開一起組建了長沙臨時大學。當時戰事緊張,黃埔軍校招生,作為有志青年,我爸爸馬上就報考上了黃埔軍校,後來就參軍出征。
1943年時,他們的部隊在大理休整,他接到了以前的老師的來信,想讓他回校續讀。後來他就接受了老師的好意,去了西南聯大繼續讀大三。1945年大學畢業後,他留校從事教學和科研工作。
他很喜歡中國龍膽科的研究,1950年他在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期《植物分類學報》上,發表了一篇論文《中國龍膽科新屬扁蕾屬》,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個新屬。在當時引起了廣泛關注,因為他還非常年輕。
1951年,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次中國植物學大會在北京召開,他作為大會唯一的秘書,也就是秘書長了。

▲ 1950年中國第一次植物分類學會議,圖源《中國植物誌編纂史(1950-2004)》
之後的事情並不像他想象得那麼順利,國家發生了很多政治運動。他因為自己的天真幼稚,差點把自己葬送了,所以他後期在北大待得很不開心。
當時我媽媽也在北大,她是北大幼兒園南園的園長。錢學森全家從美國回來後,他們的孩子就是在我媽媽的護理下成長的。
1957年,國家要在少數民族地區成立第一所大學,內蒙古大學。我爸爸積極報名參加了支援邊疆的工作,因為那時他覺得在北大待下去生存空間有限,我媽媽也一起報了名。
我是1953年出生,1958年的時候我5歲。我現在還能記起來我們當時坐上了西去的列車,經過一晚上的顛簸到了呼和浩特,下了火車了後坐三輪,慢慢悠悠地向很荒僻的地方走。遠遠地看到了有幾棟教學樓,還有幾個教職員宿舍樓,還有一些工友的平房,這一切在我腦子裡面還很清楚。
北大支援內蒙的有一二百名老中青的師資,還有一些即將畢業的大學生,所以當時內蒙古大學號稱是北大分校。
剛開始建設的內蒙古大學是一窮二白,什麼也沒有,所以我爸爸媽媽他們就進入了非常繁忙的工作狀態。我現在都記得,當時的生物樓燈光徹夜不滅,大家都在拼命地工作。
那個時候我爸爸他們常年奔走於教學和野外採集工作之間,經過了多年的努力,內蒙古大學終於初見規模了。
但就在這段時間,1964年我媽媽又因為我爸爸的歷史問題受到了別人的迫害,被開除公職回家接受勞動改造,結論是現行反革命。所以,“文化大革命”期間發生的事,對我們家來說已經不算什麼問題了,因為在這之前我們已經經受了很多的風雨。
因為我爸爸是中國龍膽科方面的專家,六七十年代開始編《中國植物誌》時,他是龍膽科分卷的主編。但1973年他又受到了迫害,因為收集標本過程中發生的一件事,幾乎要把他開除公職。《中國植物誌》編委會三番五次地下文給內蒙古大學,要求對馬毓泉進行處理。
當時內蒙古大學的領導,那個時候不叫書記,叫革委會主任,他對我爸爸稍有一些瞭解,因為我跟他們的孩子是發小。他把我叫到他們家,讓我跟他詳細地敘述事件的過程。他聽完後跟我說,你爸爸是好人,讓他安心工作,《中國植物誌》不讓幹了,內蒙的工作還很多嘛!
我把這個話帶給我爸爸,他非常高興,心裡非常踏實,從此這個事就壓在了革委會主任的抽屜裡,再也不拿出來了。這一劫就此過去了。
到1976年,科學的春天來了,我爸爸覺得《內蒙古植物誌》的編撰工作可以啟動了。因為他這個人非常寬厚,學問和待人都很好,他提出的很多要求和意向大家都很踴躍地支援,所以開第一次工作會議時,就有這麼多人參與。

▲ 1981.10《內蒙古植物誌》編委會成立會議合影,前排左六為馬毓泉先生
他們確定的目標是,《內蒙古植物誌》一定要在全國的地方植物誌中拔得頭籌,要做到文圖並茂,每一個物種除了介紹文字,也必須要有插圖。但是當時缺少植物科學畫畫師。
1976年正好是我下鄉知青返城,回到呼和浩特家裡後我爸爸就說,你願意不願意幫我們做繪圖工作?我說,行,沒問題。當時外面很多中專和工廠也都在招人,但我沒有想去。
參加了繪圖工作後,我就開始積極地到野外去寫生,或是練習自己的毛筆和鋼筆繪畫技法。我爸爸也很早就對我進行科學方面的基本訓練,教我查科學文獻和壓制標本。
這個工作進行了僅僅一年後,1977年中央通知恢復高考,這對於我和當時的那些年輕人來說,是非常非常激動的事情。
可是,如果我要報名參加高考,那《內蒙古植物誌》的工作怎麼辦?我爸爸那時已經60歲了,這一輩子到了60歲才開始自己夢想中的科研工作,終於等到了要開花結果的時候,如果我那個時候離開了,他的事業怎麼辦?
當時我跟我爸爸有過一次長談,這次長談是我後來不願意再提起的一段經歷,我們父子都說了很多心裡話。最後我自己就決定了留下來,幫助我的父親完成他的大業。
我爸爸認為他肩負著責任和使命,要奉獻自己,對內蒙古自治區的植物自然資源做一個總結。但我對此沒有那麼重的責任,我只能對我的父親負責。我決定留下來,是犧牲我自己,成全我父親的事業,對我來說這是一件很難的事情。
從那時開始我就決定了,這一生要投身植物科學畫了。
植物科學畫
那麼什麼是植物科學畫呢?通俗地講,植物科學畫是為植物分類學研究服務的一種專門的小小的畫種,也可以應用在博物繪畫和科普繪畫中。
這是我們畫植物科學畫時用的鋼筆,這個鋼筆桿在我手裡已經握了將近50年了。買的時候2塊錢一盒,10支,筆尖可能是2塊錢15個還是20個。這個筆桿我現在還在用,當然筆尖已經換過很多次了。

既然我願意為我父親承擔起這個責任,那麼我就要全心全意地去完成它。所以我一邊跟著父親和內蒙古大學的學生一起上課,學習植物學知識,一邊自學和練習繪畫。在非常短的時間內,我的繪畫的水平和質量就已經達到了一定的水平。
這是肉蓯蓉,是由我爸爸定的種。除了地面上的花,它還有一部分在地下,在中藥裡叫大雲。

▲ 肉蓯蓉,該植物由馬毓泉先生定種
這是完整的肉蓯蓉的科學畫,也是對我爸爸的一種紀念。這幅畫無與倫比,可以說誰也沒有畫到我這種程度。

▲ 此圖繫馬平為紀念父親而作
畫中有肉蓯蓉的花的正面和地下部分,右下角是肉蓯蓉花的展開,把花切開後攤開了看;右邊還有肉蓯蓉的各個組織部分,雄蕊和雌蕊的花柱,還有它的果實、種子;左上角是果實子房的橫切面和縱切面。
現在有很多人說,有了照相機以後為什麼我們還需要植物科學畫呢?植物照片只是用照相機在某一個地點某一個時間,拍下植物那一瞬間的影像,它不具有科學的模式性。
植物科學畫不僅可以呈現植物在一般情況下的形態,還可以包括它整個生命歷程中各個時期的狀況,透過描繪它的解剖結構圖,也可以讓我們瞭解很多東西。
比如這是薏苡、玉米和小麥的植物科學畫。

▲ 從左至右分別為薏苡、玉米和小麥
在小麥的解剖圖中為什麼要畫這個漿片呢?其實漿片就是禾本科開花的奧秘。在它們開花時,漿片的水分會變多,它會像吹氣球一樣膨脹起來,花就被整個撐開,讓雄蕊和雌蕊從裡面伸出來。這就是它發揮作用的機制,但之前很多人在繪畫時都疏忽了這一點,沒有考慮到這個問題。
從1977年到1985年的8年中,《內蒙古植物誌》出了8卷, 幾乎每年一卷,這個速度全國領先。總共有 2000 多種植物,其中大部分插圖都是我畫的。

國際知名的植物分類學家胡秀英博士,1986年訪問了內蒙古大學,她在翻看《內蒙古植物誌》時注意到了一幅鎖陽的圖。她看了以後說,這張鎖陽的解剖圖畫得非常好,鎖陽跟寄主的關係表現得很清楚。

▲ 鎖陽
這個寄主是什麼呢?鎖陽是寄生植物,它寄生在白刺上,我這張圖把植物體和它的寄主都畫上了,而且各種花的解剖圖和果實也畫得非常好。

▲ 鎖陽
她馬上就問這張圖是誰畫的,我爸爸說,是我小兒子。她說能不能讓他去香港中文大學,幫我工作一段時間?我爸爸說好。就這樣我在1989年的時候,以訪問學者身份去了香港中文大學。
我到了之後,她出去採了兩個植物,一個是蘭科的綬草,還有一個菊科的植物。拿來以後她就隨便地放在桌上,說,馬平,你來把這個東西解剖一下,畫一個解剖圖給我看看。
我腦子一轉,心想這是在測試我呀。我馬上動手,花了半天時間就把兩個種畫完了,然後讓她看。
她說畫圖時用的這些參考文獻是你查找出來的?我說,對,標本是我從標本室裡拿出來的。她問,這些都是你畫每一張圖前要做的工作嗎?我說,對,我爸爸就是這樣培訓我的。
她說,你是第一個我認為合格的繪圖員。這是給我的一個最高的褒獎,很難從她老人家嘴裡聽到這麼一句話,非常非常難得。
這是胡秀英博士跟我在香港時拍的照片,她個子比我矮許多,但她比我偉大多了。胡博士是世界著名的冬青專家,全球400多種冬青中,有300多種是由她命名的,所以也有人叫她冬青之母。

▲ 左為著名植物學家胡秀英博士(1910-2012)
這是我為她畫的鐵冬青的科學畫。為什麼畫鐵冬青呢?她去世之後,在香港、深圳和她的老家徐州,很多地方為了紀念她都栽種了鐵冬青。因為鐵冬青的適應性特別強,生命力很旺盛,結的果紅彤彤的,也特別好看。大家一致認為鐵冬青代表著胡博士的一種精神。

▲ 鐵冬青
我在香港跟著胡博士一起採集標本、繪圖,先後參與了《香港植物誌》《澳門苔蘚志》等著作的繪圖工作。在那期間,我畫出了一批自己非常滿意的植物科學畫,我認為我已經達到了自己的頂峰了,不可能再超越自己了。
新的探索
那個時候我40歲,就開始想我退休了以後幹什麼。除了畫植物科學畫以外,我想在生物界中再找一條適合自己的路。
後來我在業餘時間,在兩年裡畫了100只狗的肖像。為什麼畫狗呢?我覺得狗跟人很親近,是我們生活中特別熟悉的物種。這100只狗畫完了以後,我拿給我的蒙古族朋友看,他生活在錫林郭勒草原。

他看了後說,你知道狗會笑嗎?我說,狗還會笑?!他說,你連狗會笑都不知道,你還畫什麼狗!城市裡養的狗都是寵物,只會向主人獻媚,它沒有體現狗的性格。你要真想畫狗,你得到錫林郭勒草原深處去接觸野性的狗,看看真正的狗的性格是怎樣。
聽了他的話後,從此這100張狗就被我完全封存了,再也不想看了。兩年的時間白費了。
但是,我還是想從生物界找出一些缺口。我知道了以前我沒有畫出動物的情感,後來我就注意,我就到公園去觀察,比如孔雀,它一看到一個生人到它眼前,馬上就會非常警覺,在扭頭看你的一瞬間,眼睛裡會放射出一種警惕的目光。

馬也是這樣。這是一匹阿拉伯馬,我跟著馬術隊的主人,我藏在他後邊,走到馬的旁邊時我忽然一露頭,這個馬突然一閃,閃出來的動作就是這樣。
它的鼻孔馬上張開了變成方形,嘴唇緊閉,縮在一起。再兩秒鐘,它就要呲開牙想要咬人了。就在這一瞬間,我抓住了它的神態。
植物生態畫
從40歲到50歲,從1993年一直到了2003年,這10年我畫了很多類似的生物界的東西,實驗了各種亂七八糟的畫法,但是處處碰板、處處撞牆,一直沒有找到我自己喜歡的東西。我非常鬱悶,很多時候處於一種非常焦慮的抑鬱的狀態。
後來我找到了一種方法,我知道音樂是最高階的藝術,音樂的旋律要在你的大腦中經歷一個迴路,你才能產生出對它表現的場景的理解和想象。
有一次在香港的兩個月中,在標本館裡,晚上沒人了之後我就開始聽音樂,用音樂“轟”了兩個月。
有一天晚上我聽到了貝多芬的《“皇帝”協奏曲》,腦海中就像一個黑屋子裡突然打開了一盞燈的開關,在我腦子裡馬上出現了很多畫面。
那個畫面是我在大興安嶺採集的時候曾經遇到的,我馬上回想起了更多的場景,我抓住了這個場景,我就要把它畫下來。

▲ 《針葉林下·大興安嶺》2003 年
我馬上開始查資料,查大興安嶺和東北的植被,因為我要畫的這個場景必須要有科學性,符合當地的植物生長狀況才能畫出來一個生態畫作,它才能夠保留下來。比如100年或200年後,我再到這個地區可以看看還能不能看到這個景觀。
這裡有很多樹,旁邊的是白樺,前面倒伏的是興安落葉松,最後面倒下的一棵是楊樹。在大興安嶺的森林環境下,倒伏的樹幹上會長很多苔蘚,下面還有很多蕨類植物,還有一些禾本科植物。再高一點的還有灌木。
這個作品我畫了四五個月,就是用前面提到的那個鋼筆畫的,當然四五個月的時間不是每一天都在畫,而是工作之餘。這就是我的第一張植物生態畫作品。人家說你畫的東西非常抑鬱,是的,因為我畫這幅畫的時候心情是抑鬱的。
這是我在深圳仙湖植物園遇到的一個場景,那天我跑步跑到一個轉角,忽然發現光線特別美,我蹲下來後就看到這個場景。我盯著看了好久,身上被蚊子叮了好多包。第二天我帶著相機又去了一趟,但光線已經完全變了,不再是這個樣子了。

▲ 《林下路邊·廣東》2005 年
因為我蹲在那看了很長時間,對光線的效果和每一株植物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還是能夠把它畫出來。
這是湖南衡山的柳杉林。我到這個地方採集標本時,坐下來休息,側目往那邊一看,覺得這個地方特別生動、特別美。

▲ 《柳杉林·衡山》2003 年
這張畫用了我半年時間,因為它非常複雜,這裡邊光線的關係太多了。我不懂藝術,也沒學過畫,只能自己慢慢摸索著畫。
剛才那些是比較宏大的畫面,我也畫過一些小的場景。其實在植物界,一株植物的死亡,比如一棵樹倒了,就意味著其他的植物,次生的植物生長起來了。這個場景我給它畫了出來。

▲ 《路邊》2008 年
後面倒的樹根是芭蕉,長得最高的這個是菊科,叫一點紅。我認為繪畫時關注的點並不在於宏大,路邊很多細節的東西,也都有它存在的價值。
有一次我在看電視時,看到新聞中介紹臺灣森林起火的情況,拍到了明火剛過去後的場景。畫面只有十幾秒很快就閃過去了,但我馬上就把整個場景中重要的部分記住,把它畫下來了。

▲ 《過火後的森林》2012 年
明火剛剛熄滅,溫度特別高的煙騰出來了,往上飄時逐漸地消失。地面上也有很多煙,它溫度沒有那麼高,沉了下來。
這是我畫的一棵比較有趣的樹,一棵旱柳。我們知道生物都是有情慾的,人有人的感情,你跟對方之間產生愛慕之後,你投去的目光和你的身體語言都是不一樣的,其實植物也是如此。

▲ 《旱柳》2017 年
我畫的這張圖應該是5月底6月初時的柳樹。我們經常在野外工作,在草原上遠遠地看到一棵樹後,經常馬上可以判斷說,這棵樹正在開花或者馬上要開花了。學生問老師你怎麼知道,我說你看它張揚的狀態,樹枝伸出來的誇張的動作和葉片反射的光,跟別的樹完全不同。
這張畫是在疫情期間畫的。大家都處於一種非常鬱悶非常壓抑的狀態,我忽然想起來我在川西考察時,遇到山體滑坡後,泥和石頭裹挾著一些大樹從山坡上滾下來的情景。

▲ 《殘枝斷幹》2020 年
這幅畫裡上面是毀滅了的冷杉,很多石頭壓著樹幹;而下面就是一株生長得生機勃勃的毛建草,旁邊還有一株薔薇科的植物,還有很多苔蘚、蒿屬。我給它起的名字叫毀滅與重生,那個時候大家的情緒就是那樣的。
這張畫是我在內蒙古西部見到的胡楊。很多人畫胡楊都喜歡畫深秋時黃黃的葉子,擁有非常絢麗的顏色,我覺得那是一種非常討好人的感覺。我希望畫出胡楊在一個非常嚴酷的條件下的狀態。

▲ 《胡楊·阿拉善》2014 年
沙塵暴來襲,滿地上滾的是豬毛菜,胡楊樹上沒有一片葉子。為什麼要畫這樣的胡楊呢?我要畫胡楊的精神,我畫的是支撐它在嚴酷條件下能生存下來的精神,畫它的氣質,而不是畫它的顏色有多絢麗多美,不能畫它非常討好人的一面。
我畫了幾十年,但我覺得自己的科學畫和生態畫算不上什麼藝術。一位朋友曾經對我說,你不要把這些畫拿給美術學院科班出來的人看,你的東西就是你的,沒有必要讓別人去承認。你畫的是一種非常客觀的作品,帶著自己的情感,這就有自身存在的價值。
這就是我的報告,謝謝大家。

▲ 以馬平老師的作品為素材設計製作的現場門票
📖更多馬平老師的作品見簽名版《自然灰》
策劃丨恆宇啊
剪輯丨大凱
字幕丨馬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