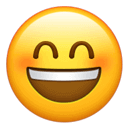埃裡克-E.施密特是法國著名的小說家、劇作家、電影導演。1960年,他出生於法國里昂,曾就讀於音樂戲劇學院,並擁有法國高等師範學院哲學博士文憑。他深受18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狄德羅的影響,繼承並弘揚了法蘭西文學與哲學融合的優良傳統,不斷地對人性謎題進行深入挖掘和反思。他的作品有《訪客》《利己教派》《紀念天使協奏曲》《鏡子中的女人》等。在文學創作上,施密特駕輕就熟,在藝術與圖書市場之間實現了完美的平衡,是當代法國作家中讀者最多、作品被改編次數最多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被翻譯成40多種語言,其中“看不見的迴圈”系列全球銷量達1000多萬冊,根據他的作品改編的戲劇和電影在50多個國家上演。
21世紀以來,施密特的作品在中國備受青睞。2004年,《外國文藝》發表他的劇作《迷幻變奏曲》。同年,方智出版社翻譯出版了他的小說《最後12天的生命之旅》(又譯《奧斯卡與玫瑰奶奶》)。2011年以來,《我們都是奧黛特》《來自巴格達的尤利西斯》《諾亞的孩子》先後在中國問世。2024年12月27日至2025年1月12日,北京人藝在曹禺劇場上演的跨年大戲《迷幻》,就改編自施密特於1996年發表的《迷幻變奏曲》。

1
施密特的每一部作品都進行過精心的構思,且似乎都離不開愛與救贖的主題。在法國,跟《小王子》《聖經》一樣,《奧斯卡與玫瑰奶奶》已被列入“改變人生”系列書單。在這部小說中,一個叫奧斯卡的小男孩得了不治之症,當同齡的孩子在運動場上玩耍時,他卻在病房裡與癌症作鬥爭。在他的世界裡,護士取代了同學,醫生代替了老師,甜點變成了藥物,他多麼渴望擁有正常的生活。終於有一天,奧斯卡迎來了他的陽光——玫瑰奶奶。玫瑰奶奶是個穿著粉紅制服的義工,她鼓勵奧斯卡給上帝寫信,要他把一天當成十年來過。奧斯卡照她的話做了,經歷了人生中的不同階段。在信中,他寫出了童年的快樂、青春的悸動、成長的煩惱、婚姻的危機、中年的困惑以及生命的告別。這個故事濃縮了人的一生,讓人為之動容。

《奧斯卡與玫瑰奶奶》
該書的主題很嚴肅,但施密特優美的文字和幽默的口吻給讀者以輕鬆、愉悅的感受。這本書就是奧斯卡寫給上帝的書信集,講述了小男孩最後十二天的生命歷程。因為玫瑰奶奶,奧斯卡度過了不平凡的一生,並且懂得了生命的意義:“生命是一份奇特的禮物。起初,我們往往高估這份禮物,以為得到了永恆的生命。後來,我們又低估了它,認為它會腐爛,轉瞬即逝,想把它拋棄。最後我們才明白,其實這不是一份真正的禮物,而僅僅是一次出借。於是,我們就試著配得上這個生命。”

根據《陪我走到世界盡頭》改編的電影
《陪我走到世界盡頭》也是一部感人肺腑的小說,是對父子關係的一種全新闡釋。故事的情節是這樣的:摩摩是個11歲的男孩,遭遇了父母的拋棄,只能用自己的方式長大。在遇見伊博罕先生之前,他是個壞孩子,劣跡斑斑。伊博罕先生的出現,給他的人生軌跡帶來根本性的改變。“摩摩,假如你必須偷東西,就到我的店裡偷吧。”就這樣,從那一天起,摩摩和伊博罕先生便成了忘年交。伊博罕先生是摩摩家樓下的雜貨店老闆,他十分浪漫且有包容心,他帶摩摩去旅遊,去認識外面的世界。慢慢地,摩摩學會了愛自己,學會了與生命中的不完美妥協。在新的生活中,他開始體會人生,瞭解生命和愛的真諦。在伊博罕先生的引領之下,摩摩逐漸長大。這部小說一問世就在歐洲引起轟動,好評如潮,連續數週蟬聯暢銷書排行榜冠軍。後來,這部作品被改編成舞臺劇並拍成電影,讓更多的觀眾感受到人性中溫馨、感人的一面。

《諾亞的孩子》
施密特是個講故事的能手。在《諾亞的孩子》中,主人公是個七歲的猶太小男孩,名叫約瑟夫。七歲的孩子本應有個幸福的童年,但約瑟夫卻經歷了戰爭與恐懼,而這一切只因為他是個猶太人。面對納粹慘絕人寰的大屠殺,他的父母只能把他託付給好友,後來,他被轉移至蓬斯神父的“秘密基地”——黃別墅。這個猶太小男孩不得不改換了自己的姓名和年齡。蓬斯神父在黃別墅裡教他希伯來語,為他講解《摩西五經》和《塔木德》。在蓬斯神父的教導下,他懂得了不管是什麼樣的人,不管是什麼樣的人種,他們的生命都值得尊重,而且尊重是理解差異的最好方式。後來,蓬斯神父離開了人世,成了他曾施救過的271個孩子心中永遠的思念。這部小說以孩童的視角展開,用靈性的文字追問了生命的意義,回答了許多成年人也難以回答的問題。《諾亞的孩子》全文共八章,這部小說與莫里哀、伏爾泰、雨果的作品一樣,已經被法國政府列為教育經典之作。
2
施密特善於以最簡單的方式回答“我們如何活得更好”以及“我們怎麼用好身邊的一切”等問題。他的作品大多表達了同一種信念,即生命並不荒謬,只是很神秘,其意義近在眼前,但必須透過反思才能發現它。

《來自巴格達的尤利西斯》
《來自巴格達的尤利西斯》就是這樣一部作品。青年薩德在大學裡學習法律,不幸的是,海灣戰爭爆發了。母親建議他趕緊離開家鄉,以便為家人減輕經濟負擔,同時也為他自己爭取更好的未來。就這樣,薩德決定偷渡到英國。從離開巴格達的那一天起,薩德便放棄了自己的姓名、語言、身份和證件。小說的第一段是這樣寫的:“我叫薩德·薩德,這個名字在阿拉伯語裡的意思是希望·希望,但在英語裡卻是悲哀·悲哀;隨著一週又一週,有時是一個鐘頭又一個鐘頭時光的流逝,甚至於在短短一秒鐘的爆炸聲中,我的實際情況便從阿拉伯語滑到英語。”
不言而喻,在逃離家鄉的過程中,他遭遇了意想不到的磨難。到英國後,這個被父親稱為“我的血中血、肉中肉”的青年自以為逃脫了苦海,但他的膚色和身份使他遭受鄙視,他舉目無親,流離失所,也不知心上人蕾拉何時才能從巴格達前來與他團聚。透過薩德逃離戰亂的故事,小說對人性、民族、文化、生命展開了深度的追問和思考。
這部小說結構緊湊,行文簡潔,字裡行間充滿了對人類的深切悲憫。作者善用貌似天真的黑色幽默,將自己的思想巧妙地傳遞給廣大讀者,再一次向世人證明了其高超的寫作技巧。在這則看似平淡無奇的故事裡,施密特沒有落入俗套——只是描繪一場硝煙瀰漫的戰爭,而是生動地表現了普通人對生存權利的追求。

《假如一切可以重來》
無論是施密特的小說還是戲劇,都充滿了對生命、對人性的叩問。施密特說,他的許多作品都是由一個年輕人物來講述的,《假如一切可以重來》就是其中的一部。在這部劇作中,60多歲的老醫師亞歷山大回到童年的家中。他注視著每一件傢俱、飾物,睹物思人,臉上露出了甜蜜的笑容。但是,對於主人公來說,青春已逝,他已進入老年。突然間,客廳裡的掛鐘掉在他的頭上,將他擊倒在地。當他醒來的時候,光線出現了奇妙的變化,明媚的秋天變成了一個陽光燦爛的夏天,一個快樂的、對未來充滿希望的年輕人突然出現在他的面前。他穿越到了40年前,看到了年輕的自己(薩夏),看到了他慈祥的祖母以及追求過的女孩。
但是,知道後來將要發生的一切,他要不要進行干預?他會不會改變事物的發展程序?答案是否定的。亞歷山大與青年薩夏展開了對話,與“另一個我”心心相印。在這部充滿柔情的超現實主義劇作中,施密特讓思想的大門敞開,讓每一個讀者來做出自己的選擇。

《我們都是奧黛特》
《我們都是奧黛特》由八個短篇小說組成,講述了八位女性關於愛的八段故事。這些女性來自不同的社會階層、不同的年齡階段,儘管結局並不盡如人意,但每一個人都在努力地追求幸福。這些故事構思精妙,充滿了懸念。
除了小說和戲劇外,施密特還拍攝了電影。童年時代,他很想成為一名電影製片人,拍攝無聲的黑白電影。後來,他決定把影片中缺失的詞和句子撿回來,文學創作因而成為他的表達方式。40歲之後,當有人建議他拿起攝影機為人們講故事的時候,他欣然應允,顯然,答應這麼做的人並不是中年的他,而是他身上那個一直等待他迴歸的小男孩。
施密特是個才華橫溢的劇作家、小說家。這位故事能手善於將柔情和詩意注入不同的藝術形式,用短小精悍的故事探尋人性的謎題,用一部部作品走入世界各國讀者的內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