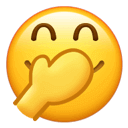1997年,墨西哥城。烈日之下,一個男人推著巨大的冰塊,在街道上費力前行。

9個小時後,冰塊完全融化,除了地上未乾的水痕,他一無所獲。
這個曾經在社交平臺上被大量討論的人類“迷惑”行為,其實是藝術家弗朗西斯·埃利斯(Francis Alÿs)的一件作品,他將自己長達9個小時的推冰行為剪輯成一段9分54秒的影像,併為這件作品標註“有時行動只能引向虛無”。
荒謬、幽默、詩意、徒勞是很多人對他作品的第一印象,他也因此被冠以當代“西西弗斯”的頭銜。

《實踐的悖論1:有時行動只能引向虛無》
Francis Alÿs
1997
“當你行走在街上時,
你會察覺到周圍發生的一切”
出生在比利時安特衛普的弗朗西斯·埃利斯如今常常被認為是墨西哥藝術家,因為他的許多藝術創作都發生在墨西哥街頭,但其實,墨西哥並不是他的故鄉。
1986年,艾利斯作為建築師被比利時軍隊徵召,前往墨西哥參與地震災後重建。三年後,重建工作順利完工,但他不打算回到比利時,而是決定在這個帶給他很多文化衝擊的異國他鄉開啟自己的新一局人生——以藝術家的身份定居在墨西哥。

對於埃利斯而言,複雜,多彩,粗糙而充滿能量的墨西哥文化帶給他極大的衝擊,也讓他體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身為“局外人”的他一開始覺得自己和這座城市格格不入。“我太高、太白、太像外國佬了”。於是他從自身的外來性為起點,開始嘗試用藝術實踐來回應和融入陌生的地域和文化,嘗試從旁觀者變為參與者。
1991年,埃利斯開始牽著一隻內建磁鐵的“寵物狗”在墨西哥街頭散步。他給這隻狗起名叫《收藏家》,每天都會牽著這隻“狗”在大街小巷穿梭,而這位“收藏家”每天都會被它蒐集到的金屬物覆蓋全身。
“它不停吸,直到有一天,這位收藏家被自己的戰利品完全淹沒。”埃利斯在影片中解釋道。

The Collector
Francis Alÿs
1991
對他而言,這種漫無目的的散步是異鄉人探索一個陌生城市的最佳方式。他說:“當你行走在街上時,你會察覺到周圍發生的一切,氣味、影像、聲音……散步也許是當代人最後的私人空間之一。”
作為他的第一件作品,這件觀念藝術讓埃利斯一度成為墨西哥人口口相傳的都市怪談,也讓他在國際藝術圈初露頭角。只是這些名氣並沒有消除他對於自己「外來者」身份的定義。
1994年,他乾脆標明自己的“遊客”身份:墨西哥街頭,一些工人們站在介紹牌後等待僱主,埃利斯站在他們中間,在自己面前放置了一塊“遊客”的硬紙板,這個行為讓他顯得格外突兀,立刻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Turista
Francis Alÿs
1994
在一次採訪中,埃利斯對自己的這件作品做了解讀。他認為,對於藝術創作,比起創造,更多時候他所做的只是“看見-進入-記錄”,以觀察者的身份在墨西哥街頭漫遊,這種“看見”本身有時候就意味著“干預”,而他也自然而然地從旁觀者變成了參與者。
在此之後,他相繼創作了文章開頭提到的《實踐的悖論1》;在耶路撒冷停戰邊界,用身體移動畫下的作品《綠線》;以及花費十年,一次又一次手持攝像機衝進暴風眼拍攝而成的《龍捲風》。

The Green Line
Francis Alÿs
2004
埃利斯拿著一罐洩漏的綠色油漆沿著巴以停戰的邊界漫步,他用58升綠色油漆“描繪”了一條近24公里的“綠線”,這條”綠線“是1948年以色列和約旦戰爭結束時由摩西·達楊(Moshe Dayan)用鉛筆在地圖上畫的。這條邊界線一直維持到1967年的六日戰爭,之後以色列佔領了該線以東的巴勒斯坦人居住的領土,這條線也隨之消失。
埃利斯以一種“不實用”卻詩意的方式,重現了這個嚴肅的歷史事件。他不偏袒任何一方,也不發表政治言論,只是行走,僅僅是行走,以及引發人們的思考。就像他所說的,“有時候做一些詩意的事情會變得政治,有時候做一些政治的事情會變得詩意。”

Tornado
Francis Alÿs
2000-2010
從2000年到2010年的十年間,每年旱季結束,埃利斯都會前往墨西哥城東南部的高原,這是龍捲風會出現的季節,他會在不做任何安全防護的情況下,手持攝像機一次又一次跑進巨大的龍捲風漩渦之中。龍捲風中夾雜著沙塵和當地農民焚燒秸稈後產生的灰燼,進入龍捲風的過程無疑是艱難而痛苦的,可一旦進入暴風眼,周圍只有一層薄薄的塵土圍繞著他,彷彿進入了另一個空間。
”龍捲風“專案的開始是因為埃利斯享受進入風暴之眼後被包裹的那種感覺,但在這個專案的十年間,墨西哥的政治和社會環境也在發生著變化,這些變化讓他對自己這件作品的思考也發生了變化。埃利斯用「龍捲風」隱喻了變化中混沌與秩序的關係:秩序從混沌中誕生。
這些作品中,無論是有關地緣政治的隱喻,還是有關空間的界限,“邊界”自始至終都是他關注的焦點,他自己也始終是鏡頭下的主角。
無論和平與戰爭,
孩子們都玩著同樣的遊戲
在創作生涯前期,埃利斯的每件作品幾乎都與自己相關,他是自己作品的主角。但之後,他嘗試從自己的作品中心退出,將主角讓給了孩子們。

Sandlines, the Story of History
伊拉克, 2018-2020
其實,這個轉變在他之前的作品中已經有了隱喻。比如在那件最著名的推冰作品最後,鏡頭轉向一群孩子,他們圍著冰塊化掉的一灘水,露出好奇又天真的笑臉。
他說:“每當我有困惑的時候,我就會重溫童年時光,那是我通常能找到答案的地方。”“孩子是大人的起點。什麼事情對他們都是新的;另一方面,跟孩子相處,也將我帶回自己的起點。”
埃利斯坦言,自己80%的藝術靈感都來自童年,推冰這件作品也或多或少是受到兒童遊戲的啟發。

實踐的悖論1:有時行動只能引向虛無
Francis Alÿs
1997
從1999年開始,埃利斯以一種近乎“民族誌”的方式,考察、探訪、捕捉並記錄世界各地孩子們在街頭的遊戲日常。他將這一系列作品命名為《兒童遊戲》,至今已經積累了40多個影片。
這些影片最長不超過10分鐘,非常直白地記錄了孩子們在戶外做遊戲的過程。在他的鏡頭裡,孩子們專注遊戲,並與周遭的環境默契呼應,埃利斯只是鏡頭之外的旁觀者,對於孩子們的遊戲社群不做任何干預。

Children’s Game #28:Nzango
剛果,2021
乍看之下,在埃利斯的《兒童遊戲》系列作品中,他走訪了很多不一樣的城市,在不同的空間誠實地記錄了境遇不同的孩子們最日常的玩樂現場。
他們有的在摩洛哥的石階上拍畫片,有的在阿富汗的廢墟里放風箏,有的在墨西哥的操場上搶椅子,有的在丹麥的草地上用頭傳遞橘子,也有的在比利時的沙灘上堆城堡……但仔細體會就會驚喜地發現:即使地域乃至文化差距巨大,這些並未有過溝通的孩子們之間的遊戲卻有著普遍性,一些在和平地區常見的兒童遊戲,在戰爭地區一樣可以見到。

Children’s Game #38:Ellsakat
摩洛哥,2023

Children’s Game #10:Papalote
阿富汗,2011

Children’s Game #12:Musical Chairs
墨西哥,2012

Children’s Game #34:Appelsindans
丹麥,2022

Children’s Game #6:Sandcastles
比利時,2009
兒童遊戲,
總是驚人地相似
“作為藝術家,我感興趣的點恰恰是兒童遊戲的普遍性。兒童遊戲不多,但它們往往有著許多變化。一個很好的例子是「跳房子」,它有著無數的變體,但在我所瞭解的許多文化中,基本機制相似。你離開地球,穿過地獄,到達天堂,然後回到地球,跳過地獄,獲得重生。這是一個關於救贖的遊戲。”

© Francis Alÿs
兒童遊戲雖然以一種看似脆弱的“口口相傳”方式被延續,但孩子源源不斷地想象力總會在傳播過程中對一個老遊戲重新組織編排,最終賦予它們穿越世界和時間的張力。
2010年,埃利斯受邀在阿富汗進行一個藝術專案。很快,他就在街頭髮現當地的孩子們喜歡用棍子推著廢舊的輪胎跑,這是一種在當地孩子們之間非常流行的遊戲。

Children’s Game #7:Stick and Wheels
阿富汗,2010
這個遊戲對於所有人來說都不陌生,全世界任何角落都曾見過“同款”,甚至在16世紀荷蘭繪畫大師老彼得·勃魯蓋爾的名作《兒童遊戲》中,都能尋得蹤跡。

兒童遊戲
彼得·勃魯蓋爾
1560
儘管周遭環境惡劣,但生活在這裡的孩子沒有因為戰火和動盪喪失快樂,孩子始終是孩子,他們在玩耍時有一種實實在在的輕鬆氣氛。
塔利班禁止在當地播放電影,並且焚燬了大量電影檔案,埃利斯把廢棄的電影膠帶卷軸拿給孩子們,他們很快就用卷軸代替輪子,“更新”了這個遊戲,一個外界看來悲劇性的物件,只不過是孩子眼裡更好的玩具。他們總能快速運用手邊現有的工具,靈活機智地制定遊戲規則,在孩子眼裡,玩耍永遠擺在首位。

© Francis Alÿs

© Francis Alÿs
埃利斯說:“他們的確是戰爭的受害者,但同時,他們也是非常有想象力、快樂的人。”
這樣的遊戲並不是個例。在埃利斯的另一件作品中,墨西哥郊區,男孩們在廢棄政府救濟房中拿著鏡子的碎片,用太陽折射的光線互相照射對方,嘴裡模擬著射擊的聲音。被光線射中的孩子意味著中彈“死去”,他們甚至會俏皮誇張地表演“死亡時刻”。

Children’s Game #15:Espejos
墨西哥,2013
和阿富汗一樣,在這些我們常在新聞中聽到的城市,除了暴力和犯罪,窮困和流離失所,埃利斯顯然捕捉到了和新聞記者不一樣的視角:無論身處多糟糕的環境,孩子們總能把腳下踩著的這片土地就地化成為遊戲場。
埃利斯希望透過作品反對主流報道,他記錄了孩子們的快樂,並且不贊成主流報道中一味地以悲劇式的口吻概括這些地方。至少屬於孩子的最平常的一面不應該被抹殺。

Children’s Game #29:La Roue
剛果,2021
在不同城市的記錄過程中,埃利斯還發現不少地方的兒童遊戲都受到當地風俗或者日常生活的影響,且大多數遊戲都有共同之處。
比如墨西哥的孩子也會使用“剪刀、石頭、布”決定輸贏,約旦安曼男孩會在響徹城市的禱文聲中專注“彈珠”,尼泊爾的孩子們則會尋找大小形狀完美的石子“擲距骨”,摩洛哥的孩子會在水邊比試“打水漂”……

Children’s Game #14:Piedra,Papel o tijera
墨西哥,2013

Children’s Game #8:Marbles
約旦,2010

Children’s Game #18:Knucklebones
尼泊爾,2017

Children’s Game #2:Ricochets
摩洛哥,2007
在世界各地,兒童遊戲總是驚人地相似,這似乎是人類天生自帶的一種集體意識。在埃利斯看來,“遊戲就像是檔案庫,在孩子與外在物質接觸的時候,就像回到人類的起點,就是去玩、去互動,這也許是人所以為人的原因。”
孩子在街頭玩耍時,
也在模仿大人的世界
透過觀察孩子們在街頭玩耍,埃利斯還發現,當變化或者災難來臨時,比起成人,孩子有時能更快地適應改變。

比如說難民營裡的孩子往往比成人更快地適應生活,因為他們沒有“更好的過去”用以緬懷。他們只會根據周遭的改變,快速重建自己的遊戲規則,在有限的條件下,最大化地尋找樂趣。

像是伊拉克街頭,他曾觀察到一群男孩子在興致勃勃地踢足球。在當地,ISIS禁止踢足球,於是他們的遊戲中其實並沒有足球,他們腳下踢的只不過是空氣,但這絲毫不影響他們奔跑、搶球、射門……

Children’s Game #19:Haram Football
伊拉克,2017
疫情暴發後,埃利斯在中國香港發現當地孩子在玩一種名為“大流行”的遊戲,這是一種由原本普通的“追人”遊戲改良的新遊戲,“感染者”戴著口罩追逐其他人,被他追上就是被“感染”了。
埃利斯在和孩子的聊天中發現,他們中的很多人並不知道“感染”是什麼意思,但電視報道和大人每天都在說這個詞,於是他們將這個“熱詞”加入進日常遊戲,遊戲似乎變得更有趣了。
埃利斯說:“當孩子在公共場所街頭玩耍時,他們也在模仿大人的世界,兩者之間會有相似之處。”

Children’s Game #22 Jump Rope
中國香港,2020

Children’s Game #24:Pandemic Games
中國香港,2020
俄烏戰爭一年後,埃利斯在烏克蘭哈爾科夫街頭觀察到男孩子喜歡在路邊玩一種“檢查站”的遊戲,這是一種與他們生活緊密相關的新式“戰爭遊戲”,他們學著士兵的樣子,在路邊向過往的車輛示意暫停或放行。

Children’s Game #39:Parol
烏克蘭,2023
埃利斯說:“孩子們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重新詮釋任何空間或地點。在基輔,我遇到了一個公園,正好有一枚俄羅斯導彈爆炸了,在兒童樂園旁邊形成了一個極大的彈坑。孩子們很快把這個彈坑佔為己有,把它變成了遊樂場。”
在埃利斯的這一系列作品中,孩子們展現出的既有互相協作,也有互相競爭。即使鏡頭離他們很近,孩子們顯然也知道攝像機的存在,但他們並未表現出被打擾或是做作,天真和殘忍都會自然而然地在鏡頭前流露,有時甚至喜歡對著鏡頭表現和炫耀。
在委內瑞拉,他記錄下孩子們在草叢中捕捉蚱蜢的情節,男孩和女孩們一旦抓到蚱蜢,會冷靜地把它們的後腿拔掉。畫面中的孩子們興奮地尖叫,把去掉後腿的蚱蜢拋向空中,失去後腿的蚱蜢無法飛行而跌向草地。

Children’s Game #9:Saltamontes
委內瑞拉,2011
如今,弗朗西斯·埃利斯依然持續在他的旅途中收集世界各地的兒童遊戲。
在他的影像記錄中,孩子們就像是早期作品中游蕩於城市中心的埃利斯,無論是在和平還是戰亂的地方,都能利用平凡的手邊物件以及純真的觀察,在日常空間中創造想象和隱喻。
藝術評論家們形容埃利斯為“檔案管理員”和“觀察家”,埃利斯則認為,對於很多戰亂地區的孩子來說,藝術也許是一束射向他們的光。“如果說我對藝術史有什麼貢獻的話,可能就是這些了。”
他形容自己的作品是“一種散漫的論證”,隨著時間推移,意義會自己浮現出來。

Francis Alÿs:Ricochets
倫敦巴比肯藝術中心
🪀
編輯:二郎 運營:小石,yida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