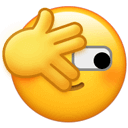△《從來》海報 ©Timelight Films
機艙已經關燈,開啟飛行地圖,莫斯科正北方向,距離上海還有七個半小時。我掐著頒獎儀式的時間,隱約有預感:《從來》應該能拿獎。空中WiFi的龜速加重了懸念滋生的興奮和焦灼,下一秒便是德明(導演)、漢森(製片人)、Gugi(監製)三人在歡呼聲中起身的小影片。這預感既有身為同窗的祈禱,有玩笑猜測多日的心切,更多是因為親眼目睹了信念和行動的力量。
兩個大男孩在2025年CPH:DOX(哥本哈根紀錄片電影節)拿了主競賽最佳紀錄片大獎。《從來》自2023年參加印尼提案會Docs by the Sea 後開始被國際市場矚目,一路幾乎暢通無阻,順利入選多個高質量訓練營及扶持計劃,並終於在上週迎來它的全球首映。這部在寒春裡亮相的處女作以優雅凝練的影像語言,真誠熾熱的創作過程,耐心沉靜地將一個愛寫詩的孩子的村莊生活徐徐展開。
為他們高興的同時,我感受到的,是嘈雜的當下對「返璞」的精神需求。因作品剛剛開啟它的國際影展巡迴,中文讀者尚無觀看渠道,大談內容無益。我和兩位主創商量,儘量先從製片的角度分享。從舉起攝影機到捧起獎盃,他們一路走來的風景如何?困難如何?收穫如何?赴會的一週裡,我們找了幾次零散的時間,在火車上、會場中、餐廳裡……老同學坐在一起,聊得自然舒展。我相信兩個青澀又自信的創作者闖出一片天的經驗能對眾多創作者有所啟發。以下是幾次對話的整理:

△出城郊遊的火車上採訪 ©陳德明
「要跟用心的好人合作」
紀錄公社:每次看到你倆在一塊出現,我都覺得這片兒能做成是註定的,你倆綁一塊兒真的又甜又噁心。
陳德明:他有很多我沒有的優點。
林漢森:他有很多我沒有的情感。
紀錄公社:(大笑)我知道你們在22年秋天第一次見面,之後很快就確定了合作。我想先聽聽你們是怎麼一拍即合的。
林漢森:我們在一個提案會認識的。首先這專案真的很吸引我,所以我很認真地觀察了他整個提案的情況。之後我主動跟他約打影片電話。他當時非常肆無忌憚,住在一個帳篷裡,一邊打著影片一邊換衣服。我想說好傢伙,第一次工作會議不該是很嚴肅的嗎,但我一下子就打開了。好像創作沒怎麼提,聊你在北京幹嘛?住在哪啊?像老朋友一樣,敘上舊了,我印象很深刻。
紀錄公社:你一共去那個村子跑了多少趟?
陳德明:實際的拍攝日總共只有60天,但是從2018年就開始了,一直是拍拍停停。我沒什麼正式的工作,也沒這麼去統計過,只要是覺得這個季節我該去那裡,我就會去到那邊。
紀錄公社:從導演的角度,漢森給你提供的幫助是怎樣的?聽說你在跟他合作前自己也投了很多工作坊、創投類的機會都不太順利,彷彿他的出現讓這個專案轉運了。
陳德明:我覺得是互相補充,他更加知道市場是什麼樣,要怎麼樣提煉影片已有的特色,讓它能有亮點地去展示。我比較感性,經常把提案文書當成詩在寫,很多人都看不懂。
林漢森:我覺得他給我的情感支援更多。德明本來就是一個很詩意的人,很多關係都處得比較浪漫,片子的氣質也是如此 ——不想明確什麼是過去、什麼是現在、什麼是時間—— 所有東西都模糊了。但這不是渾濁,它是一種很溫柔的質感,有點像山水畫的那種筆觸。但是說到這個關係,我覺得他只要在這個專案中覺得舒服,覺得創作沒有受到限制,就可以了。

△陳德明、林漢森在CPH:DOX的合影 ©unknown audience
紀錄公社:聽上去你們在保護彼此。
陳德明:其實簡單一點,能遇到這麼一個好夥伴也是命中註定,就像找男女朋友一樣。比如剪輯上,也不一定是要找技術多好,或者是做過有名氣作品的人,重要是他願意為你用心工作,他會不會花時間?他有沒有可能比你還要投入情感?因為你剪50遍、100遍,都有可能的。
林漢森:有時候跟天才合作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很多東西會很順,但其實也不一定適合合作,你要和對的人、好的人合作。
陳德明:然後審美這是必須的。從電影上來說,你要知道什麼是好的。再奢求一點的話,就是看你們是否有一些情感上的共鳴,需求是不是互補,我覺得這樣才能夠成為一個比較好的合作關係。不然,像我們作為新人,那個關係可能是不對等的,所以必須要像齒輪一樣契合上。
「導演的DNA」
紀錄公社:說到審美,我記得你首映問答環節提到這個選題是透過一個朋友瞭解到這個村子有小學生在寫詩。想把日常生活拍出詩意很難,但這部電影卻非常豐富充實、不空洞。你是如何操作攝影機,把畫面構圖安排得如此恰到好處的?
陳德明:我到那個村莊的時候,發現這好像就是我小時候的場景,它似乎一直沒變,只是我長大了而已。 我有一個自己的方法,就是不去關注正在發生的事情。我關注的是事情之後。當我這樣做的時候,我就有充足的時間去準備,去思考眼前捕捉的究竟是什麼。因為我拍攝的是日常,而不是某個突然發生的特殊事件。剪輯時,我會先把字幕和聲音去掉去看,讓素材保持最初的感覺,電影是這樣的。
林漢森:德明喜歡的很多電影都是劇情片,他有提過在過往經驗裡,很多時候會因為在現場失去控制而沮喪。所以他在拍《從來》的時候,更加篤定了一件事情 —— 他當時把相機貼上了 4: 3 的膠布,那不是後期做出來的,是他想能夠更加專注在畫面上,於是慢慢這種很風格化的東西它就出現了。當時我(第一次)看到素材,那個靈氣就已經在那兒了。

△《從來》截幀 ©Timelight Films
紀錄公社:那麼從最開始拍攝到中後期剪輯,這些風格化的元素如何慢慢找到了它專屬的影像語言?
「對製片人的升級理解」
紀錄公社:漢森,作為製片人,你確實是靠實踐一步一步學習整個體系裡製片意味著什麼,這裡面有很多的取捨要做。首先,經歷這樣一個專案後,你對製片人的角色如何理解?
林漢森:其實我也在做自己的作品,而且我之前的製片經歷大多都是在片場,負責的東西非常專一具體。所以當我在做這個專案的時候,作為主製片人,管的事特別多。另一方面,我也有點像是在盤活這個事情,你的觀點跟導演碰撞以後,你怎麼在這個事兒上給它鋪開,然後一項項地去執行?這樣的全域性觀應該是對我挑戰最大的,因為我不是不知道怎麼做片子,或者說哪裡有錢或是什麼,這些綜合來說只是很小一部分,但這些部分要如何有機地組織起來?透過怎樣的策略?我很開心自己能夠兼具兩方面(導演、製片)的經驗,一方面能夠更加接近作者的心態,彼此順利溝通,保證我們的聲音不會被各種環境影響。另一方面,我可以分析如何在這些外界環境中去精準定位專案,殺出重圍。當然,在這個兩個角色的轉換之中,很考驗學會如何把握這個不同角色上的邊界。
我覺得這個東西,必須要透過一個專案,去實踐了以後,才能辨別以前接觸到的資訊情況和真正實踐後的區別。比如,有可能參加工作坊意味著什麼?這些工作坊是不是進了真的有意義?還是說我們其實有更智慧的方式去解決我們所面對的一些問題和困難?我覺得到現在為止,可能到走完整個專案以後,自己對於在獨立專案當中怎樣去盤全域性會有比較大的升級理解。
最後,製片是一個很長期的工作,專案的結束往往不是片子定剪交影展了,對於導演來說可能是這樣的,但對製片人來說,工作還沒有結束,這片子的生命才剛剛開始。對我來說還得繼續做各種各樣的決定來幫助這個片子給觀眾更好的放映體驗,以及更好的宣傳,讓觀眾看到片子。

△《從來》截幀 ©Timelight Films
「收穫幫助的關鍵點」
紀錄公社:這幾年過來我看在眼裡,《從來》真的是一個相互成就的過程,特別可愛。你是紮紮實實透過實踐來體會、認知、總結。 作為案例分享,你能就專案在產業環節裡經歷的關鍵節點,放在時間線上面梳理一遍麼?比如哪個階段誰進來了,提供了哪些幫助?
林漢森:我當時也是一張白紙,更多是因為我的反應速度很快,遇到問題就去想我應該要做一些什麼才能幫助專案獲得下一步需要的支援。我們最初深聊後,即便我當時沒有很清楚的答案,但是我知道這個專案有點卡住了。
紀錄公社:具體卡在了哪裡?是缺故事線,還是說紙面上的東西沒有辦法傳達到位?你是怎麼解題的?
林漢森:我覺得他缺的不是這些傳統的東西,是如何能夠讓他這樣藝術的表達能夠變成一種語言,就是從無形化成有形的東西。德明在視覺語言上的創新是非常清楚的,他知道自己想要呈現的視覺效果。這聽起來很讓人興奮,但是可能很難讓人能想象這個故事(visualize the story),因此很容易讓大家覺得東西都是在飄著,很抽象。你可以把它理解成 R&B,它經常會給你一些很靈感爆發的東西,不會順著這個曲子。但你想把它做成影像作品,該怎麼把情感放在一個安穩的框架裡,讓大家可以去感受。

△《從來》截幀 ©Timelight Films
紀錄公社:那麼識別出問題後,你怎樣開始一步步去組這個“盤”的?
林漢森:我跟德明聊完後就落到紙上工作了,因為你要呈現一個提案文書(pitch deck)去見資方等。我應該大概花了三個月的時間重新把現有的東西,還有無論是從文字還是視覺材料,統統都過了一遍,不斷修改出了一個新的版本。它肯定比之前在概念闡述上清晰了很多。不是說那個所謂故事線出來了,而是我們在做什麼,接下來計劃怎麼做?這方面的東西變得更加清楚了。之後就開始去投遞申請一些工作坊。
《從來》的製片方法非常特別,很多時候我們出場提案,大家對這個專案有很多不一樣的理解或者看法。那麼到底這個片子要做成什麼樣?我們倆要去討論這件事情。所以很早我就開始問不同的製片人,中國的、歐洲的、美國的,問他們在這樣的專案裡看到了一些什麼東西。我會大概知道,如果想要在國際上尋求幫助,這樣一箇中國故事應該從哪裡出發。於是我選了一個離我們特別近的國家,印度尼西亞的工作坊。
我記得我們當時其實去到巴厘島的時候(Docs by the Sea Editing Lab)很興奮,因為那時候我做了一個很大膽的決定,我提交了很長的素材,解釋了一下我們的情況是什麼。其實到後來我們有機會去和他們的選片人聊天,他們說感覺到最關鍵的是覺得我們的東西很真誠,很乾淨,它沒有很多很宏觀的,我要怎麼拯救或改變社會這些想法,都落實到我們非常作者化的東西上。

△《從來》截幀 ©Timelight Films
紀錄公社:《從來》在巴厘島具體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林漢森:我們在到 Docs by the Sea 見到了非常好的剪輯導師雪美蓮, Mary Stephen,她是一個非常耐心的老師。你說在剪輯上我們有得到實質性的幫助嗎?並不是,但我們養成了一個心態,就是做事兒不要著急,慢慢來。
去巴厘島之前其實有兩個月的時間是線上的,我們在做一些整理的工作。我們把所有的素材過了一遍,德明挑出自己想要的素材,截成圖全部整理成了表格。我們給Mary看了之前德明剪過的兩小時長的版本,然後開始重新想這個片子應該從哪裡開始修改。我們在在巴厘島海邊很舒服,會一起到小酒館、小旅館裡看素材,一顆顆長鏡頭看過去,我會在他們討論的時候在旁邊觀察記錄,能清楚地確定這些長鏡頭的呈現方式可以有,但是不能夠都是這樣,它必須要有自己的節奏。我把這些資訊做了整理,然後跟德明會後再去溝通做這件事情。其實這個對他幫助也挺大的,他可以知道他的哪些是實踐成功的,哪些是實踐不成功的,或者是哪些是他可能要做一些改變的。
從Docs By the Sea開始,這專案開始慢慢長出了一點形狀。但它的影像語言其實還沒成型,只是開始冒出苗子,有了一個方向。
「剪輯師上陣」
紀錄公社:有了巴厘島這段經歷後,進度如何?
林漢森:其實那段時間以後有進入一個“創作冰窗期”。對於製作來說,給的反饋是有幫助的,但是實質上還是要回到剪輯室。當時我們還有一個問題:融資上的挑戰,沒有剪輯師也不知道需不需要。因為我們倆在素材上都已經接觸很深了,覺得這樣搭配應該沒什麼問題,直到這個冰窗期,我感覺到效率不是很高,我們依舊卡在導演自己的想法上,他其實有被現有素材限制住,做的一些東西他經常會推翻,每次可能都在做新的東西,但達不到一個能讓片子連貫起來的視覺語言,所謂調性(essence)這個東西。
藝術創作就是越打磨越出彩,但是我感覺到還是需要有一箇中間人來給我們來叫停,來給我們說這個專案對一個完全沒看過的人來說是怎樣的。我在專案裡也有一段時間了,那種新鮮感(褪去)也有了疲憊。
紀錄公社:在那之後是先參加的DOK.Incubator(剪輯工作坊),還是在那裡找到的剪輯師?選擇剪輯師的標準有哪些?
林漢森:應該是在參加之前就確定了怡初來做我們的剪輯師,因為 DOK.Incubator 的形式是導演、製片、剪輯三個一個也不能少。有時候導演可以自己做剪輯,但不推薦,他們覺得還是三方各司其職好。當時在我的認知範圍內其實沒有特別合適的剪輯師。最後確認剪輯師首先一定要講中文,有這個文化背景,知道我們詩歌背後的情感,那麼對畫面表達的哲學性上的一些東西,也會理解得更加精準。
第二點就是,這個剪輯師一定要有一些長片的經歷,儘可能路數是比較開放的,而不是剪傳統專題片。她一定也是喜歡看書,比較喜歡散文性的東西。很巧,我們遇到怡初的時候,她在看一本書,剛好是德明很喜歡的塔可夫斯基的《雕刻時光》。這是一個特別好的訊號。然後我們就去了DOK.Incubator,在那兒很暢快地剪輯。

△《從來》截幀 ©Timelight Films
紀錄公社:我印象裡這個工作坊是橫跨了一整年,分成幾個階段。
林漢森:三個階段,4月開始第一個,然後6月一個,10月一個,最後11月份在IDFA有一個進度彙報展映(showcase)。當時第一期我們做了一個訓練,讓製片、剪輯、導師,我們大家都坐下來,一起進行「導演DNA」(*DOK.Incubator的一種指導方式,讓主創團隊與導師共同挖掘影片的核心特質)去深入瞭解我們面前這導演是誰、他為什麼做這個片子、他身上的氣質跟作品的關係是什麼,相當於把我也拽回到了第一次跟德明見面。這讓我深刻意識到一件事情,這是非常作者型的電影,很多東西要從“心”出發,一個是心臟的心,一個是新舊的新。所以,我們團隊裡面的所有人都要儘可能地靠攏在一起,要並肩站在一起,這個片子才能迸發出它最大的生命力。
工作坊每個階段持續一週,不僅有開題報告,完事以後還有總結報告。開題報告是大家會看我們現階段有什麼,展現給參加工坊的所有人,你會收到 12 個人的反饋,來自選進來專案的導演、製片、剪輯、加上導師。我把這些反饋都記下來,再整理反饋給我們團隊,梳理出哪些東西是現在要先解決的,哪些可以往後放,有點像攻堅突破先解決大問題,可能下面的一磚一瓦它就都解決了。最後的報告會展現我們都做了些什麼,大家會看到我們在一週裡的變化。

△《從來》截幀 ©Timelight Films
紀錄公社:這等於是2024 年密度很大的一項工作。其中遇到什麼重大挑戰嗎?
林漢森:強度非常大。我們其實沒有走很多提案會,後面一個都沒參加,就是專注做後期,然後我們一邊剪輯一邊找錢。當時第二期的剪輯我們有點卡住了,因為要從粗剪定剪的第一個版本到精簡,這中間還是要調整的。
工作坊請了產業的人來開會,基於我們的粗剪的定剪版本來給我們反饋,但是他們(導演和剪輯師)的情緒情非常低了。所以我就沒讓他們完整參加會議,我還是像那個中間人,去和產業嘉賓對話、記筆記,擋掉了很多負能量,讓他們能專注放心在剪輯上。
「順水行舟」
紀錄公社:從觀感上來講,你們這一路挺順的,從 Docs by the Sea 到哥本哈根用了不到兩年時間。我想問問過程中有多少申請是被拒的?
林漢森:我們申請的所有工作坊沒有失敗的,提案也沒有失敗的,還至少都拿了獎。我們製作資金申請都是海外的,鑑於是新人導演新的視覺語言,包括現在的經濟環境之下,我感覺大家都變得稍微保守了一些,不會輕易說OK。他們會綜合很多因素,你是不是歐盟國家的成員,你的專案對歐洲觀眾,或是說對國際觀眾是怎麼樣的?我們有很多都進到第二輪,但是對方必須按照各國家的名額分配,沒辦法把《從來》塞進去。
紀錄公社:那真的也很幸運。我指的是你們這一路嘗試的東西,會得到正向反饋跟回報,成為激勵。
林漢森:很幸運。但是在幸運的基礎上,我們是非常真誠的創作者,也沒有在包裝這個專案。你如果回去再看一下那些申請材料,肯定不是完美的,但它一定是最真實的,最接近作為創作者想表達的東西。很多時候我們都在想,什麼樣才是一個精彩的提案?對我來說就是真誠。

△陳德明、林漢森在CPH:DOX的映後現場 ©unknown audience
紀錄公社:DOK.Incubator之後其實就等定剪,準備電影節了。為什麼選擇在CPH:DOX首映?你們在那個階段是如何規劃的?宣發和發行這方面是怎麼考量的?
林漢森:我們進到 DOK.Incubator 的第一天,我們就開始籌劃節展和宣發策略,已經在想我們的受眾是誰、我們要去什麼樣的電影節。我們有根據最理想的情況做一個計劃,還有一個根據保守估計做了一個計劃,第二個版本更多是基於參加完各種產業會議後有的一個感覺,即《從來》在哪裡會最受歡迎。當然,最後我們實踐了最理想的計劃。
但回顧在剪輯到投遞影展這個過程,根據專案還需要的幫助,我們還需要做很多決定,很多時候都是基於現場產生的直覺性反應,那個時候我會想著下一步怎麼下這盤棋。其實我知道這個流程是什麼,但是我沒有把坑都給填滿。可能有一點要大膽嘗試的心,我做了很多調研,研究很多別的專案。這裡值得一提的是,以前沒在做電影之前,我看電影很少會去看署名(credits)。現在自己做了,經常會去關注它,從裡面獲得一些借鑑和思考。
總結到我們做這個專案為什麼那麼順?最重要的原因還是那種很真誠的感覺,大家互相感受得到這種相互選擇、相互信任。我只要能非常強烈地感受到,就會是非常對的。
在選擇影展上我們當時已經建立了很多影展的聯絡和收到了投遞的邀請,最後到確認CPH:DOX的國際首映,有一部分感性考慮的原因是因為當時我們專案在發展的時候,有其中的策展人看到了我們的素材並給予了很大的認可,現在我們成片如果能去一個真正接納自己的影展,我認為在關注度和推廣的力度上一定會有很大的幫助!其次,第二層肯定是更實際、理性上來說,首映要考慮市場活動以及觀眾體量以及節展的選片風格。把片子放在在百花齊放的環境下,而非同型別的大池子裡,我覺得這樣作品更能脫穎而出。現在回頭再來看,我跟德明都覺得這個選擇很正確,因為我們在這裡非常受歡迎,他們(CPH:DOX)真的在推這個片子,在他們影響力上儘可能支援著我們,例如在最後一場放映中讓我們給觀眾帶來了一場臨時安排的問答環節,完美結束了我們在哥本哈根放映。
「所謂中國故事」
紀錄公社:在處理包裝定位的時候,你們有過把它說成是“亞洲專案”嗎?這樣到底是優勢還是劣勢?會不會反而讓人反感?
林漢森:沒有,我相信好的東西是世界的。我們都有海外生活的這經歷,不知道你能不能共鳴,就是以前沒出國之前看了很多美劇英劇都覺得國外的世界好文明啊。當你真正開始在美國生活,你會發現他們也有各種歧視、暴力、愚昧,你會發現大家其實核心的東西作為人是一樣的,都有慾望,都渴望愛,都在尋找我們生活生存的意義。所以在包裝這個專案的時候就是跟德明一樣,我們認為《從來》不應該只是一個受眾群體。童年這樣熱烈的情感和孤獨的體會是我們都有過的,所以我們的定位拋棄了所謂什麼留守話題,只傳遞給你更深的情感上面的一些東西,這樣的位置我覺得也更容易理解。
我們在Dok.Incubator的時候也是同樣的,大家其實不會想什麼技法,怎麼發展敘事,完全打破了我們之前在學校學的那種三幕式、五幕式結構。我們一直都在問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感覺我和這個主人公近不近,有沒有和螢幕裡的故事產生情感連線?我們所有的流程都是在問要以什麼視角開始進入這個世界,然後慢慢地我去感受些什麼,見到些什麼,然後再繼續往下剪。一旦你覺得跟這個主人公有疏離感了,那就不對了。當然,在國際市場上針對中國故事我們常常會獲得很多不同的建議,有些可以感受到是西方自帶的審視中國故事的視角,作為製片就要有敏銳的辨別力,知道如何融會貫通這些建議到自己真正想發展的片子上,保證作品本質的聲音不會被改變。
陳德明:其實這回我也是挺有感觸的。我們必須要講我們自己的故事。我們需要透過藝術或者是電影這個方式把它轉一下語言,只是轉一下開關。
紀錄公社:你只是找到它的形式(art form)。
陳德明:對,我們只是在藝術本身上面做一些工作。你講好你的故事,就是講好了中國的故事,而不是反著來。

△CPH:DOX現場照片 ©陳德明、林漢森
「好好生活」
紀錄公社:你們倆各自說說這一路走來最大的收穫吧。
林漢森:我在Eurodoc(歐洲向國際開放的製片人訓練營)學的第一課不是說怎麼做一個好製片,而是你只要和對的人合作,你做出來片子就是最棒的,真的。
所以包括我接下來就是想做的方向,也是希望能對於這種剛開始嘗試第一、第二部片子的導演來說,讓他們能遇到不是最牛逼的人,而是最對的人,能讓他們在專案上真的有實質性發展。我覺得創作過程就是一個永遠在磨合、在溝通的過程,這樣專案才會越來越好,不然的話你很容易投入到一種虛晃的幸福跟崇拜裡,慢慢地,你的聲音也會失去。這真的像談戀愛,如果兩個人太愛對方,你會失去自己。但是在那種對等、健康的關係裡,你們能聊天,能一起發現問題,這其實是最好最穩定的感情方式。
紀錄公社:嚯,這是從失敗的戀愛經驗中學到的嗎?
林漢森:所以最後總結這段話我想說,做片子跟人生是一樣的,只要把自己生活和過好、觀察好,其實都是一樣的。做片子也是好好生活一種方式,德明,來告訴一下大家,你的剪輯指導當時送你的一番話是什麼?
陳德明:好好生活,好好旅行,好好聽音樂、看書,嘿嘿,沒了。其他的都不重要。嗯,這就是電影的一切。

△陳德明、林漢森在領獎後的合影 ©CPH:DOX
《從來》主創作團隊
導演:陳德明
製片:林漢森
聯合制片:讓-瑪麗·吉貢,周嘉羲,陳嘉佩
採訪 、撰稿 | 洋
關於紀錄公社
紀錄公社是一家啟動於2021年的獨立藝術中心。由非虛構影像藝術出發,我們致力於營造一個擁抱一切介入現實的故事創作空間。透過探索、挖掘、製作、分享豐富深刻的紀實作品,凝聚多元的創作群體,沉澱人類體驗的表達,提供解讀當下和內心的視角,並激發對未來的思考和願景。




凹凸鏡DOC
ID:pjw-documentary
微博|豆瓣|知乎:@凹凸鏡DOC
推廣|合作|轉載 加微信☞zhanglaodong
放映|影迷群 加微信☞aotujingdoc
用影像和文字關心普通人的生活